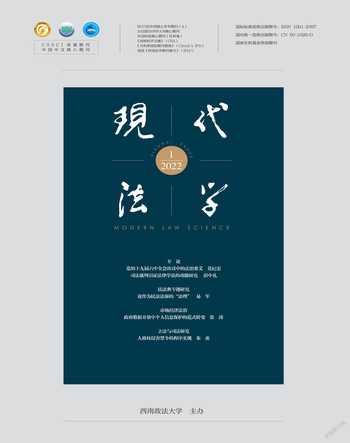司法裁判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研究






摘 要:法律学说是连接立法与实践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桥梁,也是推动司法与社会互动的知识引擎和理论动力。学者的学术观点是法律学说的直接体现。在我国,存在司法判决引证法学学者观点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268份样本裁判文书中,有60位法学学者的观点被引证307次。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发挥着解释法律、论证说理及补充法律漏洞等作用,从而增强法官对法律事实性质或裁判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从应然层面来看,法律学说要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能的参考答案,为司法裁判提供有效的法律方法以及通过司法裁判总结科学的司法规律。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表明,虽然司法判决可以成为法律学说的“试验田”,但是从主题任务和实践立场两分的角度看,法学与司法的适当分离是法治持续进步的阶梯。
关键词:法律学说;学者观点;引证;司法裁判;裁判说理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2.01.03
一、问题、方法与材料
在古罗马法时代,五大法学家不仅著书立说,而且相关法律学说只要达成一致就具有法律效力。盖尤斯说:“法学家的解答是那些被允许对法加以整理的人的意见和见解。如果所有这些法学家的意见都一致,他们的这种意见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相互分歧,审判员可以遵循他所赞同的意见。”①当时的具体情形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安三世共同颁布了《学说引证法》。[该法规定,遇有疑难问题,成文法无明确规定时,要按照帕比尼安等五大学家的著述解决;观点不一致时,以多数观点为准;意见相当的,则遵照帕比尼安的学说。[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古罗马的法学家们用自己的智慧劳动和原创性的渊博知识赢得巨大声誉,书写了法学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甚至可能后无来者的法律/法学时代。
当下,法学学术研究虽然日益繁荣,但是法律学说[关于法理(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学者观点、法律学说与法理与学说等概念的关联,参见彭中礼:《论法律学说的司法运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90-113页。]超然地位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必须公允地说,法学家们的工作并非无足轻重。如魏德士所说:“法学在法政策方面的广泛的咨询功能以及规范制定机关常常以公认的法学权威的意见作为依据这些事實可能得出如下结论:立法者或最高法院制定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本来’就是法学的成果。”[[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虽然法律学说在当代已经不能直接成为法律(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是补充性法律渊源[如《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使用本法。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者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在前款情况下,法官应依据经过实践确定的学理和惯例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39页。]),但依然是连接立法与实践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桥梁,也是推动司法与社会互动的知识引擎和理论动力。这说明,法学家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学者而言,其学术观点在司法裁判中被引证[学术研究中有关文献运用的问题均采纳了“引证”一词。如苏力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就用的是“引证”。(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而成凡则对此有更为具体的分析,他认为:“虽然引证一样可以表现已有资料和学术传统,可以防止剽窃,但引证除此之外,还实现了一种证据的功能,它增强了作品的说服效果,言而有据才言而有信。”(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在裁判文书中,存在引用法律学说,但是却不认可或者采纳它的现象,此时不属于引证。所以,笔者认为,引证必然是引用,但是引用未必是引证。],对其学术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随着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学者队伍越来越庞大,学术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术创新层出不穷,能够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变成“现实中的法”,是学术思想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
彭中礼:司法裁判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研究——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需要,我国的司法改革不断地吸取外部智慧,进而促进司法实践不断发展。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13条规定,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法官可以运用“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论证裁判理由。这是我国首次提出法官可以运用“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进行司法论证。然而,如何从制度上运用“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并从方法上保证“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得以有效运用,尚缺乏具体的制度建构,也罕见有学者的具体研究。因此,基于现有制度的激励,有必要对我国司法裁判如何引证法学学者观点的具体状况进行整理和反思,总结司法裁判中应当如何运用法律学说,进而从理论上洞察如何保证法律学说在司法裁判中的正常功能,为未来运用法律学说的制度建构提供经验依据。
为了有效展开对生效裁判文书引证法律学说的现状研究,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观察和探讨法律学说的引证问题。具体操作路径是: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搜索样本裁判文书,整理分析直接引证法学学者观点[应当注意,可能有裁判文书引证了学术观点,但是没有指出来源,此种现象可以称之为隐性引证。本文只考察明确注明了引证来源的裁判文书,因而隐性引证不在本文观察范围之列。]的裁判文书,最终对其中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分析检讨。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法定的司法判决文书公布网,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有裁判文书115510717份(截止于2021年2月25日下午19:00),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书网,因此成为本文搜索相关材料的重要数据库来源。不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建设较晚,对于2012年之前的裁判文书没有收录,为此,笔者又辅之以北大法宝数据库和把手案例数据库进行搜索。通过研读,最终确定样本裁判文书268份。[具体搜索过程如下:第一,以目前中国法学界的知名学者的名讳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以及把手案例网进行检索。比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和把手案例网中以“梁慧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再根据本文的需要进行对比审读,最终得到符合本文意图的样本裁判文书205份。知名学者的名讳来源主要根据长安大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于2017年9月24日发布的法学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该排行榜发布了法学学科最有影响力的300名法学学者以及法学各二级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874名法学学者。鉴于法学各二级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包含了法学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所以实际检索学者人数为874人。(参见《法学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版(2017年版)》,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网站,http://evaluation.chd.edu.cn,2019年5月1日)但是,此种方法的缺陷是,可能有部分著名学者因为最近几年没有发表论文或者发文数量非常少而未上榜,因而未能进行检索,笔者对未检索到的著名学者表示歉意;还有一种情形是,司法裁判引证了某些可能在学界名气并不是很大的学者的观点,在本文的研究中却没有被检索到(可能他们的观点也被裁判文书引证),笔者亦表示歉意。第三,还存在一种情形:在检索过程中,笔者并没有预先检索该学者的姓名,而是再检索其他人时“牵连”发现,此种情形下检索到的样本裁判文书有5份。第四,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只研究有具体出处的法律学说,有些类似“根据民法学基本原理”“根据民法学相关理论”“根据刑法学基本原理”之类没有明确指出观点来源的比较笼统的说法,不在本文的统计范围之列。第五,司法裁判引证法谚、格言以及引证罗马法上的名言的情况,也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列。第六,学者提供的专家意见书或者法律论证书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第七,本次检索没有统计我国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数据,没有统计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数据,也没有统计对外国学者的引证。第八,特别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国内法学学者的检索并不完全,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形。因数量庞大,请允许笔者的“漏万”,特别是因某些原因没有被检索或者没有检索到的学者,请谅解笔者的疏忽。整体而言,对部分学者的漏检,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最后,特别感谢周星宇、周佩、何文念、吴联梅和彭娟等同学在以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二、司法引证法律学说的经验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笔者对样本裁判文书进行了仔细研读,对引证的法学学者进行了详细统计,主要结果如表1所示:
就表1来看,268份样本裁判文书一共引证了60位学者的观点307次。从引证前五及引证频率的角度来看:第一名是杜万华,51次;第二名是梁慧星,28次;第三名是韩世远,27次;第四名是孙森焱,22次;第五名是王利明,18次。从学者的职称/职务的角度来看:60位学者当中有教授35人,法官17人(主要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和最高院的法官),行政官员4人,还有未知职称或职务者4人。
从学者知名度的角度来看,上述被引证的60位学者中,大多數是所在学术领域的代表人物,甚至有部分学者在整个法学界都是声名显赫。大体而言,作为法学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法官对这些学者的作品都有或多或少地了解。从这个层面来看,法官如果着力去引证某个学者的观点,自然会引证知名学者或者有代表性的学者,以加强论证的说服力。还值得指出的是,对于部分学者型法官而言,他们所著述的法律学说更能针对现实法律问题。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因为能够深刻地影响立法,所以其观点也更容易得到法官引证。例如,一些学者深度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制定,属于法典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学者。他们对于《民法典》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从条文到章节体系,都有细致入微地思考,并最终转化为法条的主要内容。这些影响立法过程的学者,其学术观点更容易获得法官们的青睐,对其引证也能使裁判文书说理更具有说服力。整体来看,上述被引证的学者当中,既有十分知名的学者,也有知名度并不高的学者;既有纯粹的学者,也有“学者型官员”;既有基层法院的法官,也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这说明,法官引证法律学说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规律。进一步而言,亦可以说明法官引证法律学说带有个人偏好。
从引证学者所分布的领域来看,被引证的学者当中有31位民法学者、10位刑法学者、9位行政法学者、5位知识产权法学者、2位程序法学者、2位劳动法学者和1位国际法学者[研究领域的基本归类原则是以作品所属领域进行分类。有极其个别的学者因其职务原因,研究领域比较广,选取其在某个最主要的领域进行归类。](如表2所示)。这意味着,样本裁判文书引证法律学说依然是在传统的部门法领域,即在民法领域和刑法领域。可能的原因:一是民事纠纷是社会矛盾的集中领域,也是法院审理的案件最多的领域,常常会产生一些较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法官认真识别案件核心争议点,并对此进行相关论证;二是刑事法律虽然强调罪刑法定,但是罪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有严格的界定,甚至还有一些新行为是否能够纳入罪名当中,需要细致论证。从中还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民法学、刑法学及行政法学等领域研究者众多,但其研究成果在司法裁判文书中被引证的比率相当小。据中国法学会官方网站介绍,中国法学会会员有10万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法学研究人员。相比于数量庞大的研究队伍,被引证的学者数量及其研究成果比较偏少。另外,从中还可以发现,有较多的部门法如经济法和环境法等学术领域的学者观点没有被引证;而且,当代中国法理学学者的观点也没有被法官引证,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从学者所在单位(机构)来看,如表3所示,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占据了样本裁判文书引证法律学说来源单位的排行榜前四强,其频次和比率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是13人,比率为18.8%;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是6人(应松年教授的工作单位分别计算为中国政法大学和国家行政学院),比率分别是82.7%;中国人民大学有5人,比率为4.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机构)的法学学者相比之下更受法官关注。
从单位(机构)性质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其与司法有关的行为均备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最知名的高校之一,许多人文社科学科(包括法学)在国内学科排行榜上一向成绩较好;而中国政法大学作为近二十年来崛起的政法类高校,法学学科已经成为该校的王牌专业,并且入选了国家“双一流”学科。可以说,无论是中国人民大学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其法学专业、法学学者在国内都有较强的影响力。此外,还有部分高校虽然在国内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坐镇,也登上了“引证榜”。在表3中,还要注意到基层法院表现不俗。样本裁判文书中有两篇文书出自基层法院法官之手,但并没有指出其所在单位和身份,笔者根据文章名称找到了作者及其单位。基层单位的上榜虽然出乎意外,但细思亦在情理之中。因为大量的案件审判均发生在基层法院,许多法官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基于案件审判而总结相关经验,并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能够提供真知灼见。
通过样本裁判文书引证法律学说的文献来源,既可以管窥法官的阅读视野,也可以管窥法官对新知识的接受度。表4表明,样本司法裁判文书注明引文文献来源的分别是学术专著(128次,51.61%)、学术论文(23次,9.27%)以及学术会议(3次,1.21%),没有指出引文文献来源(未知来源)的有110次,占44.35%。由表4也可以看出:第一,从样本裁判文书的文献运用来看,虽然有部分法官注重引证的规范性,但较多裁判文书并未载明引证的来源与方法,只能知其文字,而不知其文本(论文或著作等)。第二,从样本裁判文书的类型来看,学术著作的传播比学术论文的传播范围相对较广,可能的原因是法官们不太注重阅读学术期刊上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而是注重其所收集的学术名家的著作。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受到法官们欢迎的著作类型是关于特定法律的条文解释与释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商标法修改条文释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释义》和《中人华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解读》等。第三,从总体上看,虽然法官对学术专著的关注程度远远大于学术期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后者毫不关心。表4表明仍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被法官所关注并引证,这说明有些法官依然不忘及时获取最新学术动态。
从法律学说的引证方式来看,样本裁判文书可以概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观点中心型,即直接说某某教授提出某个学术观点,但是关于这观点来自于哪里,并没有详细说明。例如,在“张志明与临汾市尧都区乡贤街社区居民一组、赵新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指出:“关于何为恶意串通合同。郭明瑞教授认为……江平教授认为……王利明教授认为……”[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1561号民事判决书。]二是观点与观点来源并重型,即既注重学术观点,也注重学术观点的来源。比如,“陈某1与陈某2分家析产纠纷”案中,法院指出:“2015年第18期的《人民司法(案例)》所载的《农村宅基地流转与违章建筑有限权利保护》一文也认为……”[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终589号民事判決书。]仔细观察样本裁判文书,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即如果法官引用耳熟能详的知名学者(如梁慧星、王利明等学者)的学术观点,都会指出其姓名,但是如果引用的不是十分知名的学者,甚至可能仅仅只是基于兴趣对某个具体问题有精湛研究的学者,则不会指出其姓名,而是指出其观点来源。可能的一种解释进路是,知名学者基于“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而连带其学术观点都具有权威性(注意:此处所说的权威性不等于准确),而不知名的学者获得信赖的依据就是其学术观点本身。三是讲究格式型,即按照论文格式来撰写裁判文书,学术规范十分到位,具有复制推广价值。在“潘某某与张某某、孔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中,法官有8个注释,分别是引证法律学说或者进行解释说明。其中,四个注释分别引证沈德咏、杨立新、王利明以及韩世远的著作或者论文,其他四个为对裁判文书的解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7民初14838号民事判决书。]而在“麦曼(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华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官列出了54个注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这种“论文式”的裁判文书随着司法说理的不断深化,司法说理方式的不断改革,可能会日益为人们所接受。
三、司法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解释
从法律层面来看,我国并无法律规定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当中引证法律学说,最高人民法院也直到2018年才出台司法文件对该问题有初步规定。因此,从上述实证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司法判决引证法律学说带有自发性。基于此,我们需要追问,法官为什么会自发引证法律学说?理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者从根本上对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的实践作用进行总结分析,是本文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法律学说在司法裁判中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实践功用,所以法官才会在司法裁判文书中自发引证法律学说。基于对样本裁判文书的整体阅读,笔者根据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的实践功能进行整理分类,如表5所示。
从表5来看,在样本裁判文书中,法律学说主要是在四个方面起作用:对法条的学理解释、对裁判的论证说理、对法律的漏洞补充以及“混合使用”。“混合使用”为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混合运用了对法条的学理解释、对法律的漏洞补充以及对裁判的论证说理,因而不是独立功能,下文不对其进行单独分析。
(一)通过法律学说解释法条
从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引证法律学说主要用来解释概念或者解释法条。从表5来看,将法律学说作为解释法条依据的有156个案例,占样本裁判文书的58.2%。法官引证法律学说解释法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引证法律学说对概念进行学理解释。法律概念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但是在与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时,法律概念就可能产生歧义,此时如何来理解法律概念,法官需要寻找权威依据。从样本裁判文书来看,有118份样本裁判文书通过引证法律学说来解释概念。具体而言,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是直接采用学者对概念的解释作为依据。例如,在“李×交通肇事罪”案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中,法院指出:“所谓‘明知’和‘会’,是指清楚明确地知道发生危害后果的必然性,而‘已经预见’和‘可能’则只是行为人对危害后果可能性的一种认知。正如我国刑法学家王作富教授所概括:‘间接故意是明知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过于自信的过失是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假定可能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刑终字第1797号刑事裁判书。]此处法官引证王作富教授的话语直接目的就是阐释什么是间接故意,什么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不再需要去解释概念,而只需要根据概念进行必要的结论分析。
第二,引证法律学说对法律条文进行学理解释。司法实践中有两条运用进路:一是当某一词语需要解释时,法官可能对其解释方法产生疑问,此时法官会先厘清解释方法,然后再对词语进行解释。例如,在“兴丰建设景观有限公司与西部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指出:“关于‘协调’之含义的合同解释问题,具体说即:是否是因为西部公司未全面履行协调义务导致绥阳政府要求广龙公司垫付拆迁费,进而导致《公路协议》未实际履行,崔建远教授在其主编的《合同法》一书中指出,‘本书所谓合同解释,专指有权解释,即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及其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分析和说明’。本院认为,合同的解释,应从文义解释入手,即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合同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4549号民事裁判书。]法院在这里通过引证崔建远教授对如何解释合同的方法介绍,选择文义解释方法,为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了理论来源。二是直接引证法律学说对法条进行解释。法律条文由语言文字来承载,具体的语言文字如何表述,就可能导致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法官要能够正确理解法律条文,需要寻找权威理论作为依据。从样本裁判文书来看,从此层面来引证法律学说的相对较少,计38份。如在“王跃峰、王玉禄等与赵吉祥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指出:“对该条特殊共同侵权的理解和适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专家编写的条文释义中大多引证的案例就是本案这种两辆不同的汽车相继对同一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制定的著名法学家杨立新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解与司法适用》一书中第66页至69页对该条的讲解采用的就是与本案事实相同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第176页至177页对该条的讲解也采用了与本案相同的案例,对这种侵权的因果关系讲解为等价的因果关系,两辆机动车应负连带责任。”[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2017)冀0682民初1800号民事裁判书。]对法条的理解问题,属于法律解释问题。不过,此处法官所引证的是以案例来作为正确理解某个法条的依据,本质上属于判例的运用问题,鉴于研究主题限制,不再详细讨论。
(二)通过法律学说进行论证说理
虽然我国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之时,对论证说理并不十分重视,但是这并不是说法官就没有论证说理。法官论证说理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寻找说理依据并对说理方法进行运用的过程。因而引证学者们的法律学说进行论述,是实现裁判论证说理的重要方式。从表5来看,将法律学说作为论证说理依据的有91个,占样本裁判文书的比例为34%。
从样本裁判文书来看,通过引证著名学者的论述进行论证说理,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比如,法官在“刘兰波与周子强、王新杰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说理过程中,是如此推理的:“如果像原告主张的那样,被告周子强是买受人,他应不应该在收货单上签名确认?为什么没有签名?是时间匆忙来不及签名,还是书证写满没有地方签名?为什么事后没有要求他补签名字?——原告对上述合理疑问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诉讼过程中,原告称其与王新杰不认识、不能形成买卖关系。这里引证王泽鉴教授的一段话:‘现代社会生活复杂,交易频繁,事必躬亲,殆不可能,因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常须他人辅助从事一定的工作……’本案正是如此:周子强联系葡萄种植户、清点数量,冯腾飞等负责运输,高玉强储存保管……只有一个人与上述诸环节都有连结,那就是王新杰:王新杰发放果箱、委托收购,王新杰雇佣车辆运输,王新杰租用冷库储存,王新杰支付货款。”[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17)鲁0285民初5851号民事裁判书。]在这里,法官的本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事情不需要本人亲为,可以委托给他人进行。所以,社会分工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常态。法官引证王泽鉴教授的话语就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分工的必要性,从而支持法官本人的判断:因为有分工,所以本案中每人可能存在不同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之间存在相应的必然联系,从而可以确定谁是老板,谁是员工(雇员),进而确定谁应当是真正的付款人。与此相似的案例并不少见,其共同点是:为了确立一定的事实依据而引证权威人士的话语,可以事半功倍地强化论证效果。
关于某个法律问题,可能会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此时,法官会选择某个特定的法律学说作为裁判理由或依据。例如,在“刘国定、浙江省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指出:“在现有证据下,作为一个理性人,为了防止更大的损害发生而采取了导致较小损害发生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故本院认为原告在医生建议下进行化疗具有合理性。梁慧星教授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况下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判断非依法官个人主观臆断,而是要求法官依一般社会见解,按当时社会所达到的知识和经验。”[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921民初1571号民事裁判书。]目前,至少存在五种不同的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学说,如“条件说”“原因说”“法规目的说”“盖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等。每一种学说对因果关系的成立条件都各有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导向不同的判断。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而需要法官对这些学说进行取舍。通过引证他人观点来选择法律学说,是进行司法决策的有效方式。
事实上,人们对于相同的事物,总会产生不同的看法。通过理论说理论证提供一种可行方法或找到某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学者的基本任务。无论法律学说是否被法官引证或者采纳,其都是研究/探究性质的,唯有这些学说被立法采纳以后,才能变成法律。所谓研究/探究,当然是要追寻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从而为立法寻找可能的规范路径,或者为司法提供说理的选择依据。虽然法学被视为规范之学,但是法律规范本身需要有理论支撑。面对不同的案件事实,可能形成不同的观念进路。采用何种观点来说明某种现象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对于法官来说,既是一个决策过程,也是一个利益的分配过程。所以,学者的工作是预见或者预测,并辅之以理论说理;而法官的任务在于通过决策作出司法判断。如果说法官与学者的工作是相同的话,那么“同”在都需要有“思想”。只不过,法官可以简单地说采纳谁的观点学说;而学者如果轻易就采纳别人的思想,那就变成了“传声筒”。
(三)通过法律学说进行漏洞补充
虽然人类一直都想制定一部毫无瑕疵的法律,但是这一梦想在《法国民法典》的实践中逐渐破灭,人类社会的制定法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理性不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所有的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有可能存在漏洞。
在司法案件中,一旦法官发现了法律漏洞,就有填补的权力。正如拉伦茨所说:“只要法律有漏洞,法院就有塑造法的权限,此点并无争议。”[[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9页。]所以,法官应当想方设法填补法律漏洞,这是法官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样本裁判文书中,就有通过法律学说来补充法律漏洞的案例。在“安徽省化皖通信有限公司诉安徽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官首先指出“关于民事诉讼中出现未涵盖在生效刑事判决中的新证据,致民事判决与生效刑事判决可能存在冲突如何协调的问题,法律或司法解释缺乏相应的规定。”而恰好有学者对此提出过专门的学术观点,所以法官直接使用法律学说作为补充漏洞的依据:“对此,南京大学民法学专家叶金强教授在刑民交叉研讨会上认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应当采取分别判断、个案判断。即在该类案件中,案件的事实是同一的,但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审判程序关注的重点不同,需要的案件事实、证据材料不同,裁判的结果也应当根据刑法、民法分别作出判断。刘艳红教授在刑民交叉案研讨会上认为,刑民交叉案件没有一个简单的处理模式,无论是‘先民后刑’还是‘先刑后民’都是教条化、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最重要的原则还是取决于具体个案中民事关系和刑事關系的关联性和相互影响程度。”“本院认为,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证据的认定标准远高于民事证据。就同一法律事实,刑事判决在先,民事判决在后,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但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出现新的证据,民事案件不应仍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作出裁判,而应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作出独立的判断。因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故也不存在两判决认定事实冲突的问题。”[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3)玄商初字第580号民事判决书。]“先刑后民”是传统的思维方法,但当刑事判决书生效后又产生了新的证据时,再依据传统方法进行裁判将不符合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原则。因此,叶金强和刘艳红等学者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法院对于这种态度也予以采纳,从而为新问题出现的解决提供了“补漏”的方法。不过,通过法律学说来补充法律漏洞,既需要法官对法律法规的整体性、体系性有较高程度的认知,也需要其仔细把握法律学说的内涵,因而相当考验法官的裁判能力和学术水平。这与传统的大陆法系关于法官的“专业书记官”的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
其实,司法裁判的过程就是通过证据进行推理和证明的过程。无论是上文所谈到的法律解释、论证说理,还是漏洞补充,它们都是引证法律学说进行司法论证的场域。第一,法官们引证学者对法条的解释,不仅仅是想借用学者们对法律条文或概念的解释结果,而且也希望通过该学说的引证来增加判决结论的权威性,从而使司法论证能够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第二,表面上看,漏洞补充的原理是采纳法律学说所提供的某种规则,但实质上这又是法官对漏洞补充之行为合理性的进一步说明。一言以蔽之,法官引证法律学说就是为了有效推进司法论证,增强其对法律事实性质或裁判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四、司法引证法律学说的理论反思
从上述分析还可以看,被司法引证的法律学说,一般都是研究具体法律条文或者研究法律概念,都属于部门法研究,否则就很难进入法官的裁判视野。那么,需要追问,是不是学者们都应当进行部门法研究,从而满足法官们的实践需要?或者说,法律学说没有进入法官的裁判视野,就足以说明法律学说没有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达维德说:“法官常常阅读法学家的著作,并根据各国的不同传统引证或者不引证他们的观点,但不能认为他们忽略这些著作中的观点。”[[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39页。]法律学说进入法官的裁判视野,可以说明该学说有较好的实践价值;法律学说没有进入法官的裁判视野,并非就没有重要意义。甚至很多重要的法律学说,是通过影响部门法学者来影响具体法律制度的建构以及具体法律内容的设计。因此,对于法律学说在司法中的功能,应当具体、辩证地看待,从而实现学说与司法裁判的高度统一。
(一)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能的参考答案
法律学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很多法律的发展与变革,均与法律学说存在千丝万缕地联系。梁启超对此有过中肯的评价:“采学说以为法律,实助长法律之进步最有力者。罗马法所以能为法界宗主者,其所采之学说多,而所含之学理富也。”[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8 页。 ]既然法律学说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对于司法实践来说,法律学说是不是应当正视司法裁判中的可能问题,并给予十分精准的回答?换言之,法律学说是不是也应当回应司法实践?具体而言,应当明确的是:法律学说当然可以为司法裁判提供答案,但是并非能够为所有司法问题提供答案,即使提供的答案也可能并非法官想要的“标准答案”。
第一,法律学说可以为司法裁判提供答案来源。上述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有部分法律学说为司法判决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从而使之在司法判决中被引证。司法是法律适用的过程。法官通过对案件事实的甄别,选择合适的法律,做出裁判结果,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从而将“纸面上的法”变成“有实效的法”[彭中礼:《论法律学说的司法运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90-113页。]。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受人类本身的理性不及和客观不能等现实情形的影响,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法。在制定法中,法律漏洞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已经发生的纠纷没有现成的答案,那么法官就可以依据基本法律原则续造法律,或者依据其他合法合理的理由续造法律,其中法律学说就是最重要的理由。对于法学学者而言,他们不仅要关注现实中的法律问题,而且也要思考和探索各种疑难法律问题。他们或许从具体的问题着手,研究疑难法律问题背后隐含的基本规律;或者从基本理论着手,试图解释社会中法律运行的基本原理。法学学者们可能是实践导向的,也可能是理论导向的。因而,法律学说可以研究司法现象,也可以研究立法现象,更可以研究其他现象,此时的法律学说并不存在是否应当只关注司法实践的问题。从态度上看,学者们可以研究司法实践问题,并不等于其只能研究司法实践问题,“能”与“不能”并不等于“做”与“不做”。如果研究司法实践问题,法律学说自然可以为司法裁判提供答案来源;但是不研究司法实践问题,并不等于其没有回应社会实践。
第二,法律学说不可能为司法实践始终提供现成的“标准答案”。上述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有部分裁判文书引证法律学说,但是更多的裁判文书却没有引证法律学说。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法律学说未必能够理所当然地回应司法实践,但是可以尽可能地回应司法实践:(1)社会的新发展会在一定时间阶段之内使得法律学说可能处于空白状态,因而难以及时回应司法实践。人类可以预见社会的发展,但是难以保证社会的发展不离开人们的设想。“人类不可能准确地预知未来,因此法律必须被应用或者不被应用在未预见到的新情况中,而最初通过法律的人显然无法为新情况提供法律依据。”[[英]布莱恩·辛普森:《法学的邀请》,范双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如果社会的发展离开人们的设想,那么法律学说可能就失去了回应价值。换言之,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型事物不在人们的设想之中,则法律学说也失去了回应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学说只有能够及时地发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提出可能的参考答案或者对策建议。比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类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哪怕是有学者意识到了互联网的“社会威力”,但也不可能马上就能建构一套完整的制度学说来及时规范互联网的发展。(2)人类行为难以按照预设展开,因而难以及时回应司法实践。法律学说是关于法律运行的学问,奠定在人的行为之上。但是关于人的行为,组合排列方式多种多样,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行为类型,法律学说当然也不可能关注所有的行为规范。司法实践本身就是直接面对多种多样的人类行为,因而法律学说也难以对司法实践到底需要什么给予预设性质的回应。法学家们不是预测师,不可能对未来生活会如何变化因而法律会如何变化有精准的认识。人类对于社会变化能够做的是,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事实规划已有的规则。实际上,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法学学者们的法律学说被较少引证的终极原因所在。从这個方面来说,如果要求法律学说必须为具体法律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远远超出了学者们的应对能力。拉伦茨虽然认为法律学说可以为司法裁判提供助力,但也认可法律学说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为司法裁判提供预测,比如,法律学说需要发现实定法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从而促使立法的改变或者司法的改变。在面对新的社会事实之时,不仅法官需要有应对,法律学说也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促进司法裁判有相应的变化。可见,法律学说既是司法之学,也应当是立法之学。(3)新的法律学说如果过于超前很容易成为空想,因而难以及时回应司法实践。法律学说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针对性和一定的超前性。所以,法律学说可以针对现实问题设定解决方案。此时,法律学说可以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一种参考答案,但这种参考答案本身属于对未来的设计。能够被未来社会发展适用的法律学说就成为“哲学的哲学”或者“精华中的精华”,不能够被未来社会发展适用的学说就容易成为了历史的过眼烟云。但是,遗憾的是,历史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能够真正做到对未来有精准设计的法律学说并不多见。所以,未来司法实践会如何,应当如何,只能给出可能的进路,而不能给出必然的进路。
(二)为司法裁判提供有效的法律方法
上述实证研究中,有个别案件讨论了该如何运用法律方法来处理案件中的争议点。[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4549号民事裁判书。]可见,法律学说虽然不可能对未来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并不意味着法律学说不可能为未来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方法。换言之,虽然对于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法律学说不可能完全给予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法律学说作为一种基本原理或者基本方法,已经深蕴了对具体问题解决的基本路径。所以,实务界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还是得从基本法律学说着手。“借着处理由法律及法院裁判中获得的素材,法学努力在现行法及其基本评价的范围内,取得解决法律问题的具体标准,并借此对法律事件作出判断。”基于此,“法学主要要做一些能获致裁判基准的陈述,它们可以转换为法律事件的裁判。借此,法学想帮助实务家,特别是法官及行政公务员,他们必须就具体的情况作符合法秩序的决定。实务家受到必须作出决定的强制,因此不能等到问题在教义学中被彻底讨论。”[[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2页。]
法律方法是法学发展的核心要义,法律争议的处理必须有方法的参与。对于司法而言,方法不仅可以为顺利解决法律争议提供思维和路径,而且可以根据方法来推论司法裁断的结果。首先,在司法裁判当中运用方法可以保证司法案件公平公正的裁决。“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同意,要求一个不具偏见的刚直不阿的司法机关进行公平审判的权利,对于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社会来讲是最基本的要求,尽管这项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并未以上述术语明确表达出来。”[[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公平的裁判既需要法官刚正不阿的处事风格,也需要法律制度的有效保证,更需要成熟的方法运用。法律学说通过对疑难案件的探索和整理,总结出系列有效方法,可以供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和评判。其次,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方法可以限制司法权力的恣意。方法的本质作用就在于,运用方法的人受到了某种规范的制约,从而通过方法适用的法律就不会是恣意的结果。“当‘法律适用的精神和目标’毫无约束地专行时,方法就发挥报警器的作用,反之,如果赋予法律适用自身以单独的‘精神’,那么已经意味着踏上了非理性的道路。也许只有具体的法律适用者的精神在起作用。如果法律适用者不打算用其自身的法政策愿望与目标来代替立法的地位的话,那么方法上的自我约束是有益的。”[[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最后,在司法裁判当中运用方法契合司法的基本性质。司法裁决过程的性质几乎被所有的法哲学家讨论过,它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是:法院能否通过一种演绎的或者逻辑的方法获致裁判结论。[[美]理查德·瓦瑟斯特罗姆:《法官如何裁判》,孙海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8页。]因而,对司法裁判过程性质的追问实质就是关于方法问题的追问。唯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让司法无差别地适用法律,从而与司法的性质相吻合。可见,法律学说既是知识的总结,也是方法的凝练。通过对法律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作为系统知识的法律方法,是法律学说对司法裁判的重要贡献。由此可知,法律学说为法律争议的解决提供方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法律方法的来源与证成离不开法律学说的智慧贡献。人类知识既有经验性的因素,也有建构性的因素。通过人类主体的“实践——提升——反思——实践——提升”,人类的知识才有不断的发展与积累。如果说知识是关于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学问,那么方法就是学问中的学问。任何学术成果的取得,既是思维不断探索的结果,更是方法运用的结果。法律学说本身既需要通过方法论探求真理,也要在探求真理过程当中形成自己的方法。霍恩说:“方法论是一个法学学派的核心。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是由对象和方法来构成的。人们通过对具体学科中所运用的方法的一般陈述来对一门学科进行分解。”[[德]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可见,方法本质上是与学说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在任何学说的形成以及发展過程当中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作用。“颇有意味的是,20世纪以前的法学家们很少怀疑自己是否拥有适当的方法,他们相信,以法学的基本要求为准,他们确信的方法较之于其他学问的方法毫不逊色。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他们从不谈方法问题,因为它们明白,如果一门法律学科不谈自身的方法论问题,那么必定是出了什么问题。”[雷小政:《刑事诉论法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人类几千年的法治追求史,不仅仅是法治的学问史,也包含了如何追求法治的方法史。人类不断总结法律争议的解决方法,不断为法律方法添砖加瓦,法治的发展也就越来越迅速。从这个层面来说,法律学说本质上是方法的学说。
第二,法律学说供给法律争议的解决方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任何时代都有任何时代的问题,解决时代的问题是所有学术的重要使命。任何学说都必须来源于问题。问题意识越强,其所阐述的学术思想就越能接近当代的实践需要。法律学说是一个时代的法律哲学精华,必然承载引领时代法治发展的重任。如果一个时代缺乏法律学说,那么这个时代必然缺乏先进的法律体系及其制度。唯有方法,不仅可以指引法官寻找对策,也可以让法官反复运用,并成为千古流传的真正学问。
(三)通过司法裁判总结科学的司法规律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治理方式,源于国家治理的不断实践。可以说,有关法治的学说,与国家治理的历史一样悠久。人类社会的法治能够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与法律学说关于法治的不断追求有着莫大的关系。法律学说对于法治的追求,既通过理论推演而得出,也通过经验总结而获得。其中,通过司法实践获取经验,是科学总结法治发展规律的重要路径。上述已经指出,学者未必是预言家,但是学者可以根据司法判决的进程、结果展开相关研究,预见、归纳和理顺司法判决中的真实问题,总结其中的规律性,是法律学说的重要使命。具体而言,对司法过程进行全方位认识,既需要对司法过程进行规律性总结,也需要对司法制度进行规律性总结,进而促进法治不断发展。
第一,通过司法判决,法律学说可以总结类案的裁判规律。应当看到,具体的司法实践在不断地推动着法治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是个案推动法治进步,而且基于个案的司法总结也在推动法治进步。所以,法律学说既研究个案,也研究个案的集合。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经常通过地方法院的判决,就某种类型的案件审判结果总结出一般规律,进而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文件形式颁布裁判规则。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总结某个类型案件的裁判结果并总结出裁判规律,本身就属于法律学说的范畴。只是与普通学者的法律学说相比较,最高法院的法官能够将其法律学说通过法律程序转化具体规则,而普通学者一般是通过提出政策型建议或者撰写学术论文才有可能转化为规则。从个案的裁判,到个案裁判的集合,不仅可以看到具体法律问题的规律性,而且也可以通过不同法官的裁判结果展现同一类型案件的应有裁判规则,进而为其他类似案件提供规则来源。从这个层面上说,裁判案件是法官的事情,但是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进行总结,却是学者的基本职责。学者通过个案提升到类案,是法治发展的重要推力。还要注意到,通过个案可以看到司法裁判本身的规律。比如,有些案件的裁判结果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可能经历过较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或者是不同学术观念的深刻交锋,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压力,法官能不能顶住各种压力,能不能根据法律和自己的独立判断进行裁判,本身就是司法规律的重要体现。能够顶住压力裁判,就符合司法规律;不能顶住压力裁判,可能就破坏了司法规律。司法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和重要路径,因此,通过司法来寻找或者发现规律,进而保护这种规律,是判断司法效果的基本指标之一。司法规律不可能自身展现,而是需要有深刻洞见的学者创造法律学说去发现,这就是学者使命的真正展现。
第二,通过司法判决,法律学说可以总结制度的优化规律。苏力教授曾说:“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因此,社会制度的变迁,并非必须是宏观层面的巨大变化,也可以是微观制度的少许改进(毕竟,通过量变实现质变是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司法判决的形成,表面上看仅仅只是法官的一纸文书。但是深层次来看,它就包含了诸多制度意蕴。因为司法裁判的作出,本身就是制度综合运行的结果。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司法制度,也有权力配置制度、权利保障制度等各种宪制意义上的政治结构与制度。同时,司法裁判结论的得出,也与部门法当中的各种具体制度密切相关。法官一个“不经意”的司法裁决,可能展示了部门法制度中存在的某些缺陷。通过司法裁判发现制度的缺陷,进而进行有效的理论总结,是实现制度进化的基本路径。例如,指导性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就弥补了一个常见的交通肇事赔偿案的制度漏洞。在该案之前,就受害人特殊体质影响侵权责任的责任分配问题,没有相关制度予以说明,且各级法院判决不一。但是,该指导性案例发布之后,几乎所有的案件均判决基于特殊体质的侵权责任赔偿与特殊体质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优秀的司法裁判特别是效力较高的司法裁判,能够在制度层面树立起标杆,从而成为让其他法院参考的标杆,进而实现制度的优化。通过司法裁判实现具体法律制度的改良或者进化,是制度优化规律的重要展现。法律学说就应当对司法实践中的作法进行总结,并对比已有的法律学说,创新法律制度。
第三,通过司法判决,法律学说可以总结法律的修改/制定规律。法律是不断发展的,但是立法的保守性和落后性总是难以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当时立法落后的时候,司法总是那只最早深知“春江水暖”的“鸭”。当司法感知到社会的变革,并将社会的变革以裁判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时候,通过法律学说的总结,就可以成为上升到立法的重要一手材料。正如拉伦茨所期待的一样:“事实上,一系列构成今日现行法‘坚实部分’的法概念及裁判基准,均系以司法裁判及法教义学的合作为基础,才发展出来的。”[[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3页。]法学可以研究法律问题及实证法对此等问题所提供的解答背后之特定法律思想(“法律的理由”)、其主导的法律原则、一定的事物結构以及因差异结构而要求之差别处理,借助它们或者可以对前述解答提供根据(将之“正当化”),或者要求应提出新的解答。而只有大家理解待决的问题及其迄今的解决方式,才能真正了解新的解答。[[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8页。]并非一遇到社会变化就需要进行法律修改或制定,还需要有多种“综合反应”之后才可能进行立法或者修法程序。比如,当某个法律问题有重大争议时,法官们的裁判就可能不一致,甚至是法官们难以进行裁判,此时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甚至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的对立,于是对于新法制定的呼唤或者对于旧法律修改的呼唤就会成为时代的旋律。此时,学者们就可能基于司法展现的问题进行理论总结,提炼法律修改/制定应有的规则内涵,形成法律修改/制定的动力。
结语
上述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已经表明,通过观察司法裁判是否引证法律学说来推进,进而反思法律学说在司法裁判当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以及应当起到何种作用,是十分有价值和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既是反思司法改革面向的重要路径,也是反思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关系的重要契机。从实践层面来看,在法治发展过程中,司法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不断推进公开公正的司法,才让我们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得以有效实施,不断加深人民对法治信仰的追求。“既存原则的核心是国内的所有人以及机构,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立机构,都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并且享有法律的利益,而法律则是公开制定的、在公布之后生效的(一般而言),并且在法院公开执行的。”[[英]汤姆·宾汉姆:《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所以,司法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力量,而既有的司法判决则可以成为检验法律学说的场所,更可以成为新的法律学说形成的起点,为法治发展提供了学说基础和经验借鉴。从理论层面来看,法律学说不仅能够设计法治的制度框架,也能够预设司法审判制度的应然走向。人类司法制度的每一次变革和重大进步,都与法律学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自从法律学说诞生之后,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低估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法学家们该如何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时代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时代任务。正如季卫东教授所言:“现代法制的建設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政治的力量,也有赖于学术的质量。因为无论是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把它抽象为普遍适用的规范,还是借鉴外国的成功方法以缩短摸索的过程或减少失误的代价,都需要能保证择优决策的见地,从而也就需要在法律、制度及其社会效果研究上的理论造诣。”[季卫东:《“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评介(选登)》,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2期,第50页。]法学学术质量水平,不仅决定法律学说能否承担引领司法裁判的重任,也考验法律学说能否为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提供必要的智识来源。毫不夸张地说,理想中的法律变迁,是法律学说与司法实践演唱“双重变奏”的结果。
总之,法治生命力的来源,既有司法裁判作为内在的动力,更有法律学说作为理论的动因,二者共同构成法治发展道路上相互倚重的“双子座风景”。一方面,司法判决应当成为法律学说的“试验田”,展现法律学说的公理性;另一方面,法律学说应当成为司法判决的“动力源”,展现司法判决的规律性。然后,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看到,司法裁判和法律学说的主题任务有较大差别,即司法判决的实践立场是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而法律学说的实践立场则是通过学术研究保证司法实现裁判的公平正义。可见,鉴于主题任务与实践立场的差别,法学与司法的适当分离亦是法治持续进步的条件。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s Citing Legal Doctrin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ffective Adjudication Documents
PENG Zhong-li
(Law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Abstract:Legal doctrine is the knowledge reserve and theoretical bridge linking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intellectual engine and theoretical impetus driv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udiciary and society. The academic views of scholars are the direct manifestation of legal doctrines. In China,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judicial decisions citing the views of legal scholars.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views of 60 legal scholars were cited 307 times in 268 sample adjudication documents. Legal doctrines play the role of explaining the law, arguing reasoning and supplementing legal loopholes in adjudication documents, thus enhancing the reasonableness and legitimacy of judges' judgments on the nature of legal facts or adjudication results, and enhanc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adjudication results. On the contingent level, legal doctrine should provide possible reference answers for judicial decisions and provide effective legal methods for judicial decisions as well as summarize scientific judicial laws for judicial decisions.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analyses show that although judicial decisions can be a "testing ground" for legal doctrine, the proper separation of academia and judiciary is a stepping stone for the continued progress of the rule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the thematic task and the practical position.
Key Words: legal doctrine; scholarly opinion; citation; judicial decisions; decisional reasoning
本文责任编辑:董彦斌
青年学术编辑:任世丹
收稿日期:2021-12-01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司法政策百年发展史研究”(21ZDA120)
作者简介:彭中礼(1981),男,湖南隆回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