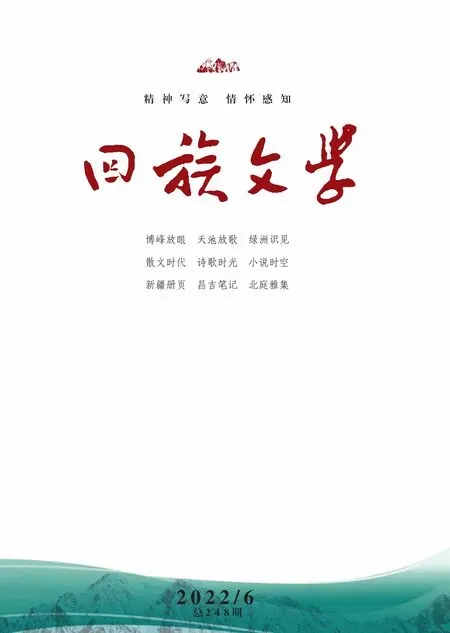火盆中的旧址(三题)
周蓬桦
青瓦与三种遐想
古街很短,依傍梅山寺。每当我路过街口,都会忍不住驻足,朝深处凝视良久,心生几分疑虑,几分惆怅,却终是没有走进去。事后思量,我只是想远远地感受一下那里的沧桑况味吧,听一听时间深处的幽寂之声。而眼前,闪过一片青瓦。
类似的青瓦建筑,我在江南的水乡见过多处,朱门深宅,屋檐翘立,通体氤氲神秘的涟漪,地气弥漫到墙角——几年前,朋友约我到扬州过春节,算是透彻地体验了一回南方的年节。直到今天,鼻孔间依然萦绕着茴香豆和黄酒的气味,还有瓦檐上的积雪,瘦西湖冰层下冻僵的白鱼。
而这一次,又路过梅山寺,却是怯怯地朝街里走近了些,蹑手蹑足地站在了那幢青瓦老屋下。稍微抬头,便见一株发了芽的老梅树,灰砖白墙似一幅淡墨国画,像包浆开片的青花瓷器,令人无端地生发许多联想,平添了些许愁绪。尽管,起初我不知晓这幢旧建筑有什么来历,经历了几代主人,有哪些缠绵悱恻的故事在这个院落里发生。
断断续续地听到八卦,在哪一朝的哪一个时期,有某一位心思细腻的书生在这个宅院里长大,他文文弱弱,说话慢声细语,冬天在脖子上系一方蓝布围巾,伸出冻凉的手去烤木炭火,再饮一杯案前冒着热气的红茶;他过着贾宝玉式的“公子哥”生活,每天游手好闲,偶尔被荷尔蒙吸引,到西园去与姐姐妹妹们调笑,满身散发脂粉气。年年岁岁,门前的车马停了又走,恰如树巢里的鸟雀来了又飞。那少年渐渐长大,唇间长了男人的胡须,他就要出发远行,到远方的城里,求学或求职,经世间的苦。他腋下夹一把发黄的油纸伞,在飘飞的柳絮下出发,途中乘坐轮船,过码头,进入喧嚷的街市,店铺与酒幌映入眼帘。在战乱年代,人的命朝不保夕,这个从富宅里出门远行的后生,原本一日三餐都要讲究,每天的下午茶也必不可少,他压根儿就没有应对江湖的能力,江湖人的一声呵斥就能把他唬住,不敢作声;几杯水酒就能被灌得烂醉,手舞足蹈地说胡话。在那样硝烟滚滚的乱世,他若要过得舒坦滋润,必得经过一番蜕皮脱骨的涅槃。而在忽然的一天,他像一滴水从人间蒸发,家人再也收不到他的一封家书——像一首钢琴曲的篇头戛然而止,那个隔三岔五地写信要钱要物,总是招惹讨嫌的人按下了暂停键。家人免不了火烧火燎,女人们哭闹一番,急急地央手下人去寻,搜遍世界,自是没有线索,白白花了不少银两。时间一久,便也成了一桩悬案。当然,在那个年代,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听得多了,人们也并不以为稀奇。
故事讲到这里,忽然想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这篇小说中,博氏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曲折悠长、忽明忽暗的迷宫,让人物在历史与现实中来回穿梭,像一根生长在墙壁上的茑萝花藤,或长或短地适应着时空的凹凸结构,最终抵达玄幻迷人的叙事效果。而在我看来,少年的命运具有同样扑朔迷离的性质。如若沿时间的河流刨根溯源,甚至可以无限漫延开来,像一只盘踞在高山之巅的愤怒猛禽,实现无尽头的飞翔。此时此刻,我呆立在现实的地面,望着青瓦屋檐上新长出的一簇春草,脑海里冒出三种遐想,附录如下。
画面一:随着他的失踪,各种混杂的消息传来,议论是免不了的,每每从报纸上看到一则照片模糊的认尸启事,都会给宅院带来一阵不小的骚动,人们前往报馆打探,结果都是失望而归,让哀伤的话题卷土重来。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事实上,少年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遭遇不测——原来,是他在偶然的一晚看了一场戏,遇到了一个民间戏班子,他和班主聊得投机,班主赏识他的书生气质、才子佳人的容貌,便有心拉他入伙,还说他的前生乃是梨园名角云云,拣玄妙的话语哄他。他着了道,便决定加盟戏班,让生命从头开始,或者叫再续前缘。自此,他跟着戏班开始了漂泊流浪生涯,彻底告别公子哥的形象,他要把此生的命运与一帮走江湖的人绑在一起。这对他而言,既是宿命,又是必然。他是从心底里对自己不满,决意要告别旧的家庭出身,把从前的一切像泥胎一样打碎,让风雨塑造一个全新的个体。他更姓改名,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而若要完成这些,头一桩事便是断绝旧交,与过去做个了断。他还年少,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消费与试错。
他的个案,让一句话得到验证:“人的改变,是从讨厌自己开始的。”
画面二:在他走后不久,西园的一位女子便像被秋霜打蔫了的花,病恹恹的,提不起精神。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每天搽粉抹黛,关心自己的容貌。在她看来,女为悦己者容。她私下里叫他“毛弟”,因为他长得像她豢养的一只花猫,毛色光亮柔软,瞳仁闪闪。如今,她心悦的毛弟走了,美貌于她失去了意义,眼中的事物也起了变化,园里的茶坊与荷塘没了往日的味道和光泽,连同瓦屋顶上的树冠,都散发一种淡淡的哀愁。姐妹们约她采花或女红,她婉言谢绝;正月十五,表妹约她去梅山脚下看花灯,她勉强去了一会儿,就溜回了闺房,被冻得牙齿咯咯打战。在阁楼里,她抱了暖手袋,浴了足,洗了铜盆,点燃一炷香,来到花梨木的窗格前,手托两腮,望着一轮明月叹息。当时,东园的少爷还没有从人间失踪,她不过是在盼望一封字迹工整的书信。只是有一件事,始终让她困惑:他是家族独苗,为何偏要远行呢?放着现成的安乐不享,丢下蜜一样的生活,偏偏要到外面吃苦遭罪,要知道,祖上创下这么大的一摊子家业,是足够他挥霍享受一生的呀。她听说书人的唱词里讲,富贵不出三代,换句话说,无论你的祖上如何精于算计,荫求祖荫、余祈富余,但到了后辈的某个时段,家族里必定要出一位逆子,他会神使鬼差地败了家,破了产业,让一幢日积月累的大厦迅速倒塌,而这乃是上天所注定。她每每听了这种话,是不相信的,认为这是贫穷的人家盼着富家败落,是嫉妒心理作祟,当他失踪的消息传来后,她信服了。她结结实实地哭了一天。而此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三个多月了。她原本没有任何经验,万没想到,在他离家前两个人仅有的一次温存,居然能够生根发芽。要命的是,躲在深闺里没用,因为肚子会一天天大起来,这个秘密像一团火,会连同包装纸一起燃烧。而她的命运,将由此改写。
画面三:多年之后,名满天下的戏曲名角慕容秋荣归故里,他带领的团队要在老城的梅山剧院义演七场,为当时的南方水灾进行募捐。回到故乡,眼前的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他对此态度却显得极为淡然。其时,他的生活已经不再依赖记忆,甚至把少年时代发生的一切早已全部清除,当地的演出组织者在宴请席间每每提及——提及他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他都显得一脸冷漠,含含糊糊地说,记得自己的旧居是一幢深宅大院,如今已无亲人故交可识。他笑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他已与旧时代彻底切割。故乡的人对之表示不解,觉得他不近人情,但也不好违了大师的态度。当然,人们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人们看到的只是他表象的光环,而永远无法触及其人性深处的本真相貌。准确点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曾从悬崖上跌落,在林中被劫匪追杀,七次中弹负伤,全身上下换过数十人的血浆。最后一次,他从马背上跌落,脑袋遭到地面撞击,得了严重的脑震荡,成了植物人,躺在床榻上长达九个月零八天半,靠输液维持生命。有人给出诊疗方案,对他实施了当时堪称冒险的开颅手术,整个后脑勺都换掉了——他后面的半个脑袋是另一个人的,终身都有隐隐的排异反应。好在手术做得很成功,让他苏醒过来,并经过一段休养后重新登上舞台。如今,残存在他脑海里的,已经不再是他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多个人的记忆杂糅梦的碎片,时而呈黏稠的糨糊状,时而呈冰河的凝固态。在他的耳畔,回响着遥远的幻觉,时而是子弹的啸声,时而是锣鼓的喧鸣。尽管,从表面上看,他容颜光鲜,甚至是有几分和蔼可亲的样子,尤其站在舞台上,一招一式,招招式式炉火纯青,他把一种唱腔发挥到了极致。往往,声线停止后会激起三波潮水——掌声,掌声,掌声。
总而言之,天才的不凡的命运造就了他,致使他无论转身、行走或停留,都显得多维、传奇与复杂。当大幕落下,他的人生已经走完,留下了一幢青瓦旧居,供后人观瞻,也留下了重重雾霭与N种遐想——这就好比一个故事的多种讲法,你无法确定它属于虚构,或者真实。
火盆中的旧址
遥远的夏天,风雨飘摇,一幢破败的茅屋——雨水顺着瓦檐狂泻而下。轰隆隆的雷声,闪电照亮雨中的天井。
那一年我六岁,接连几天不吃东西,因为生病而哭闹不止,身体瘫软在母亲怀中。得了什么病呢?大约是肺炎,咳嗽不止,还出黄疸,似乎命悬一线。母亲用臂弯摇晃着我,企图让我安静下来,但我虽然双目紧闭,却分明听到周围都是哗哗的雨声,还有从天际传来的阵阵杀伐声,脑海里出现各种画面,险象环生。恍惚之中,听到母亲在我耳畔嘀咕:“姥姥去请大夫了,救命的人要来了。”
听了她的话,我突然睁大了眼睛,我的视线移开了母亲布满忧愁的脸。在那一刻,我的视线掠过屋顶,望见了窗外比屋梁更大的雨柱,还望见了远处被雨水泼打的硕大的树冠——更为奇怪的是,我望见了裹着小脚的外婆,吃力地行走在一片泥泞的乡道上。她的头部顶着一块遮雨的黑布,身后跟着一位胡须飘飘的乡村郎中。
很快,雷声熄灭,一场阵雨也收住了脚,青草浓郁的气息弥漫到房间。那位胡须飘飘的人在屋内坐定,虽然留有胡须,但似乎并不太老。他用手抚摸我发烫的前额,又捉了我瘦弱的手腕把脉。我能听到自己的脉搏突突跳动的声音,那是向世界发出求救的信号。
接下来,郎中命母亲把我抱到木床上,仰躺下来,赤裸的上身袒露出肚脐,用酒精洗净周围。郎中一番忙碌,从药包中取出几根蜡纸筒,用火柴点燃,又取出一枚铜钱,将铜钱置于脐上,钱孔对准脐心,再将蜡纸筒扣于铜钱上,蜡纸筒下端与脐相接处用湿面围成一圈,固定密封,勿令泄气,脐周用毛巾围好,然后将上端点燃,待燃至离脐半寸,迅速将火吹灭,以免灼伤皮肤。
当一根蜡纸筒燃尽之后,肚脐上出现了许多残留的黄色粉末,像一堆耳屎。外婆和母亲守在旁边,见状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这是什么?”
郎中回答:“黄疸毒素。”
郎中说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孩子的病就好了。那一天,郎中给我灸了三针,燃掉了三根蜡纸筒。临走时,郎中将灸法教会给母亲,留下几十根制作好的蜡纸筒,起身告辞。在我模糊的印象中,郎中的话语不多,表情比较肃穆,他离开茅屋时腋下夹着一把油纸雨伞。
天晴了,郎中消失在雨后洁净的乡路上。他有些驼背,远远看去,仿佛把整个村庄移到了肩上。
听母亲说,郎中走后,我大睡了一觉,醒来感觉病好多了,当晚便有了饿意,喝了一碗小米粥。
此后,母亲依照郎中的叮嘱,每天给我进行灸疗,不管怎样,眼瞅着我一天天好起来,全家人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灸疗法进行到第三天时,发生了一点意外——那一天,母亲正在如法炮制,我突然感觉一阵腹疼,疼得大声哭叫。母亲停止动作,并且把在院子里收拾炉具的外婆也喊进屋来。
而我边哭边叫:“嗷,疼,疼。”
母亲将蜡纸筒从我的肚脐移开,发现上面已经堆积了许多粉末——这是体内的毒素!每次灸疗完,母亲都遵照郎中的话,把灸出的粉末拨弄到一个纸片上,放到火盆里焚烧干净,以防止病毒传播。此时,母亲望着纸片上那些残留的黄色粉末,呆愣良久。毫无疑问,灸疗引发的副作用让母亲对郎中起了疑心。接下来,她做了一个堪称聪明的试验:将一根蜡纸筒点燃后,放在一块石板上进行灸治,结果不出所料——当蜡纸筒燃尽,石板上留下了同样的一堆黄色粉末。母亲惊讶地叫起来,骂了一句“骗子”。
当然,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也不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发觉上当受骗后,母亲气得脸色涨红,可恶的郎中让她花了全家半个月的生活费不说,主要感觉太窝囊耻辱了。这个可恶的骗子,连一个小孩子也不放过,也不怕遭雷劈啊。
那一天,母亲骂了能骂的脏话,还把外婆责备了一顿。
其实,外婆相当无辜,她和郎中素不相识。常言说人病乱投医,她是在沙河镇上打听诊所,被一个在街头闲逛的老太太带路,七拐八拐地穿越了好几条胡同,最终找到了郎中的家。
好在娘儿俩发泄完毕,火气渐渐消退,最终自认倒霉——权当这件事没有发生。一番互相开导,她们决定接受教训,把剩下的十几根蜡纸筒投入火盆中,连同郎中留下的一个地址,付之一炬。
母亲和外婆不再提及此事,因为这件事不让人愉快。几天后,我的病竟然好了,又回到了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队伍中。于是,与郎中再次发生交集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断绝了。
话说多年之后,我读到一本自故乡邮来的《沙河年鉴》,随手翻到“地方名士”栏目,从一则词条中了解到郎中的事迹:他用高超的医术终身行医,广受乡人称道,享年八十七岁。其实,在成年后我就知道母亲当年误会了郎中。因为蜡灸黄疗古法运用并不广泛,人们难免对它认识不足。至于其能够直接从石板上提炼出粉末,虽然颜色相同,但此粉末非彼粉末,也就是说,从石板上提炼的粉末不含人体毒素。
这小小的偏差,仅用肉眼是看不到本质的。
我想,当人们回首往事,会发现曾经的误解、愤怒与争端,往往出于认知的局限与偏差,它们导致了判断的失灵与失误。面对那些发生了的过往,当省悟时一切都晚了,只好将错就错——假如事情放到现在,我会从火盆中救出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而此时,我们只能凭借想象,祭奠郎中一生风云密布的表情。
削掉的铅笔
那天在白山脚下沿河散步,看到一个低头的孩子伫立河边,全神贯注地用一把小刀削一根柳树的枝条,我意识到又一个春天到来了——这是山林里的春天,几天后会有一个万物花开的画面出现。
我忽然驻足,回头观望河边的少年。不知怎的,他削柳枝的样子让我想起削铅笔。
当时,我们家还住在鲁西平原的沙河镇上,背景是贫穷的70年代。印象中,那里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生长着在风中起伏不定的苇子林,还有一棵挨一棵的果树。当夏天来临时,一场风雨会吹落许多树上的果子,我和伙伴们便潜入苇子林中,捡拾落果,每每从苇子林里钻出来,赤裸的胳膊都会被荆草划出许多血道道,好久才会结痂。
那天一大早,我被母亲叫醒,我一边含糊地答应,一边翻身向里继续睡觉,企图接续一个被打断的梦。但母亲这次不客气地掀翻了我的被子,大声嚷嚷说:“快起床,从今天开始,你要上学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上学这件事让人兴奋,因为从此以后,不必再羡慕街头那些背着书包昂首挺胸的大孩子了。母亲已经把昨晚缝制好的书包递到了我眼前,里面装着演草本、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还有一个铅笔刀。而课本是到学校后才发下来的,至今记得新书拿到手里,一股油墨香扑鼻而至,它在鼻尖萦绕多年。
起床后,原本想体验一下削铅笔是什么感觉,可惜母亲已经替我削好了。望着木桌上留下的一堆碎末末,我噘嘴赌气,责备母亲多事儿,猜想她是把一桩开心事揽给自己享用了。母亲不清楚我心里的想法,拿出一块抹桌布,把那堆碎木屑轻轻地扫进竹篮里。
学校离我们家不算远,绕过两条胡同就是,校址在一片操场上,远远地看到一棵老槐树,树杈上悬挂着一口生锈的老铜钟。
时间过得很快,上学大约半年之后,我就改变了看法:事实证明削铅笔是一项技术活,而我真的削不好。手持一个又细又长的怪物,不知从何处下刀,有时候好容易削出铅芯,却一不小心就折断了。我把这些统统归罪于铅笔刀太钝——当时,旋转式铅笔刀还没有普及呢。为此,母亲把一拃长的小刀往磨镰石上蹭啊蹭,刺刺地冒火星。她神情专注,像是要完成一桩改变世界的大事情。
眼瞅着锋刃足以达到削铁如泥的程度了,才把小刀收回铁鞘。不料,却因此发生了一桩小事件:
被磨亮的铅笔刀太过锋利,有一次削破了我左手的食指——小刀切割木屑的同时飞快地钻到了我的肉里,手指肚上渗出了一颗大大的血珠。我忍着疼,又怕被人发现,只好把手指头含在嘴里,远远地看上去,像傻瓜的经典造型。
血流到嘴里,一丝丝腥而咸的液体。
我的同桌叫什么名字来着?一时想不起了,只知道她是个贼机灵的女孩,轻轻一瞥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她当场“扑哧”一声笑出来,现场顿时一阵骚动。当时正上晚自习课,听到笑声,全班的同学都转过头朝我张望,神情诡秘好奇。女老师姓戴,及时发现了问题,来到我的书桌前,她以为我在课堂上搞怪捣乱,口吻严厉地命我把手指头从嘴里取出。我在张口的同时,引发了全班同学惊诧的叫声。
因为牙齿上有血,形象可怖。我的脸一阵发烧,恨桌子底下没有地缝可钻。尽管,戴老师在了解情况后没有当面做出批评,还宽慰了我几句。但这件事却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出了糗,同学们议论纷纷:没出息的笨蛋!连个铅笔都削不好,将来还能做什么呢——一个差等生。
这话似乎没错,因为在刚入学的头一个学期,全班上下就知晓我不是个好学生了,人人都知道我太贪玩,诸如课堂上偷看小人书,听课时脑子开小差;每天的作业不好好做,考试靠“打小抄”蒙混过关。而且,老师一不留神,我就哧溜一声跑出课堂,到校园外的小树林里去了,那里有一湾大水塘,水塘边飞着蜻蜓、蝴蝶和各种花翅鸟,我本打算进去捉一只蝴蝶再放飞,听到哨子声立马就离开,但往往因为太忘情太投入,就把课堂的事忘到了脑后,直到放学的铃声响起了,我才从中惊醒,撒开腿离开小树林往回跑。
第二天,我为此遭到罚站,但总是屡教不改。唉,这一次,戴老师一转身就去了我家,把我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
那天,放学回家,我原本欲向母亲诉说委屈,哪知母亲一脸严肃,当即下令:“晚上别睡觉了,老老实实地练习削铅笔。”
当天晚上,我就着一盏煤油灯,把一支好好的铅笔削成了碎屑,那只受伤的指头在哭泣,头发被油灯火点燃,烤出了一股焦煳味。
我一边练习,一边在心里责怪同桌。接连几天,我对她不理不睬,撂脸子给她看。哪知这个女生太聪明了,很快揣摩到了我的小心思,在一天上晚课的时候,悄悄地把一支削好的铅笔用胳膊肘“塞”给了我……
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意思。后来,学校里筑起了一道院墙,把去小树林的路彻底封住了,我的一颗躁动之心,也渐渐平息下来。这么着,渐渐地我迷上了课业,尤其是作文课。
多年以后,写作的习惯让人常常陷入回忆:童年的往事,少年的冲动,以及削铅笔这类的小事例,都会在记忆中浮现,感觉苦涩又美好啊。去年春节,从县城绕道,去了一趟故乡沙河镇,有好事者召集了一次小学同学聚会。结果,原定两桌人只凑了一桌。席间的忆旧是免不了的,我向人打听这位聪明女同桌的下落——仅仅因为她帮我削过铅笔!记得我还回赠过她一块水果味的橡皮,以示和解。
遗憾的是,人们把头摇得像货郎鼓,竟没有人知道她成年后的去向。
我在心里感慨:从小学到中学,削掉了多少支铅笔啊,砌起来应该是一堆柴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