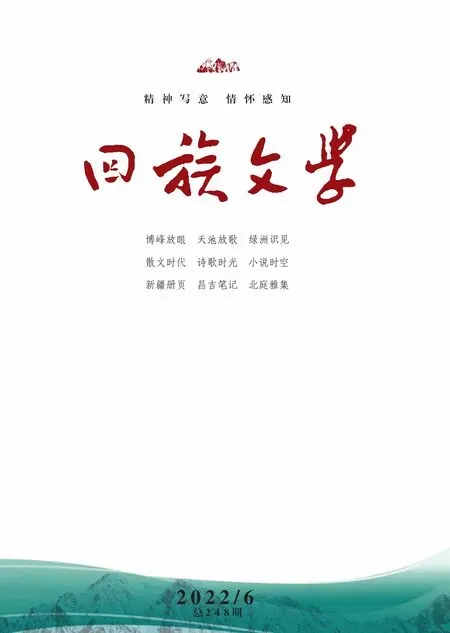走进米东的四种方式
张映姝
做客玉希布早村
十几年前,我路过几次玉希布早村。去峡门子风景区,沿着公路一直往山里开,快到林场时看到的村子,就是玉希布早村。村民的房子沿着公路两边延伸,不宽的马路上经常被壮硕的黑底白花的奶牛挡住,你使劲打喇叭它们也不理睬,还扭过头睁着无辜的大眼打量你一番,然后才优雅地不慌不忙地挪动脚步。羊群也经常遇到,二三十只不用担心,一打喇叭,就往路边涌去。若是几百只,那就有点麻烦,羊群是跟着头羊走的,羊群的队伍那么长,你怎么打喇叭,隔着两三百米的头羊都不理视来自后方的动静,眼睛只盯着前方,一根筋地沿着公路向前进。车子就这样跟着羊群前进,若不是骑马或骑摩托车的牧人见状赶到队伍前面,把头羊赶到路边,车子慢腾腾地过去准保得浪费十几分钟。
村委会在进山的路的左边,若不是那块牌子,路人是不会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的。那些年,我们每年春季、秋季进山去玩。春季去踏春,挖蒲公英,掐苜蓿头,看远处的灯杆山、马牙山,遥想当年的道士走几十公里山路下山,然后背着粮食、日用品等,再走几十公里山路上山。遥望雪峰的时候,经常想起山顶上的灯盏初一十五都会点亮,为山下的民众祈祷平安。秋季去看金色的白桦林和胡杨树,看秋天的太阳一点点西落,莫名的忧伤一点点浮起,这时,只有羊咩牛哞的声响和袅袅的炊烟,才会把忧伤一点点地驱赶,让我生出生活就在此处的感慨。
我从未走进这里的一户人家,聊聊他们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生活。这个村子,像一个童话,离我这么近,又离我那么远,直到姐姐带我去看她的亲戚纳西一家。短短的几年时间,姐姐一家和纳西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亲戚,纳西家的大小事情都会征求姐姐、姐夫的意见,纳西家族里的婚丧嫁娶一应事宜,姐姐一家都会出席、帮忙。遇到内地来的朋友,想了解、体验哈萨克民族风情的,姐姐也会安排到纳西家坐坐,喝一壶正宗的哈萨克奶茶,尝尝正宗的哈萨克饭食。纯朴的纳西一家会让客人带着满心的好奇而来,带着满心的欢喜而去。
第一次去纳西家,同行的还有安徽来的潘老师和宁夏来的杨老师。走进院子,就闻到抓饭的味道。一锅抓饭在院落里的大灶上雾气腾腾的。走进房间,我们被惊到了,宽敞的客厅里一大半是炕,靠南墙的一面垛满了绣花的被褥,炕上大大的长条桌上摆满了吃的:干果类,油炸的馃子(包尔萨克),各种水果,居中是两个高脚的大玻璃盘,托着摆放整齐的馓子。桌子四面的炕上摆放着大大的靠垫和坐垫,绣满各种艺术化的羊角图案,色彩搭配醒目,绣工精细繁复。我们不由发出赞叹,竟然不舍得坐在上面。姐姐说,这些都是纳西绣的,她的手艺好,参加了村里的绣花合作社,靠绣花一年的收入也不少呢。纳西能听懂汉语,却说不出来,腼腆地笑着,低头给客人倒着奶茶。
纳西的婆婆陪我们坐着,纳西和丈夫赛里木汗忙活着饭菜。我打量着这个殷实富足的家庭,总感觉有点冷清,缺了点什么。姐姐悄声说,纳西不能生育,没有孩子是这个家庭的隐痛。幸好与赛里木汗感情很好,否则……我这才明白,这个家里缺少的是孩童的喧闹和欢笑呀。难怪纳西的眼神里除了羞涩,还有一丝落寞呢。纳西已过生育年龄,最终的希望就是抱养亲戚家的孩子了。
第二次去纳西家,我专门给纳西带了一件礼物,是苏绣的一条蓝色丝巾。我猜想,蓝色是娴静的纳西喜欢的颜色,自由而宁静。我还想让精于哈萨克民族刺绣的她,看看苏绣的花样和绣法,说不定她会受到启发,开发出新的图案呢。姐姐把我的心思告诉了纳西,纳西略显粗糙的手轻轻抚摸柔软的丝巾,脸上、眼神里的欢喜流泻而出。
吃过饭后,我们在院子里聊天。一会儿,就来了好几拨女人。见了面,就紧紧抱住姐姐问候。姐姐笑着给我们介绍,这个是纳西的姨姨,那个是纳西的嫂子……亲切熟悉得就像一家人。我们看着她们说话、拥抱,内心洋溢着朴素、良善的情愫。
过几天,我又要去纳西家做客了。姐姐说,纳西要带我们去她家的牧场转转,那里的花就要开了。纳西也知道了,我喜欢花花草草的。
哦,忘记告诉你们了,玉希布早,是哈萨克语三个牛犊的意思。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牛那么牛气冲天了吧。
锦鸡儿花开哈熊沟
从玉希布早村的纳西家去新地梁,我们走了一条近道——进哈熊沟,翻山到独山子村。车子出峡门子后不远,在丁字路口向右一拐,就进入哈熊沟。
据林管站人员说,上世纪50年代建站时,这里能看见雪豹、哈熊等大家伙,北山羊、黄羊、狐狸等更是经常见到,常见的鸟类多达几十种。这话我是相信的。那个年代,新疆很多地方人烟稀少,却是动物的自在之地。我听50年代末就在准噶尔盆地屯垦的父亲说,少有人去的林地草深枝密,蹲在草丛里方便的职工,竟然能一把搂住觅食而过的马鹿的脖子。现在,雪豹像个传说,哈熊也不见踪迹,只留下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哈熊沟。
路越来越窄,路面的砂石明显增多,上坡下坡交替而来,车子颠簸起来,几个女人不时发出惊呼。我提醒姐姐开慢一点,安全第一。开惯了山路的她嘴上答应着好,车速却一点没减。车内的几个姐妹的叫笑,起初是因为颠簸,后面夹着有点夸张的故意。久居城市的她们,需要一场山野里的疾驰,为波澜不惊的生活,或者死水般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注入活跃因子,增加一点刺激感和新鲜度。况且,况且,这是5月,5月的山野,5月的天空,5月的春天,5月的我们。
越来越多的灌木丛铺展在山坡上,连成一片。野蔷薇、锦鸡儿,还有爬地松,大多是这些。眼下,盛开着挤挤挨挨的黄色花朵的是锦鸡儿,野蔷薇的黄色花朵掀起的蜂蝶的盛宴还没有开席。我坐直身子,深情地望着窗外春意盎然的山野,望着清香浮动的锦鸡儿花。这雀舌般的花朵,我每年都要摘一些,尝尝鲜,其余的就珍藏在冷藏柜里。闺蜜小聚,气氛氤氲之时,酒香茶香之后,一盘清香扑鼻的锦鸡儿花饼的隆重出场,是众望所归,把友情的相聚推向又一个高潮。今年,眼看着花期半个月的花季就要过去,我还未采摘呢。想到一年内都无锦鸡儿花饼的高光时刻,心情不免黯淡起来。
这些黄色的是什么花?有人问。锦鸡儿花。姐姐回答。哦哦哦,就是映姝姐做花饼的花吗?就是这种花。我头也不回地说,眼睛仍然盯着窗外。那我们去摘吧,这样就可以经常吃花饼了。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现在就可以摘呀,我们原本就是为踏春而来的呀。
几个女人在盛开的灌木丛中,像蜜蜂般辛勤忙碌着。在黄色花朵铺排出的春天的背景里,她们像五朵盛开的花朵。我不禁为眼前的场景和脑海里涌现的比喻欢愉起来。
采摘锦鸡儿花,并不是件轻松的事。锦鸡儿枝条密布硬而长的刺,一朵朵黄色的蝶形花就长在刺丛中,每摘一朵,都得小心翼翼避开。不时传来姐妹们被刺中的叫声。这个花为什么要长刺呢,不长刺就摘得快了。子茉咕哝了一句。因为每一朵花,都度过了寒冬,每一种美,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我说。5月的阳光下,蜂蝶飞舞,清香淡淡,有那么一阵,“我们不说话,就很美好”。
映姝姐,我以后再也不要求你做花饼给我吃了,我从来不知道,采摘锦鸡儿花这么不容易。子茉面带愧色地说。采摘了半个小时,她的塑料袋里才有一丢丢的花。当她再吃花饼时,每一口,除了美味,还会有更复杂的味道和心绪吧。
南果北种柏杨河乡
几年前参加米东作协的一个采风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观长山子村的设施农业基地。走进高大的温室大棚,看见一排排整齐的地沟,有通常大棚里枝叶茂盛、花团锦簇的模样。仔细一看,一株株硕大的仙人掌科的植物规规矩矩地生长着,三棱形的叶片长达一米左右,被固定悬挂着左右对称生长,每个叶片上有多个绿色的芽苞。此前,我无数次吃过白肉、红肉火龙果,知道它是热带、亚热带水果,却对火龙果这种植物一无所知。我围着植株转了又转,不确定这灰绿色的仙人掌科的植物,能结出鲜艳、汁水丰富、个头不小的火龙果。我问,果实结在哪里?棚主笑了,指着叶片上的芽苞,这就是它的花,一个花结一个果。我更好奇了,这个叶片上有三个芽苞,难道结三个果?他微笑着点点头。带着一路疑惑,回到家,我就百度了一下火龙果的内容,果实累累的火龙果种植图片让我瞬间惊呆了。
就是那次采风,我还头一回知道了五彩稻、稻田蟹、东海子景区等等。在我的脑海里,关于米泉的零星认知,才完全让位于米东区的崭新发展形象。
友人知道我对植物感兴趣,去年邀我去米东看自然风光。返回的路上,专门带我们去柏杨河村看人参果种植基地。走进大棚,一行行植株整齐排列,植株近一米高,却不见人见人爱的果实。原来人参果已经收获完了。我看见植株上还有一些小小的花苞,两三个月后,它们就会成长为带紫色条纹的白皮果实,水润、爽口,伴随着淡淡的雅香。
大棚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水果大王”张运华。自2016年开始种植南方水果以来,从人参果、火龙果,到百香果、木瓜,他已成为柏杨河村“南果北种”的带头人。如今,围绕“南果北种”产业带动的休闲旅游、采摘观光发展模式,带动了村里的花卉、蘑菇、草莓、多肉种植。具有独特优势的乡村振兴产业已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并形成良性循环。
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无论成败,都值得称赞。张运华是本地人,从1996年开始种植大棚蔬菜,春秋种西红柿茄子,冬天种毛芹菜,勤于钻研的他早就成为种蔬菜的行家里手。2015年他得知张掖大棚种植火龙果和人参果成功的消息后,也萌生了种植大棚水果的念头。说干就干,在去张掖实地考察之后,来年春天,他开始试种火龙果和人参果。如果没有他的心思一闪,没有把一闪的念头落实为具体的考察行动,如果不是有不计得失的放手一搏,也许他还在轻车熟路地种菜,周围的村民还在原来的种植模式上打转,柏杨河村还是原来的模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是一个例证。
大棚的另一边,是百香果植株。百香果,又叫鸡蛋果、紫果西番莲、洋石榴,是西番莲属草质藤本植物。绿油油的百香果藤蔓铺展在棚架上,垂挂一个个青色的果实。过不了多久,这些果实就会变成紫色,就可以采摘上市了。
我们没有见到水果大王,正在大棚里劳作的女人说,他去村民家的大棚里了,去技术指导,他忙得很。我们相视一笑,走出了大棚。
蹚水水磨河
当一个地方,可以让你重温记忆深处的某些场景、某种心境,它就是个值得被记住的丰饶之所。它像带着密码的基因细胞,埋藏在身体里,随时光流逝,潜移默化又不为人知地影响着你,丰富着你,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你。
水磨河流淌在米东的土地上,流淌在独山子村的山野,流淌在新地梁村的坡下。开过去的车,走过去的人,都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因为公路沿着河道而走,公路悬在高处,河水哗啦在低处,在山谷里。依河而居的村民,到处闲逛的牛羊,也不会轻视它,因为它是此地唯一的水源——母亲河。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河,一条叫水磨的河。这条河,千百年来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随着它的无尽流淌而流逝;如今,这块土地上的生生不息、时代巨变,还在它的无边吟唱中生发、繁茂。
当我们的越野车逆流而上,到达可行之路的尽头,河水一览无余地平铺在石滩上。两条小河从不同方向的山地蜿蜒而来,汇流于此。河滩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此处,河面并不宽阔,最宽处不过五米;河水也不深,最深处也只到膝盖。这样的规模,在南方只能算是溪流。它与我的预期实在不符,不禁随口而出,这水磨河也太窄了吧。友人说,你可别小看这条河,七八月份,冰雪融水丰沛之时,河面就宽阔很多,如果山上下大雨,水流滚滚而下,裹挟山石而来,河面可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我留意观察,河床是有百十米宽,两岸的树林茂密,多是半抱的老榆树、老柳树。裸露的河床上无树,小树也不见踪迹,只有小蓟、牛蒡、飞蓬、点地梅之类的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这样的河床说明,丰水期河水的流量是很大的,河面也宽阔得多。若是长期无水,河床上是会生长出灌木丛和小树的。河床上布满石头,大块的石头都在河流的中间,越往两边,石头越小。
河水清澈见底,各色石头在水底安静地躺着,安静地灿烂着。红色的石头,有的发出刚出炉的红砖的颜色,有的是枣红色、灰红色,还有一种是葡萄酒的颜色,带着细线般的白纹。土黄色的石头,有着细腻泥块的纹理和质地。灰黑色的石头,一般大而不规则,一看就是从山体崩裂的。友人在河道中看中了一块,我和她费尽力气只搬了十几米。我和她站在烈日下的河床,计划着把它安放在她家院落里的哪个位置,憧憬着它与人为设置的花境和谐地融为一体。更多的是戈壁滩常见的鹅卵石,灰扑扑的表皮带着麻点。我捡起一块小而薄的石头,弯下腰,侧伸手臂,将它扔向水面。它扑通一下,溅起一个水花,就沉入水底,完全不顾及我试图让它在水面连续跳跃几下激起一连串水花的希冀。这么多年了,我依然打不好水漂。当年教我打水漂的小伙伴,如今远在何方,他是否会想得邻居家那个怎么也学不会打水漂的笨女孩呢。
下来吧,水一点也不凉。友人的呼唤将陷入沉思的我拉回现实。冰雪融水怎么会不凉呢?我的目光犹疑到白雪皑皑的博格达峰上。它就在那里,一抬头就扑面而来,带着神山的威严气质和严寒的白色标配。我把手探入水中,凉飕飕的感觉从指尖传导向手臂,就消融了。我的手抚摸着水中的石头,水流抚摸着我的手。友人已经下水了。我的身体被水流的温柔抚摸唤醒,迫不及待地脱去鞋袜。就算冷,也要尝试蹚一下这博格达雪峰融化的河水。看到我的举动,几位女友也跃跃欲试。
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彻骨寒冷。脚刚踏入水中,一种刺激性的冷传遍全身。几十秒后,腿脚的皮肤就适应了这种冷,暴晒在烈日下的发热的身体,将冷的刺激改变成凉爽的快意。短暂的惊叫变成咋咋呼呼的欢笑,几个女人仿佛回到了童年,要么在河水中拉着手前行,要么在水中翻捡着石头,比比哪块石头好看、有意韵,要么就坐在石头上用脚撩拨出水花……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女孩,住着女孩的永不褪色的恒梦。
我坐在水中凸起的一块石头上,感受流水、山风带来的心灵悸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唯有心灵宁静方能体悟。低头,无意间发现,石头上有米粒般的黑点,在流水中颤动。我好奇心大起,捡起一块石头,仔细打量。应该是一种水中生活的虫类,附着在水中的石头上,估计靠捕捉水中的微生物为食。它们一般出现在水流平缓的水中石块的侧面,这样会方便它们捕食吧。
玩闹之余,有人提议,我们以今天蹚水的经历写一篇同题文字吧。几天后,我写了一首诗《蹚水的女人》,结尾是这样写的:
三十多年了,她早忘记那种痛
三十多年了,她已习惯于另一种生活
忍受,抗争
再次忍受,再次抗争……
她修炼成铁,如她所愿
没有什么能让她轻易融化
她从未放弃百炼成钢的打算
就这样失败了,轻易地
被雪水的冰凉,而不是火焰的滚烫
望着耸立的雪峰,她听见
咔嚓的冰裂,向身体深处爬行
——纳西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