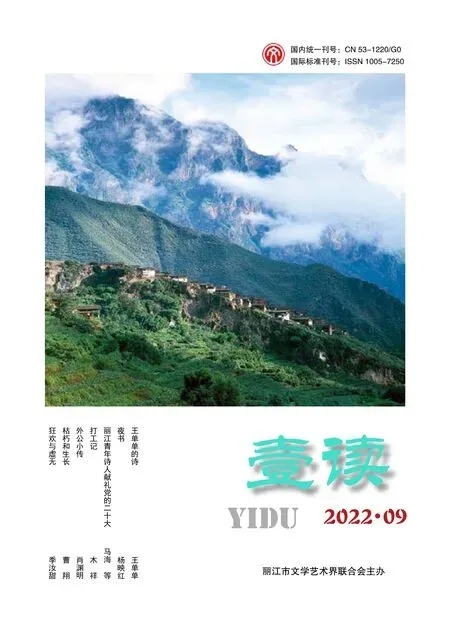人世间失踪的命运
——阅读何松的诗
◆韩艳娇
何松是80年代末成名的校园诗人,他和他的同学在云南校园文学社、校园文学发展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早早成名的校园诗人,此后的30多年,何松有过对诗歌写作日渐式微的失落,“当年那些和我们一起写诗的人大多都已‘渐行渐远渐无书’了。”他一度把写作重心转向其他文学体裁,但阅读他的诗,我们感受到了他把毕生的思想激情和想象力交给了诗,他的作品充斥着诗歌感觉的敏锐和趣味上的纯真。
一、生命的轻与重
云贵高原上的诗人们多乐于吟咏风和云,但何松几乎不写风,也不写云,他专注写有形之物:蚂蚁、羊群、河流、街边小贩、小虫子、小女孩、李大爷……有形之物都有宿命式的有限,诗人对有限的体悟微妙而深刻,“又有谁能逃得过在这人世间失踪的命运”。
一千只 一万只 一百万只
一条黑线
从山腰直到山的顶部
……
而这一切都在五分钟后的一场暴雨中结束
二十分钟过后 雨过天晴
这庞大的蚂蚁军团在雨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目睹这个过程
就像上帝目睹公元334年亚历山大远征波斯
和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的庞大军团
在时间中消失一样
像黑夜消失在黑夜
时间消失在时间之中
这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消失在雨水中的蚂蚁军团》
蝼蚁如此渺小,但“一千只 一万只一百万只”蚂蚁团结在一起就是一个庞大的蚂蚁军团,它们有秩序、有目的地行动,“像是要去参加一次改变国家命运的战役”,这样团结的队伍却在二十分钟的雨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弱可以变得强,强也可以变得弱,蚂蚁军团的溃败既是诗人对于弱和强变化的思考,也体现了诗人对于宿命式有限的感悟,而接下来的“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和“拿破仑远征俄罗斯的庞大军团”的消失是对宿命式有限的补充说明,看似坚不可摧的力量,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如此渺小,逝如落叶。
那些在地震中失踪的人
那些在泥石流、矿难中失踪的人
那些在大街上平白无故失踪的人
那些在海难、空难中失踪的人
那些在地上、海上、空中失踪的人呵
都只是人间暂时没了他们的消息
而最终,又有谁能逃得过在这人世间失踪的
命运
——《那些失踪的人》
生命最极端最暴烈的“消失”莫过于死亡,人们匆忙地投入到一生的快乐与操劳中,肉身终受死亡限制。地震、泥石流、矿难、海难、空难,在无从抗拒的天灾面前,生或者死,都是偶然。在命运面前,人只能被选择的生存。诗人对命运穷尽性的体悟,道出了个体对人生无常的恐惧。
小芸死了
早上我还看见她
扎着弯弯扭扭的小辫走出村口的
她九岁,才读二年级呢
小学校工地的一堵墙倒了,就把她给埋了
村里好心的大妈说
这孩子命苦,娘死得早
她爹给她找的后妈对她也不好
是她亲娘看着不忍心,就把她给带走了
看来,我也只能这样想了
——《小芸之死》
“人类天性不愿直面将要来临的死亡”,在难以消除的苦难面前,唯有对死后报以天真的幻想,才能慢慢冲淡内心的悲伤和遗憾,担起这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看来,我也只能这样想了”像是一种自我宽慰,但还有比“看见”却无可奈何更悲哀的吗?这或许是人世间的脉脉温情,诗人恰恰就利用了这股力量,给读者对于温情的另一种思考,也许隐藏在死亡背后的是对爱更为长久的延续。
二、生活的简单与复杂
何松喜欢捕捉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却令人压抑的、零碎琐屑却让人沉闷滞重的生存境遇。这类诗用冷静的情绪叙述出跌宕的起承转合,和罗兰·巴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为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
从青春期的写作进入到中年写作,“摆脱孩子气的青春抒情,让诗歌写作进入生活和世界的核心部分,成人的责任社会。”中年的写作更大程度展现出生活境遇的复杂性,无论是理性、责任感都有了更多地深度和广度。
李大爷78岁那年
想去看看儿子
他儿子1979年牺牲
埋在了中越边境的金平烈士陵园
李大爷想起家里还有一笔钱
是三十年前民政送来的抚恤金
那是儿子的命啊
一个信封里装着,从来就没人敢动过
而现在,这钱已不够去看儿子的路费了
最终,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李大爷才得已成行
李大爷扫墓的场景
被一个摄影师拍成了照片
起名《迟来的祭奠》
上了凤凰网的经典历史回顾
李大爷在给儿子扫墓回来的第二年就死了
——《摄影作品<迟来的祭奠>记》
这首诗具有高密度的起承转合,三节16行有4次转折。诗开篇交代78岁的李大爷有一个儿子,第一节第三行是第一个转折:李大爷儿子是个烈士,“埋在了中越边境的金平烈士陵园”。民政送来了抚恤金,“那是儿子的命啊/一个信封里装着,从来就没人敢动过”。儿子的牺牲,是李大爷埋藏在心底的伤痛。第一节第九行第二个转折:三十年后,李大爷想去看儿子,抚恤金不够路费,“最终,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李大爷才得已成行”。第二节第三次转折:李大爷扫墓的场景成为宣传的热点,“上了凤凰网的经典历史回顾”。通过报道人们歌颂英雄,但在英雄背后是一个沉重的家庭,李大爷一家的收入连路费也不够,此刻歌颂崇高性,慷慨激昂又空洞苍白。第三节第四次转折:“李大爷在给儿子扫墓回来的第二年就死了”,李大爷的故事戛然而止,情理之中却意料之外,我们不知道该感动,感慨亦或是遗憾,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情感可以抒发。
马路边的一棵树倒了
在一场暴雨后
它实在站不住
就把自己彻底地给放倒了
其实,它的根早已枯了
它的心都早已空了
只是没有人会注意到地下这黑暗的部分
这棵树被移栽到城里活了八年,倒下
上了都市的晚间新闻
而我二大爷移居到这个城市的第二年
就悄悄地死了
——《一棵倒下的树》
《一棵倒下的树》和《摄影作品<迟来的祭奠>记》有着极为相似的叙述方式,平缓的开始,激烈的转折。诗人关注到因子女工作而从农村移居城市的这一老年群体。他们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年老后却不得不移居到在城市工作的儿女身边。到了城市没有自己熟悉的乡邻,人生地不熟,回不去的农村,融不进城市。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经验都在农村,到了城市所有熟悉的劳动技能都没有用,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人“享清福”,他们感受不到存在感和自身价值,在人潮汹涌的城市更加孤独,就像马路边的那棵树,“它的心都早已空了”。何松质疑“现实”,始终护持着自身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试图承担起一种源自结构的责任与源自伦理的紧迫感。
何松的诗一直弥漫着一种无可去除的迷茫和失落感,总是在一种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无奈中展开。“一张拉羊的手扶拖拉机就停在村口/它们中的三只/明天就将在这羊群中消失”。(《回家的羊群》)“一头活蹦乱跳的猪/从这边进去/八个小时后/就变成一盒盒的罐头/从那头出来了。(《恐惧》)“在这段叙述中/人的生命,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随时可以为什么而亡、而亡、而亡。(《读史笔记》)事物的短暂性、命运的无常性使我们的感受变得紧张且真实。诗人观察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事,他以一颗敏感的心投入尘世,注视着在社会迅猛变化的当下,浮躁的生活环境和心绪不宁的人们。就像里尔克曾在《马尔特手记》里所写文字:“为了写一行诗,必须观察许多城市,观察各种人和物……必须能够回想异土他乡的路途,回想那些不期而遇的相逢和早已预料的告别……”
三、女性的刚与柔
何松的诗有生命的沉重,有人生际遇的艰难,这类诗情感表现得很直接有力,叙事跌宕、语调激烈。但还有一类诗却是舒缓、平稳、宁静的语调,这类诗大多与女性有关,呈现出诗人对女性群体的理解、同情和赞美。
我熟悉玉米
像熟悉心里的女人
玉米们从小就待在山冈上
……
转眼间
玉米们那青葱水灵的身躯
就憔悴不堪
玉米的一生
像山里女人的青春一样短暂
……
这是一个命的过程
但,自始至终
玉米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玉米》
《玉米》一诗关注到大山里女人的命运,诗人把大山里的女人比作“玉米”,这不是一个比喻女人的常见的喻体,和比喻女人常见的喻体“花”相比,玉米有着更实用的价值,更粗放坚韧的生命力。诗人注意到了这些大山深处女人的命运,“转眼间/玉米们那青葱水灵的身躯/就憔悴不堪/玉米的一生/像山里女人的青春样短暂”。没有描写苦难的字词,短暂的青春却道出了生活的忙碌与艰难:下地干活、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玉米们不停地生长/开花、结果/劳累了一生”。人们爱惜花、呵护花,何曾呵护过玉米,更何况,“自始至终/玉米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连玉米自己都不觉得需要被呵护,忘记了自己。我们歌颂奉献与付出,也期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去年夏天
我在一所乡村小学的屋檐下避雨
忽然看到远处灰白的山路上
有一个黑影慢慢地向这边移动
直到三百米处我才能确定这是一个人
他在泥泞中跋涉
这期间,他摔倒了几次又站了起来
直到五十米处
我才看清了这是一个女孩
她其实比我七岁的侄女大不了多少
直到十米处我才看清了她赤着脚
却把一双鞋子挂在脖子上
她低着头,用两只手
紧紧地把书包搂在怀里
隔五米我看见
她坐在教室的门槛上
穿上早已潮湿的胶鞋
我看见,她走进教室的瞬间脸上挂着笑
——《在一所乡村小学所见》
这首诗没有通过叙述严肃沉重的事情,刻意激发出读者的反思意识,而是在贴近生活的情境下,给予人一种主动而自觉的感慨。泥泞的乡村求学之路,小女孩摔倒了又站起来,她甚至是个低年级的小学生,“比我七岁的侄女大不了多少”,但她知道“把一双鞋子挂在脖子上/她低着头,用两只手/紧紧地把书包搂在怀里”, 她是一个出身穷困、踏实又坚强的小孩,搂在怀里的是长大后的梦想。这首诗没有何松诗中常见的迷茫和失落感,小女孩消弭了《玉米》中大山里女人宿命的悲伤,知识是希望。
母亲弯着腰在推着轮椅,推着轮椅上的外婆
隔她半步的身后是我的妹妹
妹妹的一只手若即若离地放在母亲的后背
她的另一只手牵着我一岁多的侄女
她们都没有要说的话
母亲因为要照顾外婆
妹妹因为要照顾母亲和我的侄女
她们安详地走在路上
其实只有母亲和妹妹在走
外婆的腿已丧失了力量
只能坐在轮椅上
而侄女的腿还没长出力气
得牵着才能走
从外婆到侄女只是两米的距离
而这之间像隔了一个世纪的时光
……
——《走过她们生命中各自的幸福时光》
《走过她们生命中各自的幸福时光》一诗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开朗明快的格调。外婆、母亲、妹妹、侄女四代女性,她们是血脉的延续,是母爱的传承。诗句明白如话,没有任何比喻与形容,真挚与赤诚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旁白式的口语融入叙事当中,“外婆的腿已丧失了力量/只能坐在轮椅上/而侄女的腿还没长出力气/得牵着才能走/从外婆到侄女只是两米的距离/而这之间像隔了一个世纪的时光”,生命就是这样,有人新生,有人衰老。母爱就是这样,普通却伟大。
何松的诗不囿于乡村或者城市,他的写作“诗歌精神已经不在那些英雄式的传奇冒险,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争斗之中。诗歌已经达到那篇文章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习惯且善于精妙的个性化叙事,但也拒绝了写就一些其他诗作风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