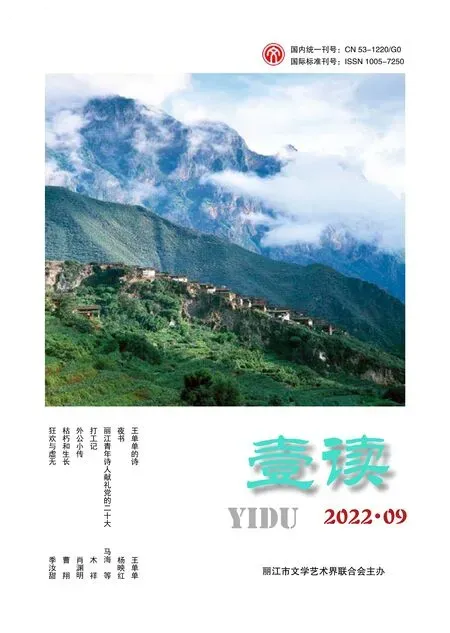一壶青色
◆朱华胜
一
天蓝得像画出来的,对于北方长大的范小白来说,仿佛是奢侈品。老家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像是冲洗照片的暗房。这样的境况,是画家的噩梦。她放好画笔,伸了个懒腰,来到门口,叫停看书的乔蒙山,挽起他,往竹林深处走去。
嗡嗡声传来,几只马蜂掠过。蜂身金黄,像一片碎金越过头顶。在范小白眼里,蜂像南方的巫,是一群神秘而热烈的舞蹈者。蜂的飞行看似凌乱却格外有韵律,像科萨科夫名曲《大黄蜂的飞行》样的,迅急而优雅。她看了一会,正要张口,被乔蒙山捏住鼻子,说,又要说嫁我是因为喜欢竹林和蜂了吧?
范小白身子晃了晃,乔蒙山连忙揽住她,穿过竹林,来到一幢小屋前。小屋两层,竹子搭建。蜂在欢飞,风摇起竹林梢枝细叶,飘动的白云托着悠悠的蓝天……
一个阴郁闷热的中午,在石家庄举办的一个画展上,范小白认识了乔蒙山,被他的一幅《蜂巢》吸引住了。画面上,流畅的线条仿佛在动,每一根都是活的。这是他云南风情系列画中的一幅,她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
范小白问他,这些是真的吗?
哈哈,像我一样真。乔蒙山说着,打量起范小白来。真像她的名字一样,皮肤很白,白得像家乡的云。着一条紫色长裙,手腕、小腿像他院里的竹笋一样细嫩。凉鞋中半隐的小脚,指甲盖是家乡马樱花的颜色。乔蒙山心一动,说,是不是真的,去看看嘛。
范小白没把这话当真,这样的客套话太多。她没料到一个月后一封请柬,把她永远留在了云南。西平市政府打造最美大城市,委托文联邀请国内部分知名画家来采风,她在列。乔蒙山悄悄说,内画在西平市还是空白,如果把这儿的山水通过内画传播出去,不失为一条宣传渠道。
四月下旬这天下午,范小白抵达昆明长水机场。她刚出机舱口,心情豁然开朗。登机时的灰沉沉,此时的亮堂堂,天蓝得像她画夹里的颜料一样。似乎画里的白云全跑来了,一朵一朵,挂在蓝天下,像白色的宣纸,那么低,离她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摘来。
人群中的乔蒙山,瘦瘦高高、轮廓分明,穿一件红色衬衣,正在笑眯眯地向她招手。
乔蒙山打开车门,范小白坐了进去。
你生活在世外桃源啊,难怪你的画有种神韵。范小白又说,哇,好漂亮!那是什么花?范小白指着坡上问。
马樱花,乔蒙山微笑着,将车速慢了下来,降下车窗。
一棵棵树立在坡上,开满了花。花朵紧紧挨着,红的,白的,黄的,像认识范小白一样,朝她笑。范小白说,停车去看看。
我家那儿就有,有你看的。乔蒙山说,车速快了起来。
采风活动期间,乔蒙山与范小白约好,多留一天,去他家看看。
乔蒙山的家在青石板,这是一个城边村,座落在南盘江边,与西平市隔江相望。村子右边是白石江,水绕过村子流入南盘江。白石江、南盘江把青石板围在中间,像双龙抱珠一样。岸边全是竹林,绿油油的顺江蜿蜒,像几条绿绒绒的毯子铺在江边。村子往后,是一片平整的田,远处,是一个小山坡。山坡后面,是连绵不绝的大山。
乔蒙山告诉范小白,村民不种田了,挖成鱼塘,养鱼,有的种花,有的种蔬菜。每到周末,城里人来这儿买鱼买花买菜或去鱼塘垂钓,去地里采花摘菜。
你们这里为什么叫青石板呢!范小白问。
好,小白,你随我来。乔蒙山没有回答,领着范小白,穿过密密的竹林,来到江边。
这就是白石江,很美吧,你看这水,多清啊。范小白一看果然清澈,靠边的水底清晰可见。岸边的石板,泛青,被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滑溜溜的,亮闪闪的。
原来你家青石板是这样叫起来的啊。范小白说着,索性躺在石板上。乔蒙山也躺在她身边,将手里的竹叶放在嘴里,嚼得啧啧响。
范小白望着天空出神,要是这蓝天白云能搬到家乡去该有多好啊。
返回时,乔蒙山说,带你看看我的画室。范小白跟着他,顺着江岸竹林小道,绕了好几个弯,来到一道红砖围墙边。
乔蒙山指着围墙里面说,我家竹林,我爷爷种的。
他们从小门进来,密密麻麻一大片碧绿出现在面前。又高又直的竹子,泛着点点的阳光,就像迸溅的水花。她有些惊讶,凑近仔细看,原来是油光锃亮的竹皮,仿佛在与阳光嬉戏。
哇,那是什么?范小白指着竹林上面惊叫。
拥挤的竹子顶端,密麻的竹节枝丫处,一个团乎乎的东西,像一个大篮球,棕褐色,表面斑斑点点,似乎在移动。
那是蜂窝。乔蒙山说,你听,还有声音呢。
果然,嗡嗡的。抬头望去,一只只黄澄澄的东西在头顶飞。
那是马蜂,蜂窝的主人。乔蒙山说,我曾在一幅画作上写过几句,我朗诵给你听:
蜂是竹林的保护神,是大自然的使者。它们藏身在阳光和词语碰不到的地方,它们通晓自然的一切秘密,能预知未来的世界。它们嗡嗡的声音,常把我带入创作深处,远离凡尘俗世,每每如此,我心特别安宁。
范小白嘴巴张成O型,说,乔蒙山,你是个大诗人。
乔蒙山笑开了,说,小白,我还是做一个本分的小画家吧。你看,到了,前面就是我的画室。
这时,远远传来一个声音,山儿,来喽。
乔蒙山停下脚步,说,那是我母亲在喊我吃饭呢!走吧,咱俩饭后再来看。
乔母频频夹菜给范小白,望着她,笑得嘴都合不拢。
范小白长得很好看,个子高挑,鼻梁高,眼睛大,尤其是皮肤雪白。她也不知道父母为啥给她取名为小白,也许是父母见她长得白吧,女孩嘛,肤色白净当然好;也许父母是希望她一生清清白白。看到乔母望着她的模样,范小白知道,乔母是把她当儿媳妇了,不禁脸红了起来。
后来,范小白不顾父母阻挠嫁给乔蒙山,来到云南。
此时,见丈夫这样问她:抓住他捏着她鼻子的手,笑着对乔蒙山说,阿山,爱上一片竹林,一个蜂巢,一块土地,还不是因为你。
范小白心里还在说,这片土地像乔蒙山一样,低调、善良、淳朴,有一种异样的诱惑力。
范小白拱在乔蒙山怀里。丈夫是云南画家,西平市兼职美协副主席,市文联画院签约画家,很有名气的,可他做人很低调。范小白加入西平市美协后,才知道丈夫在美协的任职。公开场合,他话不多,甚至有些腼腆,与他画画时的自信不一样,但他有结实而温暖的肩膀,有山一样的气质,蜂一样的勤奋。家是家,竹林也是家,范小白不仅仅喜欢在竹林里画内画,更喜欢和丈夫在竹林中私语,像小鸟在它们的窝里呢喃。
范小白记得,洞房花烛夜,乔蒙山紧紧抱着她,落泪了,说:小白,你在我心里就像竹林一样,不会变色。
乔蒙山新婚的誓言还不到两年,就在刚才,一份告知书发到范小白手里。她望着竹林,在马蜂嗡嗡嗡声中,呆住了,脸色极为难看,眉头紧锁,仿佛被马蜂狠狠蛰了。
二
婚后,范小白蜗居在青石板,静静守在竹林,聆听马蜂飞行的速度,躺在嗡嗡的蜂声里,把自己与喧闹的尘世隔绝。第一次参评,内画《蜂的私语》获得南方五省内画鼻烟壶一等奖,随即被通知参加由五省工艺美术学会主办的内画艺术作品联展,反响很大。这可把乔蒙山乐坏了,说,真的,我有些崇拜你了。我画了这么多,可没有你这么一炮打响的作品。
乔蒙山这样说,倒不是吹捧妻子。范小白真个是内画天才,年纪轻轻就成为南方五省十位内画艺术大师中的一员,光靠天赋是不可能的,她的勤奋、坚持,对大自然的洞察以及对生命的领悟更为重要。北京来的评委高度评价,《蜂的私语》意境深远,气韵生动,浑厚质朴,感天动地。那天,她获奖回来,搂住乔蒙山的脖子,叫他猜猜结果。乔蒙山连猜三次没对,当范小白告诉他结果时,他一把将她抱起,穿过竹林,冲进画室,门咯吱一声关了。清风拂过,竹林沙沙,起伏不止。两只马蜂追逐掠过,嗡嗡嗡的声音,忽高忽低。
范小白获奖的消息,在西平市文联炸开了。
各路记者采访,都吃了闭门羹,连乔蒙山都吃惊她的做法,难以理解。范小白在他耳边轻轻说,我是为大自然的生命而画,不是为了虚名。
唯有摄影记者赵林,范小白答应让他采访。
赵林是乔蒙山最好的朋友,文联的同事,《西平日报》摄影记者,西平市摄影协会秘书长。他也是在石家庄那次画展上认识范小白的,他作为记者跟随乔蒙山前去采访。当乔蒙山把范小白介绍给他时,他扶了扶眼镜。天下还有这么白净的女孩!范小白很有礼貌地与他打招呼后,又缠着乔蒙山指着画问这问那。他发觉,这两人看对方时眼神里都有光。就是到今天,范小白看赵林眼里也没有那种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友谊。赵林相信自己看范小白有那种光,但范小白一定看不见。
乔蒙山和范小白陪着他在竹林里散步。赵林挎着相机,拿着手机。他草绿色上衣,上衣和裤子前前后后都是口袋。范小白走在中间,风起时,她洁白的裙摆在舞动。
范小白愿意接受赵林的采访,倒不是因为他是竹林画室的常客,是丈夫的朋友,而是她认为,她的作品获奖,赵林也是有功劳的。她至少是受到赵林拍摄的视频和几幅蜂窝照启发,有的细节,甚至是按照片来画的。乔蒙山多次对她说过,靠近观察,马蜂不会伤人,除非你主动去惹它们。说归说,马蜂再可爱,她还是不敢靠近蜂窝。不像乔蒙山,直接搭个台子,看着蜂窝画,也不敢像赵林那样,凑近仔细瞧,还换着角度拍个不停。
嫁过来那天,乔蒙山就叮嘱过范小白,马蜂有毒刺,像毒箭,人被蜇会有生命危险。乔蒙山还说,马蜂也不愿蜇人,为了自保才蜇,蜇人后它自己也会死的。
范小白哪敢走近蜂窝,只是在竹林外偷偷观看。她觉得竹林里有了蜂窝,就像竹林里有了机场。马蜂如战机,不时起飞和返航。她特别喜欢这些邻居,从不招惹它们。
赵林也爱来竹林拍蜂窝。他照了很多照片,选了一两张后,全部给了范小白。这可乐坏了她,她正愁呢,无法接近蜂窝。她想看得更清晰一些。有了这些照片,她的笔像马蜂一样会飞。
范小白内画水平令赵林吃惊不已。他甚至觉得范小白弯头小笔有些巫,巫得像一只马蜂,嗡嗡到白石江,鱼就跳了起来;嗡嗡到南盘江,江水波涛翻滚,一老汉划船搏击;嗡嗡到青石板,人笑声朗朗,鸟鸣声翠翠,袅袅炊烟的农家院子飘出了香味;嗡嗡到竹林,一男一女相拥着喃喃细语……赵林问她,这男的是?
范小白望了一眼静静走在身边的乔蒙山,对赵林笑道,不是你。
赵林故意作晕倒状。
范小白咯咯咯笑道,挽着乔蒙山朝前走,说,阿山,我们走,让赵林倒。谁教他不去找一个人扶。乔蒙山大笑,说,早该如此。
乔蒙山与赵林都是省艺术学院毕业的,只不过是两人同届不同系,学的专业也不同。乔蒙山学画,赵林学摄影美工。两人都是从西平一中考来的,平时相处得多,自然就成了好朋友。赵林话多,乔蒙山话少,是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他们常结伴而行,乔蒙山静静坐着画画写生,赵林到处跑着摄影拍照。
乔蒙山说,赵林,你别到处乱跑了,静静看点书。
赵林笑他,再看成了书呆子,好不容易大学熬出来,我看见书就打瞌睡,拍出来的照片是空的,啥也没有。
歪道理!乔蒙山不再说他。五年后,乔蒙山硕士研究生毕业,赵林还在跑,说,蒙山,五年来,画画你没耽搁,还捞了一张文凭。我呢,与毕业时没两样。
乔蒙山结婚,范小白加了进来。赵林每次来,看到的画面总是一样的。乔蒙山在室外搭的画台上作画,范小白在室内灯光下静静画壶。
赵林笑道,真是两尊佛,绝配了。范小白来后,画室添加了一张画桌,只是,画桌旁,比乔蒙山的多了一样东西,柜子,摆放了很多瓶子、玻璃球、水晶球、鼻烟壶什么的。
看到自己占的地盘比乔蒙山多,范小白笑着说,阿山,画室还是你的,我不会夺人所爱。
小白,画室是你的,你是我的,归根结底都是我的,还担心啥呢?乔蒙山打趣道。
范小白扑过来,揪住乔蒙山的耳朵,说,阿山,看把你美的。接着又说,阿山,可不可以给画室取个名字,叫……?
叫啥?乔蒙山拿开范小白捏住耳朵的手,吻了她,轻轻问。蜂窝。范小白说。
哈哈哈,好,真的好名字。那你就是蜂后,我是你的雄蜂。
阿山,你找打。范小白羞得追着乔蒙山,在竹林里钻来钻去。嗡嗡嗡,几只马蜂被惊扰,在他们头顶飞着……
看着这对夫妻打趣调情,不避讳他,赵林乐得在旁偷拍,然心里竟有一丝丝酸意。他欣赏范小白的内画才华,也喜欢她这个人。后来,当他发觉自己对范小白的感情有了变化时,非常惊讶和不安。范小白是好朋友乔蒙山的妻子,这是现实。有了这念头,他的心是复杂的。于是,他刻意隐藏这种情感,一边是他最好的朋友,一边是他暗恋的女人。然而,他还是身不由己。他总是来他们夫妻俩的画室品茶、闲聊,或者看他们作画。他拍了很多独特的照片,让范小白画。当范小白感激地看着他时,他却害怕和范小白的目光相接。
范小白不知赵林这些心思,她沉浸在青石板的美色中,沉迷在竹林里飞来飞去的嗡嗡声中,沉醉在与乔蒙山的恩爱中。她始终把赵林当作朋友,更重要的是当作丈夫的朋友对待。她对赵林自然没有赵林对她的那些念头。
三人就这样边走边说。太阳偏西,红红的霞光给竹林铺上一层金纱,蜂窝也变得通红,像一个红灯笼挂在那儿。马蜂也是浑身通红,像一个个红精灵,在夕阳里飞舞。范小白说,可以了,赵林,你今天问得够多了。
赵林看了一眼乔蒙山,说,小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介绍一下内画,我的文章登载后,要附一个内画常识介绍,我们这里的人不知道这玩意。
一直默默走着的乔蒙山,停下,说,我说赵林,看你这问题问得,网络时代,可以问度娘啊。
赵林,这?
范小白笑笑,说,这样吧,你看我画,你自己写去。
乔蒙山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进了画室,乔蒙山说,干脆我去鱼塘捞两条鱼,今晚就在这里,做一顿酸菜鱼,与赵林喝一杯,如何?
范小白说,喝酒,那是你们男人的事。
赵林哈哈笑道,蒙山,早就该这样了。
范小白拉亮桌上的台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水晶鼻烟壶,捏紧,将弯头小笔从壶口轻轻伸进里面去画。
赵林静静坐着,盯住这画笔。嘿,奇了,笔身长,细如牙签,笔毛和笔身的角度像一把镰刀,伸进窄窄的壶口,在内壁上作画。
范小白说,你看,壶的内壁是打磨过的,不然画不上去。再仔细看,仔细看,奥妙在这里。赵林盯住细细瞧,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是反着画。赵林暗暗感叹,隔行如隔山啊,原以为自己对画的鉴赏多少还是懂点的。他听乔蒙山谈过,评委点评过范小白的内画,说线描变化多姿,富有生气,色彩搭配精致。她喜欢用清淡而洒脱的笔墨描绘背景,以达到和主图强烈反衬。她的画有形有神,有气有韵,格调温暖。可见范小白内心极为阳光。
赵林看着范小白专注的神情,有一种无法描绘的美,令他窒息。他想起上一次在南盘江游泳时,范小白完美的身材,雪白的肌肤晃花了他的眼。趁乔蒙山游远了,他对范小白说,小白,你真美,给你拍一组裸体写真照,一定能引起轰动的。
范小白愣了一下,看了一眼四周,沉下脸来说,就算我敢,你敢吗?说完丢下赵林,向乔蒙山游去。
赵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再没提这个话题,不过,他来得更勤了。范小白说,你们报社上班不用坐班,挺舒服啊。赵林笑笑,成天待在房间里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是没有生命的。这期间,他偷拍了范小白很多照片,冲洗出来,在家里一次次欣赏,几乎成了瘾。游泳当天晚上,梦里,一只透明的蜂飞过来,和他缠绵,但突然又狠狠蜇了他一下。那蜂的背影,像乔蒙山。
赵林不敢再想,正了正神,继续观看范小白作画。
范小白额头上闪出粒粒汗珠,通亮通亮的,竟有种诱人的香味。赵林一震,取过桌子上的纸巾,轻轻给她擦拭。正擦着,乔蒙山走进来,说,两条,捞起两条鲤鱼。乔蒙山看了一眼赵林手里的纸巾,继续说,今晚好好喝一杯。说完往厨房走去。随即,鲤鱼在地板上干跳的声音传来,似乎很痛苦。
蒙山,你做的酸菜鱼很好吃,赵林吃着,夸着。乔蒙山不断敬他,连声说,喝,喝!废话不说!
范小白没有想到乔蒙山喝醉了,她从未见他醉过。她守了他一夜,发誓以后不能让他再这样喝了。
当赵林打电话来问时,已是第二天中午。范小白说,醒过来了,看样子不舒服,躺在竹椅上发呆呢。
乔蒙山的酒量,范小白不知道,他赵林还会不知道,乔蒙山可是公斤级别的,在文联被称作酒司令。显然,乔蒙山是故意醉的。赵林懂了,乔蒙山表面上不在意他和范小白闲聊,其实不然。
赵林想起上一个月那次喝酒。乔蒙山喝了足足一瓶,对有些晕乎的赵林说,我的画,我尽力了,顺其自然,有小白陪我,今生足矣。赵林,你不要老往我们这儿跑,该去找一个照顾你的人了。当时,赵林只是想到乔蒙山是关心他的个人问题。
赵林觉察出乔蒙山的醋意和不满。想了想自己的言行,竟冒出一身冷汗,赵林晃了一下,把手里的一摞照片放在最底下的抽屉里。他背起摄影器材,朝西平市北边走去,那儿有一块西平市最大的湿地,旁边有一片树林。他记得,树林里有蜂窝。范小白来西平市之前,他常去拍摄那些在自然里舞蹈的精灵,尤其喜拍蜂、蝶、鸟、山鼠。
三
入秋,白白的云更低,像要落在竹林上样的。蓝蓝的天更蓝,蓝得让范小白不敢画。要是赵林在,拍下来,多好。范小白问乔蒙山,阿山,赵林哪儿去了,好久没来。
乔蒙山在画室里回答,也许他忙吧。等我画完这幅《大黄蜂的飞行》,我打个电话问问。
范小白发现竹林里的蜂这几天格外不安分,是遇到什么敌人了吗?它们总是围着蜂巢转圈,嗡嗡嗡叫个不停,黑压压一片一片的,一副守卫的架势。
阿山,范小白大叫着,慌跑进画室,把乔蒙山拽出来看。
乔蒙山紧紧搂住范小白,生怕她被群峰攻击。马蜂是敏感的动物,它们脆弱、敏感,能抱团自卫。也许它们感觉到什么危险了吧,只是我们不得而知。乔蒙山说,蜂群烦躁,让它们冷静冷静。小白,我们到外面写生去吧。
好,阿山,走。范小白立马应和。
乔蒙山替妻子背上画箱,范小白替丈夫背上画夹。两人手拉着手,顺着幽幽曲曲的竹林小道,穿过大大小小的鱼塘,走过长长短短的小木桥,越过紫紫绿绿的花地,经过一条长满牵牛花的弯弯土路,爬上一个小山坡。小山坡到处是伏地松,还有几棵马樱花树,埂子上摇摇晃晃的是茴香花。
青石板一览无余。阿山,这儿真的很美。范小白舞着手,跺着脚,啧啧赞道。
人间四月天来,更美,到处是花,尤其是这几棵马樱花,开得热烈,开得不安分。
乔蒙山接着说,其实,青石板村,一年四季都是美的。你看村子,一片片瓦房,错落有致,掩映在果树竹林中。
长着红红果实那些,是石榴吧?
对啊。
范小白指着村子最前面那栋围着红砖围墙的瓦房说,阿山,那儿是我们家。
乔蒙山说,对,竹林里,就是我们的蜂窝。只是今天,蜂王在这里会雄蜂。
等范小白反应过来,乔蒙山早跑远了。阿山,我不打你了,回来吧。
真的?乔蒙山转回来刚坐下,耳朵被范小白揪住了。
两人嬉闹了一阵,各自拿出作画工具。范小白知道,这一切,竹林,鱼塘,花地,山坡,土路,木桥,蜂窝……这些目之所及能看到的景物,在乔蒙山眼里,都是宝贝。这些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富,要爱护,要珍惜,乔蒙山多次这样说过。
我要给我画的竹林小道取个名字——白山路。范小白说。
哈哈,我给画取个名字——大黄蜂的飞行。乔蒙山说。
我要给这个小山坡取名为阿山。
哈哈哈,乔蒙山反应过来,连忙说,我要给这一对马蜂取个名字,胖嘟嘟的这个蜂王取名为小白,瘦精精这个取名为……
阿山,你敢!
当晚,范小白做梦了。梦里,乔蒙山抱住她说,我们给村庄的很多事物命名,还画下来,我们爱这块神奇的土地,爱这绿水青山,因为这是我们的精神图腾。
范小白没有梦到的是,一觉醒来,世界就变了样。
四
社区工作人员把一份告知发给范小白,她懵了,粉脸像泼上了一层灰白色染料一样寡白。她想起蜂群昨天的状况,真是精灵啊,真的有预感。她有些站不稳,忙靠在画室板壁上。蜂群围着蜂窝不远不近嗡嗡嗡飞着。它们对来自大自然的灾难有所察觉,对来自于人类的攻击也能提前知晓。范小白一时不知是难过还是羞愧,低下了头。当她再次仰起头时,已是泪水滚流。
范小白这一天在不安中度过,桌上的鼻烟壶一笔没画上。这批画,她取名为《一壶青色》,有山有水有竹林,有村有人有蜂。她答应北方老家办画展的朋友,本月底快递过去。前些日子就与乔蒙山说过。
阿山,你快回来呀?范小白快要哭了。
乔蒙山一大早就陪父母去西平市医院体检。他每年都要陪父母体检一次。晚饭时候才到家,便急匆匆往画室赶。要是平时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在家帮母亲做好饭菜,再过来喊范小白吃饭。可今天,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清楚。他先是担心父母会不会体检出哪样毛病,听父亲说肠胃有时不舒服,还特地加了一项胃镜检查。当医生告诉他两个老人除了血压有些略高外,其他一切都正常时,他才驾车载着父母返回。
阿山,你来了!范小白两眼通红,把桌上的告知书递给乔蒙山。
青石板村不安宁了。乔蒙山、范小白觉得天要塌了。青石板拆迁,就把他们的创作艺术之根给拆掉了。他们的艺术是建立在这条根上的,没有根的艺术,是不会长久的。
祖祖辈辈生活在青石板的村民不答应,一次又一次上访。
一场突然降临的大雨,让青石板村暂时安静下来,马蜂也窝在巢里,惟有风和雨滴打在竹林上发出的声音。范小白觉得这回的风声像在嚎叫,雨声像在哭泣。
西平市文联领导来了,说要看看乔蒙山夫妇的画室。绕了一圈,来到鱼塘。钓鱼的时候,文联领导说,蒙山,凡事要想开些,不要执拗。有人见你几次都在上访人员中,你还是我们文联的人嘛,注意影响。你可是市美协副主席,还有,你们两口子都是美院签约画家,难道这些你们都不要了?
乔蒙山双手背在身后,拳头捏得死死的。
这是范小白嫁过来后第一次失眠。她与乔蒙山就这样在床上躺着,你瞪我我瞪你,神色凝重。两人心是相通的,不就是一个美协副主席吗?不就是一个签约画家吗?没有了也要坚守住这一片美丽的土地,守住给他们艺术带来灵感的山水,竹林和蜂窝。
范小白说,撵走我也不搬。乔蒙山说,撤职我也不答应。
范小白泪眼簌簌,建那么多豪华宾馆、会所干什么?留一片美丽家园不好吗?
乔蒙山说,我不是美协副主席了,你还要我吗?
范小白真的翻白眼了。我嫁的是你,不是什么美协副主席。
乔蒙山道,可我不是美院签约画家了。
范小白道,看你气傻了的,难道不在那个画院就不画画了么?
第二天早上,好久没来的赵林突然现身在画室前。我是悄悄过来找你们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们不配合,还有更大的压力在后面。范小白听了,一句话不说,转身进了画室,再没出来。
乔蒙山送走赵林,返回画室。范小白脸色寡白,仰面躺在地上。
小白,你怎么了?乔蒙山踩着油门,往城里医院驶去。
范小白怀孕了。
不抽烟的乔蒙山,抽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乔蒙山红着眼,陪着父母去了村委会,签了拆迁协议。
拆迁前,赵林来看乔蒙山夫妇。太阳像醉了的老人,青山如壶,碧水如酒。赵林陪着乔蒙山坐在山坡上,吹着从竹林里透过来的温郁的风,嗑着瓜子,喝着酒。这样的生活以后恐怕再也享受不到了,留恋一会儿是一会儿吧。范小白在一旁静静作画,这山,这水,这竹林,这房子,她都要留到画板上,等孩子出世了,她要让孩子看看这一壶山色,他们曾经有一个多么美的家。
赵林明白,乔蒙山愿意签下这份协议,全是为了范小白肚里的孩子。这时候抗争是不理智的。乔蒙山说,眼前的青石板,就要成为一片废墟。一景一物,还有那些味道都要消失。我们的家乡就要消失,永远消失。
那个新建的家,没有家乡的味道,只是一个仿制品,不是原汁原味的,没有亲切感。你想,赵林,咱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总有一种气息在,就算在一块石头里也能闻得到。是不是?离开就断了,就像堵了源头的水,终将在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里干涸。我和小白本想死了以后能葬在这块地方,每天听着一群蜂在我们坟头飞舞。现在,一切都不会实现了……
蒙山,你醉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赵林瞥一眼凝神作画的范小白,垂下的发帘几乎碰着睫毛了。小笔头一点,颜色四散开来,仿佛美女脸上泛起的红晕。范小白是一个有条理的人,画墨,水,搁笔架,弯头小笔,涂擦笔,有些像医用洗耳球的一个气葫芦,还有几块药棉,依次摆放,整整齐齐。敞开的箱子里,鼻烟壶和水晶球被夕阳照得反射出些许神秘的红光。
乔蒙山正抬头往上看,听了赵林的话,转头望了一眼范小白,说,这就是她的意思。新房子就给老人住吧,我和范小白等孩子生下来,再找个山美水美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有竹林、有蜂窝的地方。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推土机挖机就在村里轰轰作响了,尘灰像火山的烟从四面八方腾起来。房子、院墙脆弱得像骨瘦如柴的老人,一碰就散架了。由于所有的住户都搬空了,拆迁起来格外快,人卖力气,机器也卯足了劲儿。
蜂失去了往日的悠闲,失了魂,鬼使神差地倾巢而出,钻进了烟尘里,很快几个人就被蜇了。然而并没有持续多久,消防队很快赶来,喷起杀虫剂。他们发现了那个藏在竹林里的巨大的蜂巢。蜂再有预感,也绝不会想到,它们建筑的小家有一天会登上《西平晚报》,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后来,乔蒙山、范小白的孩子出生了。
他们搬到了另外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小路,弯弯的,虽然崎岖不平,但清晨的阳光把衣裳穿在它身上时,也颇为鲜艳。乔蒙山挽着范小白,抱着孩子,缓缓走在绿荫荫的竹林小道上。
乔蒙山、范小白太贪恋美景了,左看右看,又仰头望着天空和太阳,丝毫没有注意到,一只小小的蜂,落到了孩子的衣服上。它蠕动的样子,就像他们孩子满月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