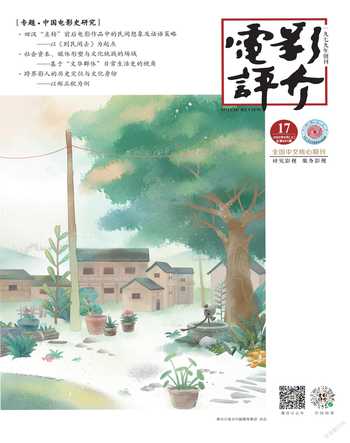《红高粱》: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影像实验

魔幻现实主义源自20世纪欧洲的一种绘画方式,这种绘画方式利用现实主义的精确性来描绘物体,但却悖论般地表现出一种由于对时空因素进行迥然不同的并置所致的奇异效果。[1]早在1925年,德国文学家弗朗茨·罗就在其著作中首次对魔幻现实主义展开了系统的表述与分析①,自此之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便被文学家广泛应用在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发轫于南美洲,与当地的传统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欧洲殖民者给南美洲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当地存在大量的原始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生活状态融为一体,形成了南美洲独一无二的“魔幻”与“现实”叠加态势。因而,几乎所有现存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皆带有传说性与原始观念下的神秘、怪奇色彩,充斥着祭祀、巫蛊、鬼怪甚至超自然现象等元素。
文艺复兴后,西方文化的渗透对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便被南美民众熟知,其写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及讽刺的手法一直深深影响着南美洲文学的发展,在不经意间促进了世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如春笋般在欧洲大陆萌生,旅欧的南美作家们开始自发地接受其文化思想熏陶,并意识到他们的写作应结合欧洲其他现代主义流派,以便更好地展现南美洲人民的生活。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寻根文学”作家,他们在审视民族历史的同时,渴望推陈出新,用现代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学传统。莫言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两部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影片秉持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以“景人合一”的叙事美学塑造出独特的情感绽放空间。
一、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的侧重点是现实,而非魔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可他本人却拒绝这个称号,他认为:“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是拉美现实。”②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用“狭窄荒唐”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一个个荒谬、超乎想象甚至是魔幻的故事就仿佛一把把钥匙,让读者打开现实的锁,对现实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复杂的乡愁情感,被誉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寻根文学”作家之一。[2]正如英国诗人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国南部的美丽田园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书中的南美小镇马克多一样,莫言将家乡的生活写实地刻画了出来,并把传统文学中的“乡土”描写转化成对人性的呈现和人生的领悟。这使得其作品摆脱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局限与狭隘气息,达到了挖掘“人性”的高度。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中,无论是描绘人物的对话、独白、心理,还是书写缥缈的时空与幻境,都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和欧洲戏剧文化里的荒诞与夸张。莫言表示其个人最喜欢两位西方文学家,即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①莫言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擅于进行时空的颠倒与快速的场景转换,这明显具有福克纳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与风格。另外,其作品中神话传说的引用及旁白角度叙事的写作手法则明显带有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红高粱》是莫言最有影响力的一部经典作品,一经发布便引起巨大轰动,而由张艺谋执导、莫言参与编剧的电影《红高粱》也于1987年上映,并取得巨大成功。如今再次回顾经典,不难发现,该片全片都充斥着“莫言式”的魔幻现实主义。
二、电影《红高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道:“《红高粱》是我最用心的作品之一,绝对算得上是一部神奇的电影。”②整部电影以神秘的色彩用力地表达着生命与人性,通过找回人与自然的连接,塑造出充满魔幻的影视空间。对生命的赞美是电影的主旨之一,电影《红高粱》享誉国际,其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寻根,更是一首充满了魔幻色彩的现实主义的生命赞美诗。该片与大多数反映农民问题的“乡土”类电影不同,它的叙事角度不仅是对土地的赞美与歌颂,更是对人性与生命的致敬。故事的非凡特质决定了叙事的特异性,在电影《红高粱》中,连当时社会的最基本场景——村落,都被淡化了。导演张艺谋在小说原有的基础之上塑造出了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框架,使电影的思想自然流淌在故事的曲折情节与人物形象之中,并尽可能地对原著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进行了还原,让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世界”以光鲜夺目的光影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色彩的过渡渲染
色彩是渲染意境、表達角色身份与勾勒人物个性的重要素材。电影《红高粱》以红色为主色调,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色彩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代表某种象征,承担特定的含义。”[3]莫言擅于在创作中使用色彩,从其早期作品的标题中可略窥一二:《白狗的秋千架》《金色孩童》《红高粱》《白棉花》《红萝卜》等;鲜艳色彩的大胆应用是莫言小说主要的特点之一。无论是表现大自然的活力与生机,还是描写人物外貌、刻画人物心理,色彩在他的笔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在五颜六色中,莫言为中华传统喜庆色彩“红”赋予了独到内涵。红色能够表达多重含义,如冒险、强烈的感觉、爱情等,同时,红色也意味着活跃的生命力,被用来表达有形的欲望、目标与冲动。电影《红高粱》全片便被那夺目的红色所浸染。影片开篇,年轻美貌的“我奶奶”红润有光泽的脸颊出现在镜头里,随后是填满了整个屏幕的红色头巾以及那座鲜红色大花轿。相较于导演张艺谋的另外两部作品《英雄》中的色彩对比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色彩冲击,《红高粱》的色彩是单一的:随处可见的红高粱,奶奶的红嫁衣、红轿子,以及伙计们腰上的红腰带、手里通红的高粱酒,影片结束时那血红色的世界;影片几乎找不到第二种色调,红色占据了观众的全部视野,整部电影仿佛炙烈又火热的红色诗篇。这种红色看似张扬,却恰如其分地衬托了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及主人公的心境。整体上看,电影《红高粱》采用漂移的空镜头,构建出色彩浓烈、豪放的叙事风格,将乡土中国、魔幻情景与现实主义美学有机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空间。
(二)“画外音”在电影中的使用
“画外音”是一种叙事视角,即以简短、有力的叙事旁白来讲述影片的主要情节、主旨思想,能够实现电影叙事内容的另类表达。电影《红高粱》采用“画外音”手法,用流畅的叙述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呈现;该片故事中的大部分叙事线皆是通过画外音补充完成的。在电影开篇,屏幕一片漆黑的时候,音响里回荡着一个“我”的自述:“我会告诉你我的祖父和我的祖母的故事,它从来没有被人提过。”这里的“我”仅仅是故事的叙述者,并没有出现在故事中。按理说“我”只是一个客观的讲述者,但“我”同时又是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后裔,这便使“我”对故事有了一定的参与感,让“我”本身也具有了被叙事意义,电影的魔幻现实感便由此产生。影片中一共有12个画外音场景——诸如,奶奶与李大头等人的关系陈述、高粱地里的“幽灵”和“鬼怪”,再到麻风掌柜李大头被杀、奶奶被秃头抢走,以及罗汉叔叔的离去、日本军队的首次出现等,这些人物和电影中的时间转换等情节转折点皆是由画外音叙述的。此外,画外音还带有一种“预叙事”功能。例如,当奶奶的大红花轿被抬起时,画外音便提前告知观众一个轿夫将会成为“我爷爷”,这便勾起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使得电影叙事变得更有张力与激情。片中,敬拜酒神和日全食的场景虚虚实实,将莫言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呈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导演张艺谋在开场陈述中便澄清了电影故事的虚构性:“时代已经过去,有些人相信,而有些人不相信。”①这使得现实的故事融入非现实的时空变得相对容易,而正是这种时空的交错与编织大大增添了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既让观众感受故事的年代感,又在叙事口吻上以当下的人物身份进行表述,令人仿佛身陷迷雾之中,响亮透彻又缥缈迷离。
(三)独特视听效果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达
魔幻现实主义往往采用荒诞的人物、故事情节,将超自然现象与现实叙事相融合。电影《红高粱》对原著进行了高度还原,将乡土元素、历史气息与魔幻元素融合,从现实社会中提取美学素材。莫言的作品对空间的构建与表达是相当精彩和到位的。导演张艺谋在该片的拍摄与制作过程中较大程度地还原了小说中的场景。电影《红高粱》的空间造型与环境描绘都带给人单一、广阔的感觉,协调的构图对比和色彩过渡都没有出现在银幕里,导演创造了一个神秘未知的生活空间。电影里有两个主要的空间环境:村外的高粱地与传承了百年的酿酒作坊。当地人古老的生存意识和生活状态,都在那风雨侵蚀下巨大的、如同城堡一般的圆形拱门山中显现出来了;那片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的“神圣的”高粱地,仿佛在向所有人诉说着它那顽强生命力。当整个电影屏幕都覆盖着耀眼的黑红色高粱时,那是生命坚毅不屈的符号,令人震撼。电影中几次高粱地的特写镜头是导演在向观众展示人性与自然的协调与统一。片中,当“我奶奶”满含泪水,躺在“我爷爷”踩倒的高粱竿上时,屏幕中的高粱随风飘摇,宛如一片红色海洋,仿佛高粱地就是生命的见证人。而在日本宪兵为了修公路迫使乡亲踩踏高粱的场景中,观者又深切地感受到生命被摧毁时心灵上的震击。电影结束时,“我爷爷”和“我父亲”雕像般地站在红色的阳光下,观众眼前那快速闪动着的红色镜头礼赞了温暖而悲壮的生命。[4]
电影《红高粱》淡化了叙事内容的“非现实性”色彩,呈现了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电影中,陕北的民歌、歌谣贯穿全片,是不可缺少的情节推进器。当伙计们第一次在奶奶面前酿酒时,唱起了《酒神曲》,曲调高昂,充满激情,张扬又醇烈。而片中第二次响起这支曲子则是在罗汉大哥的葬礼上,此时的曲调凄哀悲凉,同时又透出一种反抗、执着的意味。片中,爷爷两次唱到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第一次是在与奶奶在高粱地,带有喜悦和一种肆无忌惮;第二次是在奶奶被打死后,爷爷面无表情的歌唱仿佛是情到深处的肝肠寸断——这种情绪上的对比带来了电影叙事氛围的几度反转。张艺谋的作品是写实的,而电影的魔幻性又隐藏在那一片片黑红的高粱地与贯穿全片的歌声中,在不经意间飘进了观众的脑海里,紧扣观者的内心。
结语
电影《红高粱》情节曲折跌宕,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的节奏,生动、浓烈的光影线条让影片的视觉语言写实而又充满魔幻色彩。该片斩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音乐片、最佳录音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各类电影奖项,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片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应用开创了我国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①参见:李晓科.早期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发端[EB/OL].中国社會科学网,(2020-07-15)http://www.cssn.cn/skjj/skjj_jjgl/skjj_xmcg/202007/t20200715_5155884.shtml.
②参见:丛治辰.世界两侧:想象与真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5.
①参见:莫言推荐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和他挥之不去的《百年孤独》[EB/OL].(2021-04-22)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422/14/49165069_973585875.shtml.
②参见:张宇.张艺谋对话莫言《红高粱》像初恋[EB/OL].(2014-05-19)http://cq.cqnews.net/wtxw/2014-05/19/content_30793976.htm.
①参见:张宇.张艺谋对话莫言《红高粱》像初恋[EB/OL].(2014-05-19)http://cq.cqnews.net/wtxw/2014-05/19/content_30793976.htm.
【作者简介】 薛玉秀,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女性文学、女性电影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艾米莉·狄金森的悖论诗学研究”(编号:18WWB001)成果。
参考文献:
[1]袁春兰.莫言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J ].文化学刊,2018(11):43-45.
[2]李圣杰.莫言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J ].华中学术,2018(03):107-114.
[3]庹银泽.《白鹿原》:现实制约下的魔幻[ J ].文学教育(上),2018(09):30-31.
[4]方守永.《红高粱家族》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融创研究[C]//人文学术·创新与实践.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20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