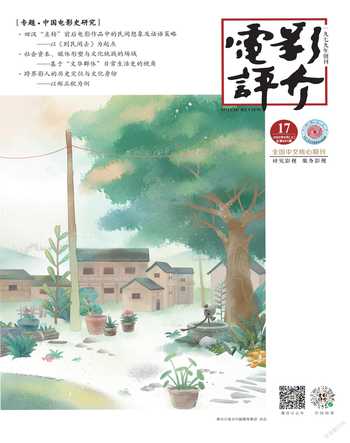形象·凝视·真实:电影的肖像学与形态学研究
作为一门视觉艺术,电影在构图、色彩、光线、样式、线条等方面都保留了肖像画的组成要素,人物、道具与场景的形象展示几乎构成了电影表象的全部内容。然而,电影实际上并不提供绘画意义上的“肖像”——一切“肖像”的面容都是活动的,并被每秒24帧(乃至更多)的机械装置记录,在特定的黑暗环境中再次播放出来。从肖像学与图形学的角度理解这一矛盾,对电影的视觉形式与视觉形态进行研究,是所有流派种类与风格电影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电影肖像的形成与流变
肖像学(Iconography)是一门关于肖像的新兴学科,也作为一种对电影视觉主题和风格进行归类和解释的方法,成为电影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1]电影中对一切人物、动物乃至物品肖像的展示不是随意的、对某类造型人物有意识的复现也是具有叙事目的,如以肖像形成一种气氛,推动情节发展,或打造导演的风格等。小到单帧画面中的特定影像,如人物的发型、着装、造型,大到整部影片的场面调度、类型与风格特征,基于各种目的对电影中的各类肖像进行研究,便是电影肖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常用的人物肖像、物品肖像等范畴中可以看出,肖像不是只表达人、事、物的存在,也不是只表达事物的外形,而是表达事物本身的、事物的现象与事物的本质的统一,是一种作为人类认知结果出现的形态。在这一逻辑下电影中出现的“任何具体存在的事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体,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同样也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统一”[2]。故而电影中的肖像是一种认识的重要形式,它既是人类认识的起点,又是人类认识的对象与终点,是具体的、无限丰富的范畴。
某一阶段的图像携带着其被记录的信息指向某一特定电影类型。以帮派电影中的肖像学为例,《疤面人》(霍华德·霍克斯、理查德·罗森,1932),《美国往事》(赛尔乔·莱昂内,1984),《好家伙》(马丁·斯科塞斯,1990),《洛城机密》(柯蒂斯·汉森,1997),《爱尔兰人》(马丁·斯科塞斯,2019)等经典帮派电影中成为类型电影里最具识别度与丰富性的电影肖像,从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帮派电影开始至今长盛不衰。美国西进运动时注重家族传统的意大利人与骠勇率直的爱尔兰人各自拉帮结派,形成了美国黑帮的雏形;而1920年的“禁酒令”则加剧了酒精与武器在地下黑市的泛滥,黑帮的传奇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巷战枪声与都市暴力一起发展壮大,直到1970年美国《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的出台才逐渐走向衰落。长达半个世纪的黑帮历史为帮派电影提供了丰富的肖像素材,衬衫颜色花里胡哨的打手、白衬衫笔挺一丝不苟的高级成员、香烟缭绕的夜总会、粗大的传统雪茄烟都成为帮派电影最具识别度的肖像符码;而在城市的黑夜里极速行驶的跑车、长风衣下掩藏的自动步枪则成为电影中匪帮成员的“行业用具”。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匪徒片中,匪帮成员往往穿着花哨,暗示着对秩序的挑战与花天酒地的生活;与匪帮对立的侦探着装则暗淡沉稳,暗示禁欲的生活与对秩序的崇尚。电影中的匪帮成员他们生活在都市的小角落中,住处大多昏暗狭小,白天睡觉并躲避侦探追捕,夜间作案或花天酒地,他们凭借内心激涌的冲动进行犯罪,但由于性格缺陷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例如《私枭血》(拉乌尔·沃尔什,1939)中的主角,便是在贫困的生活中沦为走私犯的一战老兵。摄影棚与夜景镜头中明亮的单侧照明映亮了主人公乔治的面庞,体现出角色性格的两面性与命运的悲剧性。乔治也是早期帮派电影里常见的冲动、暴力、仗义与记仇的肖像。
同时,电影肖像的符码也在随时代不断发生着变化,且隐含着超出视觉形象的权力关系。在更晚近的匪徒片中,这一传统的黑帮肖像受到诸多传奇黑帮人物的影响,出现了《教父》系列(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972—1990)中的两代教父、《疤面煞星》(布莱恩·德·帕尔玛,1983)中的古巴毒枭托尼、《情枭的黎明》(布莱恩·德·帕尔玛,1993)中的意大利黑手党卡利多等更加多元的形象。他们往往如同美国重要政坛人物一样居住在豪华别墅中,过着富豪的生活,甚至由于保护平民在普通人眼中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成为美国文化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基本不亲自参与作案,作案时间也不分昼夜。例如《教父》开场时,维托·柯里昂在女儿的婚礼前依然忙碌于工作,穿着笔挺西装、胸口别着红玫瑰坐在办公桌后接受他人朝拜,暖调顶灯在黑暗中照亮了威严稳重的面庞,成为美国电影中最著名的肖像之一,许多电影都有向这一幕致敬的镜头。由于观众的期待不断发生变化,匪帮片中的匪徒肖像也伴随着观众的心理预期不断“进化”,并影响着图像主题的表现:《盗火线》中重案组探长文森特·汉纳急躁暴力,家庭生活危机重重;而匪徒尼尔·麦考利则做事精巧利落,对待女性温和有礼,经常露出迷人的微笑——警察与匪帮肖像符码的对换也象征着两人性格的对换与两人关系的对立;在表现都市黑人暴力神话的《纽约黑街》(马里奥·范·皮布尔斯,1991)和《街区男孩》(约翰·辛格尔顿,1991)中,以黑人为主角的黑人匪徒片较为流行。
电影肖像学的研究带有历史的印痕。“一幅图是一个非常独特和自相矛盾的生物,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特殊的个别事物,又是包含一个总体的象征形式。理解这个画面就等于理解一个环境的综合全面景观,然而又是对一个特殊时刻的快照——当相机快瞄准一个画面拍照的时刻,无论那是一个庸俗的老套,一个系统,还是一个诗意的世界(或者三者都是)。”[3]肖像不仅是个别艺术形象或艺术作品的形式,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在特定创作样式的互相关系中的结构形式。电影肖像形成的并不是个别具体存在的艺术形象的形成,而是要整个电影美学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文化对艺术创作活动影响的规律,它关系着完整电影表意系统的形成。
二、凝视中的角色认同与视角转变
在关于“观看”或“凝视”的精神分析学兴起之后,许多理论家相继开始运用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来诠释电影肖像学,以及电影内部的文本关系、影像风格及社会和性别关系的转变。在拉康的镜像分析学说中,人类从差异的镜像阶段开始掌握进入象征界的语言,此时婴儿将对母亲的认同转移到对父亲的认同上,他看到了自己与母亲相分离的身份,并在想象界中开始认同父权的法则,将母亲看成是女人——一个女性的他者,并从对母亲的“观看”中获得最初的快感与父权秩序中的主体性。[4]在20世纪70年代更新的第二电影符号学中,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利用银幕与镜子的相似来类比观影者位置和观影过程中的“观看”或“凝视”,这一过程再次操演了精神分析中的镜像阶段,观影者“看”电影的过程成为是“看”向母亲眼光的再次投射,这也意味着看电影的过程也是观影者以电影进行自我关照的过程。通过观看行为,观影者以对“镜中人”即电影角色的认同再次完成了自我建构的过程。[5]许多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塑造都是俄狄浦斯故事的重新讲述,它们以异性恋或所谓爱情神话的主题在事件的解决中呼唤着情侣关系:如《云中漫步》(阿方索·阿雷奥,1995)中保罗与维多利亚的爱情成为治愈男主人公与整个中东战争期间美国国民内心创伤的一剂良药;《泰坦尼克号》(詹姆斯·卡梅隆,1997)的深重灾难见证的唯一奇迹即是“跨越阶级”的爱情;即使是在将人性阴暗面暴露无遗的《大逃杀》(深作欣二,2000)中,在相互残杀的游戏中活到最后的依然是一对“矢志不移”的异性恋情侣七原秋也与中川典子。“既然凝视是不可返回的,观众也就处于窥视癖的位置上。在雷蒙·贝卢尔(Raymond Bllour)看来,电影同时既是想象界(Imaginary)的,充当着镜像,又是象征界(Symbolic)的,主要体现为电影话语(discourses)中的语言……处于镜像阶段,即将获得性别差异的认知,通过照镜子,男孩发觉自己的性别与母亲的差异。”[6]在电影的“看”的关系中,电影以描述异性恋爱情故事以唤起观众无意识中的恋母欲望,其中女性是被看的客体,男性则是看的欲望主体,而且这种“看”在电影中的意义被“自然地”认为专属于男性。观众对角色的观看模仿了摄影机对场景的“观察”,以及摄影师对叙事情景的关注。观影者被置于摄影机的观看位置,他与银幕上正在注视的男性一样都处于“看”的主体地位上,每次观影行为都会再次操演男孩的无意识过程,即获得性别认知与观看异性快感的过程。
这一理论证实了观影过程中并不存在纯粹的“看”。当观影者坐在黑暗而安静的房间里,渴望观看银幕并从她或他观看的内容中获得视觉快感时,就有较大一部分快感源于观影者对银幕上的角色产生了自恋式的认同,在将自己误认为角色的“错觉”基础上,观影者甚至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影像。流行于各类电影中的英雄形象正是对这点最好的证明:无论是策马西部荒野的镖客,还是游走于黑街暗巷中的枭雄,甚至在外星球上征服探索的未来人或奇异生物,观众会自然地将自身放置在主角的位置上,不是因为他们在外形上具有相似性,而是因为观影者在凝视中获得了与主要角色的同一性。尽管这种基于想象的心理认同只是一种“误认”,但它却像在童年时期对父权秩序的认同一样有效地参与了凝视者的自我建构。电影中的透视法则确保了观影者是凝视的主体,而位于观影者身后的、“不可见”的放映装置令电影中的影像仿佛是观影者自身形象在银幕上的投射。换言之,电影模拟了无意识的过程来解释电影在无意识层面的运作机制。在克里斯蒂安·麦茨之后,以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为首的性别主义者采纳了源自于精神分析学说中的“凝视”概念,并且将它发展得更加严谨。主流好莱坞电影都建立在父权制的无意识基础上,电影叙事也由观看者中心的“无意识”语言和话语组成。[7]在事件接连发生、高潮迭起的电影中,人们被暗示时间是由一连串有趣的、值得拍摄的事件所组成,电影成为生活和历史的奇观化的工具。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对抗权力主体通过电影等媒介施加于人们的标准化与自然化进程。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便提出了一种否定内在关联性的不连续的观点来看世界,“在这个工业化的时代,发达国家由于对过去的恐惧和对未来的盲目,丧失了可信仰的正义原则,转而成为投机主义者,这种投机心态使得所有的事物——举凡大自然,历史、苦痛、其他种族、天灾、运动、性及政治——都蔚为奇观,就像电影里的场面。”[8]桑塔格提醒我们,电影与照相术代替记忆,成为一种资本主义需要的、建立在影像上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的娱乐以刺激消费麻醉阶级种族和性别造成的伤害。对此,不加辨别、任由无意识中的快感支配地“观看”,便等于接受连续性的奇闻异事而放弃对真实的掌控,“表演的场面造就出一种我们所期望的‘永恒现在式,换句话说,记忆不再是不可或缺和让人期待的。随着记忆的走势意义的连续性和判断,对我们来说也同时走失了”。[9]
三、电影中的“真实”肖像
如果说主流商业电影总体都建立在充满欲望的凝视之上,以满足观众潜意识中的快感,那么电影本身是否还存在着纯粹的、仅仅为了被“观看”而存在的肖像?答案是肯定的。例如,电影《温别尔托·D》(维托里奥·德西卡,1952)讲述了善良正直的退休公务员温别尔托在贫困与孤独中度过凄凉晚年的故事。导演对多名角色进行了细致的相象描绘,却不产生任何戏剧性效果。这位以精心编排事件与造型闻名的导演,在对男主人公温别尔托进行描述之外,让一名打扫房屋的女仆的形象反复出现在电影中。导演占用了大量篇幅展示了女佣的神情、动作、面部细节等多个方面,却不在故事的叙述上令这些画面发挥观众想象中“应有”的作用:她带着早起的困倦进厨房,洗手、用水管冲走水槽中的蚂蚁,或点燃报纸驱赶它们;把火柴在墙上打着,然后点燃煤气灶、烧水,再为公寓中的主人准备咖啡……在这一过程中,女仆并未遭遇任何戏剧性的事件(如被蚂蚁咬伤后得到女主人的关爱,会由于繁重的劳动引起流产,从而唤醒孩子父亲的良知等)。在这些场景之后,他与男主人公温别尔托的关系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两人依旧怀着保持距离的好感共同生活。当然,日常肖像的大篇幅呈现并不意味着导演对现实的呈现并未经过取舍,这些看上去毫无意义的片段是这部影片乃至新现实主义影片中都最广为人称颂的桥段之一。导演只是不再以传统的戏剧性结构作为取舍标准,而是以卓越的动件聚焦于寻常事件的复杂性,并以一件简单事情中,诸多富有生活质感的微观剧情取代了令人厌烦的戏剧性情节。
在这一段落中,墙上某区域中密集的火柴划痕与女仆漫不经心缓的动作,显示出一种动作的无限次重复。女仆早起的困倦还蕴含在每个稍显迟缓的动作中,但划着火柴、点燃报纸用烟熏蚂蚁的动作,又在“顺势而为”却“恰到好处”的精准和有效中发挥作用,就像用橡胶软管弯曲形成的水流不大不小一样,显示出女仆对这些动作的熟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困倦的女仆坐在圈椅中,她懒得起身开门,于是让身体下滑一段,伸长腿和脚,脚尖刚好合上门的镜头。“具象意味着精心编排,不产生任何戏剧性:所谓戏剧性是指突如其来、充满动感却不受约束,不兜圈子,没有任何情节的冗余物;它的急迫性不容迂回。具象画面恰恰相反,它非常从容不迫,用心装点趣味性,增添细节,放大和夸张动作、揽括多余的镜头并且充满了美感。”[10]这些镜头让观众看到她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在角色身上难以抹去的印痕。比起让他们做戏剧情节安排好的事情,不经意的小动作,漫无目的的闲逛,口不择言的俚语,或言不由衷的抱怨,或对故事主线“毫无影响”的“插入性段落”,才是更为高明的叙事方式。影片中的事件并非突如其来地降临到具体人物身上,它并非叙事要求的结果或人物性格导致的必然,而是一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真实”发生。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的卓越贡献之一,便是赋予了电影中的诸多事物与人物同等的地位,并将人物本身从戏剧性的主流叙事中解脱出来,从明显的创作者主观意识与类型束缚中释放到唯一的“真实”中,带着充满前现代艺术的灵韵成为世界电影中富于启示性的一页。[11]
结语
电影中的肖像与“观看”往往与精神分析学中的原初场景并行,它伴随着“凝视”的想象成为电影装置生产快感的主要机制。转换展示与“被观看”的视角,突破电影类型与主观创作主题的束缚,将电影肖像还原为不连续的、无先在意义的、带有生活本真性的生命形象,是电影创作者应该追求突破的方向。
【作者简介】 耿偲特,女,辽宁朝阳人,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全媒体时代影像语言课程混合式教学研究与实践”(编号:2021JGB279)成果。
参考文献:
[1][美]布鲁斯·布洛克(Bruce A. Block).以眼说话:影像视觉原理及应用[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2-4.
[2][苏]卡冈.艺术形态学[M].凌继尧,金亚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7.
[3][美]W.J.T.米歇尔.图像何求[M].陈永国,高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94.
[4][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11.
[5][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法]吉尔·德勒兹.凝视的快感 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吴琼,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6.
[6][英]蘇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孙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51.
[7][法]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 J ].Screen,1975(22):23.
[8][9][英]约翰·伯格.看[M].刘慧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7,78.
[10][法]阿兰·马松,弗兰克·考什,内甘·马蒂厄,法比安·加费,曹轶.电影与绘画[ J ].世界电影,2011(02):4-19.
[11][美]邦达内拉.意大利电影——从新现实主义到现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