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单边数字税对我国跨国数字企业的冲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刘方、杨宜勇
本文节选自《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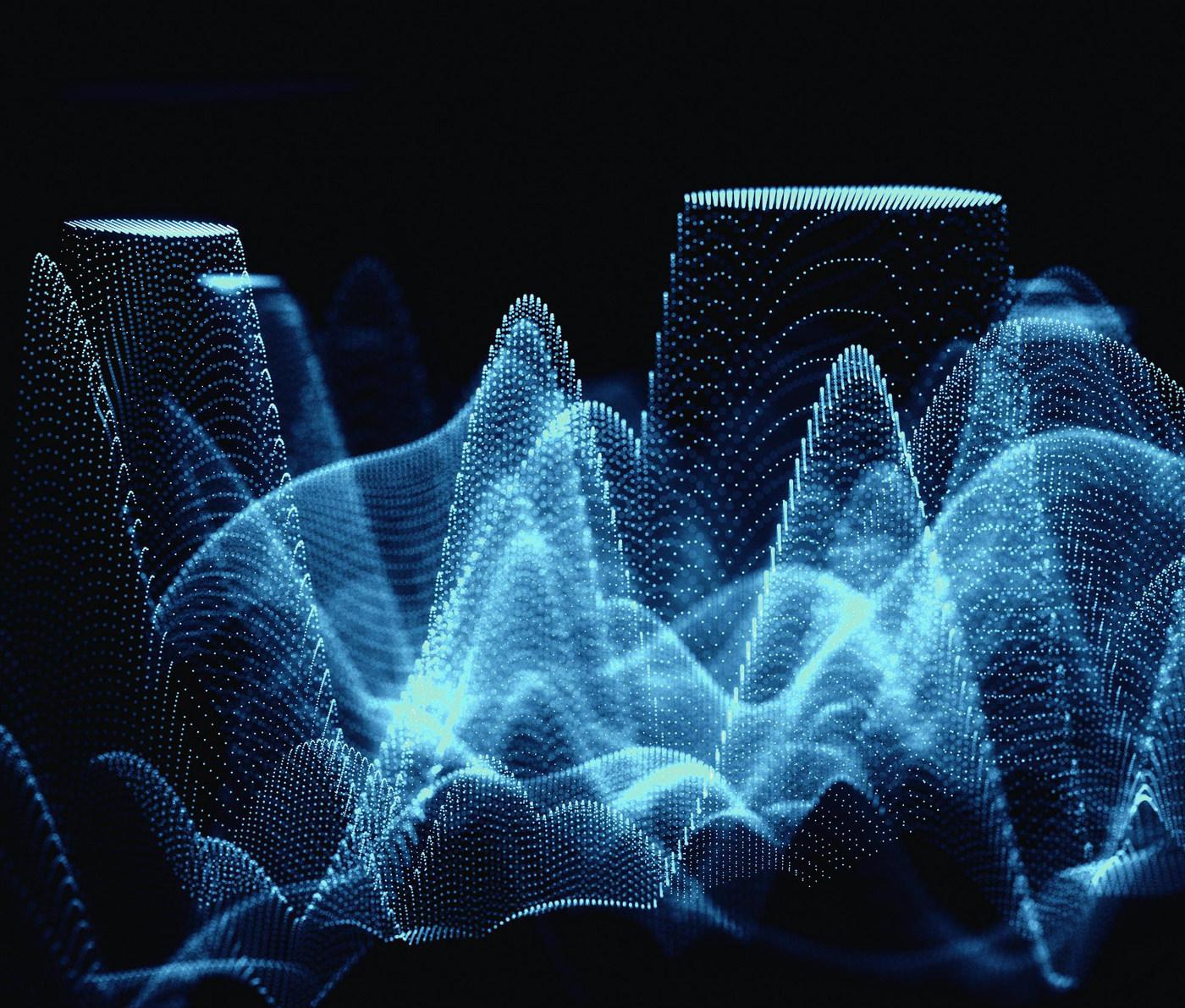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经济的出现改变了全球经济价值创造、转让及分散的方式,对国际税收核心规则形成了巨大挑战,运行了百年的跨境企业所得税国际征税规则已无法适应经济数字化下新的价值创造方式。数字跨国企业不需要设立常设机构,长期依靠用户参与活动创造价值来赚取巨额的收入。根据现行的联结度和利润分配的国际税收规则,由于缺乏税收实体,产生巨额利润的跨国企业在用户创造价值的管辖区缴纳极少的税收,甚至通过一系列手段逃避在利润来源国的纳税责任。这样的状况凸显了现行国际税收规则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缺失的公平性,同时,由于巨额的利润没有公平地在各市场辖区国征税,造成跨国数字企业与市场辖区内其他企业以及跨国企业间税负的不平等。例如,欧盟委员会对辖区内跨国数字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欧盟辖区内数字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9.5%,而传统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20.9%;跨国数字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仅为10.1%,而跨国传统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23.2%。
从实践来看,数字税主要适用于以用户参与创造价值为特征的部分数字经济活动,征收对象为在线广告服务、在线中介服务(社交网络、交友网站等)、 在线市场(多方销售平台等)、数据传输服务等。同时,征收国普遍都将数字服务收入作为税基,并且以一定规模的跨国数字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年度总收入和在本国提供数字服务取得的收入作为征税门槛。税率设置在2%~7.5%不等。
从数字税本身来看,数字税是数字经济发展较弱的国家为了弥补现行国际税收规则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避免大型跨国企业依据现行国际税收规则逃避在本国的纳税责任,加 之全球性解决方案又无法在短期内出台的情况下实施的无奈之举。数字税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扭曲性。另一方面,从我国来看,由于政策原因,目前一些跨国数字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并没有进入我国市场,它们利用国际税收规则漏洞在我国进行利润转移的问题并不严重。此外,虽然我国在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布局中位居第二, 并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大型跨国数字平台企业,但是由于相关征收国的税征收认定标准较高,我国跨国数字企业还未纳入征税范围。 基于此,结合我国减税降费的背景,我国不具备征收数字税的条件。但是,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税收治理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税收制度框架下,加快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税制,确保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税负相同,促进数字经济和税制体系的均衡发展。
从各国数字经济征税措施来看,各国对数字经济征税尚未达成一致协议,且都存在着一定的单边税收保护主义。基于此,我国还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单边数字税对我国跨国数字企业的冲击。要借助双边、多边税收协定的效力,加强与采取单边数字税国家的合作,在协商谈判中努力为我国跨国数字企业争取税收权益,为跨国数字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国际营商环境。同时,应督促企业将税收管理上升至企业战略层面,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数字经济业务的企业,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规则的变化。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我国积极老龄化战略研究”后期成果
七普数据证实,中国已经掉入 “超低生育率陷阱”,进入低生育时代的中国开启了人口学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超低生育率会引发系统性的社会风险。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优化的进一步体现,虽有重要意义但其提升生育率的作用不可高估。保持近更替水平生育率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持续发展和优化发展的人口学条件。三孩政策体现了改革的包容性和生育的多样性,其真实的受益群体应该是极小众群体。
之所以说超低生育率是未来中国最大的人口风险,是因為它是元问题,也是东西方趋同的人口生育大趋势。譬如,少子老龄化、人口性别失衡以及空巢化等系统性人口风险的根源全在于生育率的日益走低。所以,发达国家和社会都困扰于低生育,但似乎又很难摆脱。发达国家的超低生育率会引发系统性人口风险。超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就会陆续产生人口萎缩的源头效应、人口亏损的队列效应、人口失衡的结构效应、人口一代更比一代少的代际效应、低生育引致更低生育率的内卷效应。
生育的源头效应类似于上游效应和水龙头效应,因为生育从根本上决定人口的未来。无疑,超低生育率从源头上威胁着人口发展的持续性和平衡性。倘若保持目前的超低生育水平,预测的结果是,三百年后中国人口将锐减至2800万上下,这并非危言耸听。人口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是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且处于超低水平的生育率长此以往必然会出现的人口大雪崩结局,而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百年人口大变局的前夜。只要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就会到来。从2020年出生量1200万和死亡量1000万左右来推算 (两者已非常接近),未来两三年内极可能迎来中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
超低生育的队列效应是指随时间的推延,同一队列人口因为死亡的机制而不断有人退出,“低生育-少子化-少劳化”的逻辑是必然呈现的。现在的青年人口亏损是因为十多年前的低生育,而当下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今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减少。所以,为防止出现过于严峻的人口亏损问题 (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中国需要树立 “人口储备”的战略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弘
本文节选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6期
冷战结束后,原苏联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都实行代议制、三权分立和政党政治等制度。但政治转型的效果却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平稳地实现了政治转型,有的国家则仍处于混乱的政治困境中。乌克兰的政治转型历程较为曲折,经济上沦为后苏联国家中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政治上寡头政治一直盛行,政治秩序长期混乱,政治腐败现象泛滥。乌克兰为政治转型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反面案例,不仅因这个国家有着较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还因其寡头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俘获和掠夺,导致国家的治理水平较差。
第一,“转型观念”决定政治转型模式。“华盛顿共识”不仅是经济转型的模式,在政治转型上也具有重大影响力。小国家、大市场的自由市场理论也是导致国家政治转型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世纪末都形成了寡头资本主义,经济遭遇了长达十年的大衰退,而且政治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街头抗议频发。
第二,资本主义模式是影响国家形态的客观因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乌克兰再次得到验证,寡头资本主义造就了依附型国家形态。寡头利益集团对国家权力的俘获和控制就是寡头政治。寡头政治不仅导致宪政民主制度周期性崩溃,而且还威胁宪政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当人民失去公平和正义后就会选择体制外抗争,街头暴力骚乱就是对寡头政治的极端反应。
第三,政治精英是影响国家形态发展的主观因素。寡头政治在乌克兰政治中长期盛行还与乌克兰政治精英的素质有较大的联系。政治精英集团的贪婪和平庸使得他们在公共(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主动放弃了国家权力的独立性。
3722500218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