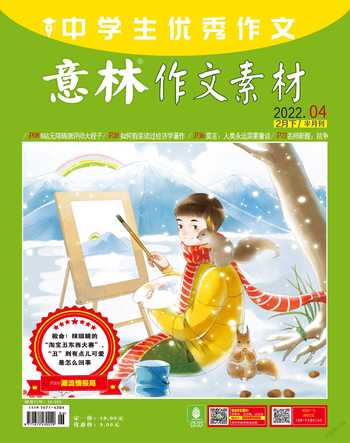好一件“笨棉袄”
司志政
【适用话题】母爱无价 常怀感恩 寒冬温情 “无用”与“有用”
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第一年的冬天。我母亲,一个农村妇女,千里迢迢,从河南老家,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绿皮火车到哈尔滨,只为给我送件过冬的棉袄。她突然出现我眼前时,我又惊又喜,嗔怪她:“邮给我不就行了,这么远跑一趟!”母亲的脸上泛着皴红,搔了搔头,“哎呀”了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忘嘞。”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起此事,我才明白母亲的心思,“目的”太过浅显——只是想看看我,摸得到,看得见的我,想想自己也够迟钝。小时候,母亲恨不能把我系她胳膊上,她去哪儿都想把我带着,我去哪儿她都想跟着,有时在同学家过夜,她都担心得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段时间,她很不开心,因为想不通,全国那么多大学,我为什么非要到哈尔滨去,“离家太远”,这是她那时候常挂在嘴边嘟囔的话。她四五天就电话问我一遍,过得怎样,安不安全?仿佛我还是那个小孩儿。
说回棉袄,那件棉袄,用的棉花是自家种的,加上邻村出产的天蓝色手工老粗布,母亲一针一线缝的。许是觉得东北冷,棉袄做得十分厚实,我穿上后“胖”了一大圈儿,鼓鼓囊囊,外衣都穿不上了。样式嘛,实在老土,跟我爷爷身上那件没区别。穿着棉袄,在宿舍扭了一圈儿,舍友们乐得不行,笑我跟电视剧里地主家的傻儿子似的。好是真好,可太丑,穿不出去。照我老家的土话说,“真是一件‘笨棉袄’啊!”纠结了好一阵子,我还是决定脱下,用塑料袋一套,往柜子里一塞,没再穿过。
毕业后,辗转去了北京工作。为了省钱,租了个没空调暖气的小房间。冬天不好挨过去,哪里是睡觉的地方,更像个冰窖。一天晚上,冷得直跺脚,忽然想起那件“笨棉袄”。离开哈尔滨来北京收拾行李时,我觉得没用,本想扔了的,但不知怎么,犹豫了下,又塞进包里。那个包里装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垃圾一样瘪瘪地靠在墙角。我忙打开包,翻出棉袄,迅速穿上,屋里瞬间像多个火炉,“腾”地一下,立马就热了。自那以后的好几年,因那件“笨棉袄”,我有惊无险地扛过一个个寒冬。
可白天出门,我一定穿另一件袄子——昂贵时髦,但不中用,身上还是拔凉的。为了所谓的“颜面”,龇牙咧嘴地忍,也没让“笨棉袄”“见过光”。只有晚上回来,关上门,才迫不及待把它换上,做贼似的。
后来回了河南老家,这里的冬天不比北京冷,暖气烧得旺,那件“笨棉袄”再无用武之地,但我一直宝贝地珍藏,成了思念母亲的“念想”,觉得孤独,拿出来看看,摸摸,对着它发会儿呆,就算是暑九天,穿在身上,也觉得母亲还在一样。
可能母亲在天上会笑我傻,大热天还穿“笨棉袄”,话中夹杂着腼腆和宠爱:“恁揍啥嘞?!”这次我不迟钝,想笑,傻笑,顺便对着天喊上一嗓子:“穿这土‘死’个人的‘笨棉袄’”嘞!”
【素材分析】这是一件“笨棉袄”,也是一件无比珍贵的棉袄。它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一针一线,母亲缝进去多少温暖、多少思念、多少希冀。而我们却往往在不經意间忽略,就像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笨棉袄,笑它穿出去“丢脸”,却又恋着它的暖,依靠它抵御无数个难挨的寒夜。辉煌时退场,落寞时陪伴,母亲的嘱托和疼爱不言而喻,简简单单的反哺与感恩,值得我们一生珍重。
(特约教师 王学华)
3914501908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