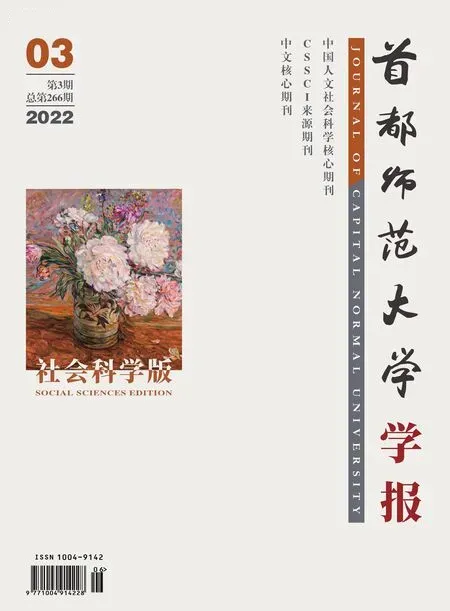考古学与19世纪后期墨西哥的古史重建
卢玲玲
19世纪,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考古学被赋予发现民族历史和重建集体记忆,建构民族起源神话的使命。它是“国家认同的可靠提供者”,能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①María del Rocío Ramírez Sámano,“‘El Nacimiento de una Ciencia’:La Arqueología Mexicana Durante el Porfiriato,”Diálogos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Historia,Número especial 2008,p.155.。独立后,如何在本土历史记忆与西方文明之中建构出连续性的历史叙事,成为美洲国家面临的挑战。美国突出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传统和历史叙事;拉美国家则将前殖民时代的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塑造出一种“梅斯蒂索化”②“梅斯蒂索化”主要指不同族群的混血和文化的融合。的历史记忆,形成了与北美不同的民族建构路径。墨西哥拥有阿兹特克、玛雅等大量古代文明遗迹。19世纪后期,墨西哥借鉴西方方兴未艾的考古学,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与保护,厘清了古代文明的基本面貌,重建了古史;阐释了本国历史演进的连续性,彰显了本土古代文明的辉煌。由此,墨西哥形成了兼具本土色彩与西方特性的历史记忆,奠定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近代墨西哥的考古活动,以及墨西哥考古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等问题。③代表性的成果有: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México: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Tesis de Licenciatura en Historia,2000;María del Rocío Ramírez Sámano,“‘El Nacimiento de una Ciencia’:La Arqueología Mexicana Durante el Porfiriato”;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o 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2004.对于近代墨西哥如何在西方的影响下,通过考古学重建古史,进而强化民族认同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以《几个世纪以来的墨西哥》①Vicente Riva Palacio etc.,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 Ⅰ-TomoⅤ,Mexico:Ballescáy Compañía,1884—1889;Lucas Alamán,Historia deMéjico desde los Primeros Movimientosque Prepararon su Independencia en el Ano de 1808 hasta la Epoca Presente,TomoⅣ,Méjico:Imprenta de J.M.Lara,1852.等19世纪墨西哥主流的史学著作为基础,尝试以跨大西洋文化交往的视角,系统论述19世纪以来墨西哥历史记忆的变化,重点阐释19世纪后期考古学与主流历史学家对墨西哥古代史的叙事,②19世纪,墨西哥具有多元化的历史观念和历史记忆。本文以简驭繁,重点分析墨西哥官方和主流的观念。为认识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的民族建构提供新的视角。
一、克里奥尔史学:墨西哥古史的再发现与历史记忆的发微
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征服墨西哥,阿兹特克等本土文明覆灭。在此后的殖民统治中,白人统治者大都将自己视为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和延续者,对墨西哥本土文明嗤之以鼻。他们将殖民征服之前的印第安人视为异教徒,认为他们处于没有法度和宗教无知的状况。③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8-29.故此,墨西哥的古代文明被污名化,湮没于大众的历史记忆之中。
但在殖民体系中,墨西哥的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与半岛人(西班牙出生的白人)嫌隙丛生。克里奥尔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次等地位,对半岛人愈发不满,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由此诞生,并衍生出凸显墨西哥本土文明的克里奥尔史学(Historiográfica Criolla)④克里奥尔史学指:独立之前,墨西哥克里奥尔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对于古史的想象与书写,及由此塑造的历史观念。,开始强调西班牙征服之前的历史。这种观念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初期便已出现,其内涵逐步演变。16世纪,一些西班牙殖民者在宗教编年史中已开始叙述墨西哥古代历史。但其叙事主要从宗教视角出发,认为西班牙征服之前的墨西哥文化无法救赎;征服之后,西班牙在墨西哥传播“福音”,改变了其偶像崇拜的状况。⑤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p.9-10.
17世纪之后,克里奥尔人对古代墨西哥文明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一些作家和史学家开始歌颂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曾经的辉煌,认为墨西哥古代文明并不逊于欧洲,哀叹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统治。1615年,托克玛达(Juan de Torquemada)撰写的《印第安人的君主制》(MonarquiaIndiana),将阿兹特克帝国与古希腊罗马进行对比,凸显墨西哥古代文明的地位。⑥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p.22-23.1680年,墨西哥人贡戈拉(Carlos de Siguenza y Gongora)设计了高达90英尺的凯旋门,以欢迎新西班牙的新任总督。凯旋门上方以12位阿兹特克皇帝的成就作为装饰,体现出阿兹特克认同深厚的社会基础。⑦Anthony 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Studies in European and Spanish-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1513-183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p.92-93.
18世纪之后,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者将阿兹特克文明与当时的克里奥尔人相嫁接。克里奥尔人的历史记忆因而“本土化”,成为墨西哥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克拉维杰罗(Francisco Xavier Clavijero)是当时代表性的史学家,他的《墨西哥古代史(1780—1781)》[HistoriaAntiguadeMexico(1780-1781)]质疑欧洲学者对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是野蛮人的污蔑,并指出克里奥尔人是阿兹特克帝国真正的继承者。⑧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23.18世纪末,墨西哥著名的史学家布斯塔曼特(Carlos María de Bustamante)则在西方古代文明史的视野下,将西班牙征服之前的墨西哥历史视为“古代”,将古代的阿兹特克人视为“我们的祖先”;他对当时的文物和文化遗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驳斥西方对古代墨西哥文明的污蔑。⑨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p.14-21.正如学者帕格登(Anthony Pagden)所言:“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者试图利用印第安人的过去,赞颂美洲出生的白人。”[10]Anthony 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Studies in European and Spanish-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1513-1830,p.10.克里奥尔史学对本土历史和文化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
在独立运动期间,克里奥尔人本土化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凸显。他们认为,墨西哥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就已存在,西班牙300年的统治为“卑鄙的篡夺”,墨西哥如今即将恢复独立。①Hans-Joachim König,“El Indigenismo Criollo.Proyectos Vital y Político Realizables,o Instrumento Político?”Historia Mexicana,vol.46,no.4,1997,p.759.他们宣扬阿兹特克末代皇帝夸乌特莫克(Cuauhtemoc)是抵抗西班牙的民族英雄,以强调独立运动的合法性。19世纪中期,智利史学家阿穆纳特吉(Miguel Luis Amunategui)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克里奥尔人流淌着西班牙的血液,却自认为是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继承者与复仇者,后者在几个世纪前被克里奥尔人的祖辈屠杀殆尽。”②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37.克里奥尔人的这种观念在墨西哥建构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却遭到西班牙长期压制的共同体,极大地推动了墨西哥民族独立运动,凝聚了克里奥尔人乃至一些印第安人的认同。③Hans-Joachim König,“El Indigenismo Criollo.Proyectos Vital y Político Realizables,o Instrumento Político?”pp.759-760.
克里奥尔史学不完全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写作方式,更是克里奥尔人为摆脱西班牙统治,实现独立的观念依托和政治文化,及由此建构出的一种“祖地”(祖国)观念和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观念渗透到当时墨西哥的历史写作、诗歌、小说、节日与民俗等各层面。其根本特征是突出克里奥尔人是古代阿兹特克文明的继承者,使克里奥尔人的历史与西班牙殖民者脱钩。克里奥尔史学成为墨西哥古史重建的起点,并为后续的史学家乃至政治家所继承。独立后,民族主义者以“墨西哥”取代“新西班牙”④“墨西哥”(Mexico)意为“墨西卡人的国家”,墨西卡(Mexica)为阿兹特克人的别称,象征着新独立的国家与古代阿兹特克帝国的传承关系。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48.作为国名、以鹰吞食蛇的形象作为国徽⑤在古代墨西哥的文物遗存中,有大量的鹰吞食蛇的形象。这是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起源神话。克里奥尔史学著作对于该传说也有丰富的记载。Natividad Gutiérrez Chong,The Culture of the Nation:The Ethnic Past and Official Nationalism in 20th Century Mexico,United Kingdom: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1995,pp.112-114.、强调古代印第安人的节日和风俗等,都体现了墨西哥对于古史的认同。
但克里奥尔人对阿兹特克文化传统的利用具有“工具化”的特征。独立后,墨西哥乃至整个西属美洲逐渐淡化古代的文明和象征,强调独立运动领导者的作用。民族主义者在演讲中不再叙说阿兹特克的历史,而是凸显革命英雄。1827年,墨西哥举行的纪念活动中,14名男童装扮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伊达尔戈,而非历史上的阿兹特克人。⑥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68.此外,墨西哥开始以独立运动的领袖命名一些城市。
由此可见,西班牙征服拉美之后,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存在两种主要的历史记忆:对于西班牙的认同,以及对美洲古代文明的认同。在殖民统治期间,以克里奥尔史学为代表的历史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并成为拉美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思想渊源。但对于西班牙的认同并未销声匿迹。1821年,墨西哥独立运动领袖发表的《伊瓜拉计划》(PlandeIguala)也有类似的表述:“美洲人,你们谁能说不是西班牙人的后代?”⑦Lucas Alamán,Historia de Méjico desde los Primeros Movimientos que Prepararon su Independencia en el Ano de 1808 hasta la Epoca Presente,TomoⅣ,p.188.一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坚称,西班牙区分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并以此歧视克里奥尔人的行为不可接受,美洲西班牙人与欧洲西班牙人具有密切的联系。⑧Rebecca Earle,“Creole Patriotism and the Myth of the ‘Loyal Indian’,”Past&Present,vol.172,Iss.1,2001,p.134.就连当时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德米尔(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也表示,他与西班牙贵族具有血缘联系,是第一代征服者的后代。⑨在另外一些场合,德米尔又自称为夸乌特莫克的后代。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42.独立之后的墨西哥处于这两种历史观念的焦灼之中,无所适从。
此外,在克里奥尔史学中,印第安人也属于被遗忘的群体。尽管克里奥尔史学家将古代印第安文明纳入民族历史叙事之中,但克里奥尔人成为古代印第安文明的继承者,现代的印第安人则被排除在外。一些克里奥尔人认为,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高贵,但被征服后的印第安人退化且平庸,两者没有相似之处。①Rebecca Earle,“Creole Patriotism and the Myth of the ‘Loyal Indian’,”p.133.一些人甚至认为,墨西哥古代的文明并非印第安人创造,而是腓尼基或亚特兰蒂斯等古代文明创造。②Sven Schuster,“TheWorld’s Fairs as Spaces of Global Knowledge: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Age of Exhibitions,”Journal ofGlobal History,vol.13,Iss.1,2018,p.70.
总之,克里奥尔史学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它既遭到强调与西班牙殖民者血缘联系的保守派的反对,也未将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纳入其中。③独立初期,印第安人约占墨西哥人口的60%,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和白人分别约占22%和18%。参见刘文龙:《墨西哥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因此,在独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墨西哥国家认同混乱,凝聚力不强。1846年到1848年爆发的美墨战争,进一步凸显了墨西哥国家的虚弱。这场战争使墨西哥丧失了近半数的领土。正如墨西哥学者所言,墨西哥没有国家、不团结,是各种敌对集团的联合。④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5.墨西哥各个阶层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冷漠,成为墨西哥人的创伤。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被赋予了建构民族神话的功能。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民族历史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没有辉煌古史的民族,在现实中难以取得成功。而在当时西方的历史叙事中,美洲被视为“文明退化”之地。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墨西哥需要重振民族自信、强化民族认同和团结。如何重建古史成为其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在古史重建的过程中,考古发掘特别是文物等物化文明象征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回应文明退化论:跨大西洋文化交往视域下墨西哥考古学的发展
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兴起了古物学,古物收藏之风日盛。18世纪之后,古物学逐渐向科学考古转型。18世纪中后期,欧洲的考古学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大量欧洲考古学家到中东、美洲等地进行考察,并将发掘的文物带回欧洲;二是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欧洲学者开始借助考古学建构人类社会发展的单线性路径,形成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阶段说⑤参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3页。。先进的物质文化成为衡量道德和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历史遗存则成为评判一个民族过去的标准。按照这种观念,古代的物质成就反映了当地民族的文明水平。⑥Mauricio Tenorio-Trillo,Mexico at the World’s Fairs:Crafting a Modern N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88.在这种叙事逻辑下,西方因拥有发达的物质文化而成为近现代文明的高峰,其发展路径也成为其他地区的模板。借此,西方建构了一套话语体系,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及其对亚非拉地区殖民的正当性。
墨西哥考古学受到欧洲考古学的深刻影响,其发展演变类似于欧洲国家,经历了从古物收藏到科学考古的演进。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后便燃起了欧洲人对美洲文物的兴趣。征服者科尔特斯曾将一些古代墨西哥的文物送给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Ⅴ),⑦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28-29.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特(Peter Martyr)指出:“没有什么比这些文物更能取悦我的眼睛。”⑧Benjamin Keen,The Aztec Image inWestern Thought,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1,p.64.但是,18世纪中后期,西方对文物收藏的兴趣转向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世界。19世纪初,东方的文物失去了新鲜感,非洲和大洋洲的文物则被归结为“原始”的古物。美洲以有别于旧世界的神秘风格和丰富的文物吸引着西方人。墨西哥有一万余处历史遗迹,其中既有壮观的城市遗址和金字塔,也有神秘的祭坛和精致的古代工艺品等。⑨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15,29.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Ⅳ)曾遣人到墨西哥搜寻和发掘文物,对墨西哥的历史遗址进行调查。[10]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64.
欧美人在墨西哥的文物发掘,使一些被人遗忘的文明遗迹得以再现。墨西哥的古物也成为令人垂涎的商品和研究对象。1821年,英国古董商金斯伯勒(Lord Kingsborough)收集了大量墨西哥文物,并出版了介绍这些文物的著作,在欧洲乃至墨西哥产生很大的反响。①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64.法国人布尔伯格(Brasseur de Bourbourg)收集了大量古代墨西哥的手稿,沃尔德克(Waldeck)收藏了众多墨西哥古代的艺术品。美国外交官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考察了玛雅文明的遗迹,运走了大量的文物,并出版了第一本介绍玛雅文明的书籍。②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32-33.但是,西方的这些活动仍以猎奇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考察为主,属于传统古物学范畴。
欧美人的古物发掘活动虽然导致大量墨西哥古代文物的流失和破坏,但也增加了西方对于古代墨西哥文明的了解。1850年,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专设了墨西哥展厅,“想要参观的巴黎人如此之多,他们比肩迭踵才能进入”③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30.。此外,19世纪后半期,在美国、德国也出现了大量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墨西哥古代文物。受此影响,西方开始研究古代墨西哥的文明,并到墨西哥进行考古发掘,墨西哥因而出现了由古物学向科学考古的转向。19世纪60年代,法国入侵并占领了墨西哥。此后,法国在巴黎建立了法国—墨西哥委员会(Franco-Mexican Commission)④RobertM.Buffington,Criminal and Citizen in Modern Mexico,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0,p.149.,美国也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
与此同时,19世纪的西方学者也开始从考古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等视角,阐释其对墨西哥古代文明的认识。其代表有: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内贝尔(Carlos Nebel)等。尽管这些西方学者对墨西哥生态环境的壮美和古代遗存有所称赞,但也受18世纪布丰(Buffon)、德波(Cornelius de Pauw)和雷纳尔(G.T.F.Raynal)等提出的“美洲退化论”的影响。该理论以科学的名义解释种族退化,以西方文明为模板阐释美洲古代的文明,认为美洲的环境导致人种的退化,美洲在文明发展上处于劣势。⑤Rebecca Earle,“Creole Patriotism and the Myth of the‘Loyal Indian’,”p.136.因此,这些西方学者仍然强调气候、饮食、环境等因素会导致种族的改变。⑥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16.其历史阐释的特征在于:将古代墨西哥等美洲文明与欧洲文明进行比较,阐释两者的共同性,但重点在于凸显美洲古代文明的特质及其落后性。例如,洪堡论及“新世界的文物”、“绘画艺术”和“文化”时,以西方流行的审美评判美洲古代的成就,认定其文明发展具有滞后性。⑦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p.24-26.
在这种语境下,不仅印第安文明落后,克里奥尔人也处于退化之中。因此,墨西哥需要为自身的文明辩护,提升本土文明在西方话语中的地位。换言之,就是以西方的学术话语驳斥西方对墨西哥古代文明的贬低,进而强调美洲并非种族退化之地。这其中,考古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19世纪的墨西哥学者塞拉(Justo Sierra)所言,在所有学科中,考古学是唯一赋予墨西哥民族特性的学科。⑧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76.
17世纪末,墨西哥模仿西方的古物学,开始进行古物的收集和展示。许多克里奥尔人开始寻找墨西哥的古迹和古物,宣彰克里奥尔人与本土的联系。17世纪末,墨西哥学者贡戈拉就认为,墨西哥的古物与欧洲的古物一样高贵和可敬。⑨Benjamin Keen,The Aztec Image in Western Thought,p.190.1790年,墨西哥城中央广场(Zocalo)扩建时出土了大地女神的神像(Coatlicue)和阿兹特克历法石(Piedra del Sol),引发了欧洲学者和墨西哥学者的争论。德波等欧洲学者认为,大地女神的神像丑陋不堪,“野蛮人”没有以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制作历法石。墨西哥人阿尔扎特(Jose Antonio Alzate)则指出,历法石是古代印第安辉煌文明的象征。[10]大地女神像和阿兹特克历法石现存于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其前身为墨西哥国家博物馆。Benjamin Keen,The Aztec Image in Western Thought,p.301.伽马(Leon y Gama)被视为墨西哥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从学理的角度指出,历法石体现了古代印第安人在天文学和几何学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以此驳斥德波等欧洲学者的“严重错误”。[11]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51.这两件文物如今已成为墨西哥历史的重要象征。
19世纪,博物馆成为彰显民族自信和悠久文明的舞台。墨西哥外交部长阿拉曼(Lucas Alamán)访问欧洲之时,为欧洲国家博物馆的收藏所震撼,极力推动墨西哥建立类似的机构。1825年,墨西哥国家博物馆成立,成为19世纪墨西哥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护的主要机构。①RobertM.Buffington,Criminal and Citizen in Modern Mexico,p.149.但19世纪上半叶墨西哥学者的研究大都属于传统的古物学,主要利用古代文献研究文物,很少进行实地发掘。即便是实地考察也往往具有浪漫主义的田园色彩。此外,受19世纪上半期政治纷争的影响,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馆藏规模小,研究水平也不高。曾任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拉米雷斯(Fernando Ramirez)曾抱怨道,研究古史的学者从未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②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52-53.
没有过去的国家只是缩写的术语,考古学一直是现代国家构建本民族历史所需原材料的供应者之一。③María del Rocío Ramírez Sámano,“‘El Nacimiento de una Ciencia’:La Arqueología Mexicana Durante el Porfiriato,”p.156.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方的科学革命以及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墨西哥对考古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忱,试图借助新兴的科学考古“重建国家的自信心”,塑造一种新的国家形象。1875年,墨西哥学者拉因扎尔(Manuel Larrainzar)指出,对墨西哥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它塑造历史的进步。④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p.77,80.1876年,迪亚斯(Porfirio Díaz)当选为总统,在其35年的执政生涯中,墨西哥社会长期稳定与和平,出现了“迪亚斯治下的和平”(Pax Porfiriana)。为了维系其统治,发展经济,重新塑造国家形象,迪亚斯大力支持墨西哥考古学的发展。
19世纪后期,墨西哥的文物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些墨西哥人与西方古董商联系,将文物不断贩卖到境外,西方一些游客和学者私采乱挖。⑤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p.138-139.墨西哥人也拆掉金字塔和神庙,建造房屋,在古迹上耕种等。因此,迪亚斯政府对于文物的保护和发掘并重,将保护文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组建考古与文物保护部门,并对之实施立法保护。1885年,墨西哥设立考古遗迹监察局(Insp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Monuments),由考古学家巴特莱斯(Leopoldo Batres)主管,负责文物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在国家博物馆之下设体质人类学研究部门,创办《国家博物馆年鉴》(AnalesdeMuseoNacional),向国外介绍墨西哥的考古成就和古代历史。由此,墨西哥在考古方面形成了双轨并行的机构:一是考古遗迹监察局负责文物发掘和保护,二是国家博物馆负责对文物的研究和展出。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对于考古的投入和支持剧增。19世纪中期,华雷斯总统给国家博物馆的拨款预算为500比索。19世纪70年代,迪亚斯掌权后,这一预算激增到12160比索,20世纪初的预算更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十倍。⑥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43,54,58.
虽然墨西哥自独立之初便开始通过立法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但不同的法律存在矛盾,而且缺乏执行力。1827年,墨西哥颁布法律,禁止文物出口。⑦María del Rocío Ramírez Sámano,“‘El Nacimiento de una Ciencia’:La Arqueología Mexicana Durante el Porfiriato,”p.159.1840年,墨西哥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参与文物发掘”,导致对文物的严重破坏。1862年,墨西哥颁布的新法禁止私人发掘。同时,这些法律对于文物保护的执行者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存在分歧。1896—1897年,墨西哥颁布了两部重要法律,进一步规范文物发掘与保护。其中明确规定,禁止个人挖掘文物,所有文物属于国家,考古活动需要在联邦政府的监督下进行;挖掘的所有文物必须上交国家博物馆,禁止文物出口;国家有权征用私人土地进行考古发掘等。⑧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55,87-95.考古遗迹监察局全面负责墨西哥的考古活动和文物保护,审查文物能否出口等。此后,墨西哥的主要文物和遗址得到保护,西方考古学家和古董商公开买卖墨西哥文物的行为基本绝迹。大量文物从全国各地运送到墨西哥国家博物馆。
随着大量古代文物的发掘,墨西哥对于本国古史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开始借助考古活动驳斥西方对于墨西哥古代文明的认知。19世纪后期,墨西哥最重要的考古活动当属巴特莱斯负责的特奥蒂瓦坎遗址(Teotihuacan)的挖掘。巴特莱斯测量了该遗址的太阳金字塔,绘制了墨西哥第一幅考古地图,将阿兹特克历法石安置于国家博物馆。同时,他对特奥蒂瓦坎遗址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该遗址分为两个文化层,分别为托尔特克人和阿兹特克人创造,两者具有继承性,出土的文物显示墨西哥古代文明处于先进水平。①托尔特克文明存在时间约为公元800—1000年,阿兹特克人自称是该文明的继承者。Leopoldo Batres,Teotihuacan o La Ciudad Sagrada de los Toltecas,Mexico:Talleras de la Escuela N.de Artes y Oficio Ex-Convento de S.Lorenze,1889,p.17.他指出,太阳金字塔“比埃及金字塔更优雅、更令人印象深刻”。②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148.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墨西哥的体质人类学家认为,导致墨西哥古代文明退化的是社会因素而非印第安人的种族劣势,印第安人在体质上并不次于欧洲人,甚至更为先进。③Vicente Riva Palaci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Ⅱ,pp.472-476.为了展示前西班牙祖先的伟大,迪亚斯政府于1887年在改革大道上为夸乌特莫克雕像揭幕,以古阿兹特克的纳瓦特语(Nahuatl)发表演讲,并将其同声传译成西班牙语,以便大多数参加活动的人能理解。④María del Rocío Ramírez Sámano,“‘El Nacimiento de una Ciencia’:La Arqueología Mexicana Durante el Porfiriato,”p.156.
19世纪后期,墨西哥的考古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在客观性上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松散的民族认同,并从根本上驳斥了西方盛行的美洲文明退化论,使墨西哥从科学的角度找到了本土文明的起源与民族自信。其中,世界博览会和国家独立100周年庆典,成为墨西哥展现其深厚文明积淀和民族风采的舞台。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墨西哥以特奥蒂瓦坎遗址为模板,建造了“阿兹特克宫”⑤阿兹特克宫顶部的雕塑既有古代阿兹特克的神祇,也有阿兹特克的杰出君主。,彰显墨西哥悠久的文明,以改变西方对于墨西哥的传统认知。在1892年的马德里世界博览会上,墨西哥展出了一万件前殖民时代的手稿。⑥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150.1910年为墨西哥独立运动爆发100周年。在巴特莱斯的主导下,墨西哥全面挖掘和清理特奥蒂瓦坎遗址,并在当地建立博物馆,作为百年庆典活动的一部分。1906年,迪亚斯总统出席特奥蒂瓦坎遗址的落成典礼,并登上太阳金字塔。1910年,迪亚斯参观国家博物馆,在阿兹特克历法石前拍照。在百年庆典活动现场,大量墨西哥人穿着阿兹特克服饰,跳着阿兹特克舞蹈。⑦Seonaid Valiant,Ornamental Nationalism:Indigenous Images in Porfifirian Mexico,1876-1911,Portland: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1997,pp.92-93.墨西哥的古代文明正式进入官方的历史叙事。
总之,墨西哥通过考古活动再次“发现”了殖民之前的文明,将之纳入墨西哥民族历史的叙事框架。但墨西哥的历史认同问题并未因此解决。从空间上看,墨西哥古代具有多元的族群和文化构成;在时间上又有不同的文化层。换言之,墨西哥的古史是复数而非单数。那么,墨西哥历史的主体是谁?如何重建和叙说古史,如何阐释古史与西班牙征服、民族独立的关系?这些都是墨西哥在国家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以考古释古史:墨西哥的古史重建与叙事逻辑
18世纪后半叶,墨西哥兴起了克里奥尔史学,强调克里奥尔人与墨西哥古代历史的联系。这种观念旨在服务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墨西哥古代文明的认识较为模糊,更多的是对古代文物的浪漫化想象。19世纪前期,墨西哥大多数史学著作侧重于对独立运动的渲染,虽然已将古史纳入叙事框架并称赞古代文明,但大都强调西班牙传统,认为墨西哥的古代文明次于西班牙征服者的文明。⑧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107.此外,墨西哥史学家对于古史的认识不一,甚至存在矛盾,由此出现多元和相互竞争的历史记忆。19世纪后期,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古代文明的图景逐渐清晰,墨西哥学者将考古学与克里奥尔史学相结合,使克里奥尔史学具有了丰富和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开始系统阐释古代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和民族历史的神话,并通过博物馆、学校历史教育和史学编撰建构集体的历史记忆。
墨西哥对古代历史阐释的逻辑起点在于凸显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大部分精英已承认古代文明是墨西哥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塞拉指出,西班牙征服之前的世界构成了我们的过去,我们将它作为历史的序言和民族历史的基础。⑨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107.但墨西哥古代文明与西班牙的统治是何种关系,两者是如何影响独立后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墨西哥的历史仍然是断裂的。19世纪后期,墨西哥一些主流的史学家尝试阐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同时尽可能放大古代文明的影响①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Ⅻ.。在当时克里奥尔人的历史叙事中,西班牙乃至西方文明仍然优于墨西哥的古代文明,墨西哥现代民族是在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形成的。换言之,古代文明为墨西哥提供了历史的基础,西班牙征服则带来了现代文明,墨西哥民族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19世纪末,墨西哥出版了五卷本的《几个世纪以来的墨西哥》②该书内容涉及从古代到1867年墨西哥的社会、政治、宗教、军事、艺术、科学和文学发展等。(MéxicoaTravésdelosSiglos),该书是墨西哥第一部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通史著作,对于重建集体历史记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书将墨西哥的历史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加以论述,将之分为前殖民时期、殖民统治时期、独立时期、共和国早期和改革时期。③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60.第一卷借助墨西哥的考古发现,全面论述了墨西哥古代的文明成就,以发掘的动物化石和人类的遗迹证明“我们领土上的民族与旧世界一样古老”,拥有与旧世界类似的生物与生态环境。④Alfredo Chaver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Ⅰ,pp.62-63.作者认为,对墨西哥而言,西班牙的征服是“一个伟大民族在更为先进的文明面前痛苦和不可避免的失败”,也是国家崛起的第一步。⑤Vicente Riva Palaci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Ⅱ,p.471.“西班牙的统治在完成使命后就结束了,在西班牙殖民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它从给予其文明的西班牙那里继承思想、习惯、教育,以作为回报”。⑥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130.不难发现,这种线性的历史观将文明的演进视为不断进步的历程,试图调和强调古代印第安起源的自由派和强调西班牙起源的保守派,凸显现代墨西哥民族兼具两种文明属性,最终将古史“墨西哥化”。
这种历史叙事凸显了墨西哥历史的连续性,彰显出墨西哥具有辉煌的过去,在进步主义的话语下,独立后的墨西哥将更为强大。但是,由此衍生出另外三个问题:(1)墨西哥古代文明并非单一的中心,族群也并非仅是阿兹特克人,如何叙说古代墨西哥文明的源头;(2)墨西哥古代文明独立于旧世界而存在,还是旧世界文明的延伸;(3)在墨西哥的多元社会中,哪个族群继承了古代墨西哥的文明?19世纪后期的墨西哥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历史阐释体系,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解答。
第一,“托尔特克—阿兹特克—墨西哥”的古史演进线索。
在当时的主流史学著作中,墨西哥不仅拥有从古到今的整体性历史演进线索,还具有“托尔特克—阿兹特克—墨西哥”的古代文明变迁主线。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主要拥有两大文明:中部的阿兹特克和南部的玛雅。在这两大文明之外,还有众多的游牧、半游牧和农耕的族群。19世纪末,考古学家巴特莱斯在特奥蒂瓦坎发掘出两个文化层:托尔特克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墨西哥的主流历史学家认为,托尔特克人是“我们的第一个民族”,也是最先进的民族,阿兹特克人继承了托尔特克人的文明。⑦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109.因此,托尔特克—阿兹特克文明成为墨西哥民族起源的神话,文明的火炬也在两者之间交接。
墨西哥则是托尔特克—阿兹特克文明的继承者。墨西哥国徽中鹰吞食蛇的形象,直接源自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的建城传说。在这种历史叙事中,玛雅及其他的古代文明被有意遮蔽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墨西哥》的作者对阿兹特克人、奥托米人(Otomí)和玛雅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阿兹特克人最完美、最强大。⑧Alfredo Chaver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Ⅰ,pp.75-76.在墨西哥官方历史叙事、国家博物馆的展示中,阿兹特克文明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墨西哥展出的几乎都是阿兹特克的文化符号。当然,这种历史叙事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墨西哥独立后,地方势力强大,多元化的古史认同势必会强化地方意识⑨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Ⅻ.。因此,古史编撰不仅是历史叙事问题,更具有重要的政治隐喻。托尔特克和阿兹特克文明的中心特奥蒂瓦坎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所在地,统一的古史记忆反映了墨西哥集权化的努力。
第二,比较视域下墨西哥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联。
19世纪后期,墨西哥史学家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试图呈现墨西哥古代文明的辉煌,旧大陆伟大的古代文明则是衡量的尺度。墨西哥学者将埃及、欧洲作为比较的对象,认为墨西哥的金字塔、美洲的雕塑、古代社会治理等并不逊于旧大陆,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先进。例如,他们将特奥蒂瓦坎的死亡之街誉为庞培的坟墓之街;比较墨西哥与埃及的金字塔,以及阿兹特克的神祇与古代罗马神话的相似性;认为墨西哥古代的陶瓷胜过希腊和罗马等所有古代文明,艺术优于古希腊和埃及等。①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66-67.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墨西哥》中,作者指出墨西哥人和旧大陆的人一样古老,②Alfredo Chaver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Ⅰ,pp.62-63.并用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证明,印第安人比其他民族甚至欧洲人的进化程度更高。③Vicente Riva Palaci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Ⅱ,pp.472-476.1880年,墨西哥政府资助出版的《墨西哥古代和征服时代的历史》(Mexico’sAncientandConquestHistory)指出,阿兹特克文明比古代希腊文明更为先进。④Rebecca Earl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ndians and Myth-Making in Spanish America,1810-1930,p.109.
这种历史叙事是“寻求同欧洲人平等及其认可的手段”。⑤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66.古代墨西哥孕育了不次于旧大陆的文明,当代墨西哥也并未处于退化状态,以此解构西方关于美洲退化的认知。进一步而言,这种文明比较,隐含着墨西哥古代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与旧大陆存在联系,甚至源于旧大陆的观念。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贝拉(Manuel Orozco Berra)指出,古代亚洲和美洲文明之间存在联系。⑥Adriana Pérez Soto,Arqueología y Nacionalismo a la Luz del Discurso Histórico Mexicano:1850-1910,pp.101-105.在墨西哥的神话传说中,此类案例并不鲜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羽蛇神的传说。墨西哥一些学者声称,印第安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拿非利人(Nephtuim),他被认为是诺亚之子闪的后代和迦南人的祖先。他们将拿非利人附会为托尔特克人信奉的羽蛇神,认为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就是羽蛇神复临人间。⑦Anthony 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Studies in European and Spanish-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1513-1830,pp.94-96,107.
第三,将克里奥尔人塑造为阿兹特克文明的继承者。
独立后,墨西哥的社会构成十分复杂,既有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也有印第安人和黑人,印第安人还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在历史叙事中,墨西哥作为一个整体继承了阿兹特克文明,但也必须回答哪个民族才是真正的继承者,以及现代印第安人与古代阿兹特克文明是什么关系。19世纪末,墨西哥官方叙事强调印第安人退化了,克里奥尔人接起了古代文明的火炬。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墨西哥展出的古代阿兹特克神祇和帝王的雕像都是古代希腊、罗马的相貌和装束。⑧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68.《几个世纪以来的墨西哥》的作者明确指出,印第安人已堕落和退化为野蛮民族。⑨Alfredo Chaver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Ⅰ,p.67.许多学者都强调,征服之前的文明与“美洲可耻的印第安人完全没有关系”[10]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65-66.。换言之,克里奥尔人利用了印第安人的历史,却否认现实中印第安人的地位。
对于当时的印第安人能否被纳入历史叙事和民族共同体,19世纪末存在两种观念。一些学者受到西方的文明退化论影响,强调印第安人是退化的族群,天生低人一等。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库巴斯(Gareia Cubas)指出:“土著是堕落和退化的,很难为共和国的进步提供活力。”一些激进派甚至希望这个“劣等种族”从墨西哥的舞台上消失。[11]T.G.Powell,“Mexic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Indian Question,1876-1911,”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8,no.1,1968,pp.21-22.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印第安人的退化并非源于“不可更改的生物特性”,而在于文化、制度与社会环境。[12]Martin S.Stabb,“Indigenism and Racism in Mexican Thought:1857-1911,”Journal of Inter American Studies,vol.1,no.4,1959,p.411;T.G.Powell,“Mexic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Indian Question,1876-1911,”pp.9-36.一些学者认为,印第安人的落后是因为饮食问题;也有人认为是因为缺乏土地;印第安人在历史上展现出“巨大的能量”,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进行“救赎”。[13]Christina Maria Bueno,Excavating Identity:Archaeology and Nation in Mexico,1876-1911,pp.62-64.迪亚斯总统一直排斥印第安人,但也认为印第安人具有优点,应该通过教育进行改造。曾任墨西哥教育部长的塞拉坚信,“已经显出巨大能量的种族不会消亡,唤醒它的时刻已经到来,教育在其中是必要的”[14]Martin S.Stabb,“Indigenism and Racism in Mexican Thought:1857-1911,”p.416.。印第安人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民族和历史记忆的双重“梅斯蒂索化”,塑造一个兼具印第安人和克里奥尔人优点的“最强的民族”,这是“高级选择”和“环境适应”的结果。①Vicente Riva Palacio,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TomoⅡ,pp.472-473.这种对于印第安人的肯定为20世纪印第安人融入墨西哥主流社会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后期,墨西哥对于古史的重建,以及上述历史叙事逻辑的形成不只是社会精英的学术争论,也成为一种官方建构的集体记忆并通过博物馆、历史教育和公共节日庆典等向社会灌输。迪亚斯就指出,墨西哥将在教室里得到巩固。②Mauricio Tenorio-Trillo,Mexico at theWorld’s Fairs:Crafting a Modern Nation,p.68.在历史教育方面,19世纪50年代,墨西哥政府在高校、中学和师范学校开设墨西哥古代史和近代史,并编写了第一本小学历史教科书《墨西哥历史简编:从征服前到现在》(CompendiodeLaHistoriadeMexico:DesdeAntesdelaConquistahastalosTiemposPresentes),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和古代文明。19世纪70年代之后,墨西哥政局实现稳定,政府建立了统一的教育体系,强制所有6—12岁的儿童接受初等教育,并编写了大量的历史教科书。③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Nacionalismo y Educación en México,México:El Colegio de México,1975,pp.42-50,67.如普列托(Guillermo Prieto)的《为军事学院学生编写的国史课程》(LessonsinHistoriaPatriaWrittenfortheStudents attheMilitaryAcademy)、塞拉的《国史问答》(CatechismofHistoriaPatria)等。这些历史教科书将上述历史观念融入其中,塑造了墨西哥人的集体记忆,奠定了现代墨西哥历史认同的根基。
余论:从古史重建看墨西哥民族建构之路
历史叙事是民族记忆的基础。独立之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存在两种历史记忆:本土记忆和对西方文明的记忆。这导致许多国家出现身份困惑,无所适从。18世纪末,墨西哥兴起的克里奥尔史学强调本土历史记忆,为民族独立提供了合法性。但独立之后,这两种历史观念相互矛盾,使墨西哥国家凝聚力松散,中央政府力量衰微。19世纪中期的美墨战争使墨西哥的虚弱一览无遗,甚至面临着亡国之忧。此时,西方正借助科学革命,在社会进化论的框架下利用考古、史学和文学等叙说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这种语境下,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成为文明退化的蛮荒之地。在内外两种压力下,墨西哥找寻克里奥尔史学的遗产,开始利用西方的考古学重新“发现”古史,并将古代文明与现代墨西哥国家进行有机衔接,形成了连续性的历史叙事与民族记忆。这使墨西哥在历史记忆上实现“梅斯蒂索化”:古印第安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有机融合。借此,墨西哥强化了民族自信与历史认同,奠定了民族建构的基本道路。
文化上的“梅斯蒂索化”使墨西哥找到了本土记忆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平衡点,在混杂的历史记忆中建构了共识。④19世纪末直至今日,一些墨西哥学者仍然认为西方文明是墨西哥历史的源头,但这种观念已不占主流。但19世纪的墨西哥更多的是利用印第安的古代文明,却未将“活着的”印第安人纳入历史叙事。印第安人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在墨西哥1910年革命中,印第安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极大地震慑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克里奥尔人。因此,20世纪的墨西哥精英不仅将印第安人视为可改造和提升的对象,而且通过“梅斯蒂索化”对之进行种族上的整合。墨西哥考古学中衍生的人类学在这一实践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文化上和种族上的融合,使墨西哥成为以梅斯蒂索人和混合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同质化的社会整合。
需要指出的是,墨西哥以“梅斯蒂索化”为基础的民族建构道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论是19世纪在历史记忆上的融合,还是20世纪在文化和种族上的融合,都是以西方文明阐释墨西哥的本土历史和现代性,试图以此改造印第安人。20世纪70年代之后,墨西哥才逐渐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开始保护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但与美国等国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和隔离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民族问题相对缓和。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拉美国家的民族是“咖啡加牛奶”的混合现象,没有族群差异,更多的是不同阶层的冲突。⑤这里的咖啡代表印第安人,牛奶代表白人,意指拉美人以混血为主,只是混血程度不同,寓意拉美社会具有同质性。参见李北海:《拉丁美洲:和谐的民族,和谐的文化》,《当代世界》2009年第8期。由此不难发现,19世纪墨西哥通过考古学重建古史之于民族建构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