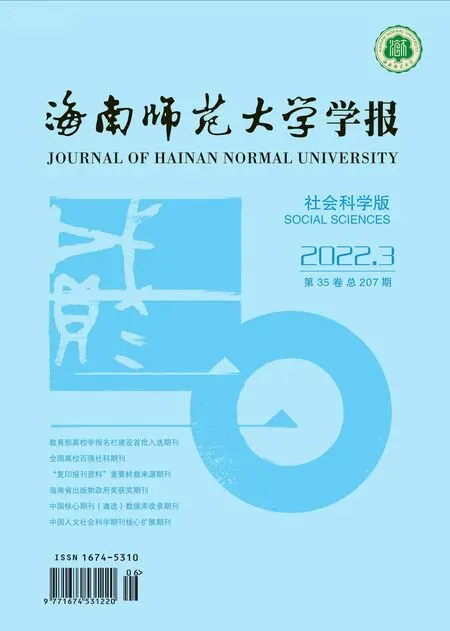风景书写与民族国家想象
——现代诗歌中国家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万 冲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226001)
近年来,风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风景(Landscape),最初是指肉眼所能看得见的土地或领土的一个部分,20 世纪初期以后,风景被定义为“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1)[美]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67-368页。。风景不仅是有别于人造世界的自然景观,更凝聚着家园情感、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等丰富内涵。正如学者段义孚所言:“风景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2)[美]段义孚:《风景断想》,《长江学术》2012第3期。而关于民族国家,根据安德森的定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8页。。正因为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和共同性,它极易诱发人们的集体认同感。而作为一种凝聚着集体记忆的载体,风景对于民族国家的塑造与认同,自然而然具有重要的作用。(4)李政亮:《风景民族主义》,《读书》2009年第2期。目前,中国学界对此问题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引用外国的风景理论,对风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做引介性的综述;二是针对某一特定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在危急时刻风景书写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而针对现代中国丰富复杂的历史情况,上述研究显然略显单薄。在中国由“天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5)[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一个重要的文学问题便自然凸显出来:当象征古典中国的“山河”形象不足以描述现代中国时,现代文学该如何想象现代中国形象,风景书写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文从现代诗歌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风景书写与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深入揭示风景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深层联系,一方面可以理清现代文学发展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或许可以为诗歌研究打开新的路径。
一、风景与文化中国认同
被朱自清称为“爱国诗人”(6)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7页。的闻一多,在西化风气盛行之时,不无激愤地说道:“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7)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在表达了对西化风气的不满之后,闻一多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我们热爱祖国的思想就是由热爱乡土的思想发展出来的”(8)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页。。黄河、昆仑、泰山等独特的自然风景,被视为最具特色的民族象征。闻一多渴望建立本土民族文化尊严的呼吁,隐约透露出民族认同危机与民族自豪感并存的复杂心态,这其实也折射出现代诗人所处的境遇发生了变化——不再以天朝上国为中心自居,而是在世界之中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经受着“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9)[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处于建构期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已然存在的形象,而是一个化无形为有形的过程(10)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9页。。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独具民族地理特色的自然风景承载着历史积淀、文化记忆以及民族美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代诗歌写作中,风景如何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呢?
在“五四”时期,将风景与国家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有郭沫若、闻一多、康白情等诗人。在旅居日本游览今津时,郭沫若写道:“我在福冈住了将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垒’在近旁,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又在渴望着踏破万里长城呢!”(11)郭沫若:《今津游记》,周作人编:《新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78页。在自然风景中指认出蒙古时期的战争遗址成为旅行的动机和目的,表现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在强烈的爱国热忱的驱使下,郭沫若采用较为粗暴简单的比附方式,将自然风景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同样葆有深沉爱国情感的闻一多,在风景之中寄托家国之思,采取更为圆熟的抒情方式,表现出更为深厚的文化内蕴。闻一多旅居海外身处异域文化中,饱受思乡思国之苦,他在《太阳吟》中寄寓了思国思乡之情。本没有地理属性和民族属性的太阳,被闻一多强行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太阳被认领为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到来的“神速的金乌”:“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12)闻一多:《太阳吟》,《闻一多全集》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页。在中国远古神话中,太阳代表华夏民族的先祖之一炎帝,它载着名为三足乌的神鸟在天空中飞行。闻一多将太阳比喻神乌,与中国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唤起的民族感情不言而喻。闻一多和郭沫若将普适性的自然认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一方面暗示了“天朝上国”的潜意识作用;另一方面,也暗示这种方式难以为继,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遭遇了危机。
闻一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转变,因此很自觉地选取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菊花”形象,作为尚未成型的民族国家的象征:“镶着金边的绛色的鸡爪菊;/粉红色的碎瓣的绣球菊!/懒慵慵的江西腊哟;/倒挂着一饼蜂窠似的黄心,/仿佛是朵紫的向日葵呢。/长瓣抱心,密瓣平顶的菊花;/柔艳的尖瓣攒蕊的白菊/如同美人底蜷着的手爪,/拳心里攫着一撮儿金栗”(13)闻一多:《忆菊》,《闻一多全集》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页。。作为一种固定的文化符号,菊花极易与中华文化联系起来,既有梅兰竹菊的文化积淀,又与陶渊明等高洁之士的精神形象相连。但闻一多并不满足于这种抽象的精神类比,而是对菊花的形体和色彩进行精雕细琢。在对菊花“形体”不厌其烦的雕刻和书写中,闻一多潜在的精神动机可能是为了刻画唯一的“菊花”形象,以对心中唯一的祖国进行赋形。如此这般,在形质两个层面,菊花便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啊/自然美底总收成啊/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啊/东方的花,骚人逸士底花啊”,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热忱同样表现在康白情身上。动身前往美国留学的康白情,回望浩浩荡荡的黄浦江时,发出了如许感叹:“黄浦江呀!/我只看见黑的,青的,翠的,/我连声呗出几句/‘山川相缪,郁乎苍苍’!”(14)康白情:《少年中国》,李怡编:《中国新诗大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49-251页,在黄浦江畔的风景之中,康白情感受到披发行吟的屈原、为民高呼的杜甫、以苦为乐的苏轼等等古代诗人形象。因此,在描写黄浦江时,他并没有对其进行细节刻画,而是优先将眼前之景与独特的文化记忆关联,个体的表达意志让位于共同的文化记忆。积淀在自然风景之中的文化记忆和美学趣味,已如文化基因一样嵌入在风景之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将自然风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的诗人,多为留学异国的青年学生。他们诗歌中的风景,除了作为本民族文化想象的载体,还在与其他民族的比照之中,显示出丰富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如闻一多将高洁的菊花与异族的蔷薇等进行对照:“你不像这里的热欲的蔷薇,/那微贱的紫萝兰更比不上你。/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啊!四千年的华胄底名花呀!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15)闻一多:《忆菊》,《闻一多全集》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页。闻一多以此来显示菊花在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深厚积淀,表达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深厚忠诚的情绪。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天下时期的中国,华夏族的我者和他者的界限都是相对的,他者可以转化为我者,原本只是中原一支的华夏族,凭借自身所拥有的较高的文明力量,将周边的族群逐渐融合进来。而在近代中国,一个绝对的他者的出现,真正刺激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觉悟,许多留学生,置身于异邦的环境之中,于是有了近代国家的觉悟,也产生了国族的自我意识。”(16)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在天下时期的中国,“我”可以通过怀柔政策将“你”转化为内部的一员,所以内外差异和对立并不明显;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关系之中,“我”和“你”的差异则是绝对的。只有通过确立一个他者,才能建构起民族内部的一致性。对确定民族身份至关重要的,是民族认同的差异性和排他性原则。自然风景作为一种具有差异性的视觉化形象,具有直接的视觉刺激性和独特的文化属性,从而能够很轻松地被用来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
除了表现出排他性和差异性,作为民族象征的自然风景还常常表现出一种延续性,河流则常常成为标志性意象。河流具有地理的延续性,也具有伸向未来的潜在性。大江大河在民族之初,便沉淀在文化记忆之中,并且延伸到邈远的未来。另外,河流拥有生动的外观,其时而迟缓、时而沉潜、时而激越的流动状态,不断转弯迂回、而又一往无前向前奔流的气势,与一个饱经沧桑、历经劫难而不断再生的民族形象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河流形象与延续性、神圣性的民族国家形象相符,表明了一种拥有丰富历史渊源的正当性,也表明了一种无限延续的连续性和不朽的梦想。作为身处茫茫宇宙之内的人,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人(比如中国古人)拥有战胜生命的偶然性以获得不朽的远大理想。在神圣的时代,宗教等等思想形式,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将宿命转化为生命的连续性,暗示生命不朽的可能性。在现代世俗社会之中,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不朽的精神想象,这种想象将从传统家国天下秩序之中脱离而出的自我整合在有意义的连续体中,获得无限延续的不朽意味,大江大河正好为之提供了便捷而醒目的隐喻。
由于共同的地理环境和负载其上的文化记忆,自然风景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色彩。作为一种独异性的美学趣味,一种人格精神境界的象征,一种传承有自而具有延续至未来的文化想象,自然风景在现代民族的认同与建构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然之道之印证,其所赞美的日月、河山或草木也意不在风景之美学效果,而在于自然神性,或者在于带有自然神性负荷的生命、家国、故土。”(17)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61-163页。自然不仅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构,而且还提供了一套价值标准和感觉体系。新诗诗人们将眼前的自然景观与负载其中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记忆联系在一起,将破碎、无序的经验整合在一套价值感觉体系之中,将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期许联系在一起,使自己处于一个连续的体系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价值失序状态,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信心。
二、乡土风景与乌托邦想象
在20 世纪20 年代,留居海外的青年学生主要是在具有文化意味的自然风景之中,寻求文化中国的认同,表达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当资本主义侵入乡土中国时,在本土遭遇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的双重冲击的中国现代诗人,如何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格局之中想象一个乡土乌托邦,寄托美好的想象,构建现代国家的想象呢?
在古典农业社会,虽然远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已经成型(18)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3页。,但城市并没有对农业文明形成压力和挑战,乡村也没有在与城市的对照中,形成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化空间。虽然有山林与堂庙之别,但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并不明显,它们同属于一套宗法体系。古代诗人所作的山水田园诗,并非真实的农民生活图景,主要表现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与恬淡的生活情趣,并未将批判残酷的社会作为其主要目的。即便有表现农民艰难生活的诗歌,也主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表达对被剥削的农民的同情,寄予着讽谏君主施行王道的政治诉求。
乡土自然作为一种奇特景观被新诗表达,则大致上始于资本主义侵入乡土中国,是在20 世纪30 年代。很显然,资本强化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生活面貌,以及农人的生存现实,催生了一个新的诗歌群体——无产阶级诗人。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对人类的具体生活的改变是最大的,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精神在很深的程度上真正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9)[美]苏珊·桑塔格:《重新思考新的世界机制》,贝岭译,《天涯》1998年第5期。在这种视野之下,被资本主义侵入的自然进入到现代诗歌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乌托邦想象,象征和睦、平等、自由的乡土中国也进入到汉语新诗之中。
在资本主义入侵乡土中国时,有大量的新诗作品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毕奂午《春城》中有如下诗行:“过高高的城垣,到杂速的街头,见那花岗石,水泥各样的建筑物之间/……没有一棵苜蓿花!没有一棵金凤花!//一个鞋匠,/以麻缕维系其生命,摸索于人类之足底,向炎夏走去。”(20)毕奂午:《春城》,《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28页。这首诗描写棉麻农赶车进城售卖棉麻的情景。乡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之后,人的命运寄托在一丝微小的棉麻之上;在微末的个体与宏大的城市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了人物的卑微与无可奈何的艰辛命运。与毕奂午从农民命运的角度描写自然乡村之变不同,骆方则从景观的角度展现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林立在天空里的烟囱里的黑烟/冲散茅屋顶上晚炊底白烟,/来到两世界底中间!/我不能忍受/狂笑与哀号在耳中隆隆一默默地/咽下眼泪/站在两世界底中间”(21)骆方:《两个世界当中》,《水星》1934年10月10日第1期。。工业生产的黑烟与农舍的炊烟相对照,机器的轰鸣声与鸟鸣的和谐之声相对照,讽刺了城市对和谐优美的乡村景观的破坏。当然,这种讽刺和批判还停留在风景的表层,而较为深入地涉及城市对农村生活改变的,很可能是王亚平《农村的春天》一诗:“阡陌里,蝼蚁自由地挖掘穴洞/纵有妇孺驱着瘦牛春耕/但租税地繁苛/使他们不敢望秋日的收成”(22)王亚平:《农村的春天》,《王亚平诗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21页。。秋日的收成本是农民命之所系,繁重的税收则令他们命悬一线,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而不得不涌入城市谋求生计。城市和资本主义对乡土最为致命的改变,并不在于自然景观的破坏,而是破坏了小农经济的自足性,并且异化了农民的劳动。在小农经济时期,劳动维系着人的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劳动与生活的意义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为生活提供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而在资本主义侵入之后,劳动与生活之间的同一性被打破,劳动的主体不再具有主体性,被迫成为大机器工厂中的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受到资本主义的控制,农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根基。
如果说这还只是对个人境遇和局部景观的呈现,那么蒲风描写黄浦江的诗作则描绘了一幅当时中国整体的画面:“黄浦江——/你是中国最真切的写照!你是中国最压缩的形相!/在八十年前,在那古铜色的时光一你的神情/是多么安恬,舒畅:/整日夜挟着江南的轻风,/静静地溜过和平的上海滩上。/万里长城到底挡不住帝国主义的铁掌,/上海马上变成了红尘十丈的洋场……”(23)蒲风:《黄浦江》,《蒲风诗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7页。这首诗歌选取黄浦江畔之景,透视中国的状况。江南风情和渔舟唱晚的乡土中国形象,被资本主义奴役,成为尔虞我诈、阶级对立的殖民地。感到耻辱和愤怒的诗人呼唤祖国在反抗中崛起:“啊啊,黄浦江哟!/你被揉蹦压迫已经将近一世纪了!/难道你还愿意继续当奴隶,/还不打算起来跟人家算总账……”(24)蒲风:《黄浦江》,《蒲风诗选》,第7页。很显然,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奴役,同时也表达出重建平等自由的乡土中国的愿望。
上述诗歌还仅仅局限在资本与乡土之间的对立,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和表达则来自于诗人柳倩,他将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上升到文明批判的高度:“祖国哟,往昔你的光荣与伟大,/你荷锄归去,农人自由的和歌,/樵夫牧童之野语,日中集市的交易,/你富有人性的和平……/而今竟随白雾隐退/再寻不出世界的踪迹,/寻不出一切:一朵花,一株树”(25)柳倩:《雾》,《无花的春天》,中国诗歌社1937年,第18页。。柳倩把乡土与城市的对比,放置在中华民族文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抗中来表达,乡村的语义和内涵因此扩大到民族文化的层次。以和谐安详的乡土中国,控诉资本主义帝国。在二元对立之中,热爱和眷恋之情不可谓不强烈,而控诉不可谓不沉痛。在这种对农耕文明的想象里,乡土中国本身的愚昧、停滞等等均被忽略了;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原先处于精英阶层的启蒙让位给救亡图存的革命。
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之中,当大自然被人类的活动所破坏,诗人却依然向往着统一和谐的乡村世界。另一方面,在屈辱感的刺激之下,诗人蓄积了大量的革命能量,渴望建立一个改变了剥削关系,摆脱真实社会焦虑的地方,一个和睦平等的世界。这两种力量结合,则似乎很自然地产生了乡土乌托邦的想象。这类乌托邦想象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新诗之中。比如:“我歌赞秋天:/不是芙蓉满开,/不是菊花盛放,/也不是桂花争芳;/是久经风雨雷电的战斗树已结下了果实金黄/通过严冬,我们要战取新的宇宙,/哦,我们要战取新的宇宙!”(26)蒲风:《秋天的歌》,《摇篮歌》,诗歌出版社,1937年,第11页。蒲风描述了一个通过斗争而建立的新世界,再如:“春天不在那棵棵茂树;/春在我们的农村合作社,集体农场/春在我们的城市,首都;/春像愉快的太阳,天天渲染我们的国土全部/我们自己又是花,是小鸟,是大鹫/我们享受了戏院,轮船,飞艇,氢气球”(27)蒲风:《春天的歌》,《摇篮歌》,诗歌出版社,1937年,第4页。。蒲风在渴望建立新世界后,逻辑性地想象了春天的光明景象。这些诗作中充满了“新宇宙”“战争”“集体”“光明”等极具情感冲击力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含义本来极为模糊,即使一大推词语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当它们与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就有了神奇的力量,成为一种美好的未来想象,充满了改天换地的激情与号召力。
令建立在自然之上的乡土乌托邦具有强烈精神感召力的,除了上述心理作用之外,更为核心的是,他们想象的乡土乌托邦其实与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上文已经提及,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破坏,最为核心的是对劳动的异化,而这在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农人对自然的审美,首要的不是在高山流水、松柏荷菊中欣赏高洁的品性和伟岸的人格,而是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与劳动紧密联系。自然的晓月星辰、春花秋实提供了生产劳动的节律,以及劳有所获的欣喜、希望与满足。一旦劳动遭受异化之后,自然丰美的意象,便失去了审美意义。既然资本主义以异化劳动的方式异化了自然,那诗歌最为核心的应对方式,便是想象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这些诗人在想象乡土乌托邦时,在破除剥削关系的基础上重构自然的意义,试图在自然风景中寻找与落实自身的自然形象,通过劳动塑造和想象新的主体。“春在我们的农村合作社,集体农场/春在我们的城市,首都;/春象愉快的太阳,天天渲染我们的国土全部”(28)蒲风:《春天的歌》,第4页。——在一种集体劳动之中,创造丰厚的果实,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令生活和劳动重新获得同一性的意义。再如王亚平的如下诗句:“黄昏,西天染出赭色的云霞,/我们从暮霭里升上天涯,/追随着那姣好的月亮,/愉快地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就这样在黑夜中举起灯笼,/永远没有疲倦,畏怯……”(29)王亚平:《晨星》,《王亚平诗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72页。抒情主体以劳动者自居,在黑暗中启示光明,肩负起永恒,充满了强烈的进取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30)[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在这个以劳动为核心要素的乌托邦世界里,诗人不仅通过劳动创造着世界,也创造着确证自我的生活方式。这个以劳动为核心的乡土乌托邦世界,与古典文人所想象的回到黄金三世的世外桃花源迥然有别(31)孟二冬:《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也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比如何其芳等——的乌托邦想象大不一样:它充满了强烈的解放和斗争意识。它以历史的进步为目标,以未来的光明前景为指向,是一个包容了底层苦难者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运动之力和劳动之美的自由世界。
在这种乡土乌托邦想象里,原先被资本主义破坏的自然景观,具有了重新审美的可能性:“我们又回到乡村/原来都从这儿长大,/我们爱那每棵树,每茎草,/犬声吠走了黄昏,/晨鸡啼醒了太阳;/更爱那一张张忠实典型的脸,/泥腿,赤足,铁臂膀,/锄头镰把挥走流年,/风霜里终年奔忙。/你们才真是中华的主人呢,/驮起万种灾害,苦困,/把历史的生命继续,增长。/归来了,我们归来了”(32)王亚平:《回农村去》,《王亚平诗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51页。。这首诗塑造了一种在革命的洪流之中重新将自然乡村审美化的方法。农民不再是旧时代的农民,而是经过启蒙之后具有反抗意识的大众,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和阶级权利而奋起抗争。自然和乡村重新归于农民所有,宁静的乡村重新具有了审美的可能性。人欣赏自然风景,是从中感受到社会目的性,感受到社会劳动成果以及社会的前进,也就是前进的社会目的性成了合规律性的形式。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原先仅维持自身生计的劳动具有了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乡村在想象的空间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重新变成和谐的世界。
三、土地形象与民族国家建构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相较于此前的文化中国、乡土中国所遭遇的危机,民族国家遭遇的危机更为剧烈,甚至达到了灭族绝种的地步。在这一时期,个人与民族的关系更为紧密。很多诗人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家国认同之感。如何在风景书写之中建构起民族国家认同,亦表达个人情感,正是本节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抗战时期,有大量书写季候循环的诗歌。这点可以从标题中便可以得到直观的呈现,如艾青《春》《冬天的池沼》、彭燕郊《冬日》等等。蒋锡金写道:“像是山峰在一点一点披上新的光辉的/像是干涸的河床一点一点在涨满着的/象是枝头的嫩芽一点一点在萌发着的/是光明胜利真理,……/呵,中国的春天。”(33)蒋锡金:《中国的春天》,《文艺阵地》,1938年5月1日第1卷第2号。以春天欣欣向荣的情景象征个体生命的希望,以及民族的光明未来。这种“春天——光明”的象征图式,还停留在简单粗浅的层次,其他更为重要的诗人逐渐进入到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彭燕郊《冬日》有如下诗行:“萧瑟的冬日啊/风雪的冬日呵/使大地沉默/使雷雨初歇/使草木复归到泥土里去了/然而,末月的花朵/带着蜡色的容颜/终于/在行将呜咽的池边/绽放了/一年间最后的花瓣。”(34)彭燕郊:《冬日》,绿原、牛汉编:《白色花二十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3页。在冬日的严寒里,草木承受、抵抗寒冷,以更坚韧的姿态体现了承受与绽放的生命逻辑。这种以生命历程与季节循环相联系的抒情模式,在艾青那里发展到更为圆熟的阶段。艾青甚至具体到每一个月份,似乎更加具有恢弘的气势:“我是季候的忠实的使者/报告时序的运转与变化/奔忙在世界上/经过悠久的黑暗与寒冷的统治/为金色的阳光所护送/向初醒的大地飞奔……”(35)艾青:《春》,《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8页。春天孕育希望的喜悦,冬天降临不幸的死亡,生命处于持续运转之中。抒情者既游历于土地和人间之上,俯瞰着生命的生死荣枯和大道周行;又表现出对生命的深厚同情,介入到生命的困苦之中,促进生命的发展。在生命完成一轮周期之后,又开始新的传播希望之旅。在生命周期的持续循环之中,艾青呈现的是直线向前的时间观念,表现自然生命不可更改的发展进程。艾青等现代诗人诗歌中的季节循环,一方面继承了“死亡—新生”的象征意味;另一方面,又以自由、解放等丰富了季节循环的意义。他们作为一种推动力量,主动介入季节的变迁之中,表现出强烈的改造意识,令季节的更迭象征历史和社会的进步,预示着民族国家的新生。
除了体现生命运行的季节循环,空间的迁徙也被纳入民族国家新生的历程之中。穆旦写道:“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呵平原,/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着无数埋藏的年代/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36)穆旦:《赞美》,《文聚》1942年2月16日第1卷第1期。在祖国大地漫长的迁徙途中,像考古勘探家认领民族的苦难与记忆那样,与深埋在地层中的文化记忆紧密联系。邹荻帆则这样写道:“我们以沉重的脚步走向北方。/我们将以粗柄的脚趾/快乐而自由地行走在中国底每一条路上,/吻合着祖先们底足迹。/我们以红色的笔/勾写着明天的计划与行程,/在明天啊,/我们更将坚决勇敢地走向北方的北方。”(37)邹荻帆:《走向北方》,《尘土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 年,第52页。在由南方走向北方的征途中,由沦陷区朝向政治中心的运动中,邹荻帆获得了对祖国国土和文化记忆的深切感受。“北方的北方”作为一个并非实在处所的想象之地,提供了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激发出不竭的激情与行动力。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拥有辽远边界线的庞大空间,很难让人直观地去体验它。这些诗人在一步步的迁徙之中,认领土地上的文化记忆,获得崇高感和仪式感,去贴近想象中的祖国形象。
上述的时间运行和空间迁徙,还停留在个人与民族国家关系的表层。真正令个人与现代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受难意识。彭燕郊吟道:“我爱祖国/这被清洁的雪所掩盖的土地呵/从那仅有的溪涧踏过冰块的阻碍/我们横渡而过/祖国呵/我爱你/我们的艰苦的战斗……”(38)彭燕郊:《雪天》,绿原、牛汉编:《白色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9页。被雪花覆盖的洁净土地是国土的象征,却在异族的践踏之中变得肮脏不堪,使土地重新恢复洁白的艰苦行动,具有了解放民族的意义。在这方面,艾青的诗有更为突出的表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的苦难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漫长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39)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9页。以承受雪花的降落为受难的隐喻,依托于土地的死亡与复活的想象,艾青在土地的“死亡——复活”的永恒循环之中,把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暴力和苦难,转化为一种必然的光明与复活。而令“死亡——复活”的情感逻辑得以成立的,正是诗人的受难意识。“苦难的本质提供的是一种朝向真实情境和事件,从而超出私人主观性的世界构造,并以此作为个体的整个生存状况,隐秘地包容在灵魂的深层空间中,对苦难的感受是一种依赖并寻求意义的感受,涉及神或终极关怀的问题。”(40)王凌云:《词的伦理》,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第90-91页。基于共同的生存感受和生命境遇,苦难将个人、时代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基于强烈的意义感受或终极关怀,受难被放置在新生与救赎的意义链条之中获得意义。正如学者萌萌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天道自然观中,苦难只是天命向善,人命为之的一个从属的偶然的方面,它是应该而且可以在惩恶扬善除恶之中消除的。近代以来转向历史进化论,原来苦难可在周期轮回的太平盛世中得缓解,也就推向永无休止的未来期待中,为了将来的幸福,现在的苦难就变成了应该付出即奉献的自我享受了。而个人的受难则是这种中介。”(41)萌萌:《情绪与语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5页。在古典时代,天道具有最高的正当性,王朝的更迭是天道运行的结果。在天道轮回之中,苦难并不具备正面的意义,而是在秩序的好转中得以解脱,以证明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在现代进化论式的历史观中,历史变化的合法性在于是否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在一个向前进化的历史架构中,个人的挫折被转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个人的出路与国家民族的出路合而为一。受难被当作庄严而有意义的过程,具有了道德伦理意义,能够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民族国家的新生。
除了保留这种延续与进步的时间规律,土地还提供了一个阔大的空间,将大地上的人民联系起来。正如艾青在诗歌中表现的:“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生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42)艾青:《树》,《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土地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想象:在受难的大地上,各个阶级的人被统合在人民这一集体概念之下,形成了一个承受苦难与迎接新生的共同体。比如穆旦就很准确地说:“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的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43)穆旦:《赞美》,《文聚》1942年2月16日第1卷第1期。在大地上有着承受苦难而依然挺立的人民,他们正是历经劫难而依然灿然如花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正如本尼迪克特(Benedict Anderson)所言:“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4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第13页。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基础,便是对互不相识而被整合到一个共同体之内的国民的热爱。
综上所述,土地在现代诗歌中具有了丰富的意义。在时间上,它脱离了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时间,而与解放、进步、自由、人民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受难-新生的模式之中,拥有一种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在空间上,它确定了一个国土范围,将深藏在地层中的文化记忆、天降的苦难联系起来,把祖先与我们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承受苦难而迎接新生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
四、祖国的象征:从“山河”到“土地”
在古代中国,天下是华夏文化世界的空间想象山河则是标显其重要的地理形象。山河显示了华夏民族世代居住繁衍的空间含义,承载着丰富深厚的文化记忆和历史积淀,它比传统文化中与社稷相关联的“江山”更为宽广。杜甫在大历四年(769)清明,从眼下的洞庭春光中想到长安和整个神州大地,就以“汉主山河锦绣中”称赞祖国的大好山河。杜甫在山河之中认领的并非自己身处的唐朝,而是象征华夏的大汉。
在古代中国,高耸入云、直插云霄的高山,是空间中的多层次事物,充满了超越性的意义,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诗经·崧高》有言:“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45)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3页。高山大河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来自于天和受命于天的君主。就诗人与祖国的关系而言,山河所表征的人与祖国的关系,是拥有个体意识的臣民与君主的关系。诗人在对山河的热爱与崇拜之中寄托着对君主的忠贞与热忱。就时空观念而言,古典时代的中国人,以“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46)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57页。的方式观看宇宙与自然,所感知的世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时空结构,所追求的理想是在循环之中回归到原初的起点。这种观看方式也影响了古人的历史观。古人并不肯定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进步论(47)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0-33页。,而倡导回到原初起点的历史循环论,指向过去德位一致的黄金时代——尧舜盛世。在天命的授予下,在垂直形象的支撑下,山河便具有了超越一姓之社稷的意味,而体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观(48)敬文东:《皈依天下》,北京:天地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成为天下中国的象征。在古典时代,当国破家亡时、江山易代之时,诗人可以在山河之中,追忆家国之思,感发历史兴亡之叹。正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言,山河表现的是大于朝代更迭之外的“天下”含义。
与山河相比较,土地也具有神性。在以农耕安身立国的中国,土地在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古代神话中就多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大多将土地视为生命之起源、繁殖延续的象征。诚如耶律亚德所言:“凡是自然界的事物如土、石、树、水、阴影等所展现出来的神圣质性,无不被它聚拢在一起。土地这个宗教形式最根源的洞见是:丰富的神圣力量之大宝库——它是任何存在的‘根基’(foundation)。凡存在皆土上,它与万物相连带,它们连接成为更大的整体。”(49)Mircea Eliade,Pattern in Comparative Religion,Translated by Rosemary Sheed,New York,Sheed&Ward,Inc,1958,p.242.整体而言,土地作为造物与母亲形象,得到人们的依恋与崇拜。土地的如许含义都为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其替代“山河”成为祖国的象征则需要更丰富的内涵。朱自清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超越了社稷和民族,也统括了社稷和民族,是一个完整的意念,完整的理想,而且不但揭示了,简直代表着,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50)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可见,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完整理想的概念,一个超越性的抽象意念,一个要求绝对忠诚的形象。在这种要求之下,形成一种与祖国相适应的象征形象,土地则需要承载理想、抽象理念等诸多义涵。
在现代诗歌之中,祖国与土地开始了新的意义之旅。郭沫若以他发自肺腑的高音量咏叹道:“地球,我的母亲!/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51)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4页。郭沫若将地球推崇为祖国母亲,宣扬一种普泛的世界主义情怀,并不特指中华民族。这种空泛高蹈、缺乏实质的音调,难免令人心生疑窦。与郭沫若高亢的赞扬不同,戴望舒的爱国语调更为深沉厚重。他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这样写道:“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国!”(52)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全集》诗歌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在手掌抚摸土地的过程中,戴望舒将土地袖珍化和抽象化(53)[美]汉娜·艾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了,将土地塑造为一个为受难者提供精神庇护的祖国形象。在戴望舒这里,人与祖国的联系建基于对隐秘精神家园的渴求之中。对比郭沫若和戴望舒的诗歌,前者为祖国塑造的地球形象,因尺度过大而不能具体细化到民族国家;后者为祖国塑造的土地形象,因尺度过小尚不能负载起深沉厚重的民族感情。真正令土地的象征意义得以强化,以及让土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形象,则是抗战时期艾青的诗歌。
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这样写道:“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54)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诗选》,第68页。。他一经落笔,便以厚重的笔触刻画出土地与中国相连的画面。在一片广阔的视野内,在象征着苦难的雪花笼罩下,土地和中国获得了同一性,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共同体。随着雪花缓慢降落带来的视觉和心理效应,艾青也参与到土地和中国受难的过程之中。在对雪花的感受中,艾青以旁观者感受祖国遭受的暴力,更为深入的是在行走之中以承受姿态感受大地的宽广与深厚。这在其《旷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走过那些不平的田塍,/荒芜的池沼的边岸,/和褐色阴暗的山坡,/而雾啊——/灰白而混浊,/茫然而莫测,/它在我的前面/以一根比一根更暗淡的/电杆与电线,/向我展开了/无限的广阔与深邃……”(55)艾青:《旷野》,《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9页。作为一个渺小的行者,艾青在土地上艰难而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对每一寸土地、河流与道路的跋涉之中,领悟土地深刻的记忆、民族徘徊而多舛的命运。艾青塑造出回环往复、深沉厚重的音节形式,使多灾多难的土地国家形象得以显形;在这种嗓音和音质之中,艾青也将个体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承受沉重感之后,艾青也表达了渴望民族新生的信念。在《吹号者》中,艾青这样写道:“他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然而,他的手/却依然紧紧地握着那号角;/而太阳/使那号角射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像依然在响”(56)艾青:《吹号者》,《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在沉重而铿锵的音响之中,艾青塑造了一个这样的形象:站在土地尽头呼唤并引领民族新生的吹号者形象。诚如许纪霖所言:“近代的国家非古代的王朝,它是一个有着政治自主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不再是超越的天命、天道、天理,而是回归为人的自身意志和历史主体。”(57)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艾青笔下的国民承担着民族的苦难命运,又以坚强的意志为民族的新生而奋斗。
整体而言,在艾青的诗歌中,土地形成了一个时空结构形式,使个人与祖国形成一个共同体;在空间形式上,营造了一种空间纵深感,为个体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供拓展的空间;在时间维度上,土地形塑了一种线性直线时间(58)[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2页。。土地为承担当下苦难的个人提供了一个持续地必然来临的精神远景。
除了建基于命运共同感之外,现代民族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对民族精神品性的深刻认同。许纪霖说得很清楚:“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可以整合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族群、有着共享的文化和命运共同感的国族。”(59)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页。艾青便在土地之中领悟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性,例如《北方》:“我爱着悲哀的国土,/它的广大而贫瘠的土地/带给我们以淳朴的言语/与宽阔的姿态,/我相信这言语与姿态/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不会灭亡;/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60)艾青:《北方》,《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5页。。艾青感受到土地如许精神品格:宽广能普及万物,深厚才能承载万物。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循环,民族共同体的血缘乡土情感,种种因素汇聚而成的生命、自然架构,构成连绵一片的永恒连续体。土地不仅仅只是一个容纳生命的场所,更是一个象征道统秩序的天地境界;土地上的生命则是以土地为连接点、以天为朝向的共同体,而具有了生生不息的空间辽阔感以及时间的永恒感。这种土地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领悟了这种民族的精神根性之后,艾青对土地献出了最真挚的感情——一种诞生在最沉重的苦难之中最深沉的热爱,一种深深认同之后毫无保留的忠诚。
地理学家段义孚指出,现代国家是一个处于地方与帝国之间的形态,需要与之合适的情感认同尺度。(61)[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等译,第148-151页。艾青的诗歌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化土地为国土的过程,塑造了与现代民族中国相匹配的精神征象。在“家国天下”体系解体之后,以现代民族为中心的认同,成为个人获得国家认同的唯一合法性追求。这意味着必须找到一个唯一性和整全性的形象,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承载着民族生存资源、文化记忆和历史积淀的土地,相较于山河,既能提供当下的认同经验,又能整合过去的历史记忆,并投射出远方和未来的美好理想,更具有象征国家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抗战、民族受难的危亡时刻,个人难以自外于民族国家之外,而是将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命运跌宕的个体在土地之中寻求终极庇护,在土地所提供的精神形式之中容纳个体的生命与希望;另一方面,个体对土地表现出完全献身的忠诚,个体与土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正如朱自清所言:“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62)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在这种命运共同体之中,个体难以用兴亡循环的历史观,来旁观祖国的兴衰荣辱,而是对祖国保持着高度的忠诚与热爱,以受难促进土地的复活与新生,对光明的未来表达强烈的憧憬,以历史的承担者促进民族的新生。相较于受命于天的山河作为天下中国的象征,倾注了人类意志和力量的土地,成为了现代中国的象征。
五、结语
从富有文人情趣、具有文化意味的风景,到无产阶级诗人笔下的乡土风景,再到具有广阔情感凝聚力的土地形象,现代中国形象的生成与演变,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最后,承载着民族生存资料、文化记忆和历史积淀的土地;既能提供当下的认同经验,又能整合过去的历史记忆,并投射出未来美好理想的土地;能够将民族国家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个体生命提供支撑与庇护,又能承受苦难而获得新生的土地,最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这似乎成为了一个必然而唯一的选择。在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变奏中,或许可以从文学角度看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动态过程,认识到风景参与到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深层机制,逐渐厘清现代民族国家生成和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