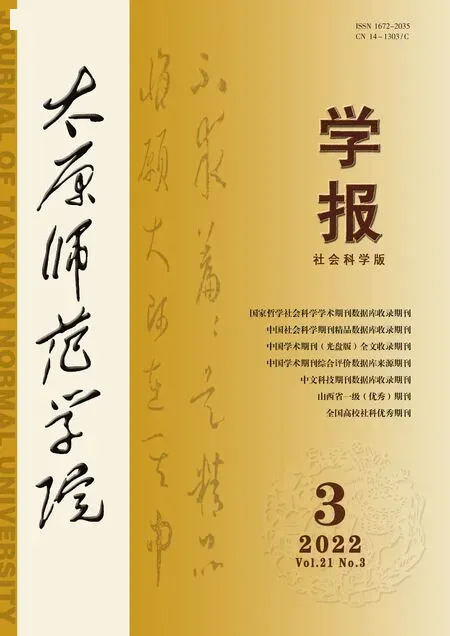夹缝中的个体写作
——以长篇小说《大刀记》1975年版为中心的考察
孙 涛
(1.山东省作家协会, 山东 济南 250002; 2.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长篇小说《大刀记》是已故山东籍作家郭澄清的代表作品,其最初的版本为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除此之外还有199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刀记》,2005年、201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大刀记》等多个版本。同时,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龙潭记》,这部小说实际为1975年版《大刀记》“开篇”的初稿,亦即作者最初构思《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的最初稿。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1975年版的《大刀记》被迫砍去原本第一部近一半的篇幅作为“开篇”放到了正文之前,这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作者的原意。[1]12直至“文革”结束后,这一初稿才得以以《龙潭记》为名出版了单行本,才让我们看到了《大刀记》第一部的真实面貌。相比于《龙潭记》与使用了作者初稿本的2005年版《大刀记》,1975年版的《大刀记》并没有完全呈现作者原本的创作意图,在艺术上也存在瑕疵,然而,正是由于1975年版的这种“修改”,我们得以清晰地窥探到在特殊年代个体写作与政治要求之间的摩擦,小说由“开篇”到“正文”呈现出一种无法弥合的“分裂”:首先,充满了浓郁鲁北农村风情的民间元素被逐渐淡化与消解,借由“民间”展开的“侠文化”叙事亦被迫中断;其次,以梁永生为代表的主要人物形象被迫做政治化拔高处理,原本立体多元的性格逐渐演变成了单一的“高大全”;再次,由开篇所铺设的深沉悲悯的抒情风格让位于对英雄人物与党的歌颂,审美意蕴由沉郁走向昂扬。
一、民间元素的淡化与消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何对“民间”进行定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陈思和的观点是:“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2]257按照这种解释,民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距离,这种距离让它获得了一套有别于政治言说的独立的话语体系。郭澄清是一位扎根于泥土的人民作家,对农村生活、风物的熟悉与偏爱,使他在写作《大刀记》的初始阶段不自觉地显示出向“民间”靠拢的趋势,保存在“开篇”中的章节在字里行间中均流溢着鲁北乡间的特有的风土人情、人伦事故以及精神底蕴,而伴随着“正文”的展开,这些鲜活而生动的民间元素也随之逐渐地淡化与消隐。
例如,“开篇”第一章的题名即为“闹元宵”。元宵节为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以元宵节入笔,不仅拉近了与民间的距离,还带出了鲁北农村特有的地域感与文化感。试看:
梁宝成把那关得严严的庙门一敞,社火队摆成一溜长蛇阵,锣鼓喧天地开进街来。前头用一队狮开路,各种角色都踩着锣鼓点儿,走着俏步儿,浩浩荡荡,鱼贯而行。引得看热闹儿的观众,可街满道,摩肩接踵,挤挤擦擦,水泄不通。
饰演散灯老人的常明义,走在社火队的最前头。
他左手提溜着浅筐,筐里盛着用碎棉籽拌成的油火;右手拿一把铁铲,每走两步就把一铲油火放在路心。一条火龙紧随其后,慢慢腾腾向前爬行。[3]7-8
诸如摆成长蛇一般的社火队、散灯老人铲油火在前面引路等生动的民俗,即是鲁北农村一带庆祝元宵节的独特传统,被作者敏锐捕捉并记录了下来。这些情节不带有政治色彩,仅是单纯地将农村的民间元素一一呈现出来,字里行间充溢着鲜活的民间气息。类似的例子还有“云城内外”中写到的城隍庙中卖艺、说书的场面,“大闹黄家镇”中对黄家镇庙会的展示,“新婚之日”中对宁安寨送枣和栗子的婚俗,作者将很多民间元素穿插在作品的叙述当中,呈现出了一种相当具体可感的地域氛围与文化背景,为我们借由文本回到那个特定的时代与场地获得了直接的便利与可能。相比之下,小说正文中的这种民间元素被明显淡化与削弱,尽管也保留了少量的渗透(如第九章“打集”写到黄家镇庙会),但后者显然不是单纯地对民间进行展示,而是混杂了特殊时代的政治话语,小说的正文中,民间变得不再单纯,而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民间元素的魅力也消失殆尽。试比较:
在这个庙会上,有卖猴的,卖马的,卖熊的,卖狗的,卖蛇的,卖虎的,也有卖杂技、魔术、样片、马戏、木偶戏用的道具,还有卖技术的——你要花上钱,认个过门师,他就当场教给你几手。就连杂技行当请师父,招徒弟,雇脚色,找事由儿,也都可以在这里成交合同。……他们这些人,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在街里街外挤挤蹭蹭,串来串去。(《大闹黄家镇》)[3]129-130
这些密密麻麻的游人,南来北往,你挤我撞。他们当中,有穿袍戴帽拉着文明棍儿的富人,也有光膀露臂泥腿泥脚的穷人;有歪戴着帽、趿拉着鞋、提溜着画眉笼子的二流子,也有荷肩负重、汗流浃背的劳动者。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横鼻子竖眼的鬼子和汉奸们。(《打集》)[3]885
援引自“开篇”与“正文”的两段内容都是写黄家镇庙会,但是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的重点在于展示庙会中的五行八作,字里行间透出了一股子民间市镇的热闹与熙攘;后者则显然更偏重于划分游客的“阶级属性”,似乎随时有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即将上演。可见,面对同样的场景,即使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其着眼点也有着显著的不同,究其原因,在于个体写作被强加了政治性的要求,让作者不得不离开原本的写作路径,走向一条更加符合当时意识形态要求的写作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当民间元素渐趋消隐,不仅那些饱含地域色彩的风土故事无处彰显,原本借由民间土壤展开的“侠文化”叙事亦被迫中断。从宽泛的层面讲,“侠文化”是一种勇武剽悍、粗犷豪放、多情重义的价值取向,它深深植根于民间的土壤,是民间社会理想人格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大刀记》的开篇,作者将这种“侠文化”渗透其中,并借由小说中的诸多形象反映了出来。例如,梁永生的继父门书海便是一个类似于“大刀王五”的人物,他传授梁永生武艺,给永生讲“大刀史”和义和团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将一种崇侠尚武的“种子”种在了梁永生身上。正是有了这种对“侠文化”的继承,梁永生才得以在“大闹黄家镇”时凭一己之力救出了翠花母女,才能够“夜进龙潭”时烧了贾家的粮仓与草垛,尤其是夜袭龙潭街的惊险举动,连门大爷都觉得“有点冒失”,但也恰恰是这种“冒失”,反而能从一个侧面凸显梁永生那种为道义而不计得失的“侠肝义胆”,从这个角度说,称他为侠士已经丝毫不为过了。阅读1975年版《大刀记》,我们很容易发现从开篇到第九、第十章,梁永生的这种侠义气息在不断增强与加固,如果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类似于梁山好汉一样的起义者,带领大家揭竿而起,走向反抗的道路。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第十章之后,这种“侠”的形象反而渐渐淡化了,从“水灾”一章之后,梁永生因生活的困境被迫卖儿,又被迫远走他乡,甚至一度想要去投靠杨翠花家有钱的表亲,这些举动无疑已经与“侠”的形象相去甚远。显然,1975年版的《大刀记》反映出作者在有意识地压抑借由民间而来的“侠文化”的展开,这从1985年版的《龙潭记》也能得到印证。《龙潭记》中,梁永生“怒打日本兵”,梁志勇“打虎遇险”这些后续章节都很明显呈现出一种“侠”的味道,但是这些无一例外在1975年版《大刀记》中被删除了,而当《大刀记》进入正文部分,梁永生又一变成为了具有极高政治觉悟的“党的领导干部”。
其实,民间元素与革命叙事并不是天然的泾渭分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完全可以进行充分的融合,从而共同完成艺术的建构。如“十七年”时期的《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这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都是民间元素与革命叙事融合的经典范例。可惜,在当时艺术理论的干预下,任何与“三突出”相悖或无关的艺术元素被强制性取消,在这样的外力作用下,《大刀记》开篇中原本生机勃勃的民间元素自然免不了被消解的命运,承载着民间理想的侠文化叙事亦被迫中断。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却随着1975年《大刀记》的出版被永远定格在了7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充满了无奈与遗憾。
二、人物形象的政治化拔高
作为一部在“文革”期间诞生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免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影响下,人物形象也被强行进行了政治化的拔高处理。通过对比“开篇”与“正文”的人物塑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方延彬、梁永生、梁志勇乃至杨翠花、王锁柱、黄二愣、魏大叔的形象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高大全”,而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还是梁永生——如果说“开篇”中,他尚是一个有弱点、有担忧、有小我的“凡人”,那么到了正文,他就已然“脱胎换骨”,一跃成为了一个毫无弱点、充满自信、无所畏惧、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无产阶级英雄”。梁永生的变化无疑具有典型意义,这恰恰显示出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放弃了自己对形象的个性化把握,转而自觉地接受当时主流文学写作的影响,按照集体主义原则、组织纪律性以及树立崇高理想目标等要求,剔除了个体英雄身上的“平民气”和“草莽气”,进而塑造出了更加神圣高大的“卡里斯马”式的英雄。且看正文第一章对梁永生的描写:
正在这时,院门口走进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便衣,一条宽宽的皮裤扎在褂子外头,前腰带上斜插着一支匣子枪,系在刀柄上的红绸倒垂在肩峰上;由于他走得又急又快,身旁带着一股小风,那红绸布就像被风吹动着的火苗一般,正在轻轻摆动。太阳泻下万道金光,映在他的身上;他身上的土沙细末儿,闪出耀眼的光亮。这一切,和他那红光闪闪、笑纹四射、春风浮动的面容搭配起来,更显得威武、英俊了。[3]256-257
“身材魁梧”“红绸布就像被风吹动着的火苗一般”“太阳泻下万道金光,映在他的身上”“显得威武、英俊了”,这些“神化”的修辞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神光四射、通体透亮的崇高形象,这个崇高的形象即是“三突出”原则中所强调的“主要英雄人物”,他一心一意为党为民,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并由此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见,从正文一开始,梁永生便完成了由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向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身份转变,至于开篇中他所显示出的那种侠气自然不再存在,就连原本对妻儿的牵挂、对生活透出的无奈也被统统视为弱点和缺点而加以净化,原本复杂的人性走向了单一的“高大全”。
实事求是地讲,对比“开篇”,正文中的梁永生形象亦有一定的延续,诸如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贫苦大众的友爱、对战友的关爱等等,这些一贯的特质可以显示出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过程中构思的前后统一。然而,又不得不承认,区别也是显著的,最根本的一点,即是正文部分重新赋予了梁永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身份”——党的领导干部,而正因这种身份的获取与确认,梁永生告别了原本普通单一的农民形象,成为了大刀队的“灵魂人物”与“主心骨”。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大刀记》在正文章节呈现出一种频频出现不断重复的情节链:县委书记(方延彬)向梁永生传达党的政策—梁永生向支委会成员传达党的政策—梁永生和战士群众们贯彻党的政策。作为一个关键人物,梁永生在这个情节链中既是上级政策的接收者,同时也是政策的传达者与贯彻者,由此,他便成为了党联系群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桥梁与纽带,也正是因有这样的人物的存在,党的政策、意志方能够在广大群众中播撒,进而得到贯彻和实施。
应当认识到,当梁永生获取了一种“政治上”的身份,这种提升并不单纯是表面化的、身份性的,质言之,在梁永生由一个农民向党的领导干部转换的过程中,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变化还不是身份上的简单置换,而是经由身份的转变获得的一整套成熟的“政治话语”,正是有了对这套话语的掌握,使梁永生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因时因地用“革命的道理”来启发群众、指导工作,并取得无往而不胜的良好效果。当大刀队遭遇挫折的时候,面对秦海城的悲观情绪,他会说:“打仗嘛,就有胜有败。不怕百战失利,就怕灰心丧气。秦大哥,你只管放心,咱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士气是扑不灭的火焰,截不断的泉源,是什么样的敌人也打不垮的。”[3]326面对战友的牺牲,他会劝慰高大婶:“大婶,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树青同志为了抗日牺牲了性命,他是我们的好榜样,他是人民的好儿子,他是共产党的好党员,毛主席的好战士。”[3]351为了更好地激励大刀队战士们的士气,他会说:“那好,锁柱啊,你要知道,我们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3]379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境况、无论是对家人、乡亲、战友或者敌人,梁永生总是会适时且毫无障碍地进行一番“政治演说”,这套政治演说从正文的开始一直延续到小说的最后,也正是在这些有极强政治意味的“大道理”的引领下,梁永生带领鲁北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取得了对日本军队的胜利。同时,也正是由于对这套熟练的政治话语的掌握,让梁永生拉开了他与普通群众、普通战士的距离,真正成为了革命战争中的指明灯,随着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梁永生领导大刀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标示的即是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军事战略的唯一正确性。
除了梁永生之外,《大刀记》中还有很多人物形象都进行了这种政治化的拔高处理。例如,梁永生的儿子梁志勇,革命小战士王锁柱、黄二愣等。与梁永生的彻头彻尾的“高大全”不同,这些人物仍旧存在着相对的不足:一方面,他们往往只是“分享”了梁永生形象特点的某一个方面并加以突出,例如梁志勇的“勇敢”、王锁柱的“聪明”、黄二愣的“进取”,这些设定鲜明体现着“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着意安排。另一方面,更有意味的是,当梁永生被塑造成“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后,其完善的人格和形象势必不允许他在工作中出现半点失误,于是,一些在抗战中出现的曲折与错误便自然由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来承担,例如梁志勇偶尔脱离群众、王锁柱因工作导致对学习文化知识的放松、黄二愣时常表现出的冲动与莽撞等等,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当然,也恰恰是由于次要人物的这些失误和不足,才使梁永生“有机会”及时发现他们的错误并扭转,以此来完成其引路人兼力挽狂澜者的身份确认。由此,其完善的无产阶级领导者形象,便借着这些途径更好地“烘托”了出来。
三、审美意蕴由沉郁到昂扬
考察1975年版《大刀记》开篇与正文的差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即作品前后在抒情风格与审美意蕴上的“断裂”。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之情,不是抒无产阶级之情,就是抒资产阶级之情,超然于阶级之外的所谓‘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61也就是说,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文学作品只能突出而鲜明地表达对无产阶级英雄的阶级之爱与对资产阶级敌人的阶级之恨这两种情感取向,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这种创作观念的引导之下,我们看到《大刀记》由开篇所铺设的一种深沉悲悯的抒情风格在渐渐消隐,取而代之的则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以及对英雄人物与党的歌颂,审美意蕴也随之由沉郁走向昂扬。
第一个明显的变化,即是受难、死亡元素的大幅度减少。在开篇保留的篇目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有意识地营造一种贫苦大众在旧社会生活的惨淡图景。这里有地主的盘剥、衙门的欺压、军阀的混战,也有水旱天灾、食不果腹、卖儿鬻女,天灾与人祸接踵而来,让苦难的老百姓挣扎偷生在贫困与死亡线上。为了增加这种“苦难”感,作者还接连不断地在叙事中嵌入死亡的元素。如梁宝成夫妇、常明义大叔、拾荒的赵奶奶、雒大叔、杨翠花的母亲、雒大娘和门书海……再加上在叙事过程中经由回忆带出的祖辈父辈们的死亡,真可谓是愁云惨淡、凄惶无比。然而,当进入正文部分,这些灾难与死亡的元素便被有意识地削弱,除了在正文第二章中简单提到了大刀队指导员徐志武、队长高树青的牺牲之外,在长达八十万字的正文中便再也没有涉及任何正面人物的死亡,即使在最后与石黑决战的激烈战斗中,亦不过只是伤了一两名,而大家还要万分悲痛一番。可见,开篇与正文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如果说前者是作者站在个人或说是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饱含深情地书写旧社会的生活绝境与死亡深渊,那么后者便是作者放弃了个体的悲悯抒情,转而按照新的创作要求全力描绘无比幸福与光明的康庄大道,其内在的逻辑是: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便再也不用经受苦难,再也不用面对家人、亲友的死亡,旧日的悲惨已经过去,幸福的日子即将到临。
同时,这种风格的转向还从景物特写的变化中体现出来。阅读《大刀记》,可以看到无论是开篇还是正文,每一章都有着为数不少的景物特写,这些描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它们更大的作用在于,借由景物描写融入抒情的风格,继而传达出鲜明的价值导向。例如,同样是写夜,开篇中是这样描绘的:“夜,黑乎乎,静悄悄。阴沉沉的漫空里,网着重重叠叠、黑白间杂的云片。在这些云片后头,又有一些更沉重、更可怕的黑云头扑上来。”[3]32而到了正文部分,则是:“天空中的云层,裂开了一道道的缝隙,继而又分成了大大小小许多的云块子。几颗星星从阴云的缝隙间钻出来,像那调皮孩子的眼睛似的,一眨一眨地瞧着夜行人。”[3]319第一段选自开篇的第一章“闹元宵”,彼时尽管正值佳节,大家伙儿刚闹完了社火,但是由于“灵堂栽赃”事件,让这节日的夜晚笼罩着一层死亡的阴云,暗示了梁宝成一家悲惨的命运。而第二段选自正文第二章“夜行人”,梁永生受命返回宁安寨,尽管这时的背景是大刀队遭受了损失,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然而伴随着梁永生的归来,一抹光明的未来透过几颗星星“调皮的眼睛”暗示了出来。实际上,“开篇”与“正文”两个部分的景物描写从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经常会出现大雪、阴雨、黑夜、黄昏、荒野等意象,而后者则清一色的太阳、春天、东风这些明丽的景物。正如有论者指出:“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作指导,……学会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眼光观察、表现自然景物,描绘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祖国日新月异的风貌和山河的壮美,抒发工农兵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豪情壮志,铲除旧时代牧歌式的气氛和情调。”[5]42可见,在政治对文艺的严格约束下,不仅连承载作者泪水的凄风苦雨不能再有,就连开篇中那些异常动人温馨的家庭和乐的图景也成为了“旧时代牧歌式的气氛和情调”,被毫无异议地排除在外了。
学者李杨曾经指出,1942年到1976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的发展过程。“生活被空前地象征化了。每个个人都是一个符码,都是抽象理念的感性体现,他必须通过抽象的国家归属、民族归属、阶级归属等等外在的理念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6]258不容否认,《大刀记》正文部分给读者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象征性的生活:无论是巷战奇观还是狱中涉险,无论是巧夺黄家镇还是夜战水泊洼,这些本应险象环生、充满你死我活的战斗无一例外地被镀上了一层“胜利的光辉”,从头到尾均洋溢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情调,给读者的印象是在梁永生领导的大刀队面前,敌人和伪军仿佛毫无招架之力,他们只能乖乖地被正义的一方玩弄于鼓掌之间,他们的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可见,在一种强行的写作原则约束之下,本应好好展现的战争的艰难、焦灼、困境以及由此而带出的那种悲壮、豪迈的审美特质被阻断,取而代之的是屏蔽了惨烈与曲折、一种彻头彻尾的大胜利与大欢喜。《大刀记》结尾,梁永生的大刀队顺利完成了对石黑的全歼,继而又投入了新的解放战争的洪流当中,尽管小说并没有继续写下去,但是正是在这种昂扬的整体风格的牵引下,那更加美好、光辉的共产主义的胜利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总之,透过1975年版《大刀记》,我们可以看出两种近乎异质的文本被生硬地“拼”在了一起,从开篇到正文,那种从生活经验中提炼的鲜活的民间元素、充满人性的人物形象以及深沉悲悯的抒情和审美风格被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与创作导向所遮蔽,它重新开启了一种去个人化的写作路向,而后者取消掉民间元素的象征式的生活、高大全式的人物以及昂扬的审美取向,或许才更加契合了那个年代的创作要求与审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