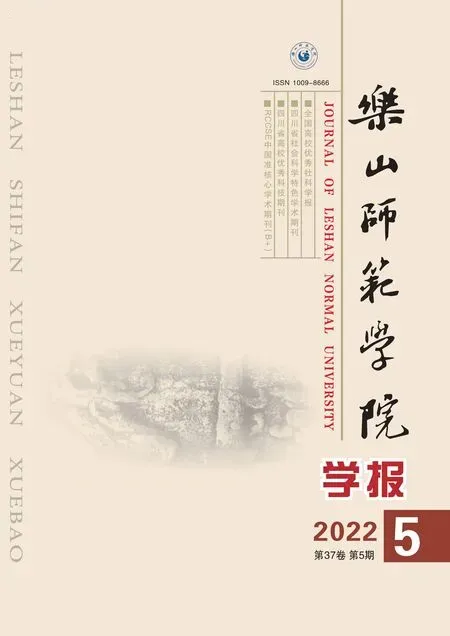大江同一味,千里共清甘
——苏轼黄州时期作品中“江”的家园建构
雍佳丽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4)
嘉祐元年(1056)苏轼第一次离开眉山,“与弟辙随父洵赴京师”[1]42,嘉祐六年(1061),“辞父京师赴凤翔任”[1]96,宦海沉浮就此开始。虽生于四川,然纵观苏轼一生,因党争等原因颠沛流离,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长江一线便是苏轼多次经过的地区。在苏轼的诗歌中,“江”出现的频率很高,是其作品中的重要意象,“江”在地理空间方面是其家乡西蜀州的重要标志,在文学景观方面又映着苏轼性格中奔腾旷达,又与苏轼旅途为伴,地理意象与文学景观结合成苏轼偏爱江的重要缘由。除家乡外,苏轼在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长江,尤其是黄州时期,在黄州,苏轼再度见到发源自家乡的江水,逐客之感与游子之念结合,成就了这一时期作品中“江”带有精神家园性质的独特意蕴,苏轼也由此经历了从精神家园失落到追寻到最后重构的过程。
一、有田不归如江水:苏轼作品中黄州时期“江”的主题变化
“一生与宰相无缘,到处有西湖作伴”[2]是后人对于苏轼一生仕途的概括。苏轼仕途坎坷,其贬谪之处也大多有水系的存在。除开杭州、扬州、惠州的“西湖”外,长江以绵延数千里的壮阔,成为苏轼作品中重要的地理意象。
苏轼自幼长于、学于蜀州眉山,治平三年(1066),苏轼与弟送苏洵灵柩回归眉山,又居丧三年,自此再未回乡。但关于岷峨的记忆伴随苏轼一生。明徐霞客之前,人们以岷江为“导江”,《水经注·江水》中便记载:“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3]苏轼以岷江为长江源头,在杭州经过金山寺时,苏轼写下“我家江水初发源”[4]607即是如此。对于岷江的深刻印象,体现在于他乡对岷江的多次回忆,在贬谪黄州之前,苏轼的作品中便处处是“江”。
首先是北上途中,嘉祐四年十月,苏轼丁母忧后出乡关,离蜀返京正是沿着水路东下,“苏轼兄弟侍父洵离眉州,赴京师”[1]65,舟行长江三人唱和,结集《南行前集》。由于以水路为主,其诗几乎首首有“江”。这一阶段作品中的“江”基本以风景描写为主,通常与山、雨自然界意象等搭配,作为诗人眼前的景象直观入诗,如:“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4]5,“山前江水流浩浩”[4]35。但无论眼前江水是何种形态,都未承载诗人过多感情,白描大于情志的抒发。其原因有二:一是乡愁形成的原因。由于空间阻隔,人们难以由异地回到家乡;由于时间流逝,人们即使回到家乡,也无法由现实的空间回到记忆中的空间。[5]此时父弟一路同行,尚未有离家之苦,且去乡不久,构成乡愁的两个地理空间(家乡与目前所在地)没有明显分离,时间流逝导致的物非人非也未形成。二是此时三苏已声名乍起,北上补录官职,前程光明而无身世之悲。
其次,在熙宁四年,苏轼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以离京暂避祸告终:
《杭州召还乞郡状》叙遭谢景温诬奏后,云“臣缘此惧祸乞出”。《墓志铭》谓“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乃杭州通判。[1]200
离京赴杭之际,苏轼至颍州谒见欧阳修,望着并不出自长江的颍水,此时已有“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的桑梓之念。首次明确出现“江”与“家乡”的关系是作于杭州的《游金山寺》:“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4]607此处苏轼对江神起誓,留存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处境的不同使得苏轼面对江水的视角开始转换:从欣赏风景到寄托乡思。前朝岑参便有诗云“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6],正是凭借眼前之水而思念故乡之川流。有学者指出:“地名不是单纯的地名,而是人的生命记忆中的情感符号。”[7]苏轼眼前的颍水与心中的长江已经有所重合。对于苏轼而言,此次外任并不意味着绝境,往后仍可有所作为。且杭州富庶,此时精神家园还未建构也没有建构的必要,其雏形依附于对家乡的地理想象上。此外,苏轼曾多次经过润州,途中有“白浪翻空动浮玉”[4]1190,可见地理空间中的长江也未曾与苏轼阔别。
最后,贬谪黄州的四年中,长江在苏轼作品中承载的内涵达到了一新的阶段。“乌台诗案”后,苏轼九死一生被贬黄州亦与长江为伴,由于经历生死后贬谪心态的变化、居住之处与长江徒步即可到达的距离,对江思索人生成为了苏轼重要的自我救赎方式。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苏轼频繁提到长江意象,多维度地描写“江城”,关注与江相关的风、月、梅、柳等意象。与《南行前集》中和江关联的自然意象不同的是,黄州时期的“江”不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承担了更为复杂的感情,诸如“赤壁”之类的人文意象在苏轼诗文中亦有所深意。长江在此成了上天赐予苏轼的自然寄托,贬谪黄州对苏轼意味着政治生涯停止,家乡、京城、杭州都成了不可触之地。现代心理学便认为“对于成年人,当他们经济拮据或者被否定时,更易产生乡愁”[8],存在感失落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追寻归属感。于是苏轼精神家园的建构开始依“江”而生,他在“江”这一意象中延伸出了许多个人感情,对原乡的呼应,对亲友的思念,对天地人生的思考,对自我思想的超越。
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所闻出塞曲亦是“半杂江声作悲健”[4]2519。要言之,在苏轼的作品中,“江”有着多重意蕴,是衬托人生短暂的存在,也有作为自然包罗万象的一面,是苏轼精神家园的最佳依托。苏轼对黄州之江的特殊感觉,不仅与其贬谪经历、思想观相关,还与黄州和故乡岷峨地理条件的同异相关。
二、归去来兮:黄州之江对苏轼心态及作品的地理影响
黄州远离政治中心,被贬于此的苏轼生存艰难,内心忧惧交布,经历生死而面临未知的将来,苏轼在这一时期对黄州风土的描写十分复杂,每觉不堪之际,又能释入旷达: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其一》[9]5270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消息。《与王元直二首 其一》[9]5943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4]2150
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黄州上文潞公书》[9]5203
对于黄州风土“僻陋”“真在井底”“稍可安”的看法,也是苏轼心理状况的一种折射。前往黄州途中,苏轼以放臣自居,如:“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4]2113;“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4]2115。直至抵达黄州,依旧是“逐客不妨员外置”[4]2150,只是多了分自嘲宽解之意。
对现实的怀疑与虚无感使得苏轼开始在黄州为自己建构精神家园。写于黄州时期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比起赞誉宇文柔奴,更像是对自己的劝慰。离黄之际,苏轼似已对这个象征着屈辱的地方有了不舍:“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4]2519诗人自述的“安土忘怀”绝不仅仅是自我麻醉,而是象征着在无期的贬谪岁月中,苏轼自觉地将黄州视为终老之地。在这种视角下,黄州的江才最大地寄托了苏轼对故乡的思念与对人生的思索。
长江与汉水交汇于黄州,在异地通过与相似景物的想象回归原乡,是构建精神家园的一个途径,“童年时代的经历为原乡想象提供了基础的材料,这些往事在回忆与想象的叠加态中得到重构,因此创建出一个满足个体原乡想象的诗意空间”[10],即是如此,四川以西是海拔接近六千米的岷山,作为岷江上游的都江堰更是有三千余米的海拔,岷江因为巨大的地势落差而有了其他水流而不能比拟的奔腾之感。江水携着高原消融的冰雪,生长于眉山的苏轼处于岷江中上游见惯了这一景象。到了黄州,诗人仍旧怀念着岷峨的江水,并不自觉地在面对黄州之江水时想到它: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记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11]6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11]79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与范子丰书》[9]5424
长江自西而奔至黄州,进入更为温热的中游,江水来源早已由冰雪融水变成雨水,苏轼在黄州见到的江水因为春暖而绿藻滋长,在阳光折射下有着岷江“蒲萄深碧”的颜色,但其“岷峨雪浪”实际上只是诗人的想象纵使江水拍岸“卷起千堆雪”,也只是形似,虽然这一时期的诗有提到“日上山融雪涨江”[4]2317,但其雪已非峨眉山顶雪。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来看,岷江之水正象征着苏轼的“生命原乡”“生活原乡”“精神原乡”[12],少年记忆与眼前景象叠加呼应,成为精神家园的建构材料,“岷峨雪浪”这种地理基因在黄州被“江”元素诱发出来。生命中第一次大落使得黄州于他而言比所谓异乡更为落寞,故面对江汉之水时,诗人不自觉地将“岷江”象征着原乡,在“岷江”这个空间里,“乌台诗案”的苦难及亲人生离死别都不存在,这一空间使其情感有了托付。对黄州之江的似曾相识感既是上天赐予的慰藉,也是苏轼在困顿之中自觉的举措,故苏轼作诗给远在他乡的苏辙时,亦选择了“江”这一地理意象:“犹喜大江同一味,故应千里共清甘。”[4]2330正如同几年前在中秋月夜而无法团圆写下的“千里共婵娟”,江水之味不变,兄弟二人共饮长江水也就等同于不曾分别。
以黄州之江弥补现在与过去的时空分裂,将建构精神家园所需的材料具象化,是苏轼心灵自卫的选择。前往黄州途中,苏轼已规划自处之道:“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举。”[4]2126接近死亡后,在迁谪中更珍惜生,当黄州没有想象中荒凉时,苏轼便更自发地接受现实。经历“乌台诗案”,苏轼已处于“亲友至于绝交”[9]2590的状态,黄州地僻,能与苏轼书信交往的亲友更是难得。在这些书简中,或是安慰亲友,或是剖白自己,苏轼总流露出以黄州为终老之地的念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与范子丰八首 其八》[9]5424
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无所归,必老于此。《黄州上文潞公书》[9]5203
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四首 其二》[9]6285
此外,对黄州之江的特殊感觉还与距离有关。前面已提到苏轼于元丰四年迁居的临皋亭与长江极近,时有大江入户之感:
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黄泥坂词》[4]5576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寒食雨二首·其二》[4]2343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其五》[4]2445
我来黄冈下,欹枕江流碧。《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4]2384
距离之近使苏轼自觉将其当作生活的一部分,黄州之江在此承载着自然景观、寄托苏轼所思的双重功能,从这方面看,黄州之江较岷江对苏轼更为特别。从黄州之江引发的乡土意识萌芽到“何必归乡”再到“本是黄州人”,原乡与流寓之地的矛盾消解,统一在苏轼思想中,由此,苏轼以黄州之江建构的精神家园基本完成,故去黄移汝之际,苏轼再度陷入根若飘蓬的虚无感:“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11]114
总之,由于黄州之江与岷江的相似、与亲友共饮一江水的心理安慰,苏轼因其逐臣的身份,结合其欲为旷达的人生性格,纵使黄州离故乡甚远,苏轼依旧通过为自己建构精神家园的方式“安于此地”。
三、江海寄馀生:以“江”重建精神家园
除了对黄州之江的原乡呼应外,“江”所构建的精神家园在苏轼思想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异乡不得意时既不能回乡,就只能就地取材构建精神家园,除直观的地理空间外,个人的学识与观念亦是关键。
吾生如寄,苏轼以释道自宽,在黄州时期之外的作品中,便充斥着佛教视角下的“江”之隐喻,尤其是在宽慰友人时,“江海”之譬喻更成了彼此的暗语:
我生本是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送吕希道和知州》[4]512
老去心灰不复然,一麾江海意方坚。《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4]3698
在佛经中,大部分将智慧譬喻成“江海”,以示其不可限量,《度世品经卷第四》即认为“心如江海,不可限量,顺诸佛法无极道慧”[13]。在地理学、心理学与佛教的三重视角下,“江”作为包容一切的地理意象,由意识折射到现实,苏轼在黄州时期时也便有了托生江海之感,从认识自己的渺小到以身融入于江海之中,诗有“今朝横江来,一苇寄衰朽”[4]2190,词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11]96,而在离开黄州的路途上,更有“他年一叶泝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4]2519的不舍,所谓“一苇渡江”“一叶泝江”正是佛教中达摩祖师的传说,而以上是以一苇或是扁舟一叶为载体,将自己融入浑茫之中,这是失意下的选择,也是以江托生的体现。作于此时的《水调歌头·快哉亭作》则于快意中融入哲理,其核心思想是苏轼理想的人生境界:“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11]107而在此拥有“浩然气”的形象则是“白头翁”,无论其是人是禽,苏轼都以其在江浪中“掀舞一叶”的姿态象征着自己所向往的逍遥与自由。总之,无论是失意或快意,江洗涤一切,容纳万物的功能都被需要,正是苏轼精神家园的最佳选址。
当苏轼以寻求出路的心态自处时,黄州之江也以地理与文化两个维度的广阔接纳了他,“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9]8135便是诗人面对黄州之江的感受。《春江花月夜》之“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14]已揭示了长江作为典型的永恒形象,与之相比的是人生的短促,一无所有的苏轼反而于此冲破了物质、时间、空间的界限,江、月一直永恒,需要转变的只是人的角色: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与范子丰书》[9]5424
醉里未知谁得丧,满江风月不论钱。《与潘三失解后饮酒》[4]2275
这种心态必定是经历过大得大失之人才能拥有,作于赤壁矶的两赋一词正是这一超越的集中体现。此地的赤壁矶虽非古战场原址,但其位于大江之畔,其名亦足以引起苏轼无限的联想。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以周瑜为历史的参照物,得出风流人物随时尽,而长江永恒的人生短暂之感。《前赤壁赋》则是在与杨道士泛舟歌酒这一乐事的背景下,再次提到“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9]27;《后赤壁赋》亦有“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9]39之叹。但这三篇作品最后又都从单纯的哀叹中脱身,从“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11]93的孤独到“物与我皆无尽也”[7]27的超越,再到从缥缈的梦中醒来,苏轼最终从长江的浩荡无涯与亘古长流中解放出来,当对人生有限而风月无边的遗憾转为接受,苏轼便完成了在黄州精神家园的建构。
四、结语
对故乡的思念使得苏轼对黄州之江产生了一面如旧的感觉,黄州之江寄托着苏轼对亲友的怀念,以诗性想象建构精神家园既是无奈之举,也是苏轼对人生的自觉选择。在以流寓者的身份面对黄州之江时,苏轼以眼前之景瓦解失意之忧,并从思想维度与地理纬度两方面出发,于此,以“江”完成了精神家园的重构,为乡土意识与个人忧乐找到了寄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