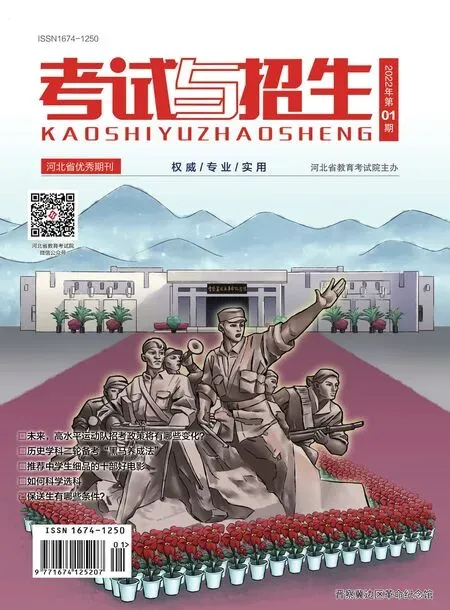弄满衣
>>>仇士鹏
关于写作,我从不敢说自己天赋异禀,但仍不止一次地畅想过,出版文集,在刊物上印上我的姓名。
于是,我如湖泊一般,兼容并蓄,淡然地接纳岁月里的泥沙俱下。
细想,我写作的启蒙,可能就是中学时期语文试卷上的阅读理解。每次考试,我都会在检查试卷时重读阅读理解,把心仪的句子标注出来,等试卷发下来后就把它们摘抄在积累本上,如果想偷懒,就把文章剪下来贴上去,等到早读课,就一句句地朗读、背诵。
我积累最多的一个本子,因为贴的纸条实在太多,合起来的厚度就像两个本子叠在一起,把它摊开,不啻一棵老榕树,沉下无数的气须根,在风中摇曳。
这是我写作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我开始有意识地锤炼语言,揣摩他人在选用与放弃词语之间的抉择,把细节和语言结合起来,让唯心主义的浪漫不羁多一些唯物主义的厚实与稳重。也是从那时候起,握住笔时,我能察觉到它的温度和坚硬,以及当它被举在半空时,那轻微的颤抖。
我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可能身体对手更加偏爱一些,于是把组织文字的能力都给了手,而让口独对寒风,沉默或是结巴。一些难以言表的、怕别人听不懂的,或是一些隐秘的,只有写下来,抽丝剥茧,呼吸才能被一点点理顺;只有写下来,人才会得到解脱和救赎;也只有写下来,逼迫大脑寻找出路,人才能从既成僵硬的情绪里突围,让裸岩长出青苔,让荒漠生出地衣,让绿意逐渐占领每一寸荒凉。
我们的初心往往都是纯粹的—我仅是想获得一方洗砚池,把我放进去细细濯洗。但过程未必脱俗。
写作不可避免地涉及稿费问题。第一次收到稿费是在初三,向一份学生类报纸投稿了一篇作文,拿到了第一张稿费单。如今我不记得报纸名,也不记得拿了多少钱。只记得那是一篇关于春天的文章,只记得老师对我说,“我要好好表扬你”,那时候的喜悦深深地扎根,一直生长到了多年后的现在,抽枝开花。
我开始享受稿费的福利是这两年。当写作与发表在多年的“惺惺相惜”中形成了“金玉良缘”,稿费单便不时地飞进传达室。固然它不多,但也足以让我时不时买点水果,喝杯酸奶,改善一下伙食。
尝到了甜头,动力就从舌尖、心房,一点点漫漶开来。写作有了炊烟的韵味,在人间的烟火中,向着青天追寻。
我不知道自己能把自己、把世界写到什么程度,最终又会如何在自我与人海、在短暂与永恒间达成和解,但我知道,在我的本业工作之外,我找到了另一种与生活问好、拥抱的方式。这是一条我自己走出的路,一条具有酸甜苦辣,却不会感觉累的路,一条曲径通幽、花木正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