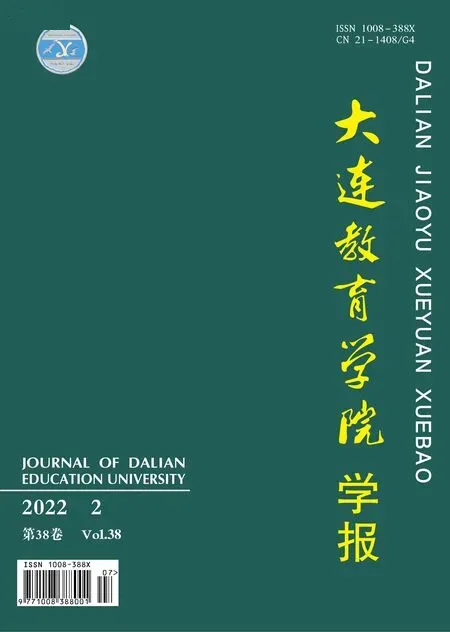从深情的乡村歌者到城市经验的探寻者
——孙惠芬的写作延展
王 莉
(大连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辽宁 大连 116600)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指出:“很多小说家对地域都有强烈的感受。”[1]孙惠芬的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在辽南乡村度过,对乡土感情深厚,融入血液,化成文化,铸就精神家园。生长在乡土的人进城后会在情感上产生与城市的“隔”,精神上产生回望乡土的需求。身为作家的孙惠芬对生活在城市后情感和精神上“回乡”需要体验得更为细腻、更加强烈,描述得更为清晰鲜明,“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了,可是心灵却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近”。[2]此时回忆里亲切可感的故乡图景抚慰了一个初到城市的作家惊疑不定的心灵,由此创造出“歇马山庄”的审美故乡。孙惠芬写的是空间转换带来的时间体验的变化。乡土给予她生生不息的活力,多年以后,孙惠芬可以由城市出发,探寻城市下一代成长的精神历程,在更深广的层面回应时代之问。
一、源自故乡的《歇马山庄》
孙惠芬在文本里建构的源自故乡的“歇马山庄”,经历了由城市返乡的寻找、发现、创作之路。由乡村而城市,她觉得自己像一棵脱离土地的稻苗悬在空中,她的根在乡土,人到了城市,心神却在寻找那个叫“青堆子”的辽南小村。“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我天天想着逃离,可你一旦逃离,它又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支撑着你脱离家园的飘浮感”[2]。小说《歇马山庄》里的月月、小青、买子……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就这样闯入我们的视野。作品以改革开放后的辽南农村为背景,表现了一代农村青年在历史巨变中的迷茫和选择,真实展现了农村人走向城市的历程和心理,获得“冯牧文学奖新人奖”,名动文坛。李敬泽很看重《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这部中篇小说,他读懂了孙惠芬对人性的探察、对由乡进城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人情感与精神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形塑,他用纯正的文学批评语言准确评价了孙惠芬创作这部小说的价值:“站在乡村的立场上,孙惠芬处理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但‘重大’没有使她的笔变得迟钝、粗放,她始终是轻盈的、灵敏的,她耐心探测人性的微妙反应,这使得潘桃成为丰富、充实的艺术形象。”[3]她的城市情结与乡村情怀扭结得非常深,“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她一直绕不开的一个主题,在这个大的主题下面,一个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日常。日常在她的创作生命中越来越巨大,她的文字传递出日常状态是人性中最难对付的状态,人类精神的真正挣扎,正是在日常的存在里,困惑和迷惑,坚韧和忍耐,使挣扎呈现着万千气象。在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光里,精神之树气象万千。《蟹子的滋味》中的两个老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潘桃和李平,还有《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的鞠广大和郭长义,《一树槐香》里的二妹子,《狗皮袖筒》里的吉宽和吉久,奔向现代化的路上心灵的万千波澜都蕴含在日常生活的一粥一饭、阴晴冷暖中。日常,孙惠芬抓住了乡村人深广内心生活的普遍形式。道不离日用常行,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心灵修养,达到超越境界是中国人参悟大道的正途,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全面发展的人的概念出发,提出人必须变成日常的人,然后才是完全的人。日常生活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生活层次,日常生活生产“人类条件”,即个体自身[4]。个体在日常中创造,体现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可以说,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的日常是孙惠芬“歇马山庄”系列的主题。当她在城市里生活过,观察过,思考过,感受到了回乡的情感和精神需要,听到了内心对故乡的呼唤,于是选择回到家乡,再次感受,再次出发,再次凝聚,再次表达。可以说,像贾平凹的商州一样,歇马山庄也是进城的作家回乡后,在人生更高处再次与故乡相遇的审美创造。
孙惠芬的“歇马山庄”是故乡对生活在城市的作家的厚赐,是人—城—乡汇合的造物。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深,乡土对于城二代只是模糊的影子。因此可以说,路遥、贾平凹、孙惠芬,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乡土描写最深情、最深厚、最深广、最深隧的当代作家;他们是用文学记录和表达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向城而生、由乡而城的乡村人情感、精神、生活、观念变迁的优秀作家。“70 后”徐则臣这一代作家也写故乡,也有乡愁,时代使然,他们对城市生活更加熟悉更加关注,写得更多也更好的是由城市出发的作品。
二、进城者的精神还乡:《后上塘书》
在《后上塘书》之前,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进城,从农村走向城市。《后上塘书》的方向开始回归——还乡,从城市回到农村。高加林(路遥《人生》)开启了新时期乡下人进城的序幕,新时期直到新世纪的小说一直在壮大这个队伍。新时期小说里第一代进城的农家子弟高加林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在于对知识和城市的向往,同样的,爱好知识、进城当工人的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是农村优秀青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其后的刘高兴(贾平凹《高兴》)只能成为进城务工大军中的一员。刘杰夫(孙惠芬《后上塘书》)是庞大的乡下人进城队伍里的成功者,也是回乡者和反思者。高加林奔向城市时年轻帅气,热情浪漫,返乡的刘杰夫则是事业成功却疲惫沉重心事重重的中年人。可以说,刘杰夫是经商版的高加林,也是成功后的高加林,城市梦的实现和对故土的留恋使他的回乡必然带有反思性质。
孙惠芬在《后上塘书》里塑造的刘杰夫是新时期到新世纪40 年来乡下人进城队伍中的转折性人物,他既是乡下人进城队伍中的成功者,成功地实现了乡下人进城的梦想,又是回归者和反思者,重建了与故乡精神上的联系,开启了还乡和忏悔之路,重建了与自我的关系,重建与故乡传统与伦理的关系。孙惠芬的确将刘杰夫视为一种新型的人物[5]。他是接受了城市逻辑的成功人物,并且将城市逻辑带回乡村社会。刘杰夫是个典型的成功者。他已经成了故乡上塘的传说,村民口口相传的都是他的财富和成功故事。经商助他走向了成功。他开过夜总会,当过矿老板,经营着一家大酒店,还回上塘当了村长,开发上塘,修了公路,把安静的上塘变得灯火通明,把从前的上塘规划成一个经济园区。刘杰夫实现了高加林当初的梦想,成功地拥抱了城市,成为城里人,而且在城市里呼风唤雨,如今回乡改变了故乡的面貌甚至乡亲的内心世界。作家肯定了刘杰夫身上的开拓精神、开放观念等新质对于乡村的积极作用。从个人与乡村的外部关系来看,的确是从城市回来的刘杰夫一个人改变了一个村子的面貌、伦理秩序和生活方式;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刘杰夫真正的问题是他和妻子徐兰一样迷失了自我:徐兰是个追求理想和自由的乡村知识女性,她在对乡村伦理秩序的恪守中失去自我,跟随丈夫,侍奉婆婆,小心翼翼对待伶俐刻薄的小姑,和气周到对待街坊四邻,当好人民教师,堪为全村人的道德表率。她进城后日渐困惑,迷失了自己;刘杰夫则是在对城市文明的追逐中远离了乡村伦理秩序而迷失了自我,通过各种合法非法让人流血流泪的手段实现资本积累,拥有了事业、财富、地位、名声之后,他还改变了故乡的生产生活。意得志满的他遭遇妻子突然死亡才骤然发现成功路上他对亲情、乡情漠视已久,失去才知珍惜,他恍然明白家庭、亲情对于一个成功男人根基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和谐的乡情对于一个从城市回乡要干一番事业的乡村带头人的重要价值。城乡文化的深层碰撞之下,返乡的成功者刘杰夫需要面对乡村自我与城市自我的整合,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融合。契机来自妻子的突然死亡,引发他的回乡和忏悔。他重新发现了道德、亲情、伦理对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意义: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成功没有意义;没有家人,财富都是垃圾;在故乡上塘的传统伦理中努力重建完整的自我。孙惠芬通过刘杰夫这个进城路上的新型人物写出了对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的双重反思,表达了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相融合的美好愿景。
还乡之路并不平坦,刘杰夫一直为是否还乡心中忐忑,决定还乡又有悔意。作家用缓慢的叙述语调写出了刘杰夫内心的犹豫、勉强、恐惧以及回忆和挣扎的过程。刘杰夫送妻子回上塘安葬与他回上塘当村长截然不同,他不再是领导、老板,不再是成功者“刘杰夫”,面对他不愿面对的贫穷卑微的原形“刘立功”,面对他不愿面对的亲朋故旧,但他最恐惧的是面对自己的过往。因此他始终不情愿回上塘安葬妻子,但最终仍旧选择了还乡,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当他在故乡面对自己的过去,在痛苦和迷茫中逐渐放下外在的功利心,接纳真实的自我,实现旧我和新我的整合,实现了真正的回归。孙惠芬写出了刘杰夫这位进城路上的成功者艰难沉重、重新整合自我的返乡之路,并寄予了作家对乡村与城市融合的深厚情感和价值判断。不过刘杰夫这个人物在内心世界探寻、精神求索方面并没有达到作家理想中自我超越的境界,作为进城路上的成功者、反思者形象,刘杰夫在内心拷问、精神超越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孙惠芬写出了故乡上塘的文化功能。城市是进城者对现代文明的梦想,故乡之外是个体生命对外面世界的永恒梦想,因此故乡是接纳、抚慰还乡者的家园。它使现代人回到童年,使分裂的自我得以重新完整,有希望有力量去追求反思后获得的新的人生意义。《后上塘书》里的上塘,已然是正在被开发的喧嚣浮躁、躁动不安的上塘,与《上塘书》里安宁古朴、略有变动的上塘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原来的上塘一派安详,岁月里生长出上塘人独有的生活方式。叙述节奏同上塘的生活一样舒缓有序。《后上塘书》以一声神秘凄厉的叫声开始叙述,血红的晚霞、神秘的叫声、池塘的白骨、惶惶不安的上塘人,这种种令人惊悚饱含戾气的事物制造了现在上塘神秘恐怖惶恐不安的氛围。
这个惶惑的上塘似乎已经不能像黄土地给予高加林归宿感和安慰一样,带给刘杰夫抚慰。刘杰夫的还乡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他回乡当上村长,开发上塘,把上塘建成了现代化的开发区,此次重返故乡仍然是他闯世界的一部分,回乡是为了实现当村长的理想,与精神还乡无关,方向上仍然是向外扩展,向上奋斗,实现英雄梦想;另一次是他为妻子徐兰送葬而还乡,这次回乡与他每天在上塘村部上班有了本质的区别,筹备葬礼过程中他见到的人、听到的事,引发心灵上的震撼,他的扶灵还乡演变为一次忏悔之旅。故乡像母亲一样重新具有了接纳、抚慰、给予的功能,使游子有力量再出发,故乡依然是刘杰夫的出生地和出发地,也是他实现村长理想的落脚点。他借徐兰之死在精神上与故乡再次重逢,开启了他的忏悔之路,故乡接纳、帮助主人公回忆、忏悔,找回自我,使其灵魂的还乡和精神的救赎成为可能。乡土文化功能的实现会随着城市化的程度有所变化,远远不只是文人情感中和审美上的乡村牧歌或者留守之地,正如孙惠芬所言:“人类真正的家园,只在自我超越的精神里。”[2]《后上塘书》的出版展现出作家由乡而城创作思路的发展和转换,表达了对乡村伦理和城市文明的双重情感和反思。
三、城市经验之下的《寻找张展》
“不论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孙惠芬写作《寻找张展》,熟悉孙惠芬的人都会有她将会创作这样一部小说的预感。她所建构的‘歇马山庄’和‘上塘’的乡土文学一定会延伸到走出乡村后的第二代城市人的精神世界。”孙惠芬由乡而城的自身经历,促使她始终在思索城乡地域空间和城乡文化,关注向城市敞开的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精神世界的微妙改变,关注乡村个体生命的价值,试图理解乡村人已经变化的精神世界。乡村人离乡进城、由城返乡来来往往的城乡之路,穿梭在城乡之间的人们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重构过程中内在的精神风暴是孙惠芬始终关注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新世纪之后步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作家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也更丰富,对人与城市的精神联系有了更深的体验。正如她对乡村世界的乡村人有着深切的关心,她对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也逐渐有了关切。城市不再只具有衣食住行医文的功能,而开始展现人与城市的深层关联。正是对与儿子同龄的“90 后”群体的关注关心,推动了这部探索“90 后”成长之路的长篇。《人民文学》2016 年第7 期发表了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2017 年2 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寻找张展》,5 月《寻找张展》在《大众日报》连载,2017 年第4期《长篇小说选刊》选登了《寻找张展》。小说当年就荣登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9 年,《寻找张展》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么多荣誉在向人们宣布,《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成功表达城市经验的作品。她的作品由自身出发的痕迹比较明显,她所写的空间和人物,必得是与她有着深刻关系的,家乡的山水和人内化在她的生命里,她在“歇马山庄”“上塘”系列作品中,创造出一系列城乡之间面目清晰可辨的乡村个体;与此同时,城市的环境和人是她每天的日常,与她关系最深刻的,是由儿子延展的“90 后”群体。已在美国读博士的儿子那句“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是她探寻“90 后”精神世界的内在动力。孙惠芬于不期然间由乡村日常向城市日常转弯,却又水到渠成。2019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丛书收录了《寻找张展》,责编的推荐语就是“一个父亲的迷失与沉沦,一个母亲的寻觅与反思,一个儿子的倾诉与救赎”。对于奔波在上班路上和送孩子上学路上的中国母亲,这是一个无比熟悉的日常,“张展”也是她们最想寻找的下一代。因此这部小说写出了全民教育时代背景下这一代的精神世界以及父母对这一代成才的期望和走近的渴望。小说在《大众日报》连载后,引发很多评论家与读者的共鸣,甚至有人对孙惠芬说“我就是张展的妈妈”。
孙惠芬依然从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去回应时代之问。这次她写城市人的日常,写出了以孩子为重”“以教育为重”的时代里父母一辈的期待、付出与误会,以及下一代在社会、家庭规定的高考升学轨道之中,自我的迷失与寻找,她代“90 后”的父母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也经由下一代成长轨迹的反思,来思考城市化进程平稳有序之后各个阶层价值观、生活态度的深层问题。列斐伏尔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实现的,社会的本质依存于人的日常生活小事,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实现出来的。[4]孙惠芬在《寻找张展》这部长篇中正是从家长、学生、教育者的日常生活接近时代内核,通过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子女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以及矛盾弥合,呈现城市化进程有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当今中国社会伦理观和价值观的焦点。“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家庭主要发挥“阻拦者”功能,20 世纪80 年代前期家庭拥有了“拯救者”的功能,使个人从伤痕中恢复过来的方式就是让他“回家”[6]。以“90 后”为主人公的《寻找张展》中,由于进城后两代人生活经历和价值观不同,家庭再一次成为年轻人想要逃离的地方,但也是重新达成理解、疗愈之所。
《寻找张展》的生活空间是城市,话题和人物的人文背景是教育,小说上部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不解和寻找,下部是下一代人的成长。小说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平民、中产阶层的表现之熟稔,对人与城市精神联系的切入绵密细致,人在城市中的情绪、感受已然有城市文学的内核和气象。这部小说也是孙惠芬文学创作城市化进程的标志性作品,意味着她对城市生活,对人与城市的情感,人在城市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状态有了足够的积淀和表达的动力。孙惠芬深谙“无尽关系”在中国社会无形无影又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这部长篇选择了最为关切的“90 后”作为主人公,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他们观念意识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一代人自身的问题,而是作为发展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精神变迁的缩影和注脚。”[7]作品中的“90 后”青年张展面对社会的不解与父母的隔阂,克服消沉,逆风生长,用爱人之心、爱美之心和积极行动融入社会,映照出父母一代追逐现代化的功利伤痕,也展现出新一代青年的理想之光。“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中青年形象和精神的复归”。[8]作品由“我”寻找张展出发,逐渐遇到不同人眼中不同的张展。他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是同学的偶像;他在大学校园不爱与人交流,不重视学业和前途,在辅导员眼中是边缘学生;他在家里忧郁感伤,不读书上进,是让父母操心的孩子;他在交换妈妈那里更是一个控制不了、不可救药的人;他去特教学院给那里的孩子画画,孩子们和老师都很喜欢他,觉得他有爱心,画画很棒。在寻找过程中,发现父母、教师等与下一代生活和成长有直接关系的各个群体对“90 后”一代存在各种不理解,折射出人与人认知的差距、情感的疏离、功利的诱惑、欲望的膨胀等社会因素,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第一代城市移民为实现城市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也呈现出他们由此而来的急切、功利、偏狭的特点,以及这些不足带给下一代的影响。
张展的父母是由乡而城的第一代,他们靠上大学走出乡村,经商、入仕一路奋斗获得成功,拥有了事业、金钱、地位和稳定的城市生活及人际关系,但无法兼顾家庭。张展小时候就被寄养在姥姥家。这样的父母在城一代中比较常见。父母是奋斗的一代,成功的一代,是在城市创下基业、建立关系、站稳脚跟的一代,他们的奋斗历程与城市化进程一致,其奋斗、成功的功利价值观是在城市生存、获得价值最大化的基础,却成为与下一代价值观不相融合的基点。进城,做城里人,是张展父母的奋斗目标,一切为城市而努力。母亲阻止张展与乡下的泥土之根发生关联,不愿意让他去看望住在农村老家的爷爷奶奶;忙于事业照顾不上儿子,把儿子送到姥姥家;送儿子去城市读书,给他找了个交换妈妈。忙于赶路,忘记了灵魂,重视外在的生存规则,无暇照顾内心,不理解审美,干涉儿子画画的爱好,认为不是读书上进的正路;阻止儿子与不如他的小伙伴交往。凡此种种,父母与儿子张展产生了价值观的差异、情感的疏远和精神的隔膜,为儿子所不解、抵触、指责。作为“90 后”父母的一员,孙惠芬在深刻反思的同时,给予城一代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们是奋斗的一代,他们努力拼搏取得了城市化第一步的成功,他们有着功利性的生活观念,对下一代的城市化寄予厚望,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难以顾及自身的健康和快乐,这些正是现代化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塑造出来的由乡而城的第一代。优秀与偏狭在张展父母这一代人身上并存。
张展是城二代,像富二代一样,他们不需要像父母那么辛苦奋斗,就能享有父母创造的优越的城市生活和家庭生活。物质不需谋求,精神就有了生长的空间。小说下部,张展以书信的方式诉说了心灵世界的建构过程和成长轨迹。张展也是寻找者,他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寻找真实的父母,寻找乡土之根的家族联系,寻找自我,寻找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寻找自己在世界上活着的价值。这种寻找同样是反思,思考的矛头逐渐由对着父母,到对着自己,解剖自己。正如父母不理解张展,张展也没有理解过父母,也没试着让父母理解过。两代人之间交流、理解的曙光已现。
更深一层,孙惠芬展现了“90 后”一代价值观形成的轨迹。张展的故事不只是张展一家的故事,而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城一代成功后无比重视城二代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的家庭影像,勾画出城二代的粗略轮廓。张展的个性和价值观不是他父母单独制造出来的,是整个社会,无数父母、教师、官员、金融业者、律师、医生、务工者合力制造的,是发展中的中国城市与乡村共同制造的。希望在未来,“90 后”张展在对父亲的寻找中实现了自身理性的成长,对父辈观念和行为的理解,对价值观的修正。张展已经准备好,去适应这个繁华又寂寥、鼓舞人又挑战人的城市化时代。
总之,孙惠芬文学创作的城市化进程中,“歇马山庄”“上塘”传递着乡村城市化的心灵消息;“后上塘”是成功的进城者和未来的还乡和反思;“寻找张展”是对城一代奋斗路径和价值观的反思,城二代连接城乡、面对当下和未来的勇气。乡土歌者向城而歌,在城而生,在由乡而城的现代化路上深情不改,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