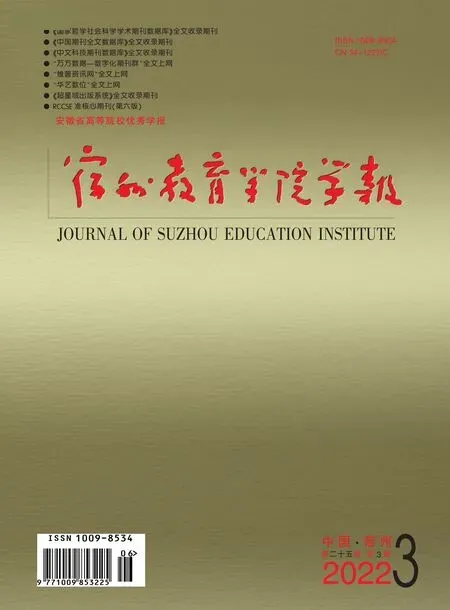弗洛伊德“梦的改装”理论视域下庄子“梦”的解析
李梦巍
(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0)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出“梦的改装”理论,他认为“有的梦未经分析以前,也看不出竟是梦者愿望的达成,如果我们把‘梦需要解释的’作为梦的一种特征,而称之为梦的改装现象,那么次一个问题便是‘梦的改装之来源是什么?’”[1]50可见,弗洛伊德认为“梦”的产生与人的愿望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而通过对梦进行解释,即通过对梦的改装现象进一步探析,可以对这种愿望的达成有所认知。随之,他对梦需要改装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梦“有所‘伪装’或‘难以认出’,必表示梦者本身对此愿望有所顾忌,而因此使这种愿望只得以另一种改装的形式表达之”。[1]55即在现实中有所求却得不到的,可以通过“梦”这种形式进行表达。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适用于庄子对梦的认知。庄子在现实中面临的是“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2]381(《庄子·庚桑楚》)的生存困境,追寻的却是随心所欲、任其自然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理想与现实割裂的环境下,庄子便借助梦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追求,通过对“梦”进行改装,借助“梦”来实现对道的追求。与此同时,庄子深知俗事缠身的社会环境不能实现自身的愿望,于是便借助于不受束缚的梦来对双重生存世界进行辨析,实现精神层面上愿望的实现与延续。
一、庄子对“梦”的认知
庄子认为梦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2]19的产物,指的是梦是一种关于人的生理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因鬼神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境遇。庄子对梦的定义与传统的与鬼神托梦或有极强象征性的解释不同。先人们通常将巫蛊与占卜之术运用到对梦的解析之中,以此解释来自自然世界的力量对世人的启示。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3]这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试图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对梦进行解析,是一种主观性较强,易受主体观念影响的方式。此外还有《梦占逸旨日月篇》《汉书·艺文志》等文献中亦有对借助神鬼与占卜解梦的记录。可见,庄子的前人大都是从一种关于神鬼托梦的形式对梦进行解析,认为梦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是由于自然界与非自然界精怪的力量作用下产生的。但是庄子对梦的认知是理性的,是有着强烈的辩证思想的。
庄子借助“梦”这一形式来表达对道的追求。庄子认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2]362圣人有着推动天地有功而不自夸的美德,懂得通达万物从而生成的妙理。所以至人无为,圣人无所造作,只是观于天地自然的无为之道。圣人观天地之美,俯仰于天地之间,通过俯仰与虚静的认知,进一步接近道,追求一种更深的美学认知。肯定神的重要性,强调在七窍之外对道的认知,即“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2]45用心神去接触而不必用眼睛观察,眼睛的功能似乎停止了,但精神的世界仍在运转。借助养生之道肯定神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强调对道的追求。这些梦与现实、思维与宇宙,融为一体,不再有着明确的界限,并且借助融凝物我的方式,为内在情感寻得感性化的载体。弗洛姆认为“象征语言的逻辑不是由时空这些范畴来控制,而是由激情和联想来组织。”[4]庄子借助梦这种象征语言,表达自己对道的追求,用俯仰与虚静的表达方式,通过联想,从而实现超越物之实而得其虚,然得其虚而未失意之形,最终实现对纯一之境的追求。
二、庄子梦“改装”的三种表现形式
(一)自梦
自梦指的是庄子自己的梦,或者是从第一视角出发所写的梦。《庄子》关于自梦表达有八处,涉及内外篇共五篇。在这些关于梦的描写中,涉及庄周梦蝶、梦饮酒者、梦鸟鱼者等梦。如梦饮酒者一篇中提到“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2]38只有圣人才知道人生不过是一场大梦罢了,而愚昧的人却自以为清醒,好像什么都被自己明察的样子。从表面看是愚者对梦的恍惚认知,并自以为了然而窃喜。但是只有圣人才能明察,而世间庸庸碌碌的却大多都是普通人,都不能做到“知此其大梦也”。此外还有庄周梦蝶中“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2]42庄子写自己梦到了蝴蝶,但分不清蝴蝶和自己,在这种物我无法辨析的梦境中,庄子认为,庄周与蝴蝶必有一个分明。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称“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将梦定义为 “一种持续到睡眠状态中的思想”。[5]庄周梦蝶所展示出来的正是他内心深处所要表达的情感与思想,在化蝶这一闹剧下,庄子的梦有种怅然若失的失落感,这是从文中透露出的更深的情感表达。无论是愚人不能对自己的梦有明确的认知,抑或是庄子分不清自己与蝴蝶,都能体现出庄子所要表达出的一种悲情感。
(二)托梦
托梦是指他人向寓言中的主人公托梦,或寓言中的主人公假托他人之梦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庄子》中关于托梦的内容共有六处,共涉及内外篇共五篇,包括栎社见梦、髑髅见梦、文王托梦、郑缓魂托梦等内容。主要表达的是庄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如庄子在《内篇·人间世》栎社见梦中写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2]68可以理解为你要用什么来和我相比呢?你要用质地细腻的树木来和我相比吗?栎树这两句话是对前文匠石对自己无用评论的反驳。栎树通过对瓜果树木正是因为有果实,于人来说有用,从而易受破坏的说明,证明正是因为自己不能做船、做器具才得以保全。从而来讲述无用亦是大用的道理。此外,庄子在《外篇·至乐》中还写到了骷髅见梦的故事。庄子之楚,见空髑髅,夜半,髑髅见梦。骷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2]287这段话可以理解为,看你白天的谈吐像个辩士,听你说的话全是人活着的痛苦,死了这些就都没有了,你想要听听人死了之后的事吗?骷髅表示,死了之后便获得永久的自在,活着时的痛苦便都不见了,表达的是死了比活着快乐的思想。但是按照庄子的观点,活着有活着的快乐,死了有死了的快乐,人应各安生死,而不是对虚幻抱有强烈的期盼。因为“在荣格看来,许多梦并没有表现出个人被压抑的欲望,而是表达了个人的天性和潜能,梦是无意识精神自发的和没有偏见的产物,梦给我们展示的是未加文饰的自然的真理。”[6]所以庄子借助对有用或无用,或对生死与快乐的关系的辨析,表达对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即安于存在,安于当下,在生死之外正确审视自己与天道的关系,正确认识到生命的意义。
(三)无梦
庄子认为古之真人与圣人都是无梦的,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至真至善的状态,实现了对道的追求。在《内篇·大宗师》中,庄子写到:“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2]95意思是古时候的真人,他们睡觉是不做梦的。醒来时也没有什么烦忧,饮食上面不求甘美,他们的呼吸深沉绵长。这一段讲的是真人无梦的状态。从文中描写的真人的特点可以看出,庄子所认为的真人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真人的快乐与忧愁不受外界万物的影响,在世上孑然一身,遗世独立。此外,庄子在《外篇·刻意》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2]247大意为圣人在世时会随着时空流转而变幻,在死后也会随着万物的变化而不断流转。他睡时不做梦,醒来也没有忧愁。他把生存视为流动的浮云,把死亡视为暂时的停歇。他的心神是纯粹而无杂念的,他的精神是充沛而无停歇的。他这样的存在,虚无恬淡,是符合自然的本性的。庄子关于圣人的描述与真人的描述都是“其寝不梦,其觉无忧。”[2]95无论是真人还是圣人,他们的生存变化都是符合自然变化的,都符合天德。文中所描述的真人或圣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庄子本人对道的诉求,即其本人所追求的与天地和道相处的状态。
在关于梦的描写中庄子借助的是理性的辩证手法。这一点从庄子对梦的定义便可看出,他认为梦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2]19的产物。即睡觉时自身魂魄的不安宁,导致自身情绪的波动从而产生的,而不是因为有上天的旨意,或者是由鬼魅托梦而生。在关于梦的具体描写时,庄子用的是严格的辩证手法。在庄子梦到蝴蝶时,庄子思考的不是蝴蝶为何入梦,是要给他什么启示,而是在思考究竟是庄子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子,从而在这样的辩证中,得出了物我可以互化的结论。在讨论梦与纯一之境的关系时,庄子提出“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2]115可理解为,你梦到是鸟而翱翔于天空,梦到是鱼而沉于渊底,但是却不知道现在的自己醒着的还是睡着的。即便是梦中的景象也不可信,仍要听从自然的变化才能进入寂寥空虚的天道,这不是靠梦实现的,而是在认清现实后靠顺应自然而实现的。庄子关于梦的内容的描写都充满着理性的辩证意识,不是借助鬼神的力量,而是借助对梦进行严格的论辩,从而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或者说,梦是庄子所借助的外衣,在一番论证之后,揭开梦这一层皮囊,再给世人展示所要表达的实质内涵。这是庄子借助理性的辩证手法实现的。
三、庄子“梦意识”的深层心理内涵
(一)清醒状态下精神活动的延续
弗洛伊德认为,梦“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作是一种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续。”[1]37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3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达成,在对这种生存状态的期盼中,“梦”成为他实现愿望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而实现他在精神生存空间对道的追求。这种借助“梦”来实现的愿望,可以视为是在清醒状态下精神活动的一种延续。这主要体现在他现实生活中的求而不得和他对道的无限追求这种心理的冲突当中。当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有正确的认知,或者说无法继续说服自己,另一重生存世界的庄子可以对他进行劝解,即超脱肉体之外精神世界存在的庄子可以对他进行劝解,而这种劝解,往往借助梦的形式实现。在经历栎树托梦并解释自己的无用即大用之后,匠石对弟子说:“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誉之,不亦远乎!”[2]69假如栎树不生长在社中,怕是早就被砍成薪木烧火去了,它不过是保护自己的方式与其他树木不同罢了,如果用常理来赞誉它,那不就是相差太远了吗?此时的栎树在现实生活中是无用的,只能被作为薪柴烧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价值。但是在梦中的栎树,不同于其他果树因为有用而易受伤害,正是因为它无用,而又偏偏生长在社中,才使得它得以保存。这是庄子对肉体的生存世界与精神的生存世界的辨析,虽然在现实生存的世界中“无所可用”,但从精神世界来看亦是保存自己的万全之策,这是他在清醒状态下精神活动延续的一种体现。
此外,在《人间世》里,庄子提出大臣在与君主相处时要“形莫若就,心莫若和”[2]65,即外表要表现出恭敬顺遂的姿态,内心要有引导劝和之意。在向君主进谏时,要“与古为徒”,要引出古人为例,加以诱导进行劝谏,而不是因不妥的言行危及自身。这是庄子提出的在现实世界臣子与君主交往需要有所规避的地方,而不是随心所欲,任其自然。但在文王托梦中他这样写:“昔者寡人梦见良人……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2]350意思是昨日我梦到一个贤良之人……向我号令说,把你的臣民托付给臧地老者,你的臣民差不多就可以免于苦难了。不同于现实中臣子向君王进谏时需要的“以古为徒”,文王梦中的人在向文王发号施令,虽假托是先王托梦,但与现实中君臣相处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可以理解为是庄子在精神层面对政治状态的一种期盼,即对圣人出现的一种期盼,这是庄子依托于梦去表达的。这可以理解为庄子对另一重生存世界的追求,一种平等的、可以被自我掌控的、拥有绝对自我的生存世界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是通过梦的无尽美好与残酷割裂的现实的对比所实现的。
(二)神重于形的表达
庄子认为神比形重要。庄子对梦的认识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2]19,指的是因为睡觉时的心神不宁才导致的醒来后形体的疲惫懒散。可见,在庄子的理念中,神是比形重要的,并且形受囿于外表的限制,只能是消耗品。这种认知更多的体现在庄子的生死观中。他认为只有神对形的完全脱离,才能真正实现对自由、对道的追求。《至乐》篇中对形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2]285在妻子死后,庄子解释自己非但不哭泣,反而还鼓盆而歌的缘由,从而引出他对形与神关系的思考。仔细考量,她原本就不曾出生,非但不曾出生,她还不曾具备形体,她不仅不具备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在形体的基础上有气。她出现在恍恍惚惚的境遇之中,因为天地的变化而有了元气,随着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因为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可见,庄子认为形是由神而来的,神不存在了,形便不复存在。
在骷髅献梦中,与骷髅讨论生死时,庄子提出让主管生死的神恢复骷髅的形体,为它重新长出骨肉肌肤,并且归还给它父母、妻子儿女以及邻里和好友,但骷髅却并不愿意,它认为自己不能放弃南面称王的快乐再次经历人世的劳苦。骷髅认为人间是劳苦的。这也是庄子的观念,在庄子对神与形的认知中,形是一种束缚的存在,而只有神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去掉形的束缚,才能实现“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2]287的追求。形体灭亡之后,没有了君主的统治,也没有了官吏的管辖,没有四季的操劳,从容且安逸地把天地的长久看作是四季的流逝,即使是在南面做王的快乐也不能比拟。讲的是死后,神得到自由的快乐。而骷髅对庄子提出建议的拒绝,可以看出庄子是赞同神大于形的观念的。此外庄子还提出“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2]21,意思是,人一旦禀受成形体,有了具体的形态,那么他的形体便只能等待消耗完为止。在这里,人便失去了自主权。在云将向鸿蒙的请教中,鸿蒙亦曾提到:“噫!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2]169意思是重要的是在养心,你只要能做到无为,那么万物自然会变化。再次强调了神的重要性。可见,在庄子的观念中神是大于形的,而庄子所描写的在梦中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状态则更符合庄子对道的追求,只有脱离形的桎梏,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才能做到万物归一,物我合一。
结 语
庄子借助“梦”的表达形式,通过对梦进行改装,从而来表现自己真实的愿望。在现实的求而不得中,借助梦表达自己对道的追求,并且认为只有抛却形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肯定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这种认知与弗洛伊德“梦的改装”理论中借助梦这种表现形式来达到欲望的满足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弗洛伊德“梦的改装”理论的角度对庄子的“梦”进行解读,能对庄子的深层心理表达与追求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进一步理解他对道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