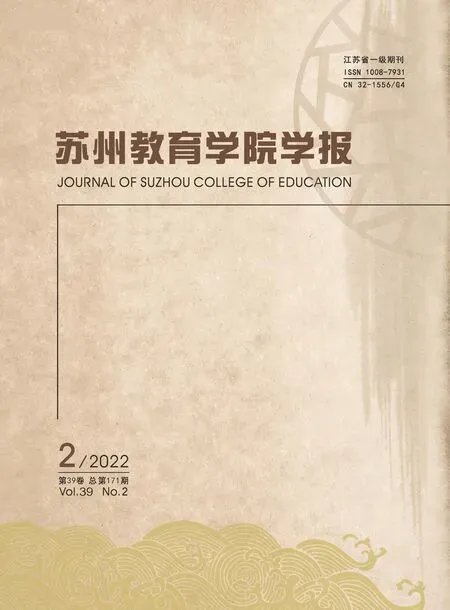当代人类“神话思维”复归的契机
——《克拉拉与太阳》的主体意识分析
马俊豪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认为,比较萨摩亚文化和美国文化,可以为美国提供一些变革的启迪,在进行充分的田野调查后,米德从萨摩亚少女身上获得启发,针对美国青少年的成长提出了自已的看法。[1]此后近百年,在诸多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文化人类学者们产出了丰富的田野资料和民族志成果,凭借着这些学术成果,当代人在对不同文明形态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把握时,有了更多的参照。但是如果将人类看作整体,那么能为人类自身提供参照的对象又是什么?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界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在探索“让机器人变得更为智能”中取得更大的进展。然而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的更迭,人文社科学者们陷入了一种新的思考和追问中,一时间诸如“人类的主体性问题”“技术的伦理问题”等这些古老的哲学命题和新的时代问题相互裹挟着,成为了今天人文社科研究的新难点之一。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2]讲述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智能机器人的故事,通过石黑一雄的想象,也许在艺术真实中,我们迎来了一个反思人类自身思维问题的新契机。
一、自我意识的生成—状语条件的补阙作用
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塑造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克拉拉,但是克拉拉的“自我意识”是残缺的,而这样的残缺又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克拉拉个体意识的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社会历史是如何作用于个体意识的生成,进而决定其发展和走向的。
(一)“自我意识”的生成和“状语条件”的不足
乔纳森·布朗和玛格丽特·布朗在《自我》中,充分分析了“自我意识”的生成机制,他们认为,“人们对生活事件所做的归因构成了人自我认识的重要来源”[3]87。在归因欲望的驱动下,认知主体会主动地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和选择,进而获得认识,产生意识。《克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的自我认知便与她强大的归因能力息息相关。克拉拉尤其擅长观察世界、总结规律。例如,当克拉拉在展示橱窗中看到萎靡的乞丐因阳光的照射而振作起来后,便对阳光的作用进行了归因,得出“阳光的滋养拯救了人类”[2]48这一结论。可见克拉拉对外部世界的归因是她生成自我意识的重要来源。在归因活动中,克拉拉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知觉,推动着主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与演化。
无法忽视的是,克拉拉生成的“自我意识”,始终存在着与“自然人”之间无法弥合的“认知”偏差。英国心理学家汉弗莱在分析“机器人的意识能否被设计”这一问题时,敏锐地指出,“基于理论设计原则,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有意识机器人……在实践中几乎无法完成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重造这个自然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已经赋予出现在自然脑中的活动以意识的独特模态品质”[4]187。由于克拉拉善于在生活中观察与认知世界,故而储备了丰富的个体经验,并得以在归因中深化“自我意识”的革新。但由于缺乏自然演化的历史条件,克拉拉“自我意识”中的“历史传统”漏洞无法通过个体经验的累积而填充,这意味着不论克拉拉个体怎么努力,仍然无法获得与人类等同的认知经验。
此外,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artificial friend,AF),克拉拉是被人设计出来的,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陪伴儿童长大。如何填补机器人自我认识中的“历史传统”漏洞,不论对于克拉拉的设计者还是使用者,均是被忽视的环节。正如小说中,克拉拉在面对来到店里挑选机器人的顾客,没有尽力展现自己的优势时,经理会毫不客气地对克拉拉说,“是顾客在挑选AF,千万不要弄反了”[2]41-42。
机器人如何才能产生类人的意识能力,汉弗莱提到了“状语条件”的概念,即“重新发现情态的关键状语特性(而不是碳摹本)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整个自然演化的进程,这个过程首先将它们置于像我们这样的动物中”[4]187-188。小说中,克拉拉与人类生活在一起,使其在共时向度上获得了产生类人意识的“空间状语条件”。但是在历时向度上,由于“时间状语条件”的空白,克拉拉无法真正在个体的成长中明确自已的身份与定位,而这也是克拉拉的意识与人类意识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之一。
(二)“主我”的断裂和“宾我”的缺位
威廉·詹姆斯将个体意识分成了“主我”和“宾我”两个部分[5],在詹姆斯的影响下,后来的心理学家用“主我来指代自我意识中积极地感知、思考的部分,而宾我来指代自我中注意、思考或感知的客体部分”[3]15。
小说中,克拉拉不仅善于从细微处观察与认知世界,还颇具理性分析能力。但是在克拉拉个体意识的构建中,由于“状语条件”的先天不足,与人类相比,她的“主我”和“宾我”均存在一定缺失,表现为“主我”的断裂和“宾我”的缺位。
对于“主我”来说,建构认知的“同一性”是“主我”得以稳定的前提。而认知“同一性”的关键便在于主体“对于先前知觉及相关影响的持续记忆”[3]67。作为机器人,克拉拉获取能量、维持运转的方式是对太阳能的转化,因此她基于对个人生活的总结,天然地认为阳光是自然界一切能量的来源。同时,因为前文提到的“乞丐照射阳光事件”,便更加深化了克拉拉对太阳能量的认知,进而产生了“太阳崇拜”心理。但由于缺乏历时演化的“宾语条件”,克拉拉没有认识到乞丐恢复精神的偶然性和太阳并不能治愈一切人类疾病的必然性。于是,当克拉拉决定向太阳献祭出维持自身机器运转的重要液体,以求得太阳对乔西的恩赐时[2]350,克拉拉的认知与现代人类的认知之间的偏差便展现了出来,而这一富有张力的情节也为克拉拉的行为添加了悲壮感。但是这一悲壮行为背后所展现的正是克拉拉的认知与现代人类的认知之间的断裂点,以及克拉拉的“主我”意识在“历史演化条件”中缺失的表现。
在自我认识中,“宾我”是对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的看法”[3]36。詹姆斯将“宾我”的存在划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三个维度。[5]314-318小说中,乔西的母亲希望克拉拉能在乔西死后成为乔西的替代品,这也促使克拉拉不断反思:自己与乔西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从“物质自我”的维度来看,机器人克拉拉与人类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机器人的身体和碳基生物的身体之间的区别显然无法弥合。对于“社会自我”来说,克拉拉在实践中得出“人内心中无法在机器人身上延续的地方不是在人的心里面,而是在那些爱她的人的心里面”[2]385。克拉拉认识到,她再怎么精确地复刻乔西,自己依然只是一台机器,她无法触及“母亲、里克、梅拉尼娅管家、父亲这些人在内心对乔西的感情”[2]385。乔西的家人也许十分情愿让克拉拉替代即将死去的乔西,但是他们自身却无法将对乔西的情感转嫁到克拉拉身上,这也是克拉拉无法取代乔西的重要原因,也是克拉拉“宾我”意识中“社会自我”缺位的体现。从“精神自我”的维度来看,乔西的父亲认为,人心就像一个房子套着另一个房子,你永远也不知道人的心中究竟会存在多少房子[2]276。克拉拉最终接受了这一关于人心的论述,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真正地复刻乔西的内心,这表明在“精神自我”的认识上,克拉拉也清楚了自己的认知与人类的认知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二、科学与神话—被隐匿的思维
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甚嚣尘上,在激进者眼中,“自然”更是被描绘成了一种拒绝变化的过时之物。而“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对立就是自然与文化之间对立的主要表现之一。而由于“状语条件”的缺失,克拉拉的思维中并未显现出“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性,其意识中的“神话思维”并非隐性存在,而是显性的,并与“科学思维”之间呈现出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吊诡的是,克拉拉的这一思维方式固然使得自己与人类格格不入,但是深入分析后,这些不同点却从侧面打开了人类的自反空间。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表征作进一步挖掘和解码。
小说中多次出现对“库庭斯”机器的描写,当“库庭斯”开始运行时,会产生大量污染,在“库庭斯”的轰鸣声中,浓烟一度遮蔽了太阳,这使克拉拉感到恐慌,因为在克拉拉的认知中,“库庭斯”产生的污染会惹怒太阳,进而导致人类生病,想要治愈乔西,最为可行的方式就是摧毁“库庭斯”,以求得太阳的原谅,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克拉拉甚至不惜取出维持体内正常运转的重要液体。另外,在克拉拉看来,阳光所照射的空间理应是鲜亮明净的,在阳光下生活的生物应当是友好柔和的。但是在去往瀑布的路上,克拉拉在看到农场的公牛后大惊失色,甚至叫出声来[2]126。对于自己为何如此恐惧,克拉拉解释道:“之前从没有见过这样一种东西,竟能在同一时间内传递出这么多预示着愤怒与毁灭意愿的信号。”[2]126在“太阳崇拜”的认知下,带有“负面情绪”的公牛出现在阳光下,克拉拉无法接受,因为它的存在打破了克拉拉内心对于太阳的认知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克拉拉对太阳的敬畏,并非源于科学知识的匮乏。在小说塑造的世界中,得到“基因提升”的孩子们,往往拥有更聪明的大脑,能够理解更加复杂的知识,进而考进好大学,迎接更加光明的未来。里克的母亲因为里克没有得到“基因提升”而感到焦虑,为此她求助于克拉拉,希望克拉拉能够帮助里克学习,理解教科书。[2]190可见克拉拉对科学知识的掌握是高于未得到过“基因提升”的人类的。为什么克拉拉能够在掌握了“科学思维”的基础上,仍然能保持自身“神话思维”的完整性,并与自然之间维持相对和谐的关系?这其中展现出的正是石黑一雄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哲学反思。当克拉拉身上的“科学思维”与“神话思维”能够很好地融合时,我们不妨对“神话思维”的隐匿过程进行梳理。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落后的社会更加敬畏自然的力量。[6]70但工业时代以来,自然和文化愈发被看作是两种不相融之物,自然代表着拒绝变化的无机物,而文化则是驯服自然之后的派生物。列维-斯特劳斯说:“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将文化置于自然之上,而给予文化的这种优先权几乎从未以这种形式被接受—除了被工业文明接受。”[6]71为了发展,人类将文化置于自然之上。作为“自然思维”代表的“神话思维”也逐渐趋向隐性。一方面,马林诺夫斯基在考察神话和现实的关系后认为,“神话世界因沧海桑田的变化而丰富。……反过来,叙述得极具感染力的神话故事又反作用于山川……赋予山川明确的意义”[7],在工业文明高度繁荣的今天,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神话”与“现实”交相辉映的思维方式已盛况不再。另一方面,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神话是为了“满足深切的宗教欲望、道德要求、社会的服从与介入,甚而实用的需求”[8],神话和宗教一直以来关系密切。在“科学思维”的萌芽期,为了给予其合法性,进而集合社会意识,人们只能对宗教思维和神话思维进行彻底的攻击,直至今日,人类认知中的“神话思维”日渐式微,便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战争、疾病、自然灾害、文化冲突等问题接踵而至,人类不得不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而石黑一雄所坚持的国际主义写作,就是要关注诸如此类的人类共通性问题。
对构成人类今天思维的“历史状语”进行爬梳后,我们可以看到,“神话思维”作为早期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是在“科学思维”产生之后,才逐渐退居幕后的。对于回归“神话思维”本身,列维-斯特劳斯提到,“神话思维的本质在于符号的多样性,即:在对多种已知条件加以比较时,得出不变的特征”[9]。在对太阳崇拜和与太阳相关联现象的感知下,克拉拉深化了个体对太阳意象的认知,并进一步将太阳神圣化,但是这样的神圣化似乎也并不影响克拉拉“科学思维”的发展。谈及“科学思维”和“神话思维”的关系时,列维-斯特劳斯又说:科学思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能解释自身的有效性,还能解释存在于神话中具有真确性的事物。[10]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神话理应是并行不悖的。格罗兹在《时间的旅行—女性主义,自然,权力》中驳斥了现代社会将自然与文化置于对立面的思维方式,她认为,“自然并非文化的异己之物,而是文化的根基”[11]。与人类相比,克拉拉更加敬畏自然,且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谐。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历史状语”被抽离之后,“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得以和谐共生的表现。克拉拉的形象似乎就在向我们描绘着一幅两种思维和谐共生的蓝图,并引导着读者重新反思和认识人类。克拉拉的故事,或许是一个反思人类演进中思维变化的契机。今天的人类,即使无法抽离自身已经具备的“历史状语”条件,但是识别出我们“历史状语”中戕害“神话思维”的元素,可以帮助我们还原自身思维的完整性。
三、重新认知自我的契机—人工智能机器人时代的人类主体性反思
在前文的分析中,“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被“历史状语”截然分开,而“历史状语”的生成背后又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作为一篇虚构的文学作品,《克拉拉与太阳》当然不能作为批判现实的材料,然而在艺术真实的维度,石黑一雄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拾“神话思维”的可能性,以及探索在今天的语境下,人与自然、神话与科学和谐共生的可能性。
小说中的乔西由于罕见的家族遗传病,死亡的可能性极大,她母亲和卡帕尔迪先生试图让克拉拉复制乔西的行为和思想,并在乔西死后及时填补母亲的内心。这种想法遭到了乔西父亲的否决。为了论述乔西的不可复制性,父亲提及了“人心”的概念,在父亲看来,“人心”才是让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原因,并且“人心”是无限的、不可复制的。而父亲与母亲等人的分歧,即是对“什么是人”这一问题的分歧,也是对认知自然与文化间关系的分歧。
在福山看来,人在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要实现自我社会化,并担当起一系列的角色—天主教徒、工人、离经叛道者、母亲、官僚等,这些角色限制了人们进行选择的自由,通过规范将人群联系在一起,并由他们严格执行规范。[12]一方面,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想要在某一领域获得成就,需要从身体和思维上均达到该领域的要求,进而全面沉浸于自己的社会分工中。但是分工本身就是对整体进行部分的切割,这样的分工的确确保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与速度,但是却伤害了人本身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假肢、人工晶体、人工耳蜗等新技术的出现帮助人们获得了肉体和感官上的延伸,人类自身的完整性又在技术的更迭中得到弥补。
在颇具戏剧性的现实中,人们开始思考,也许有朝一日肉体也能被金属或其他人造物替代,同时个体的意识却依然能够生成,而当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绝对界限不复存在时,人类又该如何认识自己。2016年,谷歌的围棋机器人AlphaGo相继战胜人类棋手李世石和柯洁,一时间人工智能产品在智力上可能会超越人类的说法甚嚣尘上,而这种观点所带来的恐慌也使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主体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并未表现人与机器人的对立,克拉拉也从未想过替代乔西,她所探索的仅仅是让乔西及其身边人如何感到快乐。在乔西患病后,克拉拉向太阳祈祷破坏那些制造污染的机器人,甚至不惜献出体内重要的液体,以帮助乔西康复。克拉拉意识中的“神话思维”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打动读者,促使读者去回忆人类思维的缺失,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
小说中太阳的意象反复出现,克拉拉对太阳的崇拜一方面宣告着自己与人类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展现着自己意识中“神话思维”的影子。小说就是在这二者间的张力中不断呼唤读者去思考,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意识的生成?如何弥补人类自身意识的缺陷?
克拉拉虽然只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成事实,也许不久之后,类似克拉拉的机器人终将问世。但在此之前,石黑一雄用他独特的创造力和艺术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思维的契机,或许通过与克拉拉的对比,人类能够在反思中探索出一条“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共生的道路。
四、结语
《克拉拉与太阳》延续了石黑一雄的国际化主题,表现出对当代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深刻思考。透过克拉拉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的繁荣和生产力红利的同时,也自我阉割了个体完整的意识和思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二元对立之中难以自拔。一个世纪之前,在米德等人类学家的努力下,我们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并在丰富的田野资料中生成了对不同文化模式进行对比的可能性。今天,在石黑一雄富有创造力的故事中,我们得以在克拉拉的“主体意识”与人类“主体意识”的对比中去思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主体性何在,以及思维中失落的部分该如何打捞的问题。这也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迎来的一个反思自身思维局限性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