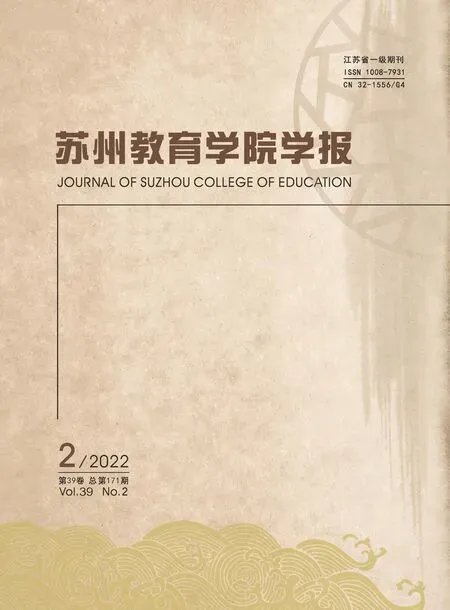民国报刊所涉龚自珍接受及其新变探析
房启迪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浙江仁和人)是中国近代史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其思想、文学成就都对后世影响颇深。民国时期,与龚自珍相关的文献资料层见叠出,有许多与龚自珍相关的材料散见于民国报刊之中,笔者姑且称之为“民国报刊的龚自珍接受”。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12年至1949年,民国报刊中所涉及龚自珍的材料有两百余则,这些材料直观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学者与大众对龚自珍的接受情况。由于梁启超对龚自珍学术地位的推崇以及南社诸子对定盦诗歌的追摹,使当今学界对民国时期龚自珍接受的探讨多集中于此。相对而言,民国报刊中所反映出的更为广阔的龚自珍接受却常为当下学者所忽略。本文梳理了民国报刊中与龚自珍相关的文献材料,并对民国报刊的龚自珍接受进行探讨。
一、民国报刊中龚自珍接受的“热点”
民国报刊中两百余则与龚自珍相关的材料,涉及龚自珍的生平思想、作品分析、著述版本、和韵集句、新书推介、会议纪要等方面内容,而其“热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龚自珍生平的讨论、对龚自珍著述的考证、对龚自珍作品的品评、“集龚”诗的风靡。
(一)龚自珍生平之讨论
就龚自珍生平考证来看,朱杰勤的《龚定盦年谱》[1]和沈寐叟的《龚自珍传》[2]都对龚自珍的行年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周铭谦《龚定盦》[3]、洪焕椿《清代学者龚定盦之生平与著作》[4]、朱杰勤《龚定盦研究》[5]等视野较为宏阔的论文均有较为详细的龚自珍小传。由于龚自珍去世时间距民国仅数十年左右,且自嘉道以来龚自珍一直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其生平行迹相对较为清晰,诸家对其字号、生卒年、世系的考证并无太大出入。洪焕椿指出《光绪杭州府志》中记载龚自珍生平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为“称敬身为段女夫,敬身实系丽正之误”;二为该地方志误称龚自珍为“道光三十年进士”,龚氏实为道光十九年进士。[4]不过,民国报刊中诸家所载龚自珍行年未有从《光绪杭州府志》之误者。就交游考订来看,上述年谱或小传所涉及龚自珍交游对象大体相同,如上述文章均据《王仲瞿墓志铭》考证得知龚自珍十八岁与秀水王仲瞿订忘年交。另外,《龚定盦研究》一文据龚自珍所作《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指出“定菴平生师友以常州派为最多”[5],并述其与常州派之渊源;而《清代学者龚定盦之生平与著作》则据“阮公耳聋,逢龚则聪”之笑语指出了龚自珍与阮元的密切交游[4]。以上生平与交游考证或提出新解,或因循旧说,进一步深化了对龚自珍生平的研究。
民国学术报刊中对龚自珍的世系、交游、行年等考证较为翔实,民间小报对龚自珍的奇情趣事也多有关注。龚自珍是一个个性鲜明、感情丰富的人,他的经历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而这样的名人轶事正与报刊这种大众传媒的传播需求相互契合。朱衣在《龚定庵诗词中的恋爱故事》记龚自珍曾有“长林丰草间,所居的自然是惑狐兔”[6]的僭越之语,以展现其疏狂不羁的个性。孔阳的《龚定盦对书法之牢骚》载有龚自珍因“不善书”而仕途不顺,龚自珍对此多有不满,“并督令其女其妻其妾其婢,悉学馆阁体”[7],以讽刺不看文章只看字的主考官,从中亦可见其玩世不恭的性格。龚自珍的情事最为扑朔迷离,学界对龚自珍的情感经历众说纷纭。朱衣《龚定庵诗词中的恋爱故事》一文对龚自珍情感经历叙述尤为详尽,朱衣认为,龚自珍先后有杭州同乡高华、奕绘侧室顾太清、妓女小云(又名灵箫)三位恋人,并将龚自珍所作情词以及《己亥杂诗》中的情诗分别对应于三人加以佐证[6],虽有些牵强附会,但仍可为一家之言。除此之外,又有小报中佚名之《龚定盦罗曼史》记龚、顾二人唱酬之情事的只言片语[8],而周策纵《龚定盦的诗和词》一文提及此事则认为,当时与龚自珍唱和之人“本江南故家女,后冒充满洲姓为西林氏”[9]。民间小报所刊载的龚自珍奇情趣事或摘自野史笔记、或以讹传讹,仅可作饭后谈资,并不具备研究考证价值,但这些奇闻逸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众对龚自珍的接受,增加了这位思想、文学大家在民间的热度。
(二)龚自珍作品之考证
民国报刊之文多涉及对龚自珍著述版本的考证。洪焕椿《清代学者龚定盦之生平与著作》一文考证了龚定盦诗文集版本的传藏和存世情况:“魏氏所定定盦遗集,今不得见,后世刊行者,同治间有钱塘吴晓帆(煦)所刻之定庵文集三卷,续集四卷,又补刻文补一卷,诗三卷,词二卷。光绪间有平湖朱氏刻补编四卷,商务印书馆并据以影印入四部丛刊中。”[4]又“吴江薛凤昌复以邃汉斋校订本付之排印”“近人杭县丁辅之藏有龚定盦先生集外文二册,系仁和魏稼孙手钞谭献录存本”[4]。周铭谦《龚定盦》一文指出定盦文集尚有嘉善张氏所校刊的《娟镜楼丛刻》中的《定盦遗著》和《定盦年谱外纪》两种[3]。刘大白则记其从绍兴王氏书商处所得龚自珍《红禅室词》钞本,认为此本为当时所通行的定盦词集《无著词选》的初稿,卷首有定盦《自题红禅室词》绝句三首,亦具文献价值[10]。此外,朱杰勤关注到了久为人所忽略的龚自珍的金石家身份,他在《龚定盦之金石学》一文中考证了龚定盦的金石学渊源及金石学成就,定盦共有金石学著作九种,虽已散佚,但有多篇金石文章传世[11]。诸上学术成果,为现代学者考证龚自珍著述的版本源流情况奠定了基石。而在佚文辑录方面,《中华小说界》收《根香室杂拾》一书中的《龚定盦逸文》一篇,内中辑录吴昌绶所藏龚自珍文《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一篇[12];《中国学报》收龚定盦集外文二首,亦来自吴昌绶藏本[13],为龚自珍诗文的辑佚提供了线索。
民国报刊中也有对龚自珍作品本事的考证和讨论。张荫麟和温廷敬二人曾在报刊上就龚自珍《汉朝儒生行》一文的本事发表过各自的观点,张荫麟认为,“关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绾军符矣”所指为岳钟琪事,以此为中心,张氏提出《汉朝儒生行》一诗是“定庵生平对清朝之一段腹诽恶诅”[14],并逐句进行了阐释。而温廷敬则认为张荫麟的观点“诬罔古人,迷误后学”,并在《张荫麟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辨正》一文中,从岳钟琪的生平、龚自珍生平及此诗的写作环境、词义词源等方面进行考证,对张氏之观点进行了逐一辨证[15]。这种深入文本的考证分析,为民国时期龚自珍研究之一大亮点。此外,对于龚自珍《己亥杂诗》的考证,柳总持曾在《前线日报》上辑录了龚自珍写给吴虹生的一封书信,这封信详细叙述了龚自珍出都南行一年的行程和心迹以及《己亥杂诗》的创作经过[16],对考证龚自珍《己亥杂诗》的本事及其行年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龚自珍作品之批评
对龚自珍作品的批评在民国报刊中也是数量颇丰的,从批评形式来看,对龚自珍作品的批评,既有郁慎廉的《读龚定盦集有作》[17]、林瑞铭的《题龚定盦诗集》[18]、曹民父的《读龚定盦诗集》[19]、谷僧的《题酉谷定盦诗钞卷》[20]等论诗诗,也有如周策纵的《龚定盦的诗和词》[9]、朱杰勤的《龚定盦研究(中篇):诗人龚定盦》[21]、方子川的《性灵词人龚自珍》[22]等研究论文。从批评内容来看,由于龚自珍诗词风格多样,或庄或谐、或豪或婉,在近代自成一家,因而民国报刊中有视野较为宏阔者,能兼及龚自珍诗词风格的多个方面,如郁慎廉《读龚定盦集有作》一诗论定盦诗歌风格云:“十年前喜读龚诗,哀艳雄奇动我思。一自海潮皈佛后,闲情刊罢罢枝辞。”[17]方子川认为龚自珍的作品风格具有阶段性特征,“他少年的作品多缠绵,中年的作品多豪放,暮年的作品多带禅机”[22]。周铭谦论龚自珍诗词云:“他的诗很冷峭,忽如山谷,忽如佛家的偈言。为词力学温李,然而功力尚不及。”[3]以上论述总括了定盦诗词哀艳缠绵、豪放雄奇、佛情禅理的三大风格特征。此外,少数学者或以独特的角度对龚自珍的诗词予以探讨。《龚定庵诗词中的恋爱故事》即从恋情词角度研究龚自珍诗词[6],刘佩韦认为龚诗《午梦初觉怅然成诗》“所含情味”,为诗境中有禅意的“绝好示例”[23]。
民国报刊中的“集龚”诗也是龚自珍接受的一大“热点”。朱家英在《论晚清民国的“集龚”诗》一文中对“集龚”热潮进行过详细论述,他提出:“晚清民国时期,‘集龚’成为风行南北的文学活动,在短短几十年中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集龚诗作……参与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创造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现象’级事件。”[24]集句诗为游戏性质的逞才创作,作品的文学价值不等,通过数量庞大的“集龚”作品,也可见时人对龚自珍作品的认同。
通过上述民国报刊所涉龚自珍接受的“热点”可以发现:第一,民国时期对龚自珍的研究承袭了传统的治学方式,在考证龚自珍生平、著述版本、作品本事方面均有较为丰富的考据成果;第二,对龚自珍作品的批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能兼及龚自珍创作的不同风格;第三,民间小报对龚自珍奇闻逸事的刊载以及“集龚”诗的盛行也反映了龚自珍在普通民众心中具有较高的接受度。
二、民国报刊龚自珍接受的新变
民国时期社会的巨大转变对文学接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报刊作为民国时期新兴的传播媒介,具有其自身特色。从内容来看,传统的文学接受史材料以唱和、评点、选本为中心;民国报刊所刊载的内容则涵括了学术研究、诗文批评、诗词文选、诗文再创作等各个方面,在杂糅传统接受史材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名人轶事等内容。从创作与接受的群体来看,传统的接受史材料以文人为主体,唱和诗词、诗文评、选本的传播也多发生在知识分子群体之间;而民国时期报刊行业的新兴则拓宽文学的通道,文学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也胜于前代。从创作目的来看,评点或选本多为阐释词论家的文学观念;由于报刊的便捷性与传播的广泛性,则肩负着更多舆论宣传与导向的使命。文学观念的更迭、意识形态的激荡以及传播媒介的变化使得民国时期的龚自珍接受产生了新变,多重因素促成了龚自珍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
(一)对龚自珍思想的进一步体认
龚自珍虽精于小学,然而他对考据训诂之学多有不满。后受公羊义理影响,留心经世之学,以文章作政论,开学术思想史风气之先。龚自珍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乾嘉汉学向现代学术过渡的关键人物。晚清公羊学盛行之时,龚自珍的地位就已被深刻体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均有涉及。民国时期,龚自珍的多元性思想被进一步挖掘。孔繁信《龚自珍的经世思想》一文指出了龚自珍思想产生于经济不振、内政衰微、排外风气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在此背景下,龚氏提出了安边、移民、重农等策略,文章对龚自珍的经世思想作了详细阐释,颇有观照当下之意。[25]胡秋原之文论及龚自珍思想则认为:“此为旧社会文化惰性庞大之表现,亦国运人才之悲剧……亦望当世之为学者,弘毅任重而道远,能不为过去之幽灵所惑也。”[26]由此可见其对未来社会之展望。
与此同时,随着民众救亡图存之心日炽,龚自珍诗文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进一步阐发。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民国报刊中有大量的文章关注到了龚自珍的地理学作品以及西北舆地学方面的成就。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亡情绪高涨,雪松《充满民族思想的一篇文章—龚自珍的〈说居庸关〉》一文对居庸关的险要与龚自珍《说居庸关》中的民族思想与亡国悲哀论进行了阐发,以宣传“三民主义”,呼吁民族解放。[27]沈北宗《从龚定盦说起》一文中以龚自珍对西北与蒙古的创议出发针砭时弊,以引起当政者对西北地区的重视。[28]杏村《龚定盦与西北舆地》一文指出“其对舆地学之钻研亦属精湛,而尤以西北舆地之研究为最”,并在文中对散见于龚定盦文集中的西域舆地著作作了梳理与介绍,以期对“近世之开发西北、垦殖西北”有所启发。[29]由于民族意识的增强,人们的地理版图意识加深,对地理学著述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因而民国报刊中有许多地理类索引目录,这些目录可检索到龚自珍地理类作品,如王重民的《清代学者地理论文目录》可索引至《定盦续集》中的杂说《说昌平州》《说居庸关》《说张家口》以及游记《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30-31];朱士嘉与陈鸿舜的《西北图籍录—新疆》一文可检索到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32]。唐景升的《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则对龚定盦的《蒙古图志》作了简单介绍[33]。
(二)龚自珍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文学思想的传入,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民国学者与大众开始以西方理论和世界视野看待龚自珍及其作品,对龚自珍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深入。一方面,他们将西方文学理论运用到了龚自珍的文学批评之中。《龚定盦的诗和词》一文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阐释龚自珍生物学上的人生观,周策纵认为龚自珍“岂徒庸庸流,赍志有贤圣”之语以及“继志与述事”的理想,“都是暗合于天择类择之理而发生的意见”。[9]又有朱杰勤《龚定盦研究》一文将柏拉图的“灵感论”运用到龚自珍的诗歌解析中,以此来解释龚自珍的天才与狂放,又以亚兰坡、兰姆等人对梦的解析来解释龚自珍诗歌中的梦与幻境。[21]另一方面,学者们又把龚自珍置于世界文学的视野下进行审视。周策纵的《叔本华与龚定盦:两位爱情上失意的怪人》一文认为,龚自珍与叔本华更为相像,他们有三方面的相似之处:第一,生平经历相似,二人的情感生活都不如意;第二,性情类似,二人都放诞孤僻,与世俗格格不入;第三,思想相通,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34]运用西方文艺理论解读中国作家的研究方法或可商榷,但这类研究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学者研究视野的扩大与新方法的尝试。
在提倡白话文学的背景下,有学者引龚自珍之语以证自己的观点。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以龚自珍“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为理论依据,认为语录皆心上笔下忽然之言,出于心声,以此来阐明语录体可矫正白话文周遭浮泛、不切实际之弊病。[35]蒋善国在讨论文言和白话时以《穷见》一文为例,提出“文言里面,虽然也有这种行文的方法,但跟这篇纯乎不同。如墨子的明鬼篇,非乐篇,和公孙龙的白马论,龚自珍的说居庸关……差不多都是这种行文的方法”[36]。龚自珍的《说居庸关》虽与当时的短篇小说行文方法类似,但无白话之特点,以此证明文言与白话的相通与相异之处。陈友琴以龚自珍《记王隐君》结尾“桥外大小两树,依倚立,一杏,一乌桕”为例讨论文章结尾的写法,这一结尾与果戈里小说《外套》、叙事诗《木兰辞》结尾类似,属于补充性质的“尾殇”,使得文章更为灵动。[37]在倡导白话文的风潮之下,“诗的解放”“词的解放”也是当时热议的话题。在诗词解放这一议题上,周策纵《龚定盦的诗和词》一文指出,龚自珍的诗词不因格律体裁而减色,以此提出了自己“诗词融通”的主张:诗须用词的句法,不呆板;词应像诗中长短句一样,废去一成不变的词谱,同时需要保留“气”和“韵”两大要素。[9]
综上,民国报刊的龚自珍接受出现了新变:其一,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得民众救亡图存之心日炽,龚自珍经世致用及民族主义的思想得以阐发,龚自珍的舆地学成就得到关注。其二,民国时期的文化转型也使得龚自珍研究呈现出新的风貌,一方面,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民国学者尝试运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龚自珍作品,并出现了将龚自珍与外国作家并论的文章;另一方面,在白话文兴起的背景下,民国学者在探讨文言与白话时也常涉及龚自珍作品。
三、民国报刊龚自珍接受的意义
综而论之,从民国报刊材料来看,一方面,龚自珍在文人群体中的热度依旧没有褪去,与龚自珍相关的文献考据、义理阐发、批评唱和等传统接受材料在民国报刊中仍然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文人轶事、中西比较、文白探讨等迎合大众需求的内容也为龚自珍接受增添了新的元素。民国报刊中龚自珍接受材料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具有多重文化意义及史料价值。
第一,民国报刊的龚自珍接受,既折射出民国时期的文学追求和审美趣味,也为龚自珍的经典化积累了丰富的材料。龚自珍能够成为近代史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与他身后百年的接受有着密切的关联,民国时期正是龚自珍接受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上文梳理了民国报刊的龚自珍接受及其新变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其一,学者对龚自珍生平和作品的考证虽相较于晚清时期稍有减弱,但从未消歇,而民间小报对龚自珍奇情趣事的传播使得龚自珍在民国时期一直是“话题人物”,这也推动了大众群体对龚自珍的接受。其二,龚自珍的思想、文学观点、文学创作恰好与当时涌入的西方文学思潮以及新兴的白话文体有相通之处,因而接受者能够挖掘出龚自珍作品中的“现代性”元素,完成新旧之间的“嫁接”,这也使得龚自珍作品在新旧转型时期更容易被广泛接受。其三,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政治背景下,龚自珍民族主义的思想与经世致用的主张,在当时得以充分阐发并日渐深入人心。
第二,民国报刊的龚自珍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龚自珍研究之基石。回望民国时期的龚自珍研究,可了解当下龚自珍研究之发展空间。民国学者研究龚自珍时,既能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出发考证其生平、著述、学术渊源,又能够尝试用新的文学理论对其作品进行阐释,从文献学与文艺学两个方面奠定了现代龚自珍研究的基石。现代龚自珍研究,多专注于龚自珍的生平考证、文学研究与思想探析。主要成果有孙文光和王世芸的《龚自珍研究资料集》[38]、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39]以及相关的博士、硕士论文。近年来,龚自珍的舆地学成就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出现了《龚自珍治疆思想研究》[40]、《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41]等学术论文。但是,相较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当下对龚自珍的研究较少从微观视角切入文本并予以阐释。如研究者从龚自珍诗文本事考索、龚自珍诗词意象的阐释、龚自珍作品的语言结构等角度入手,或许有新发现。
第三,就接受史研究而言,可以进一步挖掘民国报刊所载材料以补当下接受史研究之不足。当下学界对接受史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尽管《定庵诗的经典化历程及其文学史意义》[42]、《文学史的选择:论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43]、《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44]、《龚自珍的接受研究—以晚清、五四为中心的考察》[45]等研究论文均涉及民国时期的龚自珍接受,但这些成果多关注维新派、革命派中名流研究龚自珍的成果,而忽视了民国报刊中所反映出的更为广阔的龚自珍接受成果。
本文择其精要,大致梳理了民国报刊中的龚自珍接受“热点”及其新变,以期弥补这部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