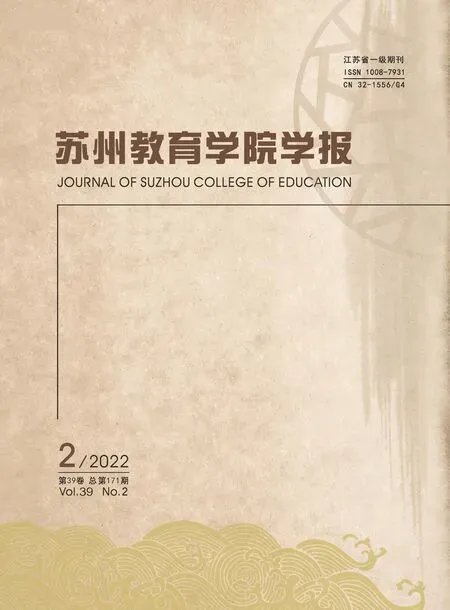生活书店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发行
陈丽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社 编辑部,上海 200083)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在文学史、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中,都是很重要的事件。不过,以往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编辑体例、序言等方面,而对它的发行工作则涉及较少。然而,在现代的图书出版活动中,除了编校工作,广告宣传、发行等对于出版这样一项具有商业性质的系统性的文化活动来说也至关重要,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出版活动都不可能顺利完成。1938年版《鲁迅全集》皇皇二十册、六百万字,它的编校和印制工作固然是一项大工程,同时,在发行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交通不畅、人们生活穷困的抗战时期。
一
1938年7月7日,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谈到《鲁迅全集》的发行工作:“复社工作,总揽其成者,为胡愈之、张宗麟两先生。在全集出版时,张先生全部精力,几近放在发行方面。……推销方法、分社友与非社友两种。凡愿为复社会员,得由本埠各社会团体介绍,廉价订购。其用意无非使鲁迅精神得以深入购买力较弱之各阶层。非会员则由通易信托公司,远东图书杂志公司,新新公司等代为豫(预)约。……至外埠推销情形,虽不甚详,但华南方面得茅盾、巴金、王纪元等先生热心号召,成绩亦斐然可观。”[1]这篇文章比较详尽地记述了《鲁迅全集》背后的运作者,发行的方式、方法以及效果,是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当年《鲁迅全集》发行工作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从中我们大体可以得知《鲁迅全集》在本埠(上海)的发行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复社会员征订;二是由图书公司代售;三是通过有名望的好友推销。而外埠(上海之外的地区)的发行情况,许广平只提到了茅盾、巴金、王纪元等人的热心号召,却没有提及负责《鲁迅全集》外埠发行的总经销方—生活书店—的情况。
作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外埠发行总经销方,生活书店的地位自然是很重要的。另外,从全集的发行数量上看,也可知生活书店实现的销售数(预约数)并非不值一提。据参与者回忆,当时所有渠道实际的预约数为“普通本预约达二千三百部,其中上海约占一千部,内地各处一千三百部。纪念本共销去约一百五十部”[2]。而在1938年10月15日的生活书店内刊《店务通讯》“第三十号”中记载了生活书店所代理的《鲁迅全集》预约数:“直至九月初,粤店始将全部通知单集齐,合计各店预约总数为一千三百零二部,可是与我店和复社最后交涉预约一千三百部之数还差二部。”[3]251由此可知,《鲁迅全集》的外埠经销完全由生活书店负责,实现的销售数也几乎占据了总销售数的一半。可以说,如果没有生活书店,一方面,外埠的读者很难阅读到《鲁迅全集》;另一方面,《鲁迅全集》能否顺利印行也是未知数(一千三百部的预约金可以提供印刷《鲁迅全集》的纸张和费用)。
需要说明的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同时印行了三个版本,即普通本(丙)和两种纪念本(甲、乙)。生活书店经销的只是其中的普通本,普通本如同现在的精装本,硬面布脊,书名烫银。纪念本甲种“文字用道林纸,插图用铜版纸,并用布面精装,书脊烫金。每部实价连运费计五十元”,纪念本乙种做工更精美,“用皮脊烫金,附柚木书箱一只,实价连运费计一百元”。[4]纪念本每种印刷两百册,与普通本的发行方式不同,普通本通过书店代销,而纪念本则由鲁迅纪念委员会负责直销。
因为普通本印数较多,生活书店为了促销,增加预约数,便有计划地在媒体上进行了充分的广告宣传。这些广告不是统一制作的,而是根据不同的媒体性质,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比如,生活书店曾在1938年7月1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发布了《鲁迅全集》的预约广告,广告上的图书信息简明扼要:“全书六十种·计五百万字 分订二十巨册·硬面布脊”“全书定价二十五元,六月底前预约仅收十四元。另加寄费二元。愿(原)在香港或上海取书者不收寄费”“预约处:各地”。[5]之后汉口《大公报》从1938年6月25日开始,一直到预约截止日,连续七天,每天刊登生活书店的预约广告,这七期的预约广告语与《新华日报》刊登的预约广告高度相同。有研究者认为,汉口《大公报》这样高密度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仅汉口一地就预售了一百部。[6]
而刊登在1938年6月18日和7月1日香港《申报》的《鲁迅全集》广告则采用了另外的形式和内容。在呈现形式上,更有设计感;内容上也更丰富。在长方形的版面中,最上面的是大字标题“中华民族的火炬 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左边是极具煽动性的广告语“三十年著作网罗无遗 文化界伟大成就 新文学最大宝库 出版界空前巨业”;中间正文是“鲁迅先生对于现代中国发生怎样重大的影响,是谁都知道的,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的大火炬,领导着我们向着光明的大道前进。只是他的著译极多,未刊者固尚不少,已刊者亦不易搜罗完全,定价且甚高昂。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使人人均得读到先生全部著作,特编印鲁迅全集,以最低之定价,(每一巨册预约价不及一元)呈献于读者”;并嵌有图书的关键信息,像预约价、预约截止日期,还有出版日期(分三期),“第一期(五册) 六月三十日”“第二期(七册)七月三十一”“第三期(八册) 八月三十一”,下方是“备有精美样书 请向生活书店索取”“总预约处:各地生活书店”字样。①参见:香港《申报》1938年6月18日第1版。
由上面这几则广告可以看出,当时复社和生活书店在投放预约广告时,将重点放在了上海、汉口、香港这样的大城市,虽然上海当时已经沦陷,但还是有很多文化人选择留下来,而汉口和香港则因为战争,有大量文化人涌入,所以,在这些文化人聚集的城市,发布图书预约广告,针对性强,可谓有的放矢。而一千三百部的预约量也证明了这样的宣传策略是成功的。
二
据许广平和茅盾回忆,最初他们计划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而且已经签订了合同。但后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日军轰炸机炸毁了商务印书馆总厂。于是,鲁迅纪念委员会便另选定复社作为出版方,那么为什么复社会选择生活书店作为《鲁迅全集》的外埠经销商呢?要知道即使商务印书馆实力受损,当时也不乏比生活书店规模更大、发行渠道更广和更成熟的书店。虽然笔者并没有发现参与其事者直接谈论复社选择生活书店缘由的回忆录或书信材料,但却有诸多间接的材料来推断如此选择的原因。
首先,复社决定选择生活书店经销《鲁迅全集》,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胡愈之。胡愈之不仅是鲁迅在绍兴任教务长时的学生,而且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胡愈之还和冯雪峰、宋庆龄主持成立了“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所以,于胡愈之而言,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事宜奔走大约是责无旁贷的事。《鲁迅全集》的出版方是复社,而复社与胡愈之之间的渊源也颇深。据郑振铎在《记复社》中回忆,“当时,几个朋友所以要办复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复社办公处就设在胡愈之和胡仲持住处,经理是救国会的张宗霖,“社长由胡愈之担任”。[7]生活书店方面,虽然胡愈之在生活书店没有实际职务,但却切切实实地参与了很多重大事务的决策,正如他所言:“我于一九三一年第一次在上海和韬奋会面。以后邹韬奋等办刊物,创立生活书店,办《生活日报》,参加救国会运动,有大部分是和我一同商量或一同工作的。”[8]更直接的证明材料是《店务通讯》“第三十号”中记载的内容:“我店代理预约的鲁迅全集,当初由徐先生与复社代表人胡愈之先生商定办法,并由港店甘蘧园先生与复社驻港代表王纪元先生就近接洽一切……”[3]250徐先生即当时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而在这次合作中胡愈之为复社的代表,共同商议合作的办法。如果没有胡愈之这层关系,经销《鲁迅全集》的有可能就是另一家书店了。
其次,复社的选择也同生活书店在全国分店的布局有关,抗战时期邮寄不便,如果书店网点众多,便可保证图书顺利流通。对于《鲁迅全集》这样耗资巨大的多卷本图书,保证一定的销量至关重要。
1932年至1937年,生活书店虽然已经开设了几家分店,但并没有在全国大规模扩张。1937年9月,生活书店第二十次常委会决定:为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大量出版战时读物,在国内大中城市设立分店。总店迁往当时的政治中心武汉,同时把大量的干部分配到外埠开展工作,“建立全国发行网的计划由徐伯昕经理负责筹划,每个分支店配备经理和会计各一人”[9]42。此后,生活书店加快建设分店,到1938年5月,在生活书店第二十四次常委会上,经理徐伯昕报告,已增设西安、重庆、长沙、桂林等分店、办事处15处。同年6月,在第二十五次常委会上,徐伯昕提出分区管理这些分店的办法:西北区—中心在西安,包括兰州、南郑、天水;华西区—中心在重庆,包括成都、贵阳、万县、宜昌;西南区—中心在桂林,包括梧州、长沙、南昌、衡阳;华南区—中心在香港,包括昆明、上海、广州、新加坡。[10]40生活书店在1938年和1939年两年内迅速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分店及办事处达52个,临时营业处3个,还有9个流动供应处。这些发行据点,遍及后方14个省份,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四省外,各省都有生活书店分支点或办事处”[9]4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期间,生活书店短时期内能够在全国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发行网络,与其创新的“流动供应处”有关。在1939年7月22日《店务通讯》“第五十七号”上,店员鲁昌年介绍了他们在沙市设立流动站推销图书的经历,概括而言,就是一两位店员带着图书、行李轻装上路,到某个可能有购买群体的小城镇,临时租个小门面,或者直接当街摆一个铺位,横布招牌一立,就开张了;有时也会兜售给当地的小书店。这种方式经营灵活,成本低,可以开拓空白市场,但是店员要积极热情,能够吃苦耐劳,这种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当时其他出版社中是罕有匹敌的。[3]692-693
正因为生活书店在短短两年左右建立了覆盖范围极广的发行网络,广州、上海、重庆、汉口印刷的图书才可以通过这个发行网络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手中。所以,生活书店才能够在三四个月内征集到一千三百部《鲁迅全集》的预约单。
再次,抗战时期,外埠订户汇款到上海,汇费非常昂贵。而复社让生活书店负责发行,可以打消订户在这方面的顾虑。因为,早在1934年9月,生活书店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新华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诚银行、大陆银行、富滇新银行、华侨银行等十大银行就已经签约,这些银行设在国内外的五百多处分支行,一律免收向生活书店汇款购书的汇费。作为回报,生活书店在上述十大银行开设专用账户,汇款记入帐内,按月结算一次。[10]19-20所以,我们在《鲁迅全集》的各类预约广告中看不到对读者汇费的说明,只提到了邮寄费用。
最后,在经销《鲁迅全集》之前,生活书店已经同复社有合作。1938年4月2日《店务通讯》“第十一号”的“文化情报”栏目登有“复社出版之‘西行漫记’初版印三千册,业已售罄,再版将由本店总经售,在广州印行”[3]46。这也为双方再次合作提供了可能。
三
此次生活书店与复社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出现诸多波折与误会。虽然当年合作参与者的回忆文章、日记和书信均没有记录双方之间的摩擦,但《店务通讯》记载了这次合作波折。《店务通讯》是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1938年1月22日在汉口出版第1期,1941年1月31日在重庆停刊,共出版108期。生活书店出版这份刊物主要是为了应对抗战初期各地分店骤然增加,书店在组织管理、日常工作和人事方面出现了沟通困难和脱节的问题,所以《店务通讯》是“报告一些关于总分店办事处的业务进行计划、出版界消息、文化人动态,以及各店和办事处的扩展情形、同仁的生活近况等等”[3]1。
《店务通讯》记录生活书店与复社合作的信息主要在“第十九号”的《总管理处通告》、“第二十号”的《“鲁迅全集”预约的周折》、“第二十四号”的《编译出版消息汇志》、“第二十六号”的《出版消息》、“第三十号”的《〈鲁迅全集〉另定通知读者取书办法》和《预约〈鲁迅全集〉之困难重重》、“第四十六号”的《出版经售》这六期中。或许“第十九号”之前几期也曾出现过对于《鲁迅全集》发行工作的记录,但遗憾的是现存的《店务通讯》遗失了“第十五号”至“第十八号”。所以,我们只能对上述六期内容进行分析和讨论。
在1938年7月30日“第十九号”的《总管理处通告》中,通告各分店办事处事务时有这样一条:“本店预约鲁迅全集计一千三百部,应付国币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元,除已汇出三千三百元及新华透支五千元(八月须划还)外,尚须续付八千余元……需款浩繁,务希各店将现款集有成数随时汇寄,以应急需为荷。”[3]96这个通告实际是总店向各分店发出财政告急,要求救助。而总店财政方面的困难很大原因是由于一千三百部《鲁迅全集》的预付款未到位。令人奇怪的是,复社实行预约购书的方式,款项应是来源于读者的预约金,为何会出现需要生活书店总店垫付的情况?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时交通不便,导致生活书店各分店的《鲁迅全集》预约款结算不及时,总店无法将所有预约款交于复社,这可能是后来引起复社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预约款,《鲁迅全集》 便无法印刷。
1938年8月6日“第二十号”的《“鲁迅全集”预约的周折》中则道出了生活书店与复社的合作出现的具体问题。生活书店一方统计的预约数为一千三百多部,但复社仅交付了四百八十部。“经一再电沪要求重版,复社以全集再版版税增加,成本提高,不拟续印……余均一律办理退款,或掣给优待凭单,在将来重版时仍得享受预约价优待权利。”[3]105从这段话来看,双方合作出现问题的原因是,首印的《鲁迅全集》销售一空,而如果重版的话,会造成版税增加,成本增加,所以复社宁可解除合约,退掉预约款,也不愿意重印。据研究者的考证,《鲁迅全集》普及本首印只有一千五百部。[11]而仅上海一地的预约数就有一千部,所以面对生活书店的一千三百部订单,复社只能交付四百八十部,这是符合事实的。复社不愿重印,给生活书店的理由是版税增加,这个理由就要存疑了。因为在1938年10月1日,许广平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全集已出书……但因不景气之故,售价未敢提高;而纸张、印工等等费去甚巨,约二万金。除预约所得,初版尚欠约八千元,生收得版税千元。现虽再版,尚未出书,版税不知何时可有,即有亦不会多……”[12]由此我们可知,因为最初设定的预约价格偏低,而抗战期间,物价不断提升,致使全集印制成本变高,使得首印一千余册盈利困难,这大概是复社不愿重印的最主要原因。此外,《“鲁迅全集”预约的周折》中还提到,“据粤港方面传来的消息,该社疑我店塌便宜货,多为预订”[3]105,这是双方沟通上面的误会,以致出现信任问题。因为在“第三十号”中的《预约〈鲁迅全集〉之困难重重》一文文末附录了一张表格[3]251-252,详细罗列了各分店的预约数,可以用作“塌便宜”只是一场误会的证明。
后来,生活书店根据实际情况交涉,承诺短期内将预付款如期付清,复社才同意即日重印装运。
但到1938年9月1日的“第二十四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又发生变化。“据称因再版时版税提高,纸张涨价,成本加重,至少每部需增收二元,方能付印,拟用复社及我店名义,会同刊登广告或发通告……”对于这种反复情况,生活书店感到非常委屈,“我店此次担任全集预约,一切条件均照复社提出者,一字不易予以签订,全为文化而工作,殊知竟发生如许波折,使我店对读者发生不良印象……”。[3]148但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出版的一切事宜都可以谈判,何况如前所述,生活书店和复社之间有关键的中间人沟通,所以生活书店对复社的要求采取的方法是继续“交涉”。最后以“我店牺牲,每部补贴复社亏本款一元,共一千三百元,全部款项计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元”[3]175,终于在1938年10月8日“第二十九号”中有了交涉结果,“《鲁迅全集》闻港复社已得沪电,全部可在本月初运抵港粤”[3]232。
事情解决后,生活书店在“第三十号”的“粤店杂讯”栏目中,刊登了两篇较长的文章—《〈鲁迅全集〉另定通知读者取书办法》《预约〈鲁迅全集〉之困难重重》[3]249-252—颇为细致地记录了生活书店后续向预订读者邮寄《鲁迅全集》的工作,以及回顾与复社合作以来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按照生活书店方面复盘的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双方的纠纷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来说,生活书店的预约单并非由一家店受理,而是来自香港、重庆、汉口、广州、贵阳、成都、长沙、万县、昆明等多地分店,然后将预约单统一寄至粤店,但战时交通受阻,各分店寄至粤店的预约单时间不一,以致预约数统计出错。主观上看,一方面是因为生活书店总店事先没有周密的办法通知各分店何时和怎样邮寄预约通知单;另一方面,各分店也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店延迟寄出预约单,有的店出现手续错误,尤其武汉店问题较多。这自然是双方合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双方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足,以致后续问题重重。
四
著名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13]一书中重点关注法国大革命前图书的发行运作网络,因为在他看来,在图书出版活动中,服务于出版社的“毛细血管”—分销环节—意义非常。这本著作给了本文极大的启发。1938年版《鲁迅全集》皇皇六百万字、二十大卷,在抗战时期交通不便、读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开拓图书市场,怎样宣传……这些无疑都困难重重,但初版一千五百部、再版一千部,另加四百部纪念本全都销售一空,不得不说其发行和销售是成功的。也正因此,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发行中种种策略、选择、各合作方的沟通曲折才值得我们去梳理和研究。虽然本文只是梳理一套《鲁迅全集》的发行,但以小窥大,也可以看到在抗战非常时期,图书贸易发行体系是如何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