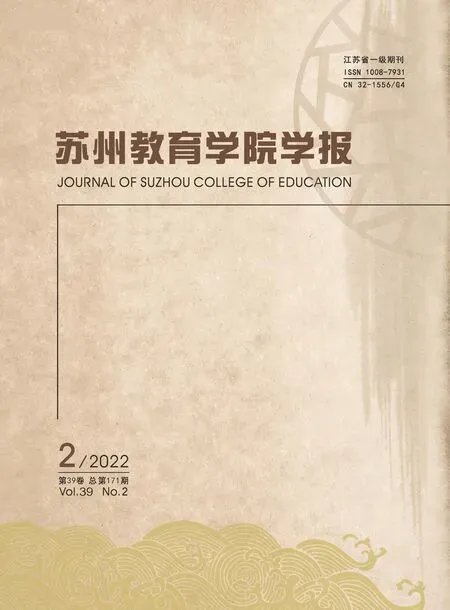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看”与“被看”:《天雨花》中的花园与性别角力
王一雯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12)
明清时期,许多小说、戏曲作品中,都将花园作为情节开展的场所。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花园被转化为可以开展详细叙事的空间场景。德-赛托认为,不同的空间可能呼应着不同的行动主体间的不同关系。[1]“花园”显然是较佳的展演世情的空间之一,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红楼梦》《金瓶梅》等长篇章回小说①如傅腾霄的《小说技巧》(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黄霖、杨红斌编著的《明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分别在不同程度上都提到了古代小说的空间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讲演、杨珏整理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谈到了明清几部“奇书”的时空布局。,对弹词作品的关注度不高。
古代小说中处于花园空间中的男性,往往对“女色”具有观看的欲望。不少男性以此为契机,心生淫念,甚至侵入内房。[2]在女性弹词小说中,庭园也多有连接闺阁与外界、凡俗与他界的功能。物理空间上的庭院、花园都是女性可以暂时摆脱闺门去畅游的空间,也因此受到女性作家的青睐。胡晓真认为,一方面,花园在屋舍平面配置中僻处一隅的特质,昭示了女性的边缘位置,以及其生活空间的闭锁性;另一方面,花园又因地处家宅内、外的交界,而成为诱发女性越界欲望的危险空间,是女性“越界”行为经常发生的场所,甚至由于花园与正房屋舍有所区隔,因此暗示进入其中是对俗世义务的疏离,甚至可以变成女性追求超越经验的神秘空间。[3]141
然而,弹词作品中的花园空间,一般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自由爱情的情节,女主人公追求的是可以自由行动和生存的空间,而“花园”的边缘意义,也是相对于“正位”的闺阁而言的。花园并不能像道观、寺庙或朝堂那样将女性独立于传统秩序之外,女性出入花园间,却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这也使“花园”有了复杂的象征意涵。
一、赏玩与窥视:花园空间的危险性
古代戏曲作品中出现的花园,多用于休闲娱乐。其中,位于住宅后部的花园大都规模较小,位于住宅前部的建筑与后部的花园有着明显的界限—女眷的住所。除了住宅主人,一般人不能穿过女眷房屋的过道进入住宅后部的花园。在一些私人园林中,位于住宅前部或其他别院的庭院是一个更加公开的场所,是可供游人赏景的花园,这类花园的空间更大,常有外客进入。因此,花园也是一种“歌舞升平”的浪漫想象空间,但身处其中的女性又有被男性窥视的风险。晚明小说中的花园往往带有情欲色彩与危险性质。
《天雨花》中,左家拥有大型私人花园,但却园门大开,无人看守,不阻游人。在第一次详细描写花园状况时,作者就把潜在的危险性揭露出来,之后的诸多事件,也都离不开花园这一“危机四伏”的空间。男主人公左维明“游园窥视”的行为虽然为自己赢得了姻缘,但同时也证明了这假山四伏、曲水流觞的花园是一个偷窥的绝佳场所。他先倚定雕栏等候,后又立在小红桥上,遥遥窥望,但看来看去不分明,一行女眷中,全然不见容貌。他认为女眷必定会到迎晖阁上登高远眺,于是决定去丽春堂窥视。[4]20-22左维明认为只有貌美的女子才是自己心中的佳人,他的视角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窥视的持续时间较长,但他窥视的动作又不似其他艳情小说中的那样猥琐,反而显得含蓄风雅,符合明清园林视觉文化对雅致的追求:“去亭中下了湘帘,坐在里边等候。帘外既不能见我,帘中却看得仔细。省得在此来窥探,被人瞧见不相应……凭高视下多明白……”[4]24
虽然左维明窥视的方式比较含蓄,也为自己的行为贴上了一层礼教道德的标签,但这也不能掩盖他窥视佳人的欲望。偷窥这一动作虽然发乎情,止乎礼,却也不符合“非礼勿视”的礼教要求。他有意识地利用园林的特点,用亭中帘子作为遮掩的工具,以达到偷窥佳人的目的,以自己的亲身行为暴露了花园空间对于女性的危险性。在他迎娶桓清闺后,岳母邀请一众女眷前去游赏留春园,桓清闺仍然没有意识到花园的危险性:“既是诸姊妹高兴,又且母命来接,自然回去顽耍一日也好。”[4]97左维明则藉“拾扇”一事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若说内才,乃是一个轻浮子弟,因在园中丽春堂,拾了你一把扇子,上边一面画的是牡丹,一边是牡丹诗一首,又有你落款书名,所以晓得你能诗能画。那轻薄子将诗扇视为异宝,但出来必持此扇,逢人夸说”[4]97。之后又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女子在闺门,岂可出外来顽耍……皆因出外来游玩,致令生出许多因。如何尚不知悔悟,还思出外去游行。一言道及园亭去,满口应承要转程。当日我闻多少话,还有三分不信心;今朝见你情如此,始知果是这般人!”[4]98两人的对话呈现了男女双方在信息量上的不对等以及一般闺中女性的毫无戒心,并且远离花园的训诫在后文中不止一次出现。花园在女性的印象中的确是自由的乐园,而左维明提“拾扇”之事的目的是为了向妻子揭示花园的危险性。但是,他在家中的绝对权力也没能阻止妻女一而再、再而三地踏入这一“禁地”,这与花园的性质以及晚明女性游春赏景的风气是分不开的。
值得玩味的是,左维明的这次花园巧遇,或者说是男主角单方面的偷窥行为,是《天雨花》中第一幕发生在花园中的有关“情”或“欲”的故事,它促成了一段姻缘,但受益人左维明却由此注意到了花园的危险性。作为《天雨花》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左维明仍然会在时机恰当的时候实行偷窥之举,更遑论故事中的其他角色。事实上,如果作者没有用婚姻这一形式来为左维明的一系列越轨举动正名的话,那么,他的正面形象势必会受到影响。
《天雨花》中,除了左维明第一次窥视女性,获得了一段美满姻缘外,花园从来都是作为惹是生非之地出现的,它往往与纠纷、私通等情节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比如,左秀贞的婢女红云托秀贞之名私通住在花园中的外男周帝臣,玷污了小姐左秀贞的名节。《天雨花》中还提到了妓女游览花园的场景。明清时期的青楼具有园林化的特点,青楼内部的园林洁净、淡雅、精致。[5]园林与青楼结合,将礼教、文化与情色相融,暗示了花园这一空间的复杂性。从某个侧面来说,花园的危险性一直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地方,作者意识到了男性的窥视与入侵带来的危险,想要藉此警示闺中女性。
二、女性的矛盾:花园中的性别角力
《天雨花》的作者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采用作者为陶贞怀这一说法。陶贞怀将左维明因“游园窥视”而娶桓清闺的情节处理得很微妙,作为女性作家,陶贞怀掌握了男性的心理,即女性以容貌为重,有才与否只是锦上添花。这类观点由一个女性作家写出,是有特殊含义的,明末清初,社会对于女性群体的“才”的要求逐步增加,陶贞怀在《天雨花》中却没有过分强调女性的才气,这显示了她符合传统礼教的一面。
事实上,明末清初女性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据高彦颐考证,明末清初妇女有“从宦游”“赏心游”“谋生游”等外出游览活动。[6]明中后期女性的“恣性越礼”“游山上冢”等越界行为并不少见,一些明人笔记小说中多记有女性出游的行为,而游览庭园更是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晚明以来,女性对于性别想象的极致,莫过于女性弹词小说中创造的最激烈的越界,即易装进入男性的世界,在政坛和战场上获取荣誉。对于女性读者来说,这是比“花园相遇,私定终身”更有魅力的情节,女性可以从被“窥视”的命运中摆脱出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闺房,施展才华。而女性的这种愿望和追求,都被明末清初的女性弹词作者们清晰地刻画出来。
《天雨花》中,几乎每个重要的女性角色都提议过要去花园玩耍,并要经历一些与花园相关的事件。但是,就算花园中发生过危险的事情,这些女眷还是照去不误。而桓清闺的态度相对于父权象征的左维明来说是比较暧昧的,众姐妹的游园计划所遇到的阻碍往往是在父亲左维明这一方,听说父亲暂时不会归来,姐妹们就兴致勃勃地准备起游园事宜。就像《红楼梦》中,贾母也经常携众人游园,这是明清时期贵族女性的重要消遣活动之一。《天雨花》中的女性,对于庭园空间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她们不愿放弃这得来不易的能够自由行动的空间,这反映了当时女性想要突破和超越的野心。另一方面,同为女性的作者从始至终都知道有男性在对园中的女性“虎视眈眈”,而她笔下的主人公左仪贞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游园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一开始,左仪贞不认为游园会有什么危险,即使有危险,她也倾向于只要消灭园中的危险,女眷们就能安心赏园。故事的最后,左仪贞却变得如父亲左维明一样,认为花园是个危险的地方,不进入园中是最好的选择。
舒 坚 男,1964年5月出生,江西南昌人,南昌航空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CCF高级会员,主要研究方向:无线传感器网络、分布系统、软件工程.
通常情况下,花园被围墙所围,有开放与封闭的双重意义。故事中,女性一开始总把隐藏着不可解释的危险的花园,当作是家族女性共享的秘密福地。此时花园是女性专属的,具有女性的正面特质,弥漫着欢愉与和谐。多数情况下,左仪贞去花园都是受到了邀请,或是跟随长辈、亲戚、客人等一起进入园中,而非是她带头起意。但左仪贞的态度很矛盾,往往开始拒绝而后又欣然同意,如妹妹秀贞提议去花园玩耍,左仪贞只是象征性地推辞一下,便欣然同往。但闯入禁地必会发生危险,《天雨花》中,每一次的花园危险,都发生在女性愉快地观赏完花园景色之后。如在一次花园玩耍后,左家的女性就在园中遇到桃、梅、柳三株树精幻化出的三名男子,他们入夜前来,欲和佳人幽会。[4]473-478这一情节暗示了女性外出会招来“妖精”。《天雨花》故事的开头,俨然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就算女性被奸贼掳去,桓清闺也从来没意识到是花园在“泄露天机”。在此之前,她刚亲身经历了被丈夫窥视的事件,女儿也不止一次在花园中遇到危险。显然作者是刻意想要表现女性在被窥视方面的不易察觉以及薄弱的自我保护能力,以此来提醒女性读者。
花园作为游乐场所,家长们也经常去。左维明更是从小就经常在花园中玩耍。在第十二回中,他和亲友结伴玩赏:“五人当下抽身起,二厅侧弄到园门。一齐徐步闲观玩,绿暗红稀夏景新。”[4]445在他们眼中,花园对于男性应该是绝无威胁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花园也威胁到了男性,男子进入花园,会遭遇到“招婿”的麻烦。在故事的结尾,花园还涉及了男性与政治的问题。花园在《天雨花》中是“危险”的代名词,这里发生过偷情、偷窃、栽赃等事件,又有许多不属于凡间力量的妖怪精魅,其中既有家庭事件,也有国家事件,来自花园的威胁在不断地增大。
左家的女性在花园经历了一系列不祥事件后,对花园有了一定的戒备,不过这还不足以彻底阻拦她们进入花园。桓清闺为了游园和左维明发生了强烈冲突,感叹嫁入左家后便甚少去花园玩耍,之后在左仪贞等人的鼓动下便随她们一起进入花园。桓清闺担心受到左维明的责怪,也怕惹怒妖怪,左仪贞表示自己有宝剑在身,并不畏惧园中精怪。但这一次窥视的主体不是才子也不是妖怪,而是强盗。花园中被窥视的女性基本上没有重复,可以说作者将所有可能性都写了一遍,并且这种窥视的结果是女方信息的全方位暴露。左维明并没有严格地把女眷限制在闺房之内,他认为外书房是一个安全地带,花园则不是,女性合法、安全的行动空间在男性眼中是狭小而有明确界限的。同时,左维明透露,从远处的花园墙外能辨清各个女眷的位置、行动,而在园中四处赏景的女子,却没有将视线投向花园的墙边,这一区域是她们视野中的盲点。
左仪贞对是否应该进入花园的激烈争辩只有一次,此事起因是母亲因游园惹怒父亲而被关在花园里。左维明将园门落锁,称“锁闭汝母花园内,待她游到大天明”[4]887。这对夫妻因花园而不睦的角力相当生动,左仪贞也加入其中,奋起反抗,用宝剑砸锁,破坏花园的物理界限并将母亲解救。左维明让左仪贞代母受过,左仪贞的反抗使得矛盾进一步升级。夫妻二人斗气,夫人故意携人当着左维明的面进入花园,这可以说是对夫权的极大挑战。然而,虽然这是一次对抗男权的行为,但女性却在游览花园权利的问题上妥协了。左仪贞将夫人和众女从花园内接出,但她与父亲的争论焦点却转移到了孝道上,她并不就花园之事多作言说,之后有人再请她游园,她也都表现出了无奈、迫不得已的消极状态。
以上情节都说明了男性势力正在向女性的花园渗透。《天雨花》虽然打破了才子佳人在花园私定终身的惯常模式,却也以“危险”为借口,更加深层地将这一限制与禁锢自由的心理锁链套于女性身上。左维明作为父权的象征,在整个文本中不断地进行宣言:“妇女丫鬟莫乱行。又唤三位娇小姐:儿等今朝听我论,虽然在此无几日,我身去后莫胡行!花园切勿轻身进,中堂切勿擅离门,左右侍儿须警戒,端坐闺中要谨行。”[4]541
左仪贞逾越了闺房的界限,却没有选择像孟丽君那样女扮男装去逾越家庭花园,而是选择留在这片本属于女性,却被男性一再侵入的领地中徘徊。左仪贞对来自花园的情欲挑逗无动于衷,她随身佩戴宝剑,一剑砍去,就让妖精现出了原形。从左仪贞整体的角色性格出发,园中精怪并非是她压抑的情欲变形而成的。相反,她砍杀了象征情欲的妖精,这与传统文人笔记中,作者因恐惧女色而对情欲进行妖魔化处理异曲同工。左仪贞像男人一样,用最直接的方式挥剑斩断情欲。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了她不敢正视个体情欲的一面,体现了传统礼教对她的潜在影响。事实上,左维明的确将她像儿子一样抚养,他曾因女儿等人游园遇精怪一事责怪夫人,却为女儿辩护,此时的左仪贞俨然和父亲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形成了另一种充满张力的性别矛盾。
三、折中与妥协:行动空间与伦理空间的双重限制
《天雨花》中,随着故事情节的一步步推进,女性逐渐丧失了对花园空间的主导权。对于男性的窥视以及一切由于游览花园所经历的危险,女性自身其实是束手无策的,只能采取规避的方式。最后,她们不得不退回到原本封闭女性自由的家庭空间中。而由于男性的窥视、侵入带来的威胁却从未减弱。
首先,女性不得不限制自己行动的空间。随着花园空间一再被侵入,女性自身也由外部的私人园林重新退回到闺阁之内的花园中。她们真正将花园当作女性的专属场域,是在排除一切来自外男的“窥视”危险之后。面对危险,她们只能压缩自由活动的空间,才获得了一个没有男性窥视、入侵风险的空间。经历了一系列危险事件后,最终女子们的活动范围从宅外园林变成了家中花园,尽管少了男性窥视的危险,但花园中依旧存在危险。比如,《天雨花》中,有婉贞不小心把弟弟推入水中这一情节。[4]1027麻烦仍然存在,不过却不再是两性之间的对立,而是花园的建筑结构带来的危险。至此,花园成为左维明成功训诫女性的场所。左仪贞已经屈服了,绝不再涉足那个充满危险的花园;而秀贞因为受到花园私情事件的牵扯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不驯服于女诫,从小寄养给亲戚,后又回到左家的婉贞,十分钟爱游园活动,但游览范围也仅限于家中花园。
不仅是左仪贞,周遭的所有姐妹也都已经转变了对花园的态度。因此,她们在左仪贞提议去花园游玩时提出了质疑,但认同左仪贞要去的理由,即游园是父亲答应了的。花园变成了众位小姐弹琴作诗的地方,就如同大观园一般:“此园系汝曾祖所建,那有妖怪?便有人家,也都是族内,那有人窥?家园一任闲玩耍,再不前来管你们。小姐听了便笑道:‘必须有伴始相应。’”[4]930至此,女性出入花园的自由被她们自己放弃了。
其次,“花园”作为赏玩空间,不再带有情欲色彩,反而成为一个展现伦理和自身道德的舞台。白馥兰认为:“在中国,房屋发挥的一个最关键作用,是用空间标志出家庭内的差别区分,包括对女性的隔离。”[7]复合式的建筑容纳了许多种对于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阐释。在正统父权制理念体系下,男性将空间隔离的原因解释为女性在道德方面天生低于男性,她们的堕落是天性使然,因此需要限制她们的行动来防微杜渐。更温情的说法是,不强调女性与男性在道德上的平等与否,而认为空间隔离是规避女性被引诱的风险的必要手段,男性甚至大部分女性都认同这一做法。《天雨花》中,左维明对限制女性活动空间的规劝主要属于后者。
《天雨花》中,左仪贞进入花园不是为了寻找爱情,她身上固然有传统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温婉娴静的特征,但也隐隐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带有一定男性化的特质,如她会佩带宝剑,勇敢地保护其他闺中女子;敢于与父亲据理力争,挑战父亲的权威;在面对家庭变故时沉着镇定。而花园也成为女性自恃端正的框架,刻意展现贞德的舞台。左仪贞只是游园行为的被动接受者,在危险发生时也可以不必承担道德的指责。
在第十回中,左仪贞在花园中与表兄巧遇,兄妹俩仅是下棋交谈,并无任何越轨之事,但心怀不轨的侍女桂香凭借仪贞落在花园的珠钗就恶意诬陷她不贞洁,左维明相信女儿的人品,调查清楚了这件事。[4]359-396当然并不是一定要在花园发展出情事才是对礼教的突破,但事实上“花园”意象的确经常被用来宣泄自然却不合法的情欲。一般男性作者笔下的才子佳人故事往往是出于满足自身情欲的需要,而女性作家则刻意将笔下的女性向社会所要求的完美标准靠拢。《天雨花》中,具有小姐一类身份的人物从来没有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越界,也从来没有在花园中做出任何和情欲相关的不当之事。她们只是单纯地在游赏花园景色,并从美景中获得诗性启迪以及快乐。《天雨花》中所有的花园私情的当事人都是婢女或妓女这类身份卑下、在当时上不了台面的女性形象。
作者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对于男性远望与偷窥花园的行径一开始并无察觉,一定要通过一次次危险的叠加,她们才会逐渐明白其中的危险性。对于窥视行为的满足机制是“被看的对象并不知道它在被看”[3]155,如果被撞破就无法满足男性的窥视欲望。而弹词作品的作者多是女性,这一创作群体在主观层面上明显感知到了这种窥视,《天雨花》的作者很好地刻画并反复强调了这一现象。女性作者和她笔下的人物都感受到了来自男性的目光。这种窥视并没有将女性作为平等的审美对象进行欣赏,相反,而是把女性身体作为满足自身私欲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对来自花园的危险的认知是出于其暴露于男性窥视下,却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名节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本身并不具有强烈的、独立的反抗男性权威的自我意志。相比自由地游赏,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名节。故事中的女性,她们最初也曾有获得自由行动空间的诉求,如左仪贞曾为母亲能否赏园一事激烈地与父亲对抗,但最终也主动放弃了游园,而不是因多次反抗无果才放弃的。这说明尽管女性作者意识到了男性的窥视,其笔下的主人公也只采取了规避的态度,这反映了女性作家在面对男性目光和传统伦理时的局限。女性将自己约束在这样一种道德要求的范围内,忍受着男性强加于她们的保护贞洁的高度要求。她们在行为和精神上都受到了限制,而本应该充满自由的花园空间也变得几近崩塌、危机四伏,甚至成为女性展现贞节的舞台。来自男性偷窥的危险,却要求女性防微杜渐,这是现代女性所不能容忍的,但确实是当时女性地位的鲜明反映。
弹词故事中的花园既是女性自由行动空间的外延,也代表了女性对外延伸的视角。花园与闺阁构成了第一层物理界限,而女扮男装,走出花园和闺阁是对第二层界限的突破。可惜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要回归原本的空间,以追求最大程度的全身而退。少数女性也有不回归闺阁的越界行为,花园成为一个折中的处所。如《金鱼缘》的作者孙德英拒绝出嫁,选择幽居斗室,屏绝人事,整日念经,“非定省严亲,登堂庆贺,从未离静室半步”[8]。她决定不嫁人之后,不得不用空间的禁闭维系自己生活抉择的道德性。无独有偶,邱心如的《笔生花》①《笔生花》讲述了明代女子姜德华之父遭奸臣迫害,姜德华为救父而同意入宫,进宫途中跳河,不料却被狐仙所救。姜德华乔扮男装出走后,改名为姜俊璧。谢函夫妇爱其才貌,招她入赘与女儿谢雪仙成婚,姜俊璧借口回禀父母后再成亲,谢雪仙本一心学道,二人相安无事。后来姜俊璧历经磨难,赴京应试,得中状元,建功立业,终于与表兄文少霞结为夫妻。谢雪仙不愿出嫁,自改道装,随姜德华回姜家居住静修,后得道升仙而去。中,易装女性雪仙在恢复女儿身后坚持幽居花园,甚至与狐仙结为道友,完全将自己置于常规与秩序之外。因为拒绝婚姻,她伤了父母之心,于孝道有亏,而选择遁居花园,弃绝女性的人生义务,用空间的分隔明确自己已与家庭分道扬镳。这些不愿局限于内帷闺阁中的女性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重新回到花园这一空间中来。花园成为闺房和外界的一个妥协之处。而这些女性的越界行为并不会为她们带来像《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式的传统圆满结局。即使她们选择退居花园,并把这个空间封闭起来,不让其他力量介入,花园也并非坚固的幽居场所。最后能维护这些女性的地位,并让她们的私人空间继续存续的仍然是男性,女性根本不可能倚仗自己的力量建立并维持一个私人的自由空间。
《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性格强势,虽然她没有女扮男装,进入朝堂,但也绝非芊芊弱质。但在故事中,她的活动空间一直局限于家与花园,尽管中途经历了明清易代,她却并没有因此跻身朝堂,也没有任何机会突破花园这一空间,这当然是男权的压力和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选择,陶贞怀的选择是通过对各种花园事件的书写,在各种意义上抹除花园的暧昧属性,花园最终成为女性刻意表现自身贞节的场域。左仪贞曾经站在与父权相对立的角度,对花园持有一种追慕的态度,并以实际行动实现了对权威的真实反叛,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种反抗。作者笔下的左仪贞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但连她都对于这种男性窥视的威胁束手无策,更遑论一般的女性了。
由此可见,女性作家虽然想利用花园空间实现自身的行动和伦理自由,甚至追求更广阔的物理自由空间,实现人生价值,褒扬女性的才能和品德,但最终都只能屈服于男性的权威。在各类弹词作品里,女性和男性在这些空间中的性别角力结果都是相同的,女性最终都会沦为男性的玩物或附属品。这些女性弹词作者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曾经也积极地利用作品进行了探索和抗争,但她们笔下的女性,大多在反抗后选择回到传统性别观念的框架下。女性作者自身的软弱与反抗的不彻底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但其反抗行为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象征着明末清初先进的性别观念的短暂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四、结论
明清以来的戏曲、小说、弹词作品中滋长了一种“窥视”与“凝视”共存转化的趋势。公开游赏花园的行为象征着女性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代表了女性自主与自由的程度。《天雨花》中,自然园林和性别空间互相重合,女性因为充分认识到花园暗含着对自身身体和生命的威胁,经过多次抗争后对男性权威进行了妥协,女性同意只在相对安全的家中花园游览。与此同时,女性人物还将“花园”作为一种展现自身道德和贞节的舞台。
两性的“性别角力”在明末清初短暂地存在过。清代中叶以后的小说作品中,“花园”重新成为文人赏玩、寄托的意象。花园通常是文人公子的居家空间,出现在小书屋的边上。男性的花园和女性的花园意义不同,男性的花园是家园的据点与隐遁的空间,他们在自己的花园中是完全自由的,甚至是充满创造性的,花园是他们隐逸人格的寄托,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布置、游赏花园的每个角落。相比之下,女性在花园中的游赏范围却有着重重限制。与此同时,除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女性“花园”书写的发展渐渐停滞。由此可见,女性在与男性的性别角力中,几乎无法避免最终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