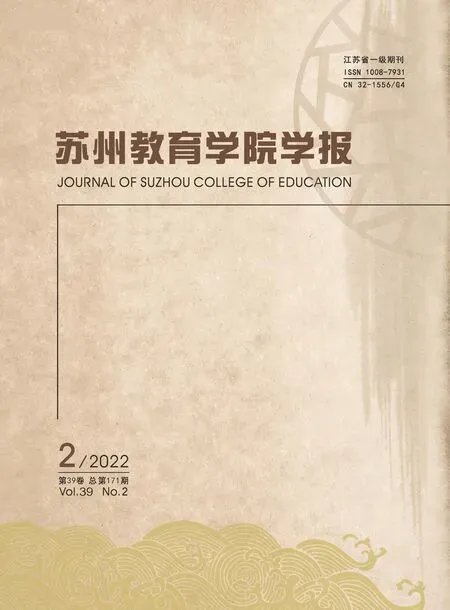玉米和柳粉香形象比较
李 霞,左敦华
(1.北京联合大学 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3;2.北京市人民政府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北京 100069)
毕飞宇“被认为是当代男作家中最关注女性命运的人”[1],从处女作《孤岛》中纯真自然的小河豚开始,毕飞宇就一直关注着女性命运。《玉米》[2]中,毕飞宇描摹出了王家庄的女性众生相,他写出了女人的善良和隐忍、原罪和苦难、伤害和畸变、挣扎和反抗,在极具语言张力的叙事中,他极有节制地把女性内心最深处的欲望与疼痛,以及女性在恶劣环境中无力回天的宿命感呈现了出来。玉米和柳粉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落后的乡村和现代化进程之间,她们是针锋相对的死对头;在压迫与反抗之间,她们又心有灵犀,互相怜爱。
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玉米与柳粉香形象相似之处
在《玉米》中,玉米最恨的就是柳粉香,但在王家庄的众多女人中,她们两个其实是最相似、最能互相理解的。柳粉香说:“我要是玉米我也是这个样子。”[2]37玉米在最痛苦时轻声叫出的那句“粉香姐”更是她们之间的一次和解。她们本可以是一对好姐妹,因为她们有着同样的悲剧命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一)最弱的弱者—匍匐在男权阴影之下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3],而在玉米、柳粉香生活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古老的乡村陋习、残酷的极权政治与世俗的男权力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农村女性普遍的生存环境”[4]。这种环境中的女人只有匍匐在强权之下才能苟延残喘,她们是最弱的弱者。
《玉米》的开篇就定下了男权至上的基调:玉米的母亲一直生女儿,现在终于生了个儿子,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变得有点傲慢了。玉米作为家中长女,在母亲生产时忙进忙出,“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有些明亮,发出难以掩饰的光。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内心的振奋……这份喜悦是那样地深入人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2]6-7,这个家有了儿子后“就不会留下什么缺陷和把柄了”[2]10。作为女人,玉米同样没能逃脱极具弥漫性和渗透力的男权阴影,所以,和母亲一样,在玉米心里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生儿子。在父亲王连方倒台后,玉米美好的爱情幻想也破灭了,她转而投向了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的怀抱,他只是说了句“休息吧”,“玉米这一刻只盼望着郭家兴扑过来,把她撕了,就是被强奸了也比这样好哇”[2]70。为了重新获得男权的庇护,“玉米怀着‘视死如归’的悲壮,屈从了依附政治权力的男性霸权,最终走向了女人隐忍屈辱的命运”[5]。
柳粉香是《玉米》中匍匐在男权阴影之下的另一名女性代表,她漂亮、嗓子好,还曾经做过宣传队的报幕员,心气很旺,处处要强。但是,她嫁了人便成了“有庆家的”,成了男权的附属品,失去了作为女性的主体存在。成了“有庆家的”的柳粉香,本想顺顺利利地生下孩子,做一个本分的农家妇,却被婆婆害得小产。为了给有庆生孩子,她像做贼一样地吃药,可是有庆天生“没有种”,“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2]33。她的悲剧并不止这些,王家庄的最高权力象征—王连方—终于将魔爪伸向了她,她“知道被他睡是迟早的事,什么也挡不住的”[2]32。最终,柳粉香怀上了王连方的孩子,为了保护腹中的胎儿,柳粉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拒绝了王连方,被拒绝后,王连方赤条条地躺在她家被窝里唱起了《沙家浜》,“有庆家的涌上了一股彻骨的悲伤,只觉得自己这半年的好光景还是让狗过了”[2]56。
(二)弱者的武器—对美好爱情婚姻的幻想
爱情、婚姻对于改变女性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布尔迪厄认为:“爱情除了促使她们摆脱男性统治之外,无论在最普遍的形式上还是在最异乎寻常的形式上,都为她们提供了一条社会升级的道路,这通常是唯一的道路。而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婚姻,在男性社会中,她们借助婚姻从低处向高处攀升。”[6]因此,爱情、婚姻便成为女性摆脱弱者身份的重要途径。
当村里和玉米差不多大的姑娘已经“说出去”好几个时,玉米心里也开始“平白无故地陷入了恍惚,憧憬起自己的终身大事”[2]11。玉米的眼光还是很高的,村里几个不错的小伙子,玉米都没有看上。虽然从相片上看,飞行员彭国梁的长相并不好,但因为他是一个“上天入地”的人,便成了玉米心中的白马王子。和彭国梁的爱情,让玉米充分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玉米的‘那个人’在千里之外,这一来玉米的‘恋爱’里头就有了千山万水,不同寻常了”[2]25。但是,千里之外的爱情毕竟太过于遥远、虚幻,玉米想要的是一个如“大地”般坚固的婚姻。柳粉香说,“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2]39,这句话被玉米听到耳朵里去了,玉米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门亲事定下来,把自己变成“国梁家的”,把握嫁人这么“一个机会”,获得女人的尊严,实现自己隐秘的渴望—前程要更好些。然而,玉米的心愿并没有达成,她的期待就像飞行员男友的“天空”一样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父亲倒台后,厄运接踵而至,对爱情、婚姻的期待成为玉米最后的救命稻草,但彭国梁的一句“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2]62彻底打破了玉米的幻想。
想当初,柳粉香必然也曾做过很多梦,幻想过美好的爱情、婚姻。但是在那个落后的封建陋习、残酷的极权政治与世俗的男权力量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乡村,作为一个年轻漂亮、风流妩媚的女人,想要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那阵子柳粉香在各个公社四处汇演,身子都让男人压扁了”[2]30。对于“身子扁了下去,肚子却鼓了上来”[2]30的柳粉香来说,曾经幻想中的美好爱情成了永不可得的镜中月、水中花,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嫁人。柳河庄的柳粉香甚至连一套陪嫁的衣服都没有捞到,便在王家庄成了“有庆家的”。婚姻是女人摆脱弱者身份的一个经典武器,但是柳粉香得到的却只是一个“空炮”,最终沦落到与最滥情的王连方偷情的地步。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玉米与彭国梁相亲前,她劝告玉米“可别像我”时的心情,“走出去四五步,有庆家的突然回过头,冲着玉米笑。她的眼眶里早就贮满泪光了,闪闪烁烁的,心碎的样子”[2]39。柳粉香的爱情梦、婚姻梦破灭得更彻底,更让人心痛。
(三)绝望的挣扎—以自我损害反抗男权
玉米和柳粉香的美好梦想接连成为泡影后,只能在绝望中继续挣扎。她们原本就一无所有,连身体也不是自己的。但是,她们拥有封建社会最看重的贞操。于是,毁掉它便成为绝望中最后的挣扎,成为一种畸形的自我救赎。
在彭国梁愤然离去后,猝不及防的玉米重重地倒下。面对这样的结果,玉米采取了一种象征意味极强的手段进行自我损害—毁掉自己的贞操。伍尔夫说,贞洁“在女人的一生上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而且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包住,若想割开把它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就需要绝大、难得的勇气”[7]。“玉米感到一阵疼,疼得却特别地安慰”[2]64,玉米在潜意识里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男权统治的公然冒犯,是对本该属于男人的“财产”的恶意透支,是对必将沦为男人附庸的身体的主动贬值。
而柳粉香则采取了“自我放纵”的策略,当柳粉香还不是“有庆家的”的时候,就已被村里强大的舆论塑造成了“天生的下作胚子”。在遭受身体迫害、肚子里怀着“杂种”、被迫嫁给老实愚拙的王有庆时,柳粉香不仅要遭受乡邻的轻侮和嘲弄,还被婆婆害得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但这时的她并未彻底绝望,她对王连方的暗示和挑逗保留了独有的清醒。但当王有庆赌气离家后,她彻底绝望了,选择了与王连方偷情,“有庆家的自己也喜欢床上的事。有庆家的一上床便体现出她的主观能动性,要风就是风,要雨就是雨。没人敢做的动作她敢做,没人敢说的话她说得出,整个过程都惊天动地”[2]34。她用身体的放纵获取了片刻的肉体快感和心理安慰,也用这种方式来损害、挑战男权。
玉米和柳粉香对自损行为虽然有着深深的悔恨和自责,但也有强烈的报复的快意,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是绝望的挣扎,是畸型的自救,到头来却更深地伤害了她们自己。
二、“鬼”与“仙”:玉米与柳粉香形象相异之处
玉米与柳粉香都貌美、要强,也都有追求好日子的愿望,却最终都殊途同归,遭遇“闪婚”的悲剧。但是,作为“千红万艳”中的不同代表,她们身上又体现出一定的相异性。玉米成长于王家庄的“权力世家”,受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毒害更深,受“人在人上”的“鬼气”浸染也更深,而柳粉香曾是宣传队的报幕员,“见过世面”[2]34,“身上的确有股子不同寻常的劲道”[2]36,这是中国乡村在摆脱封建传统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痕迹,也是她身上呈现出的一些现代女性的“仙气”。
(一)追求权力与自我
“我们身上一直有个鬼,这个鬼叫‘人在人上’”[8],也就是附着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和等级的阴影。出身于王家庄“权力世家”的玉米,爷爷是治保主任,父亲是村支书,从小就对权力有了深刻的认识,“权利就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利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个拳头”[2]12。她挟制妹妹,制服村里跟父亲有染的女人们,对于自己的婚姻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要找一个有权有势的。她会看上“箍桶匠家小三子”彭国梁,是因为他的飞行员身份,有着说不清的外在权力。当父亲失势后,她就想对她的国梁哥说:“国梁,你要提干。”[2]57当她没有如愿成为“国梁家的”后,她对于婚姻的要求是:“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2]68至此,玉米的一切单纯、心气都灰飞烟灭了,在玉米的心里只有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在与郭家兴相亲的过程中,“玉米一阵狂喜,既像绝处逢生,又像劫后余生”[2]69,毫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渴求。她为自己能够与权力结盟而欣喜若狂,甚至可以放弃尊严,附着了浓厚的“鬼气”。“她既是权的受害者,又在对权力作用的耳濡目染中,被权力意识腐蚀,滋长出权力欲望,然后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最终其实仍然不过是权力的牺牲品。”[9]
跟玉米相比,柳粉香则没有对权力的渴求和依赖,而是率真、坦诚,追求一种本真的自我。同样是匆忙出嫁,柳粉香选择的是老实木讷的普通百姓王有庆,即使她和王连方私通,也不是因为他的权势,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多少有些情意”,“作为男人,他到底还是王家庄最顺眼的”。[2]33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就连跟王连方来往,二人也是在街头巷口站着说话,事事做在明处,不遮遮掩掩。玉米把柳粉香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但率真、坦诚的柳粉香不计个人恩怨,以自身经验相告玉米,女人只有嫁人这一次机会,并送她自己的演出服去帮玉米赢得心上人。后来王连方倒台了,玉米的“国梁哥”也飞了,两个妹妹遭到淫辱,家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她又用最深切的同情给予玉米真心的抚慰,她用自己的人性和对本真的追求驱散了“鬼气”,而让自己身上多了些“仙气”。
(二)传统女子与现代女性
玉米虽然年纪不大,但内心却非常传统,她看不起父亲的滥情行为,更厌恶那些和父亲有染的女人。传统的贞洁观驱使玉米理直气壮地攻击与王连方有染的女人,对于“把王连方弄得像新郎官似的”[2]36的柳粉香,玉米尤其看不过,在她的内心深处,女人是应该有“女人样”的,不要太漂亮,要守身如玉,要是一个理家的好手,“女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就是持家”[2]12。由此不难看出,玉米年纪虽小,却早已成长为封建秩序卫道士的一员干将。当玉米要和“国梁哥”相亲时,她穿上了柳粉香送的衣裳,却吓了一大跳,她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危险,她相当伤感地把衣服脱了下来,正正反反地看了好几回,想扔,却舍不得。这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但在强大的传统观念面前她败下阵来,最终决定“绝对不可以上身”[2]40。同为女人,玉米不仅用强大的传统观念来伤害别人,也压抑了自己青春的生命张力。
柳粉香虽然未婚先孕,被认为“听起来浪,看上去骚,天生就是一个下作的胚子”[2]29,但柳粉香是与众不同的。她不仅当过宣传队的报幕员,还四处汇演,是见过世面的,就连心高气傲的玉米都觉得“这个女人的确有股不同寻常的劲道。是村子里没有的,是其他的女人难以具备的”,不仅如此,“她说话的腔调或微笑的模样,村子里已经有不少姑娘慢慢地像她了”,“男人们虽说在嘴上作践她,心里头到底是喜欢,一和她说话嗓子都不对,老婆骂了也没用,不过夜的”[2]36。柳粉香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王家庄的传统秩序,她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异类,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新生的事物视作怪物进行扼杀,“有庆现在不碰她,都不愿意和她在一张床上睡。村里的女人没有一个和她搭讪”[2]47。而柳粉香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却以自己的方式坦然地活着,面对玉米的上门挑衅,她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恐慌不已,而是张弛有度,不卑不亢。而她与王连方偷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情感的寄托和慰藉,她一次次地向王连方流泪哀求:“连方,疼疼我!”[2]35但是,当王连方要求她吃避孕药时,她却说:“凭什么我吃?”[2]34硬是让王连方吃了一颗避孕药,这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抗争男权的信号。柳粉香身上隐约呈现了反抗男权压迫、追求性爱自由的现代女性形象。
(三)反抗中的顺从与顺从中的反抗
《玉米》中的女性大多被男权同化、归并,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认命地活着。而玉米和柳粉香则对女性命运有着相当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她们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的不同,各自采取的反抗形式也不尽相同。
玉米很早就意识到了男权的霸道,并且本能地心生反感。父亲滥情,玉米便不跟他说话,也不称其为父亲,而是直呼其名。这种对于父权、男权的冒犯是尚处于朦胧时期的玉米最初的挑战。而同时,玉米又因为自己村支书女儿的身份,理所当然地自认高人一等,沐浴在男权的光环里,洋洋得意。对于村里与父亲有染的女人,玉米想法设法地去羞辱,表面上看是一种反抗和抵触,但玉米却对悲剧的制造者—自己的父亲王连方—异常地宽容,这是一种反抗式的顺从,是对男权的敬畏和向往。而她在进行第二次婚姻选择时,这种反抗式顺从则表现得更为直接,父亲失权,两个妹妹遭受伤害,心高气傲的玉米当然要反抗,她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过日子不能没有权。只要男人有了权,她玉米的一家还可以从头再来,到了那个时候,王家庄的人谁也别想把屁往玉米的脸上放”[2]68。玉米为了权力毫不犹豫地做了年老的郭家兴的老婆,主动献身于权力,以获取对抗他人的资格。“在性这件事上,玉米与父亲王连方来了个角色对调:王连方以权力换取性,玉米以性换取权力”[10],“这是一种让人震撼但又无法突破的牢笼,在传统社会文化笼罩下玉米式的突围就显得荒谬而悲壮”[11]。
柳粉香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多的是痛定思痛的女性形象。表面上看,她是顺从的,正因如此,才会“身子都让男人压扁了”[2]30。而在肚子鼓起来以后,她又顺从地嫁给了老实木讷的王有庆,想要替有庆生个孩子。当遭遇王连方的挑逗和暗示时,“有庆家的心里并不乱,反而提早有了打算”,她从容应对逛到她家天井里的王连方,“有庆家的热情得很,嗓门扯得像报幕,还到隔壁去讨开水,高声说:‘王支书来了,看我们呢。’王连方很恼火”。[2]32虽然之后柳粉香还是顺从了王连方,但她让王家庄的“土皇帝”王连方吃避孕药,还“把王连方弄得像新郎官似的,天天刮胡子,一出门还梳头”[2]35。她把对男性的仇恨,表现为对他们的玩弄,以一种顺从的姿态表达自己的反抗。但是,她反抗的结果却是让“王连方快活得差一点发疯”[2]35,怀了“小王连方”却被王连方在床上唱大戏羞辱。
对于玉米和柳粉香而言,她们的身体只是男权压制女性的载体,“无论是以玉米式的以权力对抗权力的奋挣方式,还是有庆家的清醒而无奈的顺从男性欲望的要求,都不能使女性自身得到救赎”[11]。因此,不管是玉米还是柳粉香的反抗,都是一种无奈的自我救赎,是在一次次绝望中孤独而悲怆的努力。
三、结语
多年来,毕飞宇以守望女性的姿态,塑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他笔下的女性尽管所处时代、生活背景、社会阶层不同,尽管她们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奔波突围、挣扎反抗,但因为女性本身的悲剧宿命,她们都无法摆脱权力的枷锁和欲望的诱惑,她们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