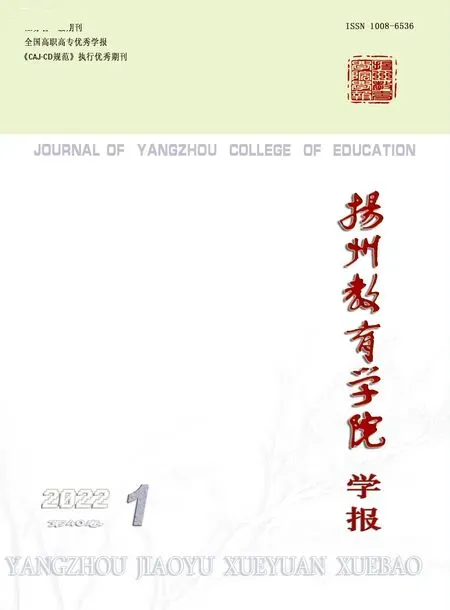雷蒙·威廉斯“共同体”视角中的加缪戏剧
于 锦 江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加缪作为二十世纪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作家,戏剧文学是他思想的载体,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雷蒙·威廉斯是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在《现代悲剧》中,威廉斯构建了一套悲剧理论,即通过对悲剧性因素(无秩序的背景、世俗化的人物、没有产生普遍性行动的情节等)的分析,试图阐述后希腊时代的戏剧何以陷入一种孤立主义的困境,他选取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依次点评。分析加缪戏剧的内在悲剧性因素,既是威廉斯当代悲剧理论的文本实践,更是对当代思想进行剖析的路径,是打开新的伦理道路的一把钥匙。
一、加缪戏剧的悲剧因素
通过《现代悲剧》一书,威廉斯系统表述了“悲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历史性变化,揭示出了一种文化状态的转变。威廉斯提及并阐述了加缪的四部戏剧:《卡利古拉》《误会》《正义》与《围困》,他在这几部戏剧中看到加缪伦理思想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都指向了一些共同的悲剧性因素。在威廉斯看来,加缪的戏剧代表了关于现代人的一种整体性伦理道路的绝望,即一种关于人类整体的理想生活不再可能。
在《卡利古拉》和《误会》两部戏剧中,加缪表现的是人与生活的隔阂,这种间隔是现代悲剧的特征之一。在威廉斯看来,希腊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其具有“一种共有的并真确的集体性”经验[1]40。但自中世纪以来,世俗化的戏剧失去了希腊悲剧所具有的整体性要素,行动背景的秩序也由此落入世俗,一切都以无可掌握的失序状态体现于现代戏剧的悲剧性中。于是,让悲剧性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主人公的处境:他预先被放置于一个无序的生活状态中。面对这种秩序的失衡以及随后即将到来的苦难,主人公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例如,在加缪笔下,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想要以一个帝王的权威把自身的自由拉到极限;他蔑视一切,甚至包含自己的生命,以期达到超越一切的不可理喻的自由。作为一个典型的反抗者的反面案例,敏感的卡利古拉意识到了世界自身的荒谬性,积极地进行个体的抗争,但这种抗争因其把个体放到凌驾一切的位置而沦为自我毁灭。帝王的唯我论遁入天命:“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2]45揭示了主体与世界之间难以破开的隔阂。
《误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威廉斯将18世纪李洛《致命的好奇心》与之对比[1]215。它们具有相似的情节与结构,都叙写了因图谋金钱把自家儿子错当陌生人谋杀的故事。看似是命运戏弄的背后实际是道德的丧失和对金钱的崇拜。威廉斯针对“日常生活没有悲剧性”的观点提出质疑,日常生活的悲剧真的只是纯粹的偶然?或者说,问题不在于如何把某件事界定为偶然或普遍,而在于这一“普遍”本身意味着什么。这普遍背后有某种意识形态,即那些人为性的苦难何以被伪装成了“绝对”或“偶然”,那些关于“普遍”的理念又是否有着对既定阶层(封建主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的潜在维护?某种悲剧的观点有意无意地被作为普遍,“这实际上是对某部分的人类经验的异化”[1]73。顺着威廉斯的思路,加缪的问题就在于,虽然他看到了这种社会因素,却又把它笼罩进绝对偶然性的迷雾中。一开篇,剧中的母亲与玛尔塔就把“金钱”问题拉入对话,人与人的关系竟然以“他有钱吗”作为联系[2]75,而情节的“意外”却不断地将一种先于人间的“命运”置于剧本,社会问题似乎不再单纯是社会问题。“意外”变成了永恒不变,人为的社会黑暗与罪恶被掩盖成了自然的“巫术”。显然,加缪通过主角的悲剧性结局在呼吁生活中的人道主义立场,而与人道主义同在的,却是某种对现实困境的逃避。
《围困》和《正义》则是关于人的具体反抗行动的写作。威廉斯将前者看作是加缪的“俄瑞斯忒斯”(对比于萨特的《苍蝇》),即一个面对世间的困局与荒诞挺身进行抗争的典型。而《正义》则更深入地涉及反抗与革命的区别,加缪坚守的是反抗而非革命。剧中,具体历史语境(沙皇暴政)的介入使矛盾集中于“刺杀大公的过程以及革命者如何牺牲”之情节展开。可是,剧中的“正义者”行暴力的合法却在于自我牺牲(还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保留)。如果,只能以个体自身死亡来确保正义,那真正的集体的正义,普遍的历史行动何以从个体抵达?现实社会的苦难又怎么解决?威廉斯在他的悲剧理论中,关于人物死亡的阐释,都是基于真实的悲剧性生活以及整体的理想而展开。如果人们面对悲剧,聚焦的不是整体的行动而是人物片面的经验——英雄在悲剧中孤独地死去,作为绝对经验的死亡被设置成了一种修辞,这不过是孤立于社群共同体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解“邪恶”的方式也是如此,对造成苦难的邪恶应当放置于人们真实体验到的生活、具体的经验中。若将邪恶做简单的归纳,给它普遍之名[1]83,它就变成是绝对的、单一的,就像加缪面对集体性实践的犹豫不决正代表了一种孤立的意识。牺牲、死亡,以及英雄们所面对的邪恶力量,这种反抗不再是革命。作为一个历史剧,人物的行动却把自己摘出了“历史”。在这些人物之上,总是有超越历史的道义不断阻挠他们:多拉想要继续卡利亚耶夫的刺杀反动人物的道路,可是,行动还没有开始,她早已为自己设置了结局——“一个寒冷的夜晚,还是同一条绞索”[2]252。正义已经不在历史之中,这些正义者预先背负了非正义的罪孽,卡利亚耶夫完成的刺杀与多拉未来的刺杀被赋予同一种性质。既然正义总是被搁置在这永恒的辩论台上,那大众的苦难何以解决?正如威廉斯借萨特之口进行批评:加缪似乎关注的是“满意的立场”,而非“结束苦难”[1]221。
从上述两点可见,威廉斯对加缪戏剧的点评主要围绕其伦理行动如何走向困境而展开,也正是对苦难的人为因素、历史普遍性、反抗无可避免的暴力等种种问题的逃避,让加缪戏剧中的人道主义走向绝望。于是,在威廉斯思考的基础上,重思加缪戏剧中的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就顺理成章了。
二、“荒谬”与“反抗”中的伦理困境
上述的戏剧点评中,威廉斯的论断其实根植于加缪自身的哲学路径。对于后者,海内外学者已有诸多讨论,威廉斯的特殊性就在于从戏剧文学这一特殊角度,将作家的伦理思想倾向在具象的作品中揭示出来,并以独到的“悲剧性”因素的观点予以解释。下文将通过加缪思想中“荒谬”与“反抗”两个关键词,评述威廉斯上述的判断与加缪思想的关联,以及这些判断如何从“共同体”的视域中得出。
第一,从加缪自身的思想来看,荒谬来自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当个人与世界遭遇时,人无以凭借理性把握对象世界本身,世界保持着沉默的姿态让人倍感无力,在此种矛盾中,荒谬就出现了。这种荒谬意味着什么?既然人与世界之间总有间隙,如何将二者勾连?加缪说,荒谬在两者中并存;“荒谬在于人,同样也在于世界”,是“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3]。这一联系是让人沮丧的,面对世界,理性或感官完全地失效,人只感受到与世界的疏离并失去了获取生存意义的可能。这里,可以看出加缪与萨特的观点不同,后者把外界看成是自足的自在存在,需被弃置或超越;而加缪将荒谬作为人之存在与世界的固有关系,它总是在那儿,你无可回避。可是,即使加缪极力避开形而上学来谈论荒谬,但这种荒谬却陷入另一种困境,它总是要依附于某个体的有限经验来体现——此个体对世界的把握就不可能是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建立在这般孤立的个人主义之上的荒谬,更像是一种情感迸发的修辞,难以被视为具体生活的普遍真理。此种荒谬涉及人间,即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处境中,事情就显得复杂了——荒谬本身作为一种必然的关于人之存在的直观体验,反而成为一切苦难成因的挡箭牌。这不仅仅是为了否定加缪,当威廉斯揭示出,历史处境、具体的现实处境无论如何都不会远离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一种新的伦理生活的去向就清晰了:人的生活必然要与他人建立关系,一种对充满“直接、共同关怀”[4]的集体性组织的允诺乃是共同体的要求。诚然,加缪曾高呼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团结与友爱,方法是“将自然世界存而不论,但却把他人视为主体,形成人间世界”[5]。但是,脱离自然世界之语境设想,个体与个体的和谐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这样的主体间性难道不是一种抽象吗?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所设想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社群共同体(作为构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组织、系统)是有差距的。
第二,这样的失落同样表现在加缪关于反抗的观念之中。尤其是在行动层面,威廉斯与加缪的思想差异直接落在两者关于“革命”的理解上。1944年,革命对加缪来说还是具有英雄主义的“激于自发冲动的集体行为”[6]。可是,面对革命必然带来的暴力,加缪止步了,1951年的《反抗者》强调反抗行为就是要反对暴力革命,任何时候都要坚守住永恒的人道主义的底线。在这里可以对威廉斯的论述做一点补充。《突围》与《正义》正是加缪关于反抗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在《突围》中,破除瘟神控制的办法就是人的反抗精神,作者对神或命运的力量进行限制,就是要凸显戈蒂耶激情澎湃的个体行动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另一面,卡利亚耶夫以自我牺牲守住底线,不变成加缪所谓的“革命”。此种“反抗”从关于人性的“肯定”出发,肯定就变成了先于行动的永恒价值。换言之,人道主义的反抗预设了永恒人性,此种人性却不依存于现实的生活与历史。无论是戈蒂耶还是卡利亚耶夫所代表的反抗的道路,都不可能代表整体生活的道路,他们更像是所谓“哲学上帝”的人间代言人——这是个体的呐喊而绝非集体的实践——那么加缪对革命的人道主义批评本身就只能是出于一种片面的理解。在这一点上,威廉斯补充道,萨特看似与加缪关于行动的看法对立,但《密室》《阿尔托的幽禁者》所秉持的人之孤立关系,仍无可避免地造成革命的“虚无主义”[1]223。威廉斯对革命的理解走进了这两位都忽视之处,因为威廉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始终把人性的价值根植于具体历史与现实生活,而非一种先于经验的设想。革命确实可能带来暴力与苦难,但这不是其全部,只有从革命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总体层面去把握,才可以避免一种孤立的认识。如此,革命就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具体的历史中涉及政治、工业以及文化。人们要“努力把这一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7]5。
回到加缪,其实,他同样想要构建一种类似“共同体”的观念。在其作品中,他也看到了单凭个人无以面对苦难,他试图将团结、友爱精神与反抗三者并置而达成一种理论的集体。只不过,关乎生活的共同体难道可以只在抽象哲学的层面言说而不触及政治、经济乃至现实的方方面面吗?即使是加缪自己,当理想面对现实,当他在主体间展开的和解之路遇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等现实问题时,便一触即碎。而其思想根源,在威廉斯关于其戏剧的解读当中,在加缪所背负的悲剧性因素当中,已经被清清楚楚地揭露出来。所以,戏剧文学的解读,同样关乎伦理思想,关乎现实生活,威廉斯正以此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那么,他的共同体理念又能给未来的伦理生活以何种启发?
三、从“悲剧性”重思“共同体”
诚然如威廉斯所说:“文化这个词比社会更适宜说明一种整体的人类秩序。”[8]143将悲剧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理解,那么对它的分析就不单纯是一种远离现实的审美领域的精致赏析(后者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人类生活的某种内在秩序在对悲剧文化的解析中显示出来,威廉斯遵循这一原则对现代悲剧进行评述。在此意义上,加缪悲剧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家自身的思想倾向,它映射了一种关于生活关系的失落,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整体性的社会生活不再被希冀。此种失落本身就是悲剧性的,人,茕茕孑立的人,根本上失去了与他人、与世界和解的可能性,生活的一切悲苦被抛掷角落默默发生、循环。卡利古拉与小镇母女体验到了世界之荒谬,把自己与世界相对立,《围困》与《正义》中的反抗,则自绝于集体性的革命之外。加缪的戏剧文学,实际上在伦理意味上把人的生活逼入绝境,而生活本身,却不得不在苦难中继续。因此,威廉斯的共同体思想之重要价值就在于,针对这样的伦理困境,它试图重拾左翼的道路,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生活打开可能。
构建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桥梁之基础何在,这就先要提及情感结构的作用。威廉斯相当重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阐发,阅读文学的经验不是抽象的、形上学的,而是与生活的经验密切相关,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投射。它意味着“一定社会时期的连贯的整体体验……表达了日常生活经验中通常不易被感知的某些深层元素”[9]。也就是说,在文学阅读、阐释的具体实践中,共同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认识以某种稳固的形态构建出一种文化的整体性,构建的共同情感、关怀的过程又直接地关乎现实的实践活动。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威廉斯在采访中坦言,存在主义(从语境看包含了加缪和萨特对人和世界关系的观点)不应被单纯地反对,而是说,作为“面对人与自然/世界的一种初始的途径”[8]258,它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在卡利古拉和卡利亚耶夫等人的行动中被体现,威廉斯敏锐地揭露出这类戏剧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同样包含了其所属的情感结构。但就像上文所说,造成加缪处于个人主义伦理困局的悲剧因素之缘起,恰是把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关系,用荒谬和反抗的孤立视角去看待,其蕴含的情感结构无以构建一种整体性的关系。
而在威廉斯那里,情感结构作为中介,从文化入手连结日常生活,那么生活的“共同体”与文化的“共同体”就绝非是割裂的关系,而是遥相呼应彼此成全。因为文化是“表现了或支配着社会关系的各种制度结构,以及社会成员赖以相会沟通的各种特有的形式”[7]51。文化共同体,关乎平等与多元。他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一种共同文化的观念以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把自然生长的观念和扶持的观念结合在一起。”[10]意思是,个体自然生发而出的观念与集体所规训的观念,都在一个文化整体当中和谐共存。这里,威廉斯关于文化共同体的设想,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保证一个人人平等的文化环境;他摒弃了“群众”作为客观对象的观念,而把它当做主观设置。个人与集体,以前者的充分发展与后者的共同关怀建立整体。这里不再有一个预设的“上帝”,也不再有关于所谓的贵族或精英文化,文化,或者说一种对具体生活的认识与理解,向广泛的大众敞开,也向多元的可能性敞开。加缪抛弃了宗教的上帝,却抛不掉哲学的上帝,里面还是难免有着精英主义的色彩,即把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转化成一个掌握“反抗”大义的特殊的英雄,如《突围》的戈蒂耶,想要振臂一呼而群起反抗,可是,人们怎能永远只是期盼英雄呢?英雄与群众,在加缪那里,必然衍生出一种不和谐的关系——平等而多元的文化共同体不被许诺。威廉斯的文学批评实践,就是在整体文化领域重思加缪的戏剧文学之伦理立场,从个体到他人,从彼此到集体。文化的共同体也就意味着生活经验的相互理解——在整体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共同关怀是可能的。
总而言之,正因为远离了希腊戏剧总是走在与整体的世界分离的孤独的道路上,加缪的悲剧,就总是在世界的一隅困守着无可奈何的生活。这种局面下,保持文化共同体的观念才弥足可贵,也许它确实未必能完全实现,但就像威廉斯在布莱希特戏剧的创新要素中看到了能够唤起观众参与而产生整体效果的戏剧作用,戏剧文学或者说现代悲剧的道路,还不至于山穷水尽。远离众神的大地,苦难在持续,另一面则是,新的生命与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在萌发。
四、结语
加缪的四部戏剧,在威廉斯的悲剧理论中,表现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割裂状态,以及构建理想共同体的失败。而威廉斯的共同体思想是要走出困境。由此,戏剧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方式,在与生活的连结中被解读和阐释。换言之,在整体的文化、生活视域中,以情感结构为中介,悲剧文学仍被给予创新的可能。从加缪出发,是要力图从中破开原有的悲剧性迷雾,否定的终点将是生活的伦理共同体,也是戏剧文学的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