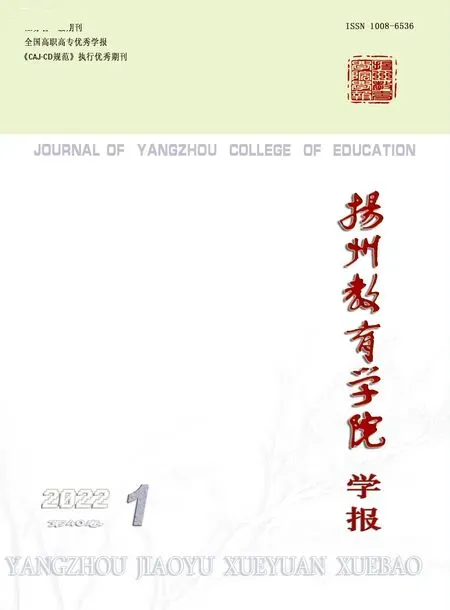盐商大安旗、广德旗家世及活动述略
明 光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清代扬州盐商,徽商如江氏、程氏、汪氏等家族,学界研究较多;而来自陕西、山西的所谓西商论述较少。西商中大安旗、广德旗系出陕西临潼张世荫一门,名声俱著。现据清代诗文和《两淮盐法志》梳理大安旗、广德旗家世、传承和相关活动,就教方家。
一、张氏家世述略
大安旗、广德旗皆张氏盐号,并见于嘉庆初年林苏门记述:“两淮西商张氏一族,如大安旗蔚彤公率子封萱,广德旗芳贻公率子敬业,时与松坪科掌坦、秋芷太史馨昆季游憩于此,布施功德最多。”[1]421结合《扬州画舫录》“张四可字薪南……子霞,字蔚彤。孙裔增,字封蘐”[2]338,“张兰字芳贻……子绪增,字敬业”[2]337,可知乾隆年间的大安旗主人为张霞,广德旗主人为张兰。
乾隆年间,姚世钰有《史宜人传》,其传主正是张霞、张兰的嫡祖母。《传》云:“宜人史氏,敕赠奉政大夫候补府同知宗庇张先生之继配史宜人……奉政公生三子,长,宜人出,即薪南;次景程,又次喆士,胥朱宜人出。……孙男五人。霦早夭;霞,名诸生;兰,候补府同知;馨,举陕西甲子(1744)乡试第一,乙丑(1745)进士,翰林院检讨;坦,同榜举人,内阁中书舍人。”[3]550钱陈群有《张母朱太恭人传》,传主为张宗庇侧室,张兰的本生祖母,“太恭人姓朱氏,世籍江都。幼端重不苟言笑,及长嫔于张,为赠中宪大夫宗庇公讳世荫淑配。……生二子,长讳四箴,字景程,即郡丞兄弟考也。次名四科”。又云:“候选郡丞张君芳贻洎两弟给谏秋芷、编修松坪走使乞传其王(亡)母朱太恭人。”[4]340郡丞兄弟即指张兰(字芳贻)、张馨(字秋芷)、张坦(字松坪)。
章学诚有《为毕制军撰翰林院编修张君墓志铭》,张君即张坦。谓张坦“先世著籍临潼,以筹盐筴侨江都,至君四世”[5]156。李斗记载张兰,亦谓“自其先世起贤、含英移家扬州,代不乏人”[2]337。起贤、含英当是张兰祖父张世荫的父辈,谁是张世荫的父亲,则待考。
姚世钰谓史宜人:“自尊嫜(公婆指张宗庇的父母)先后背弃,偕奉政(指张世荫)慎持三年之丧。丧未除而奉政复捐馆舍。自时厥后,张氏多故矣。”又谓:“自喆士出继叔父而伯仲暨两妇且先宜人卒。宜人以抚诸子者抚诸孙,以长以教,咸俾成立驯致,闻誉焯著,或连举甲乙科第。人谓张氏昌炽未艾,而宜人自如也。”[3]550史宜人先后经历公婆双亡、夫死、两儿夫妇俱亡的悲伤和孙辈中举登进士的喜悦。
长子张四可夫妇生卒年,不可考。次子张四箴夫妇卒年有迹可寻,却需从其子张坦说起。
章学诚明确写道:张坦“生于雍正建元癸卯,卒乾隆六十年乙卯,终始两朝纪元,享寿七十有三”。雍正癸卯,即1723年,张坦生于是年。又谓“张坦“未晬而孤”,即未满一岁父亡,“年甫十一,(母)江夫人殂”[5]156,则张四箴卒于1723年或1724年,其妻江氏卒于1733年。
三子张四科,过继给叔父为子。钱陈群不记叔父名,只谓“字仙洲”,李斗《扬州画舫录》谓:“张世瀛,字仙舟,好佛乐施,感梦金仙,筑扫垢精舍。子,士科,字喆士,号渔川,工诗。”[2]337仙洲、仙舟,音同字异,但都以“喆士”为子,同筑扫垢精舍,必为同一人,即张世荫之弟为张世瀛。四科、士科,音同字异,同以“喆士”为字,也应当同为一人。张四科出嗣张世瀛,亦业盐。其《宝贤堂集》“自序”谓:“呜呼,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慨修名之不立,徒欲自见于空言,可愧也已。”后署“乾隆己卯(1759)夏季清河张四科自识”。[6]据此,张四科生于1710年。卒年不详,当在1767年之后。
综上所述:陕西临潼张氏起贤、含英于明末赴扬业盐,传张世荫、张世瀛。张世荫长子张四可,正室史宜人所出。次子张四箴,三子张四科(出嗣叔父张世瀛),皆侧室朱恭人所出。张四可长子张霦,早夭。次子张霞,字蔚彤;生子张裔增,字封蘐或封萱。张四箴长子张兰,字芳贻;次子张馨,字秋芷;三子张坦,字松坪。张兰之子张绪增,字敬业。
《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临潼张氏,还有“世”字辈张世进、张世掌,“四”字辈张四教、张四杰等,必是张霞、张兰同宗长辈。大安旗主人张霞、广德旗张兰是同祖父的嫡堂兄弟。
二、大安旗、广德旗历代主人略考
清人记述盐商多以“姓氏+行盐商号”相称,而盐号多世代相承,故清代不同文献提及同一盐商,未必就是同一人。如著名盐商“江广达”,乾隆时期的江广达,为江春,嘉庆末年的则是江春之孙江大镛。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三“奏议四”、卷十四“奏议五”,已提及“张大安”。康熙十七年(1678)为增加销量、二十八年(1689)为濬河、二十九年(1690)为恳求恤商,张大安皆列名吁请。可知至迟在康熙十七年(1678),大安旗盐号已卓然自立,且为盐商的头面人物之一。
此时的张大安,主人是张世荫还是张世荫之父?
张世荫岁数、生卒年均无记载。其妻史宜人的生年为1665,则张世荫生年可能略早于此时,姑作1660年左右。到1678年,近20岁;到1689年,近30岁。据此,康熙十七年(1678)的“张大安”必是张世荫之父;而康熙二十八年(1689)及之后的张大安有可能是张世荫。有个旁证,《史宜人传》记载,史宜人“比归奉政时,重亲在堂,而舅姑每以事还秦中,率委宜人代子妇之职”[3]551,史宜人来到张家不久,张世荫的父母时常回陕西临潼办事,让史宜人替他们服侍祖父母,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已将盐务交给张世荫打理,故1689年左右的大安旗主人大概率当是张世荫。
张世荫的卒年,上限当在三子张四科出生或出嗣之后,下限在次子张四箴卒年之前,约在1711—1722年之间,姑算在1715年左右。张世荫将大安旗交给儿子掌管时间也必在这期间内。
长子张四可生年,可以据母亲生年推算出上限。史宜人生于1665年,姑算18岁生子,张四可最早则在1685年前后出生。若此,张世荫卒时,长子张四可约在30岁上下,完全可以接办大安旗。张四可卒年不详,可能晚于张四箴的1723年。
其子张霞接受过良好教育,为名诸生,成为大安旗主人,颇善经营,“工会计之事,累富至千万”[2]338。1751年前后,张霞获候补府同知衔,为五品,后来又升为候补道。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旬寿辰,众盐商参与承办庆典,八月十二日上谕:“两淮承办点景之总商……等二十五名,俱著加恩于现在职衔各加顶戴一级,以示奖励。”第七位是张大安。八月二十五日又谕旨,“颁赏三四品职衔两淮商人洪箴远、郑于吉、汪日初、王履泰、江正大、张大安、巴敬顺”[7]及五品至八品职衔商人。洪箴远是江春卒后的两淮盐商首总,这七人是当时两淮盐商中虚衔最高的第一梯队。但此时的张大安,是否张霞儿子张裔增?张霞此时约已70岁,让儿子接班完全有可能。此后,官方史料不见张大安的相关记载,意味着大安旗逐渐消沉。据林苏门写于1805年、修订于1808年的《邗江三百吟·秋雨复初名》所言“蔚彤诸公均已作古,惟敬业、封翁屏绝尘嚣,悠游仗履”[1]421,说明至迟1805年或1808,封翁即张裔增似也退出商界。
广德旗盐号是谁创立,没有明确资料说明。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张四可、张四箴两兄弟在张世荫去世前后析产,张四可继承祖产盐号,张四箴则创建广德旗独自经营:二是张四箴在世没有析产(这在盐商家族中也不乏其例),而是其子张兰创建广德旗。钱陈群记述,张四箴卒后几年,朱太恭人安排张四箴三个儿子人生道路,“垂涕谕曰:汝兄弟当分道营业,同心励志。鹾务为先世所遗,未可荒怠,孙兰(指张兰,即芳贻)人谨饬可独任之。孙馨、坦资禀尚可读书,其壹志功举子业,倘邀一第,他日仰报国恩,庶不负吾一生勤苦抚畜。”[4]340太恭人“鹾务为先世所遗”一语,值得玩味,不谓“汝父”单提“先世”,意味张兰并非从其父手上继承广德旗,而是析“先世”(祖上)所遗而自创盐号。
前述张四箴约卒于1723年,结合钱陈群所谓此时张兰“仅五龄”,即长张坦四岁,即张兰生于1719年,若20岁亲执商号,则广德旗的建立就在此时1738年,乾隆三年前后,也可能更早些,因为商号可雇佣专门的业务人员打理生意,章学诚记载:张坦“伯(兄)卒癸巳”,癸巳,为1773年,即张兰卒于此年。张兰经商时间30余年,获候选郡丞(同知)、候补监司衔,加资政大夫(正二品虚衔)。
盐商“张广德”在官方资料中的最早记载,是江苏巡抚闵鹗元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月十九日的奏折:“谨奏为明两淮运库商借银两确情恭折复奏……查与全德、伊龄阿先后所奏情节均属符合。臣随提总办商务之江广达、洪箴远、汪日初、张广德等到案,率同道府等反复研讯。”[8]这则资料表明广德旗主人跻身务本堂的总商,也是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旬庆典,八月十二日的嘉奖名单中第十三名是张广德。乾隆六十年(1795),张广德以总商身份与官员程廷镜一起负责建造扬州育婴堂。鉴于张兰已于1773年去世,此三处提及的“张广德”当为其子张绪增,他亦获候选道衔。
嘉庆二十二年(1817),恭逢嘉庆帝万寿庆典,两淮盐商黄潆泰等6位大盐商获准赴京祝寿,另有张广德等8位未赴京祝寿,御档特别注明16家商号主人的真实姓名,其中有“张广德,的名张錞,议叙盐运使衔”[9]。张錞此人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刊刻的《(嘉庆)两淮盐法志》中列为参校人员第三位,已是“议叙运使衔”,该志记载张广德与鲍有恒、黄潆泰同管泰州义仓。张錞当是张绪增之子,张兰之孙,此为广德旗第三代掌门人,获得的头衔高于其父、祖。嘉庆年间的广德旗经营活动还很强劲,在前十数位大盐商之列。
总之,大安旗商号的持续时间,从清初至乾隆末年,其掌门人至少有张世荫父、张世荫、张四可、张霞、张裔增五代。广德旗商号始于乾隆初年,至嘉庆末年,掌门人张兰、张绪增、张錞三代。
三、张氏盐商家族的文化活动
扬州盐商,不少人参与文化活动,从事城市文化建设,张氏盐商也不例外。张霞重修奉宸苑卿黄履暹的趣园(包括四桥烟雨、水云胜概两处景点),张绪增重建李志勋的蜀冈朝旭,还为该景点写过一篇《高咏楼观音大士铜像记》,记述1784年接待乾隆帝临幸之事[10]。张绪增还捐资八千金,助修江都、甘泉两县学宫。张兰则擅画,可与专业画家方士庶齐名。其他值得言说的约略有:
(一)接待文士的张家庵——秋雨庵(金粟庵)
康熙初,扬州城南有草庵三间,为杨姓夫妇出家之地,奉观世音。后张世灜,即大安旗张世荫之弟,病中梦观音赐方,服之病愈;又梦观音说:“我住竹门内茅屋中,不蔽风雨,你可要帮忙解决。”不久,张世瀛出南门外,看见一对老夫妇倚竹扉念经,入室果见观音像,即梦中之观音。张世瀛于是翻建扩大,易庵名为扫垢精舍。杨氏夫妇殁后,张氏邀请某僧人携徒主持。乾隆中期,住持是竹溪和尚,两淮盐运使卢雅雨题为“秋雨庵”。后来,浙江僧人戴某路过扬州,送给庵僧四五粒桂树种子,种植成活,遂易名“金粟庵”。嘉庆十年(1805),阮元居忧归里,觉得“金粟”人所少知,又不敌“秋雨”雅致,遂题写“秋雨庵”,刻石为门额,恢复初名。嘉庆十一年(1806),阮元又捐钱给秋雨庵僧,构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别而藏之,及其满屋乃瘗”[11],倡捐款建义冢。次年,阮元撰《秋雨庵埋骸碑记》,以扬善举。
此庵持续百余年,其财力支持者,就是张氏盐商家族,所谓“大檀张居士、蔚彤、芳贻臮芳贻之子敬业,相继捐金”[12]。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述,是“庵四围皆竹,竹外编篱,篱内方塘,塘北山门,门内大殿三楹,院中绿蕚梅一株,白藤花一株,缘木而生。两庑各五楹,环绕殿之左右。后楼五楹为方丈。庵左为桂园,园中桂树是月中种子,花开皆红黄色。右为竹圃,又名笋园。园中有六方亭,名曰竹亭。”[2]175
竹溪和尚善琴工诗,有《离六堂集》,结交文人,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与之订方外交。竹溪诗云:“公暇捐宾从,来寻释子家。风光近重九,篱落有黄花。一曲冰弦操,三杯雪乳茶。论诗情未已,归骑日初斜。”[2]175府学教授金兆燕与之相交二十多年,为之撰《金粟庵碑记》。张世进、张四科诸人皆有竹亭诗,张霞、张兰也经常来此游憩。《淮海英灵续集》收有竹溪《寄张秋芷给谏》:“五载邗江别,相思阻啸歌。羡君逢圣主,无复谏书多。我久栖岩壑,春还到薜萝。聊因归雁便,问讯比如何。”[13]
据林苏门记载:“竹溪和尚风雅,善于人交,平日往来者,皆四海知名士,无不栖借此庵,无不羡此庵秋雨之名,即无不以庵主为张家庵也。”[1]421该庵是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扬州郡城有名的文化活动场所。张四科《宝贤堂集》有多首作于秋雨庵的诗,1758年,张四科与蒋德、王藻、陈章、陈皋等文士撰《冬日过秋雨庵联句》。
(二)大安班、广德太平班,争胜扬州曲坛
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举办戏曲家班成为时尚,始于盐商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黄元德、张大安等多人效仿。
李斗记载了张大安家班有11位演员,老外、小生、大面、小旦、老旦、小丑及教师各1名,老生、三面各2名,另载场面人员鼓板陆松生。
诸位演员各擅其技,皆有拿手好戏。老外张国相《西楼记·拆书》之周旺、《西厢记·惠明寄书》之法本;老生程元凯擅演《鸣凤记》“写本”诸出,得名伶朱文元的真传;三面顾天祥以《羊肚》《盗印》诸出,《鸾钗》之朱义为绝技;小丑熊如山精于江湖十八本,是位戏篓子。正因为如此,张班才能与诸班争胜于扬州昆曲舞台。
李斗未记载张班的存续时间,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的苏州《翼宿神祠碑记》附载有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维扬大安店老张班捐银数”及26位演员名单。两相对照,有两点认识:
其一,两张名单中相同人员有三位:张国相、程(陈)元凯;陆松(嵩)山。这印证了李斗叙述的正确性;名单人员的不同,说明戏班演员的流动性。碑记的老张班名单中,有“倪殿章”者,李斗记为“洪班副净”,洪班主人洪征治(商号为充实)卒于1768年,倪殿章必是在该班散后才转入张班的。
其二,张班于乾隆四十九年还活跃在舞台上,且称为“大安店老张班”,其班必有数十年的历史,至迟在1760年左右建班,可能更早。张班被后世称为扬州乾隆时期“七大内班”之列。
广德旗张兰也办过戏班,即“维扬广德太平班”。当代周育德先生《扬州太平班和迎銮戏》一文,较早披露“维扬广德太平班”的相关情况。资料来源是北京图书馆所藏郑振铎藏书《太平班杂剧》,该书收有“维扬广德太平班”脚色、场面人员姓名、年龄及籍贯的名单,共80位,其中一人身兼教习、鼓板两职,名字两见,故实为79人;昆曲台本18出。其中部分台词显然是为迎奉乾隆帝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而临时修改的应景语言。该班教习7名,演员52名,包括11种行当,场面21人,其规模约是其他盐商家班的2倍。这些资料于认识此时的戏曲行当体制、表演、班社详情,有重要文献价值。
周育德该文抄录名单和18出剧目名,略作梳理分析,结合《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收乾隆四十八年苏州《翼宿神祠碑记》后附列为重修苏州老朗庙“各戏班、演员捐款名单”中所载乾隆二十年“维扬广德太平班”的相关材料,认为该班是“雍正末年至乾隆前期的活跃在扬州、苏州等地区的著名班社”[14];但未能介绍班主为谁。《中国戏曲志·江苏卷》《江苏戏曲志·扬州卷》《昆剧发展史》及有关论文都认同“雍正末年至乾隆前期”的观点,也都不论及班主。
将维扬广德太平班的两份资料与扬州盐商广德旗联系起来,放在当时盐商争办戏班的背景下考察,完全可以确认,“维扬广德太平班”就是扬州广德旗的戏曲家班。而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的班主就是张兰。
明确班主是张兰,广德旗太平班的活动就不会早于乾隆年间。据前述,雍正末年(1735)张兰仅17岁,其父已死多年,亦无广德旗。故该班很可能是张兰于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后组建,以适应乾隆帝于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的需要。此次南巡,早在乾隆二十年就先行谕旨地方,做好准备;扬州盐商以戏曲演出迎驾,组建戏班,正其时也。鉴于此,该班的存续时间,还是应该谨慎地表述为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至二十二年(1757)之后。1754年的张兰,也就36岁,正是壮年,事业有成好大喜功,追随时尚,办家班正其宜也。
乾隆二十二年该班演出的剧目有:《星聚》《仙集》《衢迎》《迎福》《九如》《布瑞》《九鼎》《献瑞》《堆花》和《欢迎》《笏圆》《琼宴》《访寿》《请郎》《花烛》《劝农》《五福》《长亭》。这些剧目是准备演给皇帝看的,前九出多是仙佛的华丽排场,渲染歌舞升平的气氛,平时演出不多;后九出也是欢庆场面居多,但较多民间流行的出目,反映当时社会演出的情况。
张兰有个女儿嫁给了肇泰旗的汪勋,人称“汪太太”。其夫亡于1772年,她30岁,独立支撑门户三十年,抚子成立,巾帼不让须眉,传说亦曾家蓄优伶,尝演剧自遣。
(三)张兰之孙媳“夫亡入张门”,引起一场议论
张绪增的儿子、张兰孙子的发妻去世,再定亲巴氏女。不料张兰该孙未及再婚而亡,巴贞女却毅然嫁入张家,抚养亡夫前妻之子,时在1779年。苦熬九年之后,巴氏女因病而亡。此事成为扬州文人的谈资,并形成两种不同评价。
有人称赞巴氏女定亲夫死,从一而终,堪为贞节女子。大儒焦循撰《巴贞女挽歌》谓:“九年节操蕙兰香,清泉皓月堪为伍。僭效龙门太史笔,丰神描画遗千古。世有杜夔歌此歌,柔面男儿色或沮。”[15]焦循持赞赏态度。李斗记载,也有人“援归震川之说短之”[2]338,认为巴氏女的做法,其实并不符合古礼。查明代归震川《贞女论》,其明确认为:“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16]归震川此论之实质,在于反对室女守贞的陋习,具有进步意义。焦循又撰写《贞女辨》,引经据典,认为室女守贞正是古礼;文末谓“吾为议贞女者危之”[15],表明此文意在批驳“援归震川之说短之”之人。笔者看来,此文考证自有道理,论观点则偏于保守。
(四)张四科、张馨、张坦等人的文化交游
张世荫三子张四科能诗文,自谓:“至四十始略知难易。虽天资学力不逮古人远甚,然颇自刻苦,以冀有异于言之无物者而未能也。”[6]参与以程梦星、马曰琯为中心的韩江雅集吟唱,为核心成员。他与陆钟辉合作购置的让圃,靠近扬州二马的行庵,也是韩江雅集的重要活动场所,张四科撰《让圃记》谓:“二十年来,春秋佳日,选胜探幽,多在于此。四方文人学士,知有韩江雅集者,未尝不从游于行庵、让圃间。”[6]张四科《咏胭脂》有“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无山妇女愁”句,以此得名,人呼张胭脂。其诗集《宝闲堂集》六卷,收1751—1768年十多年所作古今体诗618首。另有《响山词》四卷。
张四科与浙江秀水举人蒋德交好,后者主其家多年,为其词集作序。另一好友为浙江姚世钰,姚说:“吾友张君喆士闲居奉母,读书缵言,早著能诗,声于朋游间。自余客淮南,诵其诗,接其人,始与之定交。而喆士亦似以余为粗有知者,延主其家,今四年矣。”[17]姚世钰曾于1741年至1744年,在张四科家寓居四年,交谊深厚,故受张四科之请,先后撰写《史安人八袠寿序》《史宜人传》两篇序传,其《孱守斋遗稿》中收有写给张四科的八通书信。
张馨、张坦,是广德旗张兰的亲弟,两人走仕途。《淮海英灵续集》记载:“张馨字秋芷,临潼籍,江都人,乾隆甲子(1744)本省解元,乙丑进上(进士),官编修,改御史,与其弟松坪太史同举于乡、翰林,时目为双璧。假归不复出,筑十亩园延接名流,如王梅沜、金寿门、秦西岩诸公,弦诗斗酒殆无虚日。其侄孙步渠侍御,占籍江都,惜诗稿散佚。”[13]张馨生年无记载,兄张兰生于1719年,弟生于1723年,可知他约生于1721年左右。卒年有记载,章《铭》记为:“(坦)仲(兄)卒壬寅”,即1782年。
章学诚记载张坦较详,生于1723年,于壬申年(1752)恩科成进士,授史职;乙酉年(1765年),赴湖南“典司大比”。不久,即归隐扬州,“甫逾强仕,归休平山。林泉之乐,洒然如秋;伦叙之,蔼然如春。诗酒宾客,四方气谊,如龙如云”。卒于1795年。他工词曲,章《铭》谓“西京乐府,优伶奏技,畏君反顾”[5]156,显与其家有戏班大有关系。张坦还雅好收藏金石,分别真伪颇严,亦间有考证。
张馨、张坦交名人甚多。钱陈群,清朝重臣,为张馨会试的副总裁,后官刑部侍郎,自谓“给谏(张馨)予乙丑所得士”,来往邗上,张馨接待恭谨,故答应张馨之请,作《张母朱太恭人传》。湖广总督毕沅,少于张坦,当年与张坦同为中书、翰林。张坦去世,毕沅应其子学增之请,命幕僚章学诚代撰《墓志铭》。著名诗人赵翼有《张松坪挽诗》:“宦迹曾兼馆阁淸,遂初早赋见闲情。生来独占中秋月,老去犹高第五名。与我淸谈交最久,畏君白战句先成。何期高咏楼前宴,遽作黄垆感隔生。征歌白雪醉红霞,觞咏相随十载賖。天上神仙原富贵,江南花月最繁华。欢场丝管春如昨,暮景桑榆日易斜。他日桥元墓前过,不知腹痛几回车。”[18]
陕西临潼张世荫一支,扬州盐业至少持续六代近二百年,家族商场、官场兼跨,互相支撑,于扬州文化活动亦有贡献,洵为典型的扬州盐商家族。
——加大『四好农村路』建设 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