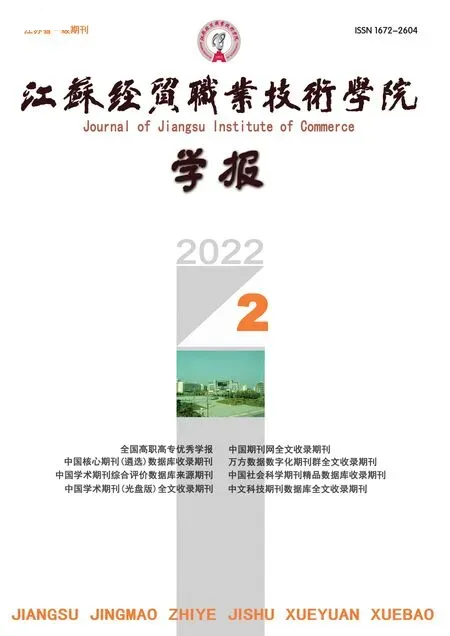当今非虚构写作中的童年书写研究
李 燕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非虚构写作在历史、新闻、文学、影视等领域蓬勃发展,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美学潮流。在这一背景下,非虚构写作对当今儿童纪实类写作的美学影响及其表现值得关注和研究。近年来,邱易东、韩青辰、殷健灵、舒辉波等作家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创作了《空巢十二月》《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访问童年》《梦想是照进现实的光》等非虚构作品,以一个个真实感人又有思想深度的童年样本勾勒出深层的“中国式童年”的复杂景观,让我们看到“非虚构写作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崛起”[1]和“中国儿童文学非虚构写作可能的方向”[2]。笔者研究发现,当今的非虚构童年书写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童年成长困境书写、童年记忆的历史探寻、大自然与边地文化书写。通过这些冷峻又不失温暖的非虚构童年书写,我们能看到童年的困惑、伤痛、梦想和憧憬,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这既是非虚构写作美学潮流在童年书写领域的回应,也是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一、童年成长困境书写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对儿童的生活、成长造成了巨大影响。非虚构童年书写基于大量儿童个体的真实现状,全面再现当今儿童的生存境遇和成长困境,以行动的勇气和“在场”的力量开辟了中国式童年书写的独特途径,引发读者的关注和思考。
进入21世纪,城镇化社会转型冲击着传统的农村生活,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输送到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统计显示:我国有2000多万 14 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在老人或亲戚照看下孤独长大,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和心理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非虚构的童年书写能带给读者更深刻的触动和思考。荣获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空巢十二月》是一份走进5800多万留守儿童心灵的报告。该书是著名作家邱易东在乡村采访的基础上完成的,他从几十万字的采访记录中精心选择18位留守儿童的成长故事,以“品味孤独—勇敢承担—同情理解—阳光照耀”为旋律,既真实再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困难和孤独心理,也表现出他们坚强乐观的一面。安徽作家伍美珍的《蓝天下的课桌》以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为焦点,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用纪实手法展现了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儿童的教育困境和童年梦想。另外,阮梅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査》、杨元松的《中国留守儿童日记》、唐天的《我的乡村伙伴》和赵俊超的《中国留守儿童调查》等都是有关留守儿童的非虚构作品,但这些作品侧重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调查思考,文学性较弱,因而远离儿童读者的阅读期待。
不同生活境遇中的儿童的生存和成长困境,是非虚构现实童年书写的另一个焦点。童话作家周锐在《吹鲸哨的孩子》中放弃想象,以纪实手法讲述了一群自闭症孩子及其家人的故事,其贴近儿童心灵的姿态和简洁收敛的叙述风格使作品充满令人潸然泪下的力量。荣获第十届全国儿童文学奖的《梦想是生命里的光》是青年作家舒辉波“以时光和温情写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聚焦城乡普通儿童成长困境,用了近三年时间,历经周折重新寻访10年前采访过的一群孩子,把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故事真实记录下来,展示了他们因留守、流动、自闭、单亲、肝病以及家庭变故等不同遭遇而走过的独特历程。袁凌继续儿童成长困境这一主题写作,在走访21个省市、自治区的140多个孩子的基础上,完成了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一书。他客观、冷峻地展现了有留守、失学、单亲、随迁、失孤、大病等遭遇儿童的生存状态与内心,让读者切身感受到他们在自我身份构建中的迷惑、挣扎与妥协,寂静无声又暗流涌动。
非虚构童年书写中还有一类较为沉重的作品,以残酷甚至血淋淋的事实把童年生活中的早恋、网瘾、追星、校园暴力、吸毒等现实摆放在读者面前,如韩青辰的《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简平的《阳光校园拒绝暴力》、胡磅的《橙色预警》等。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坦诚地直面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成长问题、暴力冲突和犯罪事件,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思考。韩青辰的笔下有一个普通的农村男孩陶力碗,父亲早逝后母亲经常对他发泄情绪,得不到亲情的温暖,又被同学欺辱和笑话,于是陷入网恋的虚幻浪漫,最终迷失自我、杀死母亲。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的多种因素相互交织,造成了上述种种童年问题,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关爱。在儿童的心理“断乳期”,来自父母、老师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爱、理解和善意有助于他们度过这一敏感时期,健康成长,而如果他们的情感需求一直被压抑和忽视,就容易产生焦虑、暴躁等问题,最终导致一场场人生悲剧。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在城乡生活的儿童都会遇到不同的成长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实童年的书写空间相对狭窄,“实际上是以一批当代畅销童书为代表、以轻松怡人的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现实”[3]。而邱易东、韩青辰、舒辉波等作家将目光投向广大农村和城市边缘的底层儿童,通过深入采访,努力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世界,见证了众多儿童个体的生存和成长困境。他们对童年困境的自觉关注和书写,有力拓展了当今童年书写的边界,深刻揭示了当今“中国童年”的本真面貌和童年境况的多重图景。
非虚构的童年书写非只关注弱势群体、底层苦难和问题儿童,当今城乡普通儿童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场景也出现在非虚构童年书写之中。如:董宏猷在《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中真实描述了不同地区的100个4~13岁孩子的梦想,从不同侧面反映当代儿童的生活和心灵,也真实地展现了各阶层百姓的生活现状,具有多元的社会内涵。萧萍的《沐阳上学记》以生活琐事和母子日常对话为切入点,多角度记录了儿子的童年生活和成长,展现了童年混沌与天真交融的自然状态,堪称是一部“非虚构”童年实录。
二、童年记忆的历史追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呈现历史是非虚构写作的又一重要领域。取材于真实历史的非虚构童年书写,常常从具有不同时代背景的童年个体的日常生活、成长经历等方面切入历史,从童年的视角讲述宏大历史的另一面,既具有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也带有鲜明的历史价值,能丰富儿童的历史认知。
殷健灵的《访问童年》是她在《上海文学》非虚构写作专栏的文章合集。作者有意打捞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尤其是与上海有关的童年记忆,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选择26个人的童年经历,其中有1922年出生的老人和2005年出生的孩童。他们的童年记忆涉及家庭破裂、青春叛逆、同伴敌意、繁重的补课压力等,既带有童年的个体体验,也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作者采用了两种写作形式:一是“访问童年”,在个人讲述实录后,以“写在边上”形式加入作者的思考和感悟;二是“重返童年”,纯粹由被采访者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虽然《访问童年》记录的是个体的童年经历,但并非个人回忆录。作者从现实关怀和审视童年出发,从个体童年记忆中抽取故事内核,使这些单纯的“自说自话”变成能引起读者情感共鸣的非虚构童年文本。实际上,作者“访问童年”的对话也是每个受访者与自我童年的对话。快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治愈。无忧无虑的童年也会有很多难以启齿的痛苦,人们常常选择忘记童年痛苦,但由此造成的性格缺陷和情感障碍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伤害着下一代。在采访交流中,殷健灵展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的素养,在耐心聆听和静观默察中激活受访者的童年记忆,帮助他们在与童年争辩、反抗中达成和解,找到真实的自己。
如果说《访问童年》通过对年龄跨度近一个世纪的个体童年记忆的历史书写证明了童年对每个人的心灵意义和文化价值,那么蒋殊的《再回1949——那时的少年,那时的梦》则通过选取一代人的童年群像,彰显出童年记忆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这部面向历史和童年的非虚构作品由24篇纪实散文组成,作者以新中国诞生为时间节点,从全国10个省份选择了24位当时年龄在8~18岁的个体,记录了他们朴素、平凡的童年经历和梦想,以24份生动的童年碎片勾画出特定历史中的儿童生活与命运,引领读者经历一次精彩的历史穿越。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在新中国成立时追着牛羊奔跑的孩童、坐在废墟里哭泣的少女,在经历了战争伤痛后内心依然充满少年人的本真纯净、朝气蓬勃,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担当精神,他们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并以不同形式完成了童年梦想和心愿,如《酸溜溜的草,粉嫰嫩的花》中的曲艺家王秀春、《太原的哥哥回来了》中的文化学者曲润海、《永久的温暖肩膀》中的歌唱家刘改鱼等。在对个人童年生活的真实描摹外,作者还将每个人的家乡历史、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融于文中,展现出非虚构写作的宽阔视野和文化底蕴。
有别于虚构性的历史小说,非虚构写作的历史书写更接近真实情况,但作者讲述历史的视角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上述取材于童年记忆、追忆历史的非虚构童年书写,把艺术重心放在某一特定时期儿童的生存命运与精神成长上,通过对个体童年记忆的还原,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融入对童年生活中微小事件、细节和意象的描述,能够增强现场感,让读者发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童年模样。
这些基于真实历史的非虚构童年书写所呈现的民间性、日常性和个体性的微观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年来儿童小说的写作。
三、面向儿童的自然与边地文化书写
充满自然气息和异域风情的边疆叙事是非虚构童年书写的一道独特风景。刘绪源认为,包括动物文学在内的“自然的母题”“爱的母题”和“顽童的母题”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而“自然的母题更受儿童的青睐”[4]。韩进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自然文学出身于儿童文学”[5]。中外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都自觉面向儿童读者进行自然和边地文化书写,以强烈的现场感和浓郁的知识性、科学性帮助儿童开拓视野,丰富心灵。
大自然文学可分为三个层次,而非虚构的自然探险纪实是“典型意义的大自然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核心层”。安徽作家刘先平是“中国大自然书写的开拓者”,他面向儿童读者,在40年间创作了50多部以大自然为主题的作品。其代表作《我的山野朋友》等都采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探险经历与发现,在生动优美的文字中融入地质、植物等知识。2012年,刘先平的大自然书写出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变化,创作出《美丽的西沙群岛》《海上红树林》《续梦大树杜鹃王》等作品,这些面向儿童的非虚构自然书写融合了小说的结构、散文的语言、新闻的现场和深刻的思辨,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为非虚构的自然书写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满族作家胡冬林是另一位值得尊敬的“大自然书写者”,他长期坚持在长白山原始森林进行民间考察和采风,被誉为中国的“梭罗”。在《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金角鹿》等系列纪实散文中,他逐一描绘了长白山森林中的青羊、熊、紫貂、狐狸等野生动物,为读者揭开了大自然的神秘一角。如:《狐狸的微笑》讲述了他多次深入林场寻找火狐狸,最终偶遇一窝火狐狸的难忘经历。作者在书写中常常穿插对动物生活习性、行为知识、生存现状的描述,介绍当地的民间禁忌,如救助母狐的老人得以长寿、猎杀狐狸的猎户不能善终等,文字细腻生动又诙谐有趣,具有浓郁的自然气息和边地风情。此外,徐鲁的《追寻》、朱爱朝的《时节之美:朱爱朝给孩子们讲二十四节气》、毛芦芦的《自然笔记》等具有鲜明纪实色彩的自然书写,都以生动的叙事、细腻的描写激发小读者认识自然、热爱自然。
吴然的《独龙花开: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一部描写云南独龙族儿童的生活与教育、成长与梦想的长篇纪实作品。作者长期关注云南大山深处的这一少数民族及其教育发展情况,在1985—2007年数次深入深山峡谷踏访,并收集、查阅了大量历史、民族和教育方面的资料。《独龙花开:我们的民族小学》从独龙族第一个识字少年在孔子牌位前得赐汉语名字“孔志清”开始,一直写到独龙族孩子的“小小梦之队”参加校际篮球比赛。整部作品以边疆民族小学的发展为主线,记录着独龙族的历史巨变,以朴素动人的诗意语言写出了独龙江边清新优美的自然景象,以鲜活的生活细节展现了独龙族的猎事、猎歌特色以及“约多”的民间工艺,既赞美了独龙族勤劳善良、隐忍倔强的民族性格,也指出了独龙族某些蒙昧的陋习。
彭懿的《巴夭人的孩子》是非虚构童年书写中关于边地少数族裔生活的佳作。作者将实录性的摄影镜头对准常年漂泊在海上、被称为“海上吉卜赛人”的巴夭人,展现了孩子们贫苦却快乐的童年和古老文化。书中纯净、唯美的画面与简洁、朴素的文字,创造出令人心驰神往的意境,也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撞,让读者感受到巴夭孩子生活的艰难与美好的两面。
以自然和边地文化书写的非虚构作品不仅具有较强的纪实性、知识性,能让儿童读者看到世界的多姿多彩和丰富奇妙,带给他们新奇陌生、神秘有趣的审美体验和心灵触动,而且以细致入微又润物无声的方式传递出对生命的赞美和对自然的敬畏。同时涉及环境、民族、文化等问题,触及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最古老的情感,能帮助儿童理解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四、非虚构童年书写的价值
非虚构童年书写对当今的儿童阅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逐渐长大、自我意识日益增强的孩子来说,带有鲜明纪实色彩的非虚构童年书写能为他们提供通向真实世界的有效途径,丰富他们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是他们成长不可缺少的支撑力量和精神源泉。
有学者指出,在欧美国家,“面向儿童的非虚构写作一直受到重视,并在一批优秀作品的积累中形成了一个与儿童小说、童话等虚构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阅读传统,但在国内此类书写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儿童正在遭遇更多复杂的社会、教育和心理等问题。李云雷认为:“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6]同样,中国童年故事的书写应关注深刻历史巨变和社会进程中儿童的生活状况、命运遭际、成长经验,并在情感上触及童年的真实内心。非虚构童年书写的作家用敏锐的思想、情感和人性触觉迅疾地捕捉童年现实和历史中复杂或微妙的角落,真实展现了中国孩子的成长、命运、心灵和个性特点。
非虚构写作既是一种创作类型,也是一种创作方法,它与虚构性创作的不同首先在于取材的对象与方式。非虚构写作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致力于非虚构童年书写的作家常常为搜集素材、查找资料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査、实地采访乃至沉浸式亲身体验,付出长达数年的宝贵时间和艰辛劳动。采访中,作家以平等、友善和尊重的姿态聆听被采访者的故事和心声,发现童年的秘密和精神,产生为儿童发声的愿望。
非虚构童年书写带来了一系列创作手法的突破。非虚构童年书写关注真实的个体经验,通过生动的细节、翔实的场景和充满感染力的诗性语言等,充分展现童年个体的生活境遇,尝试触摸儿童内心的柔软与忧伤,展现儿童个体的独特价值。如:《空巢十二月》中的女孩小琴被爷爷奶奶带大,14年没见过父母,当父母带着3岁的弟弟回家过年时,所有长辈都对弟弟呵护有加,对小琴只有训斥和冷落,她感觉自己“像是多余的人”[7]。作者通过细腻描写小琴“被遗弃”的敏感内心,表达留守儿童在长期孤独中渴望被爱又无法与父母正常交流的矛盾与叛逆。非虚构童年书写像一部部童年的纪录片,把一个个真实的童年个体最鲜活、生动的生活与内心图景留存下来,最大限度地传达了童年生命的欢乐与苦痛、挫折与梦想,并从这些个体成长经验中思考和挖掘童年的精神及其价值,为当代儿童文学注入丰厚、深广的社会内涵。
非虚构童年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世纪童年书写的叙事范式,最突出的就是叙事从外部视角的揣度与模仿转化为童年自我诉说与告白的“内聚焦”。与成长小说不同,非虚构童年书写中的人物、事件都是现实存在的,因此非虚构童年书写常采用“口述实录”的叙述方式,让来自不同个体的自我讲述以“直接引言”的方式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书中,构成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读者得以完整地跟踪他们的经历,触摸他们真实的内心,有效规避先入为主的主题预设和人物塑造的模式化,也使刻意制造苦难、情感匮乏等问题得到矫正。
非虚构童年书写采用的大多是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显示了作家以亲历的方式到达童年生活现场,以及对童年生活的细节、场景和氛围的感知和捕捉。美国儿童文学研究者乔·萨特里夫·桑德斯认为,创作“非虚构”儿童文学时最重要的事情是诚实,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我得意[8]。因此,高明的非虚构写作者常常以朴素自然、内敛节制的文笔,实现对人物更为内在的表达。如在舒辉波的笔下,女孩吴懿“眼泪在眼眶打转”,但她始终微笑,直到最后作家才道出这个女孩只有一只眼睛。就这样,吴懿追寻梦想、乐观生活的样子在一瞬间击中了无数读者的心,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非虚构写作蕴含着真实、行动、在场、独立、理性等精神品格,这种美学精神与中国儿童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精神相融、相继。纵观近期非虚构童年书写的一系列优秀文本,无不呈现出关注童年的悲悯和叩问现实的感人力量,同时也把非虚构写作的方法和美学精神带入儿童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非虚构与虚构的跨界共生和文本参照,彰显出童年精神的深度和价值。非虚构童年书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巨大而鲜活的写作空间,我们期待它在未来童年书写中逐渐引人注目,作为一条带着童年生命和精神的支流,汇入非虚构写作的时代美学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