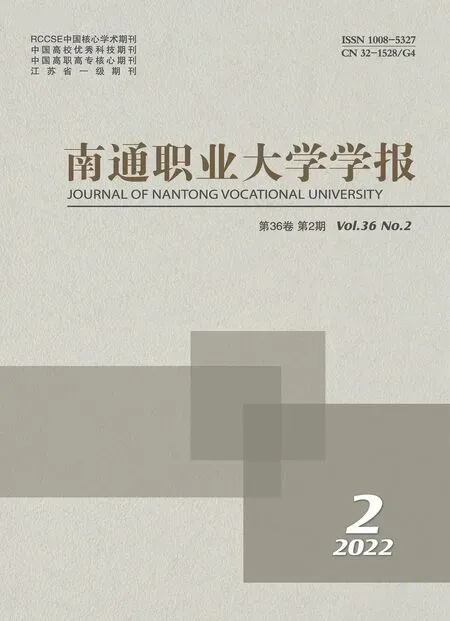湮没于历史的早期“通商”
——沙船业“通海帮”初探
赵明远
(中国民主同盟南通市委员会,江苏 南通 226018)
沙船是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从南到北有两广的广船、福建的福船、浙江的鸟船和江苏的沙船)之一,是适应长江口多沙平缓水域特点而创新的船种。南通因江海之交的区位和特殊自然地理面貌,不仅很早就有航海活动,而且是沙船业的发源地之一。通州、海门沿海一带因而涌现了一批批航海技术高超的船工及具有冒险精神和商业头脑的船户,他们走出本土,陆续来到沙船业的母港和中心——太仓和上海,凭借沙船技术优势,承揽海运、冒险奋斗,逐步壮大起来,并在清中前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通海帮”。沙船业对中国的航运史和航运技术都曾产生一定影响,但南通地方史料对沙船这一重要的江海运输工具,以及在清中期沙船业内曾名噪一时的通州、海门船帮,记载不多,南通学界相关研究也甚少。为此,本文基于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形成的部分研究成果,对涉及南通的史料、史实进行梳理,初步探讨南通海运沙船业的历史概貌。
1 南通早期的航海情况
1.1 唐宋时期的海上活动
南通地处长江三角洲北岸,东临黄海,经数千年沧桑巨变,由沙洲泽国而沃野千里。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称赞通州优越的地理位置“濒海控江,南通闽粤,北通齐鲁”,且“南濒吴会,列壤相望,旁通吴越,迨于外邦。风帆海道,瞬息千里”。南通既有江海环抱,又河道密布,自古有“鱼盐之利”,行船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
关于南通一带早期航海活动的史料甚少,目前难以考证最早的航海活动。沿海一带曾出土过汉唐时期的船只,如:1984年4月,在如东县汤园乡出土东汉独木舟,舟体长度约15米;1973年6月,在如皋县蒲西乡出土一艘唐代木船,船体长17.32米,深1.6米,船形细长,船底横板断面呈圆弧形,共分9舱,独桅,载重约20吨。但以上出土古船仍属于适合江河运输的船只。1986年3月,在如东县北渔乡出土一艘元代船只,船体狭长,船头尖削,船尾窄方,呈流线型,被认定为航海货船。
从晚唐起,由南通出港的海上活动始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此时南通尚未有行政建制,但有军事和制盐管理机构。公元875年(唐乾符二年),狼山镇遏使王郢由江北发动兵变,陆续攻陷苏州、常州,劫掠两浙,波及福建,两年后方平息,史称“王郢之乱”。史料记载其“党众近万人”,“乘舟往来,泛江入海”,可推想其水军规模。五代时,长江口曾发生过一系列海战。如公元908、913、919年,吴国与吴越国先后在长江口“狼山江”“东洲”一带发生过三次海战,南通一带的割据势力姚氏军事集团参与其中。据《资治通鉴》后周纪卷五,公元958年,后周攻打部署在“通州南岸”“东布洲”的南唐及吴越水军,双方各有战舰数百艘,可见舰队规模之大。
通州具有控遏长江入海口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南宋与金对峙的一百多年里,金国水军多次进犯通、泰地区。南宋《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地理总志提到通州,均会强调它的战略地位。尤其料角一带水势险峻,史料称“通州管下料角最系贼船来路紧切控扼去处”[1],曾任淮南东路宣抚使的韩世忠也说过,“明州定海、秀州华亭、苏州许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不可不备”,只有生长在沿海沙洲的水手能够驾驭[2]9252。因此,南通沿海一带拥有航海技术的船工、水手已颇闻名。《宋史》记载,南宋绍兴二年,御史中丞沈与求曾提到:“海舟自京东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镇等处……又闻料角水势湍险,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运。”虽然史料颇为零散,但根据自然地理条件与战略攻防需求可推测,从五代到南宋时期,通州一带的海上活动应属普遍,且主要与军事活动有关。
这一时期海上活动中有关货物运输与贸易的情况仅散见于一些“负面”记载。如《宋会要辑稿》记载,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二日,枢密院上书:“闻海、密等州米麦踊贵,通、泰、苏、秀有海船民户贪其厚利,兴贩前去密州、板桥、草桥等处货卖。”[2]9237反映了包括通州在内的长三角一带的海船民户,获知金国的海州、密州等地粮价暴涨的商机,通过海路向那里贩运而获利。又载嘉定十年(1217年)三月一日,有位官员建言:“沿海州县如华亭、海盐、青龙、顾迳与江阴、镇江、通、泰等处,奸民豪户,广收米斛,贩入诸番,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或南或北,利获数倍,谷价安得不昂?”[3]反映通州等沿海州县的商民突破禁令,盗运粮食到“诸番”牟取暴利,并造成了本地粮价上涨。宋金对峙时期商贸不畅,且南宋对民间贸易限制较多,官员的上书和建言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南北贸易的艰难及这一带船民的逐利意识、冒险精神。
已知史料反映了南通从唐末到南宋数百年间最早的航海信息。这一时期正处于王朝分裂和南北对峙时期,此时正值南通地方行政机构建立,南通位于长江口的地理区位与军事战略价值愈发凸显。海战与战船建造的需要促进了这一带的造船业,也造就了大批有经验的舟师水手,为南北及海外贸易创造了海上航运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史料的零散与缺乏,尤其贸易方面仅反映包括南通的长江口诸地的共性状况,这一时期南通一带海上航运的概貌仍不清晰。
1.2 元明时期的沙船海运
沙船出现于以崇明为中心的长江口沙洲水域,为便于在该近海水域航行而发明,并因此得名。资料显示,沙船名称最早出现在明代。《南船纪》卷一有“二百料巡沙船”图,按语曰:“所谓沙船,象崇明三沙①崇明三沙即崇明岛。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长江口涨出东、西二沙;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续涨出姚刘沙与东沙接壤;建中靖国初(1101年),于姚刘沙西北50余里处涨出三沙。船式也。三沙浮海,人长吞天浴日之区,靛盐为业,履险如夷,走船如马,家海门江,朝吴暮楚。苟惊风立浪之相遭,则鼓气扬眉之有候矣。”[4]乾隆《崇明县志》卷十九引明人所撰《再陈海运疏》已直接提及南通:“沙船以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5]这段史料首次提到了通州、海门拥有沙船。
有史料描述了沙船的外形特征,即平底、方头、方尾,有帆、用橹,还拥有水密隔舱、减摇龙骨的技术。明万历《两浙海图防类考续集》卷一〇有“沙船式”云:“沙船能调戗使斗风,然惟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北洋浅,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清中期名臣包世臣说:“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6]古代,长江口以北为“北洋”,以南为“南洋”。北洋近海潮起潮落,海中沙脉坍涨无常,明沙环布,暗沙隐伏,沙船平底、吃水浅,近海浅滩水区行驶不易搁浅。所以,沙船是适应北洋,也适应长江、内河两种不同航运环境的船舶。
一般认为,明清时期沙船的前身是宋元史料记载的“平底海船”。元初,因大运河漕运不畅,朝廷招安了崇明一带的海盗头目朱清、张瑄办理漕粮海运,“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7]2364。崇明、苏州、太仓、嘉定、昆山等地的府州县志,以及文人笔记(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对朱清、张瑄均有大量记载。明万历年间通州文人彭大翼撰著的大型类书《山堂肆考》略记有朱清、张瑄开海运事迹,提到“朱、张皆扬州府通州人”①五代杨吴天祚三年(937年)设“崇明镇”。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设天赐盐场,隶属于通州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崇明州,隶属扬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崇明改州为“县”;洪武八年(1375年),崇明县改由苏州府管辖;弘治十年(1497年),太仓建州,兼隶于太仓州。宋元之际,崇明一度为通州管辖,故其时可言朱清为通州人,而张瑄则非。清乾嘉年间金榜纂《海曲拾遗》引用《山堂肆考》的内容,并进行修正,仅言朱清为通州人。。
元代,承载南北经济交流的交通方式主要有陆运、河运、海运三种,而海运是比较经济和便捷的方式,所以终元之世,海运不废。《元史》对朱清、张瑄开辟海运航线的具体线路,以及其后两次优化航线缩短航运时间的情况记载如下:“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墺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觜,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7]2365-2366到至正元年(1341年),通过海路运输的漕粮达380万石,较元朝第一次海运漕粮翻了90多倍,可见当时海运漕粮的繁盛。元代漕粮海运的起点是太仓刘家港,经崇明、海门黄连沙出洋,沿途需停靠苏北、山东沿海各州口岸,只有这种“平底海船”方便于航行。但沿途“路多浅沙”“其路险恶”,后来向东优化航线,离海岸更远,不再停靠苏北。这段史料确切提到通州、海门在海漕中的关系,与南通史志中有关漕粮海运的记载可相呼应。
清道光年间通州徐缙、杨廷所撰的《崇川咫闻录》摘抄了《元史》这段有关“海运”的内容,同时指出通州建有“通济闸”,“乃元时漕运出海之处”[8]。通州一带漕运船只由通济闸“出舟”过江,集中于刘家港。南通文史专家穆烜据地方志记载指出,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年),通州、白蒲建有三座通济闸,在至元二十九年之前,元朝政府还曾在通州设立提举司,掌管造船,可认为通州在元代海运中已有“重要地位”[9]。但由于漕粮海运并没有对南通经济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南通海运在全国的地位不高。
1.3 明末清初的商贸活动
太仓刘家港是元明时期的“天下第一码头”。元代时刘家港就有“六国码头”之称。当时的刘河(娄江)近长江之处宽约二里许,深五六米,既是太湖最主要的泄水道,又是沟通太湖、长江和东海的主要通道,连接着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河深江阔,可避风浪。刘家港在江流、潮汐和风浪的作用下,渐成江南地区河阔港深之重要口岸。明《太仓州志》及陈伸著《太仓事迹》称,刘家港“番商贾客云集,粮艘商舶,高墙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计。四方谓之第一码头”。元代时刘河镇设有分管漕运、贸易的行泉府司及四所万户府,还设有提举司,专管海船征榷贸易之事。明洪武七年(1374年)设置有刘家港巡检司,并在港口附近建有烽堠六座。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均自刘家港起锚。永乐十三年(1415年)后,会通河的开凿使南北大运河重新贯通,海运漕粮方告终止。但至嘉靖三年(1524年),明政府仍然通过刘家港从海上往辽东运输棉花、布匹,刘家港仍保持其江南口岸之地位[10]。
承担漕粮海运是沙船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职能,明永乐十三年,漕粮海运被河运取代后,沙船业并未因此而衰落。明中叶以后,北洋航线的沙船贸易已经相当繁荣,据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商人“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够贸易,疾驰数十里如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嘉靖十四年(1535年),巡按直隶御史张题奏称,“近年以来太仓、崇明、江阴、通、泰沿海居民视海洋为庄衢”,从事沿海贸易,靠经营沙船业致富[11]。
明代,沙船除贸易用途,在军事上仍是重要的航海工具。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江南海船被征用于运输军需援朝物资,因为船员“皆轻熟”海路与操舵,且“其船必以太仓、崇明、江阴、靖江、通州、海门沙船为最可用”[5]。
由于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加上清初的“海禁”政策,这一时期沙船贸易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日趋萧条,上海也由于“海禁严切,四民失调”。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海禁,沙船贸易很快复苏并发展起来。翌年,清政府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设在上海县城,上海统辖长江入海口南北600余里海岸线、大小24处分海口。清政府规定,江南沙船收泊于太仓刘河镇,闽粤商船收泊于江海关所在的上海。清代史料中出现了通州商人的身影。清代金端表在《刘河镇记略》中记有通州刘姓、吕四赵姓的海商,还有来自吕四从事运输的高、姚、包、赵等大船户及诸多小户,均在刘河镇设立了运输字号。
自清代乾隆末年,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因刘河镇河道淤塞及河口拦门沙隆起,往日明令收泊刘河的北航沙船先是渐渐不遵旧例,越规收泊上海大关,后来几乎全部改为停泊上海,刘家港最终完全废弃,而在清初与刘家港平分秋色的上海,此时取得江南地区一枝独秀的口岸地位。
2 “通海帮”沙船业鼎盛时期活动
2.1 对上海沙船业产生重要影响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洪泽湖决堤,土沙流入运河;道光四年(1824年),黄河决堤,运河淤塞,漕粮阻滞。在大臣们的奏议下,漕粮海运于道光六年(1826年)重开,并由江苏先行试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各地粮船均至上海交兑,招雇沙船承运。同时,历来走运河水路的内河贸易也多改走经上海口岸的海路。数量众多、船籍分属长江三角洲各县的江南沙船齐集上海口岸,促进了上海海运贸易的繁盛和上海口岸的发展。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12]。到鸦片战争前,随着南北洋沿海贸易的兴盛,上海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南北洋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重要商港,上海口岸常年停泊的北洋沙船已达3 500艘,南洋海船近千艘,航运总吨位42万吨以上。
在上海取得江南地区一枝独秀的口岸地位之时,从事沙船业的“通海帮”也迅速兴起。倡导漕粮海运的苏州知府齐彦槐曾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13]道光五年(1825年),“经世派”名臣包世臣说:“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尤多大户立别宅于上海,亲议买卖。然骄逸成性,视保载行内经手人不殊奴隶……其大户有船三五十号者,自为通帮所敬厚。”[14]协办大学士英和指出:“闻上海沙船有三千余号,大船可载三千石,小船可载千五百石,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所造,立有会馆、保载牙行,运货往来,并不押载,从无欺骗等情。”[15]可见,此时通州、海门“沙船帮”在上海的沙船业中已有一定的声势,不仅拥有众多沙船和自己的商行,还设立了会馆,并已在上海过上富裕生活。
2.2 在南北海运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南通因沿海的地理位置优势,培育出大批熟悉航线、技能高超的船工,出现造船业和海运业,南通的舟师船商勇于冒险、创业奋斗,以上海为母港,逐步发展为实力雄厚的沙船船帮,在南北海运贸易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沙船海运贸易联系了江南与山东、东北,货物除漕粮外,南运以大豆为主,另涉其他北方产品,北运以江南一带出产的棉花、土布为主。沙船贸易因江南土布业而发展,当时土布“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吾沪所产,又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迁南北”……“而沙船之集,实缘布市”[16]。又与蚕丝业的发展颇有关联,用沙船从东北运到上海的豆类,既是江南地区的食品和加工食品的原料,也是农业生产所需的重要资源,例如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饼可用作桑树的肥料。
日本学者松浦章在日本、朝鲜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批清代江南北行商船遇风浪漂流到朝鲜半岛、琉球群岛,被当地官方调查、询问的档案记录。据松浦章统计,从康熙到同治年间,江南商船因遇风浪漂流到朝鲜半岛、琉球群岛的有130例,其中属通州、海门船籍的达36例,可见当时“通海帮”的地位。松浦章摘录分析了一些案例,其中有11例涉及通州,可从中窥见“通海帮”沙船业在南北海运贸易中的基本情况[17]。
记录1: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有通州沙船(船主不详)由徽州商人吴仁则雇佣从通州装载棉花253包,2月抵山东莱阳卸下,3月到达关东南金州,5月受太仓商人周豹文所雇,装炭380担运抵天津,10月又为商人徐梦详所雇,到山东海丰运大枣回江南,途遇恶风,漂流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珍岛。船中共有16人,均为通州籍船工,常以船受雇于各处商人,从事海运为生。
记录2: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通州籍沙船主彭世恒的商船在山东胶州装载白豆、盐猪、紫草等货物赶往苏州交易,途中遇大风漂流到琉球,船损坏、货物损失大半。船中共有乘员14人,均无伤亡。其中有通州船工11人,除船主彭世恒外还有2名通州商人搭船。
记录3: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通州籍沙船主崔长顺的商船从通州吕四出发,在山东胶州装货、搭客后赶往苏州交易,途中遇大风浪,船舵损坏,在海上漂流2个月后到琉球。船中共23人。
记录4:嘉庆五年(1800年)十二月,通州籍沙船主黄发林的商船(通字549号),运载纸、木等商品往山东交易,途中遇大风,船桅折断,丢掉货物,漂流十数日后到琉球。
记录5: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一月,通州籍沙船主蔚廷的商船(通州牌照,船号庄发增)运载纸、木等商品,从吴淞口出发往山东青口交易,途中遇大风,船坏抛弃货物,漂流1月余到琉球。
记录6: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四月,通州籍沙船主彭在天的商船(通字576号,船号彭洪庆)受雇于商人朱大昌(籍贯未记),从上海出航,5月到达辽东皮子窝,运载青豆等货返程,途中遇大风,船坏,漂流十数日后到朝鲜忠清道。船员12人,均是吕四人,彭在天居于吕四,有沙船四五艘。
记录7: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通州籍沙船主袁翼天的商船(通字号,船号袁万利)受雇于上海沙船巨商郁盛森,空船从上海出航赴辽东牛庄运豆货,途中遇风船坏,漂流到朝鲜忠清道。船员14人,有7人住吕四,7人住上海。
记录8: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通州吕四船员11人受雇于旅沪赣榆县籍巨商孙同德的沙船,运送棉花、西洋布等货物,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往山东金口,途中遇风船损,漂流到朝鲜济州。
记录9: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上海籍顾同盛的商船,受通州商人张顺福雇用,在南通州收购土布、棉花后于9月到达关东牛庄换买黄豆。返航途中遇大风,漂流至朝鲜济州。船员25人,为上海人。
记录10: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旅居上海的通州籍商人田福顺的商船,受上海商人丁氏雇佣,从吴淞口出港往山东购买豆货,途中遇风漂流到朝鲜济州。船员18人,为通州人。
记录11: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苏州府元和县曹东帆的商船(元字30号,船号张复盛)在辽东大孤山购买豆货,返航途中遇风漂流到朝鲜济州。船员13人中11人为通州人,均住元和县,行船为业,另2人为崇明人。
这11份记录呈现的整体状况与中方记载一致,且提供了更具体的事例补充。分析这些记录,可知“通海帮”主要不是为本籍做货运服务,通州籍船商无论登记在通州还是上海,主要受雇从事江南与山东、东北间的运输,通海船工水手也受雇于其他非通海籍沙船。除记录1通州沙船受外地商人雇用及记录9上海沙船受通州商人雇用在南通一带收购棉花、土布外,没有更多的沙船业与南通经济联系的信息,特别是11份记录竟无一通州籍沙船由通州商人雇用,在通州办理货物的情况。通州商人雇用上海沙船在南通收购土布、棉花一事本身也说明,“通海帮”沙船在承揽本土生意时并无优势。
到清中期,通海船商有了足够的勇气、资本,但南通缺乏物产丰富的腹地和货物汇聚的区位条件,无法支持较大规模的沙船业。而上海的区位、港口、资源和行商环境为通海船商提供了广阔海天,通海船商得以发挥船工技术优势、冒险精神,承揽海运、创业奋斗,逐步壮大起来,大户可以“立别宅于上海,亲议买卖”,甚至“骄逸成性”,但未见通海船商如徽商一般反哺故土的事例,实乃憾事。
3 通海沙船业衰落的原因
3.1 受开放“豆禁”影响巨大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外商轮船的出现开始对航运业产生影响,但专门经营北洋航线沿海贸易的上海沙船业短期未受很大影响,而因上海对外通商频繁,沙船业一度从中受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和长江增开了十几个通商口岸,其中有北方沿海的牛庄、登州和天津等港口,外国商船开始经营北洋航线的沿海转口贸易,上海沙船业受到较大影响。《天津条约》尚有限制外国商船参与从牛庄到上海豆货贸易的条款,即“豆禁”政策,但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为争取外国人协助镇压太平军,被迫同意开放“豆禁”。“豆禁”的开放为外国船只侵入北洋沿海贸易开了方便之门,对上海沙船业而言是致命打击。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的奏折中说,“自同治元年,暂开豆禁,夹板洋船,直赴牛庄等处装运豆石,北地货价因之昂贵,南省销路为其侵占。两载以来,沙船货本亏折殆尽,富者变而赤贫,贫者绝无生理”;“今沙船无货贩卖,停泊在港者,以千百号计。内地船只,以运动为灵,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即化有为无矣。将来无力重修,全归废弃”[18]。短短十年时间,上海沙船业拥有的沙船就从3 000余艘,锐减到400艘。另外,原承担漕运的沙船也因1874年轮船招商局的开办逐渐被替代。从此沙船业再难起死回生。
3.2 错失“关庄布”运输机遇
清代南通渐成土布产地,通海土布随沙船转运东北,交通较先前陆路便利,北销量因而增长。林举百《南通土布史》描述:1858年营口开埠后,上海、营口间的海上运输迅速发展,通海土布运销东北的交通条件更为改善,北销数量持续增长,进而形成近代闻名的“关庄布”业。通海土布业发展并不完全因为海运交通发展,上海与东北之间的海运交通是畅通的,但南通土布业的增产期正是沙船业的衰落期。因此,通海土布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对苏松土布北销市场的替代,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南一带的经济社会受到战火影响较大,曾经“衣被天下”的苏松土布受影响严重,而此期间南通土布通过已开辟的海上航线北运,填补了苏松土布北方市场的缺口。
1884年前后,印度的机制棉纱开始销于通海地区,逐步将劳力从低效的手纺中解放出来,投入织造,土布产量从此突飞猛进。且机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土布质量也明显提高,更受东北市场欢迎,逐渐代替了尺套布的销路。19世纪八九十年代,通海每年约有两三万件(每件40匹)大尺布北销。
直至19世纪末,通海土布仍有通过沙船运送营口的记载,但主要是由“宁波帮”商船承运。可见“通海帮”未能抓住巨量“关庄布”北运的机遇,未能挽回沙船业的颓势。
3.3 受“宁波帮”及轮船业冲击
据上海及宁波本地史料,“宁波帮”的实力并不亚于“通海帮”,宁波地方文献称:“航业为岛民所特长,南北运客载货之海舶,邑人多营之。”[19]据阮元在嘉庆年间的调查,经常泊于镇海、上海、松江的宁波船约400艘之多[20]。咸丰、同治年间,“宁波帮”商人经营的帆船航运业也达到了极盛。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一的《申报》称:“上海沙船坐港者常有七八百号,宁船也数百号。”光绪年间,宁波人自称:“吾郡回图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航天万里,上下交资。”[21]道光年间,宁波商人打入了本来由江苏沿海商人经营的沙船业,例如,慈溪董氏开设的大生沙船号、镇海李氏的久大沙船号,都是上海有名的沙船号。后来,上海的沙船业形成了以宁波商人为主的号帮,这些号帮控制了上海商船会馆的大部分事务。
“宁波帮”也控制了“关庄布”的北销。据林举百《南通土布史》记载,自1858年营口开埠以后,宁波的号帮开辟了通海土布北运的航道,除代山东客帮装客运花布外,“又收买一批吕四的海船,船员多为吕四、余东、余西人,因此更加接近,有了发展,遂成为专门营运布业的号帮”。专门运“关庄布”的号帮有“久大”“新记”“镇康”三家,都是商船会馆的董事,在运输业有较强的实力[22]。
开放“豆禁”以后,宁波号帮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其经营的帆船运输业虽然已趋衰落,但能顺势应变,购买“通海帮”的沙船,并开拓轮船运输业,继续在船运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例如,早在1852年,宁波籍买办商人杨坊,向英商购得机器动力的宝顺轮,领“宁波帮”经营近代轮船业之先。后叶澄衷开办鸿安轮船公司,虞洽卿集资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朱葆三等商业巨子也投资轮船业,先后兴办了长和、永利、永安、大达等十几家轮船公司[23]。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经过多年艰苦经营,拥有宁兴、明兴、长兴、瑞康等轮船30余艘,总吨位达9.1万吨[24],占全国民族航运业总吨位67.5万吨的1/7,成为长江下游和沿海航业中最大的商办航业集团[25]。
而曾经名噪一时的“通海帮”在这一时期逐渐销声匿迹,除前文所述的历史原因之外,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未能如“宁波帮”因时而变、创新进取,以及史料记载中“骄逸成性”的问题或为诱因。
“通海帮”作为最早走出南通并名噪一时的“通商”商帮,并没有与南通本土结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在遭受轮船业冲击时缺乏应变与革新的能力,因而错失通海“关庄布”业迅速兴起、产生很大北运需求的机遇,走向衰败。南通地方史料缺乏“通海帮”相关记载,一定程度上与其未与南通本土结成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关。而“通海帮”的衰落警示人们,在新的市场竞争、新的生产方式面前,市场主体必须及时转型、变更图新,否则将会被市场竞争的大潮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