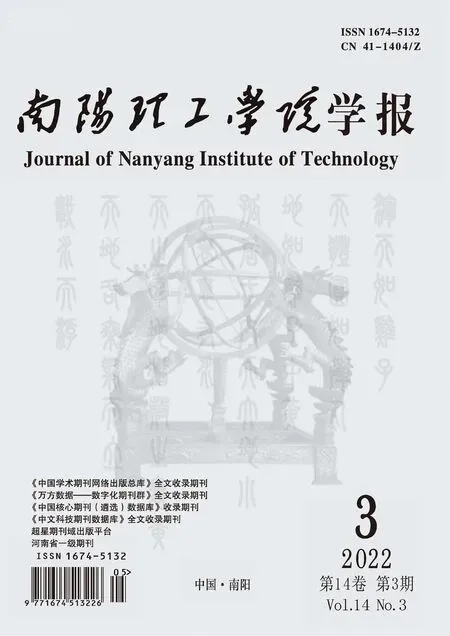试析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币信用确立的原因
张立华,魏 鹏,齐春雨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北海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创立的北海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是山东根据地的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依附到独立的历史见证。北海币发行之初是作为法币的辅币形式存在的,因其发行量、流通范围小而信用较弱,币值也随法币而涨落不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海币逐渐成为山东根据地本位币,在民众中树立起了绝对的信用,最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组建打下了良好的信用基础。有学者从货币金融角度探讨了中共对北海币信用建设的问题[1]。笔者拟以群众路线为视角,探讨北海币信用确立的原因。
一 北海币的为民、便民、利民性质受到民众信赖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经济上推行“以战养战”策略,用武力手段破坏并掠取法币以换取外汇来支持对华的军事侵略。
在山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土崩瓦解,山东的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国民党各地政府和军队均滥发货币且名目众多,数量巨大,甚至无人能详加统计。这些货币“在群众间的信用与地位大都低劣,他们自己也不使用,民众更不用说了”[2]221。
在中共领导下,北海银行于1938年12月1日在山东掖县成立。“山东北海银行的成立,是适应抗战的需要与人民的要求而成立的”[2]206,是“为了统一山东的币制,避免土票充斥,澄清金融市场,解除人民痛苦”,“便利人民之买卖交易与日常生活”[3]169。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信用素著,妇孺皆知”[2]63。北海币信用的确立有着诸多因素,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为民、便民和利民性。
1939年初,因日伪进攻,成立月余的北海银行被迫撤出掖县,胶东抗日民主政府也被迫撤出掖、黄、蓬三县,群众担心北海币就此作废。“区党委研究了这一情况,认为北海币是我们自己出的票子,不能停止使用。因为停止使用就等于不要群众;不要群众,还谈得上什么抗战呢?因此区党委决定北海币继续使用。这样,群众情绪逐渐稳定,我们的北海币仍然公开地在非敌占区流通,甚至在伪军中也广泛地使用着。有的伪军因为使用北海币,甚至被抓去毒打一顿,但总是没有效果,北海币仍然在暗里流通着”[3]25。
北海币发行之初,就是站在群众立场上的,被群众称为“屋里钱”[3]27。当时的法币只有壹元的,零票很少,为解决市面需要,北海币“发行了壹角、贰角、叁角、伍角等零毛的辅币,颇受人民的欢迎”[2]26,“他们对于北海银行的票币很信任,因此伪钞受了很大的抵抗。这原因一方面是地方的私钞都已完全收回,感觉到辅币的不够用,北海银行的辅币在货币的流通上给了很大的方便;二方面北海银行的钞票是有保障的”[2]32。北海币发行之初,就是以这种便民的辅币身份登场的。“北海银行的设立和发行小票,轰动了远近,城乡居民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有的说小票真美,舍不得花。也有的说共产党有办法、有能力,办了件大事,解决了大问题”[3]111。
尽管这一时期法币在流通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北海币发行和使用范围的扩大,民众对于破旧法币开始出现拒用现象,尽管民主政府“将破法币驱走换进好法币,但是人民挑剔过严,流通较前日益艰涩,现在信用已在北钞以下,部分地区且有较北钞下价现象”。而“北钞随着我们影响的扩大,在群众中的信仰也日益巩固了,地位已驾于法币而上之”,“现在北钞已到处成了宝藏的东西了,商人收到北钞就不愿向外花了”[2]222。这说明法币信用已开始下降,而北海币的信用已大幅提升,其斗争性也初露锋芒。
北海币之所以为根据地民众接受和拥护,根本原因在于北海币不是依靠“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是依靠所掌握的粮食、棉布、花生、食盐等重要物资作保证,因为“持有抗币的人民所关心的不是抗币能够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够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2]407。北海币所依存的这种源于群众、为了群众的“物资本位制”理论,为其信用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们是人民本位,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发票子,实行保护人民的货币金融政策,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这比金本位、银本位还重要,力量还雄厚”[3]122。
北海币的为民性还表现在根据实际需要控制发行量。1940年4月1日,中共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正确认识银行作用,积极运用银行去开展生产事业(农村中主要的是农业生产)。树立自力更生的基础,反对眼睛望到印刷机,把无限制发行新钞当作解决经济困难唯一办法的错误观念”,“各银行发行新钞额,应随时具报北方局,不得自由增发”[3]166,力戒采用“发行量过多,饮鸩止渴,慢性自杀的办法”[3]133。“非经银行许可,任何地方政权不能随便发行纸币或流通券,立刻停止以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挖肉补疮’、‘坐吃山空’的办法”[4]87。在以后的“排法”货币斗争中,北海银行将货币发行量的一半投入到工商管理局,以此来吞吐物资,调剂外汇,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逐步建立起了良性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机制,稳定了北海币币值和市场物价。北海银行“根据市场流通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控制货币发行量,切实做到能发能收,决不允许以盲目地增发货币来抵补财政上的赤字”[5]。这与同时期法币和伪币滥发而导致物价暴涨相比较,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对北海币更加信任。
二 开展货币斗争赢得民众对北海币的普遍信任
北海银行首先是因抗战和人民的需要而成立的,“因此北海银行的成立是负有统一山东币制,肃清充斥山东市场的杂钞之责的”,“只有扩大北海银行钞票的使用地区与范围,才能保证经济营垒的巩固与提高北海钞票的信用”[2]206。正是北海银行的这一历史使命,赋予了北海币对敌货币斗争的历史任务。北海币的信用形成于系列对敌货币斗争,并以“排法”斗争的全面胜利而最终确立。
抗战初期的山东币种林立、混乱繁杂,给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武装斗争带来了极大不便。“因此与敌人开展货币战,以正确的货币政策,战胜敌人之货币阴谋,是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2]207。山东根据地开展的货币斗争是抗战时期金融领域内一场复杂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斗争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对敌军事斗争和民主政权建设的成败,当然,也直接关系到北海币信用的确立。山东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大体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抵制伪币,保护和维护法币信用,后期主要是建立本位币,驱逐法币和伪币,以形成北海币绝对的信用为目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改变其货币政策,把巨量的法币倾销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敌人“利用这些被排出的法币进行其对根据地金融经济的大破坏,这种破坏对根据地的影响比几次扫荡还要严重,甚至有使某些根据地塌台的危险”[2]235。因为北海币币值一开始是依附法币币值的,敌人对根据地大肆倾销法币,导致了北海币币值大跌和根据地物价暴涨。据当时北海银行内部的材料反映,“最近沂蒙、滨海各地,物价陡然上涨,同一东西,在同一集上,一天即涨五、六次之多”,“究竟为什么物价这样上涨呢?只要留心最近报纸上所反映报道的消息,也不难了解这是敌人有计划地高价收买,破坏我根据地,掠夺我资源的措施”[2]233。这表明,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北海币信用也面临严重挑战。
为摆脱这种严峻局面,1942年至1944年,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战工会”)领导下,山东各根据地开展了排挤法币的斗争,也称为“排法”斗争。1942年1月,山东省战工会财政处发布《关于一九四二年财政工作的指示》,提出“为提高北票信用,巩固我抗战金融,各地区应迅速确定以北票及民主政权所发行之纸票为本位币,对法币实行七折、八折、九折等使用。对伪杂钞在我占区流通者,一律禁止使用(如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等票)”[6]122。“针对敌人的毒计,我们的具体办法,首先是严格执行法币贬值使用的命令,并逐渐做到完全停用法币”[2]283。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宣布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规定“自七月一日起,所有军政民间之来往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币计算。北币与法币则应以北海银行规定比价折合使用”,并要求“健全各级银行组织,有计划地发行、管理北钞,提高信用,扩大我钞流通范围,逐渐达到取消法币。凡党政军民所办公营合作事业,应保证我钞之信用”[6]310。从此,开始了以北海币排挤取代法币的斗争。
为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胶东根据地于1942年9月发布了《胶东区行政公署关于停止法币流通的布告》,“政府要求全体人民,把这一问题提到抗日救国、保卫自己的重要意义上来认识,……以彻底粉碎日寇的经济侵略”,虽然“在经济上暂时受到一些损失,但是为着抗战,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为着自己后世子孙的长远打算,这种损失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政府这次变更币制的决定,基本上是要依靠人民的自觉,自动地贯彻执行”[2]247。胶东人民对此热烈响应,对敌人运进的法币“亦多不收受”[2]245。胶东区经过这次“排法”斗争,“过去各种票子都通用的区域,现在只剩下北钞在流通”[2]252。对于胶东地区“排法”的效果,北海银行行长陈文其指出“如不停用法币,现在一尺布就得二十多元,现在根据地物价已相对稳定,胶东地区物价比其他地区便宜四、五倍,北钞与伪钞的比值从四百元降到一百二十、三十元,北钞与广大人民的关系血肉相连。停用法币建立本位币控制我根据地金融,求得逐渐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的必要措施,是适合人民要求的正确政策”[2]250。在胶东北海地区,“年初北钞与法币的比值相平,但北钞在群众中的信用比法币高,因为民众有了经验,相信无论鬼子如何扫荡,八路军是不会离开老百姓的”,“很多民众拿着法币到处兑换北钞……蓬东敌区刘家旺、泊儿沟一带渔夫,喜欢把钱卖给带北钞的渔贩,甚至贱卖都行”[2]260。北海币在胶东根据地诸多币种中脱颖而出,在胶东民众中确立了绝对的信用,民众对北海币也倍加珍惜。
第一次“排法”斗争在胶东取得成功为以后其他根据地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尤其是广大胶东人民舍小家顾大家、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觉悟精神推动了这次货币斗争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真实写照。尽管第一次“排法”斗争在其他根据地均未获得成功。
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在1943年下半年和1944年2至4月开展了第二次“排法”斗争。1943年初,奉中共中央命令经山东赴延安的薛暮桥,被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请留,以帮助解决当时山东根据地在对敌经济斗争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薛暮桥提出了“驱逐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7]的主张,得到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同意。1943年6月30日的《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对敌货币斗争的指示》对前期的货币斗争失败(除胶东外)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在于“仅由政府通令禁用法币,而没有用一切方法动员公私资本来排挤法币,把法币秘密送到敌占区换回各种物资。”[8]517随后,“滨海专署……决定于七月二十一日起停用法币”[8]541。之后的“排法”斗争山东分局一方面加强了对各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采取了把货币发行量的一半由工商管理局来收售物资的措施,保证了北海币值和各根据地物价的稳定。到1944年4月,“排法”斗争相继在滨海、鲁中、渤海和鲁南区取得胜利,北海币越来越为广大民众所信任。“北海票是最受山东人民欢迎的,这首先可从各种货币的比值变化观察出来”,老百姓说“只有北海票最牢靠”[2]348。
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反攻及“排法”斗争的胜利,各区币值日趋一致,统一各区本币的条件已经具备。1945年8月,在滨海、鲁中和鲁南三区试行本币统一发行和自由流通。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成立,29日,山东省政府布告《决定北海银行本币在全省统一流通》。至此,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排法”斗争,北海币最终确立了在山东根据地货币市场的独占地位,标志着北海币系列货币斗争的最终胜利和北海币信用的最终确立。“货币斗争胜利了,民主政府的威信更高了”,群众都说 “民主政府没有一件事不是为着咱老百姓的”[2]334。
之后,随着日军投降,北海币打入新解放区,将几十亿元的伪币从新解放区迅速排挤出去,使新解放区人民没有因为伪币贬值以致变成废纸时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北海币在新解放区民众中也建立起了良好的信用。
三 宣传为北海币信用确立起了先导作用
北海银行成立之初,亟须扩大北海币的使用地区和范围。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高度重视北海币的宣传和推广,召开各级地方政权的干部、群众团体、士绅代表会议进行层层传达,组织新钞推行队到重要的集镇开展宣传,分组进行商号访问与家庭访问。“开业的这一天,在县政府门前扎了台子,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讲了话,表示祝贺和支持”,“这时县长是于烺,开业那天也到银行办公室看望,表示祝贺”,“银行发行了宣传小册子,题目是《北海银行浅说》,约五千字,主要说明银行的性质和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设立北海银行的必要性。”[3]111“通过以上几种宣传办法,主要是深入宣传发行北海钞的意义,使群众明了北海银行是有基金有组织的银行,它不但以整个抗日政权的收益作保证,而且存有大量的基金,随时随地都可以兑换法币,并可互相调剂、互相兑换,以平准物价”,“一年以来,北海银钞在广大人民中树立了不可撼动的威信,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2]207。
针对敌人在扫荡中阴谋破坏北海币,而部分落后群众竟公开拒用北海币的现象,中共山东分局认识到进一步加强北海币宣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1941年4月1日专门颁布了《北海银行总行推行新钞宣传大纲及三个附件》,三个附件为北海币的宣传提供了详实具体的可操作细节,要求“每一个人要负责向自己的亲友、邻居、街坊、同乡扩大宣传发行新钞的意义,鼓励并说服他们兑换新钞,使用新钞”,并提供推行北海银行纸币的标语和口号,有三大类共27条[3]169-175。宣传工作的大力开展,形成了广泛宣传北海币的人民力量,促进了北海币信用的建立。1942年1月,省战工会财政处发布的《关于1942年财政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为提高北票的信用,巩固我抗战金融,各地区应迅速确定以北票及民主政权所发行之纸票为本位币,但必须通过各级机关、团体、部队向民众宣传后方限期执行,反对不加解释强迫执行的方法”[6]122,突出宣传先行。
为了让群众知晓停用法币的法令,滨海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要求“各机关部队团体学校进行传达讨论,并利用各种方式普遍向群众进行宣传,使停用法币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军队应有计划地分组到各大村镇及集市进行宣传,税收贸易局要有计划地派干部到各县,配合当地政府召开商人座谈会,带法币到敌占区购买物资并进行宣传。各县民运工作队及征粮工作队,对村民应进行会议的个别的宣传,解释为什么停用法币及停用的办法。经过各种组织、各种会议,使村民讨论如何停用法币,如何将法币集中到敌占区买东西,以免奸商渔利。各学校应组织宣传队,每日到周围集市宣传,‘七·七’宣传周应将停用法币作为主要宣传内容之一”[2]303。甚至“沭水王县长亲自到朝家村集上,主持兑换工作。各个集上均可看到小学生成群结队地宣传停用法币。区干部即配合XX小学分组进行宣传解释,并先后举行三次晚会,由XX农村剧团表演停用法币短剧”[2]308。在民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滨海区的停用法币活动很快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货币问题内容复杂,针对“有些人怀疑政府为什么不规定一元法币兑换一元本币,而把法币七折兑换?他们以为把一百元法币兑换七十元本币,似乎太吃亏了”的问题,民主政府进行了详细宣传和解释。政府还对商人到敌占区购买货物需要法币及民众对破旧法币不能兑换的担忧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告知民众可到兑换所自由兑换法币,凡是市场能用的破旧法币,兑换所也能兑换。
宣传工作在北海银行开展的农贷中也颇显重要。由于民主政府和北海银行初期对农贷宣传不深入及贷款程序不健全、村干部的敷衍塞责等,导致民众对农贷产生了不满情绪,急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于是民主政府和北海银行向陕甘宁边区学习,组织成立宣传小组和检查小组深入根据地基层群众当中,宣传农贷的意义,破除敌伪的谣言,调查贷款的实际情况。宣传工作的改进为开展农贷创造了条件。
四 农贷促进了北海币信用的确立
在北海银行11年的革命历史过程中,除了开展货币斗争,农贷也是其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海银行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贷款称为农贷。农贷是北海银行帮助部分农民解决经济困难、改善生活、积极参加抗战的直接手段。通过农贷,使北海币深入到广大农村,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通过农贷,农民实实在在地领受到北海币的好处,从而扩大了中共和山东各抗日民主政权在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影响,增强了北海币的信用。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给山东抗日根据地带来了巨大困难,1942年,山东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时期。开展农贷,对农民和根据地经济建设无疑就是雪中送炭。
开展农贷工作初期,北海银行成立农民贷款所,开展低利贷款。之后,北海银行不断完善和扩大农贷范围,改进农贷办法,从失误中不断改进农贷工作,帮助许多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如“文西生格庄有人说,若不是今春北海银行贷款给经营,一家四五口就得饿死”[9]。广大民众对农贷心存感激,“谁都知道,……穷小子是取不到半文钱的,即便能够东借西借的取得几文钱,也是受到高利贷的重利盘剥的(掖南的利息达七、八分之多)”[2]446。这与省战工会通过的北海银行贷款利率相比较,农贷给予民众的利益不言而喻。省战工会“规定北海银行贷款最低利率为:农业贷款四至六厘,工业贷款六至八厘,合作贷款八至一分,商业贷款一分到一分二厘”[2]429,这是北海币利民性的直接体现。
在大生产运动中,北海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工作中,同群众建立了新型的信用关系,巩固了减租减息的成果,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对发挥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增强抗战的物质基础,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都起到了极大作用”[3]35。北海币通过农贷“在农民中如一朵鲜花一样开放在眼前,也象下一场甘露美雨一样,是会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与爱戴的”[2]447。农贷的开展,无疑会促进北海币信用的建立。当然,抗战时期的农贷,除了胶东地区取得了显著成绩外,其他地区的农贷因失误较多,没有明显达到增产目的,但不能否认农贷对北海币信用确立的积极影响。
五 反假币、反谣言、反奸细保障了北海币信用健康运行
在北海币信用确立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假币和谣言的困扰,尤其在各根据地渐次取得“排法”斗争胜利后,敌寇利用倾销法币盗取根据地物资的阴谋破产,便采用向根据地倾销假北海币这一更卑劣的手段,以此扰乱根据地金融,破坏北海币威信。 “几乎我们发行哪种票卷,敌人就伪造哪种票卷的假票”[3]28。为此,山东省战工会于1942年12月11日做出了《关于查禁伪造北海币的指示》,要求“首先我们应该从政治上认识伪造北海币,是敌寇有组织有计划破坏我根据地的整套阴谋表现之一种形式,他的目的是在以假乱真,降低北海币的信用,提高根据地的物价,从金融问题上来破坏根据地的经济壁垒,以配合其政治上军事上摧毁我根据地的阴谋”[2]575。假币和谣言多系奸细所为。为树立北海币威信,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反假币、反谣言、反奸细三位一体的反制斗争。这里所说的奸细是包括汉奸、特务、奸商及根据地内与人民为敌的人的统称。
为了杜绝假北海币来源和巩固北海币的信用,《北海银行总行推行新钞宣传大纲及三个附件》中的附件三《对付假造本币的办法》提出,“伪造北海币的出现,是日寇、汉奸、阴谋家、捣乱派一贯的卑劣勾当,……企图以伪造币的混迹市场来损污北海币在群众中至高的威信,来阻碍北海币在广大地区的发展,来达到他们破坏北海币、破坏我抗战事业的阴谋”[3]173。其中规定了对假北海币的处理及奖惩办法,“如确系故意携带假票在五元以上企图使用变利者,经县府调查属实后呈报上级机关核办,以私造伪钞扰乱抗战金融论罪,定予严厉处分”,对于“凡拘获使用假票犯送交政府或报告政府因而捕获者,经证明属实后”,给予奖金、名誉奖或颁发奖章。《对付假造本币的办法》还具体传授如何识别假票,如在纸质上,“假票比本币的纸质低劣柔薄”,在号码上,“假票的号码往往都是重复的”,在花纹上,“本币贰角周围是网丝状,轮船小旗是黑色;假票贰角周围是点状,轮船小旗是白色,其他各种花纹也模糊”[3]174-175。
山东省战工会要求各级组织加强反假币宣传,要人人都能识别真伪币;召开商人座谈会,从商人本人做起禁绝假币;利用各种报纸书刊及冬学等群众参与度高的教育机构来教授、普及群众识别伪币的方法,形成查禁伪币的群众运动;对“查获大批使用伪造北海本币,确与敌寇勾结,计在破坏我根据地金融之奸人,应即处以极刑,以资镇压”[2]576。1942年,省战工会要求各地北海银行会同当地政府成立假币识别所;1943年,省战工会制定了《处理伪造及行使伪造北海币本币案件暂行办法》,规定伪造北海本币,意图使用者处死刑,使用假北海币并经证明确系勾结日寇、扰乱金融或意图营利者,数量达500元以上处死刑,不足500元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以行使数量一至五倍之罚金等[2]579;1944年胶东分行出台《关于查获伪造、变造本币(包括本票)发给奖金的规定》等,严厉打击伪造和使用假北海币的行为。省战工会还在各根据地开展公民誓约运动,宣誓“不当汉奸顺民、不给敌人汉奸做事、不给敌人汉奸送粮食、送钱、送礼物”等[6]159。此外,胶东地区的北海支行还建立了赶集制度,派银行的出纳股长到集市上现场识别假币,一方面取得识别假币经验,同时也向民众当场宣传,帮助民众识别假币。1943年黎玉在谈反假币斗争时讲到,在我们的宣传查禁、建立识别所等办法的打击下,假币较严重的鲁中地区也先后绝迹[2]587。
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以及投降派在大量伪造北海币的同时,还不忘造谣和污蔑中伤北海币。他们派出大量的奸细,散布说“鬼子打击法币,八路也打击法币,这难道不是帮着鬼子做事吗?”还散布说“这是八路的阴谋,八路军准备走,所以大量收买法币。”甚至有的说“这是土匪的行为,等于抢老百姓的钱。”[2]277他们还“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如说我规定使用法币种种办法是排斥法币,便利推行北钞,是共产党在北方限制国民党的办法,政治上落后的分子受其骗者亦颇有人在,如东海文登崖头集红卍字会分子就这样认为”[2]217。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投降派的活动日趋猖獗,“他们到处造谣说:北海银行组织不合法,谁用北海币谁就是汉奸,北海银行钞票的流通是破坏金融”[3]31等。在农贷中“有些地方出现了不良现象,如群众尚不了解贷款意义,加以敌奸多方造谣,因而不敢贷款”[2]428。谣言的散播影响了农贷的开展。对于上述谣言,在中共领导下,根据地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严查奸细谣言,特别是赣榆、郯城、海陵、临沭更应格外注意,倘或查明确系奸细,即行逮捕严处”[2]308。北海银行也“从政治上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无限制地兑现,提高北钞的信用,坚定群众对北钞的信心”。
六 结语
北海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的地方银行,北海币承担起了金融领域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根据地进行经济掠夺的神圣使命,是山东革命金融史的开端。从北海币应运而生、开展波澜壮阔的货币斗争到北海币信用的绝对确立,无不体现出中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北海币发行之初就是“为人民谋福利”,在信用确立过程中紧紧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普遍拥护,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革命金融力量,有力配合了山东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以湖北为个案(1935—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