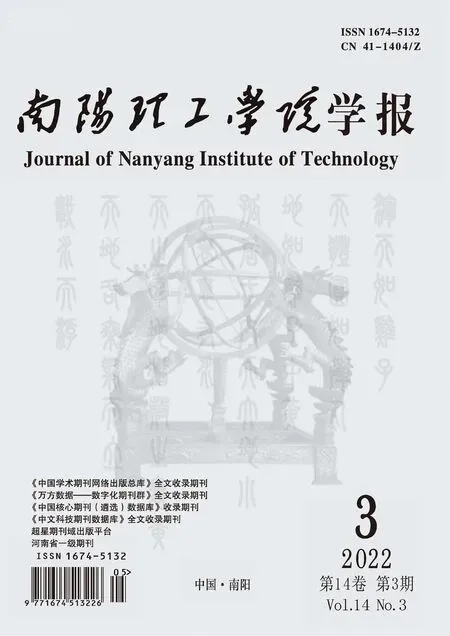行政协议的范围界定问题研究
葛荣荣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一 行政协议及范围的法律界定
(一)行政协议的背景
在传统的行政关系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权力服从的关系,行政权的行使是单向的、强制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行政机关开始由“干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传统的行政权行使方式已经不完全适用这种状况下的行政关系,于是,借由私法工具来实现公法目的的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的行政权行使方式产生了[1]。
行政协议优于传统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地方在于它更为缓和。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性行政权行使方式,行政协议带有一定的可协商性。传统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难以引起民众的积极配合,不利于相关行政事务的开展,而借助行政协议,通过招标、投标、询价等公开公平公正的行政程序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意思在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2],则可以有效解决原来行政行为单方性、强制性所带来的问题,并且能平衡各方利益,有利于行政管理目标和协议目的的达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2015年为截止日期,可检索出全国法院审结行政案件504138件,其中再以“行政协议”、“行政合同”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全国法院共审结行政协议诉讼案件2436件,占比0.48%。以2020年9月为截止日期,可检索出全国法院审结行政案件2812150件,其中再以“行政协议”、“行政合同”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全国法院共审结行政协议诉讼案件55558件,占比1.98%。大量增加的行政协议类案件使得对行政协议的法律界定标准的需求变得迫切。
(二)行政协议的法律界定
在2015年5月1日之前,行政协议的法律规定在我国一直是缺位的。新《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这两种类型的行政协议,为我国行政协议法律制度构建打下了基础,但这一条规定并不足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多样的行政协议问题。
在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四年半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解释》”)。该《解释》的第1条为行政协议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该《解释》第2条列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符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属于行政协议的受案范围。
从《解释》第1条可以看出,我国对行政协议的界定采取“四类要素说”,即行政协议需要包括行政机关主体、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目的、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和双方通过协商自愿作出的意思表示这四类要素。由于该《解释》中规定的“公共服务目的”要素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所以该《解释》中对于行政协议的界定仍然是模糊的,不利于行政协议的适用。
二 行政协议范围界定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行政协议认定标准模糊,未对行政协议范围加以限制
行政协议是行政与合同的一次“联动”,行政协议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行使方式,它的特殊就体现在它的强制性减弱,反而带有“契约性”。行政协议需要双方协商一致才能够订立,这体现了契约的基本原则[3]。但在遵循契约原则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它的“行政性”,这种行政性不单单体现在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协议的一方主体,更体现在行政协议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对公共资源予以最大化的利用与保护。我们需要明确并非所有为公共目的考量的行政权行使都可以转化为行政协议。
《解释》第1条指出行政协议必须具备四类要素,但是由于“公共服务目的”这一不确定因素的介入,使得该行政协议的认定没有那么明确。“公共服务目的”是一个内涵极为宽泛的概念,行政机关在管理公共事务时,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为公共服务的目的。再结合《解释》第2条中规定的“其他行政协议”这一兜底性质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运用自由裁量权来扩大行政协议的界定范围,这样不仅会导致行政法“侵占”民法的领域,也会导致出现行政机关利用行政协议转移自身责任的问题。
(二)关于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出让协议的规定,行政法与民法重合
《解释》第2条指出,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出让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而民法中也有对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的规定。我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为了充分发挥国有自然资源的作用,国家将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流入市场,通过拍卖、招投标的方式,将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出让。而基于拍卖方式取得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主体与行政机关之间签订的出让协议,在民法与《解释》中均有规定。基于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特殊地位与享有的特殊权利,一个协议不能既受行政协议法律规范又受民法规范。
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享有“行政优益权”,即行政主体在追求公共利益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过程中依法享有的主导行政协议签订、履行及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甚至制裁对方当事人的强制性权利[4]。这种权利是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特有的,在民事合同中并无此种权利规定,因此,区分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出让协议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协议很有必要。
(三)地方制定行政协议标准不一致
由于此前行政协议立法的不足,地方为解决行政协议问题,自行制定了有关行政协议的规定与办法。截至2020年10月20日,在北大法宝中以“行政协议”、“行政合同”、“行政机关合同”、“政府合同”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找到17部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和68部行政机关合同或政府合同管理办法。其中有55部对行政协议的类型进行了规定,对其中六种主要合同类型是否被认定为行政协议进行统计分析:49部认可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转让、承包、租赁合同;42部认可政府特许经营合同;43部认可行政机关与企业的战略合作合同;46部认可行政征收、征用合同及行政委托合同;48部认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租赁、承包、托管、出借、买卖合同;13部认可资助、补贴合同。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政府对于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
这些并不统一的认定标准,使得各地行政机关签订的同一类协议因地区不同而产生的影响不同,不仅不利于行政协议在全国的普遍适用,而且会干扰市场。同时地方政府在确定本地方行政协议类型时,可能会出现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协议规定,不负责任地转移自身责任的现象。在我国的传统上,“官”对于民众而言是一种带有距离感与强权性意味的存在。我国的行政权力也素来强势,尤其是某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内部部分官员素质不高,他们极有可能利用行政权获取甚至夺取不法利益,行政协议若规制不足,便会成为这些人招揽钱财的工具。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行政协议的标准必须更严格地予以规范,以防止部分官员与行政相对人勾连而损害公共利益。
(四)司法实践中对行政协议认定存在偏差
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个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的判断,法院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在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前,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公共工程建设合同、招商引资合作协议等合同的审查法院意见不一,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的主张都有[5]。虽然在新《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对于行政协议的争议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同时,模糊的行政协议界定标准使得法院对于行政协议范围的认定开始逐步扩大。
《解释》中在判断一个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时仍然给法官留有较大的裁量自由。对于协议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是否为公共服务目的,取决于法官的判断,不同的法官可能会对一类协议做出不同的判断。例如,在2020年薛文选与昌吉市北部荒漠生态保护管理站、昌吉市自然资源局承揽合同纠纷中,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二审法院却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协议在行政协议的受理范畴之内(1)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再100号裁定书.。协议的性质判断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判决的结果自然也不同。法官对行政协议的认定是保护行政协议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法官的职业素养尤为重要。
三 完善行政协议范围界定的建议
(一)通过反向排除的方式限定行政协议的范围
基于行政协议为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目的的考量,它的定义就难以具体明确,我们只能通过反向排除的方式来限定行政协议的范围。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协议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有些行政权不论何时都不应该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行使:纯公共物品的提供事项,如国防、外交、司法等;财政税收,税收是一个国家资产来源的重要支撑,关系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公产的划分;需要行政机关确定统一标准的事项,如货币;与公民生存利益利害相关,如消防、城市管理[6]。
除了上述绝对不可以签订行政协议的事项以外,实践中也有一些特殊的行政权专属。行政协议的本质是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契约从而为公共服务,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时享有一个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行使的行政职权。有了这一前提之后,法律明确规定由某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或法律明确规定需要以强制性方式行使的行政职权就被排除在了行政协议的范畴之外。对于这些行政权,行政机关不得采取行政协议的方式实行。
(二)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出让协议应纳入民事合同范畴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然资源市场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服务监管作用,并在明确自然资源权属的前提下扩大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范围,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市场配置制度,实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相统一。由此可见,我国在出让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时虽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但同时也希望国有自然资源能在市场中通过充分流转来发挥作用。既涉及公共利益又有市场因素,那么如何平衡二者就是判断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协议的关键了。
若将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出让协议纳入行政协议的范畴,行政机关就享有了可以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制裁行政相对人的行政优益权,这必然会使行政相对人在受让使用权时产生更多的考虑和担忧。这种协议比起民事合同而言,单方面也加重了行政相对人的负担,自然是不如民事合同能够促进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效用充分发挥。
因此,为实现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市场配置制度,应将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出让协议纳入民事合同的管理范畴。这并不是说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机关放弃了它的行政权或者说对国有自然资源的保护减弱了。相反,在行政协议签订之后,国家对于国有自然资源仍然享有监督的权力,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监督者的身份来保护国有自然资源与公共利益。不以行政协议范畴管理只是缺少了行政优益权,但在行政相对人有危害国有自然资源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时,行政权仍然可以强行进行管理。行政机关对国有自然资源保护的权力没有减弱,也给行政相对人一种安全、放心的交易保障,不用担心自己的前期投入会因为行政机关单方的行为而遭受损失。
(三)明确地方行政协议认定标准
从上文中可知,地方政府对于行政协议有着自己的规定,但各地的认定标准并非全然一致。虽然这之中大部分的行政程序规章和办法是在2019年《解释》制定、出台之前为方便管理地方事务而制定的,但在2020年1月1日《解释》正式施行以后,各地对于行政协议的规定现今仍然是有效力的,也就是说不一致的行政协议认定标准仍然在地方适用,这极其不利于行政协议制度的发展。地方应当紧跟中央的步伐,依据《解释》确定新的行政协议认定标准,这样更有利于行政协议法律制度的构建。
《解释》对于行政协议范围是“授权型”的,行政机关应当明确其在行使行政权时并非“法无规定即自由”,而是“法无规定不可为”。行政协议虽然带有契约的性质,但它依旧是受行政程序法调整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不可以通过与行政相对人协商的方式任意签订协议,地方的行政协议范围应当是具体明确的。地方政府为了管理各自事务的需要制定的不同于中央的行政协议类型,应当在考量之后经批准、备案方可以适用。明确的地方行政协议认定标准才更有利于我国行政协议法律制度的完善。
(四)司法实践中明确为公共服务目的的判定方式
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行政协议认定的不统一主要是基于对是否为公共服务目的认定的不统一。行政协议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或保障公共服务的良好运作,《解释》中所称的“为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的目的”,究其本质就是为公共利益考量。对一个合同是否具有公益目的,要从多个方面考量,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合同是否直接实现公共利益或保障公共服务。在判断时,法官应当透过协议的条款,看到合同的本质目标,形式上没有规定不代表实质上不会影响公共利益。
例如,对公共设施的出租,看似是民事合同,但其实质在于充分利用公共设施资源来谋求公共利益。相反,某一行政机关改变机关环境而签订的买卖或租赁合同就不能认定为行政协议,因为行政机关的目的在于更高效、更好地开展工作,但这只是为了帮助行政职权的行使,而不是直接行使行政职权。因此,判断合同目的时要在合同内容基础上,辅以合同的实质作用。
四 结语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行政机关在行政关系中的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化的过程中,它行使权力的强制性也在渐渐减弱。党中央明确要求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应当慢慢减弱,更多地以行政协议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到市场中。这样,行政协议必然成为未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重要手段。我国对该制度的法律构建才刚刚起步,对于行政协议范围的限定是保障行政协议不滥用的重要方式。只有中央与地方,立法、执法与司法相结合,才能更为有效地确定行政协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