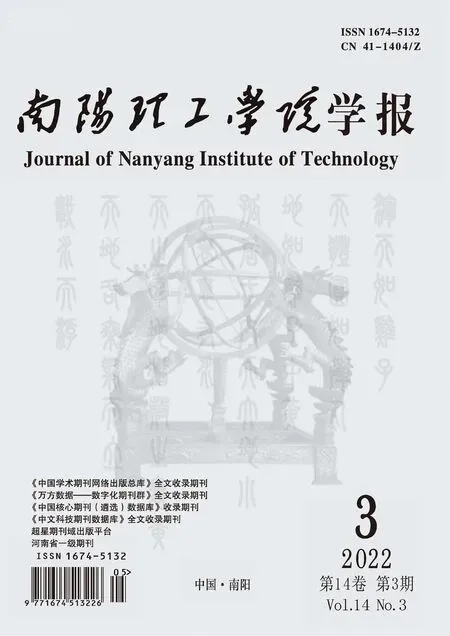“身份政治”视角下美国社会分裂解析
——以特朗普总统任期为例
李丙坤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唐纳德·特朗普上任第58届总统后,美国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在全美境内国民认同削弱,“身份政治”凸显。“身份政治”在美国尽管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方面比如给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但其负面影响也同样引人深思。“身份政治”带来的消极影响正在挑战美国的社会秩序。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美境内国民认同危机加深,政治冲突愈发严重,二是“身份政治”着重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反过来这些不同的利益加剧了美国社会各族群之间的分裂。
一 “身份政治”与社会分裂
(一)“身份政治”的内涵
“身份政治”作为对个体认同的心理意识的描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欧美出现的各类民权、女权、同性恋权利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地都突出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就“身份政治”的定义而言,目前并没有一个严格、明确、公认的概念。按字面意思解释“身份政治”就是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政治形态。《斯坦福哲学百科》一书将“身份政治”定义为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成员共享的非公正经验的政治活动和理论化描述。一些国内外学者也对“身份政治”进行了定义,比如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身份认同:对尊严的要求以及愤懑的政治》一书中指出,“身份政治”来源于一个人内心的真实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社会规则、规范的差距,当内心的价值或者尊严没有获得外部世界的充分承认时就产生了对于承认自己身份的要求[1]。中山大学谭安奎教授则将“身份政治”定义为以基于特定身份的诉求为目标,或以特定身份为优先考量乃至政治判断或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的政治形态[2]。在本文中,笔者把“身份政治”定义为“一种人们仅仅根据特定的宗教信仰、种族、社会背景、阶级等身份因素结成排他性联盟的政治立场和方法”。
(二)“身份政治”的特征
“身份政治”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资本、信息、商品等流动迅速,全球移民数量激增。这些因素都对一个国家的人口比例及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最为显著的便是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加深了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身份政治”在美国呈现出以下几种较为显著的特征:
1.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少数群体的身份意识觉醒
这部分群体由于存在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等问题而急于改变当前及未来的命运。在这样的目的驱使下,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属性而集中向政府提出诉求,以期获得更多的利益,改变当前的处境。
2.部分群体的国家意识、种族意识和民族意识重新唤醒
这部分群体主要包括美国五大湖地带的白人工人、其他州的“低收入的白人群体”以及数量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对于他们而言,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外来的大量移民与他们一起竞争有限的就业资源、医疗资源、社会福利。这些数量庞大的白人中产阶级丢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及优势身份,不得不抱团以期重新获得原有的地位及身份。例如,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均选择了无限放大“身份政治”的逻辑,激化底层白人的文化焦虑,巩固自己的基本盘[3]。这使传统的欧洲裔白人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强化,开始重新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甚至将这种身份开发为政治武器。
3.社会冲突由温和向激进转变
这主要体现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甚至有暴力事件的发生。如黑人群体鼓吹专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认同,批评白人群体的文化专制现象;女性群体在全社会追求性别平等,希望摆脱家庭压迫;同性恋群体在公开场合向民众表达独属于本群体的恋爱观念。由此带来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
4.身份重叠交叉且具有重复性
“身份政治”的身份具有多重含义,“身份”在整个国家中既可以以民族、宗教、阶级为基础,也可以以性别、收入等为基石[4]。这就导致同一个人可以同时处于不同群体之中,因而拥有了多重身份,并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中自由转换,在不同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
(三)“身份政治”与社会分裂的内在关联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当受到威胁时心理会变得狭隘且具有防御性,对他人产生抵触心理,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状态。当这种心理从个人拓展到群体中时,某个特殊的族群出于对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宗教信仰和种族尊严等因素的考虑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排他属性。
对于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而言,这些群体认为他们的身份——民族、宗教、性别、肤色等——都没有在社会中取得足够的认可,因此他们渴望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和社会表达愿望,要求社会尊重他们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差异,希望获得与主流群体一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来说,每当他们的诉求被忽视时,“身份政治”就会兴盛,并引发主流群体和非主流群体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
在美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白人群体更有可能过度偏爱自我身份而陷入对其他群体的不满甚至产生敌视,从而引发族群冲突[5]。自美国建国以后,白人就一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主导着这个国家,其他群体则一直生活在白人的阴影之下,这种主导地位使白人在政治上感到十分安全。如今随着大批少数族裔移民的到来,白人社会地位逐渐跌落,即将成为少数群体。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相关数据显示,预计到2044年少数族裔的人口总数将超过白人,即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在被“褐化”,白人群体有朝一日会成为少数族裔[6]。这给土生土长的欧洲裔美国白人带来的恐惧与焦虑尤为突出,他们危机意识的强化无疑会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据美国NBC新闻网2021年4月25日发布的民调显示,有8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处于分裂状态,种族和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加剧。
二 特朗普任期内的“身份政治”与社会分裂
(一)“身份政治”在美国的重新兴起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美国本土产生的一系列激进的社会运动,身份问题逐渐被贴上政治的标签,成为特定群体的政治抗争方式。
冷战结束后,“身份政治”在美国有了新的内涵,不再强调“身份平等”转而强调“群体认同”。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有三件大事重塑了“身份政治”。其一为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9·11”事件表明,当前人们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认同不再局限于国家、意识形态,这种认同也可以是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对于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信徒而言,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才是决定其对某些政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的首要因素;其二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大衰退,进一步引发了诸多激烈的政治对抗及冲突,加重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现象,强化了“身份政治”;其三为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尤其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纲领都是与“身份政治”有关的议题。“民主党所代表的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与作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的白人中下阶级之间的对峙,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7]。拥有商人和真人秀明星双重身份的特朗普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赢得总统宝座靠的就是分裂、发掘怨恨、武器化种族问题等。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看来,只要国家分裂,特朗普就有捍卫者,也就能削弱那些攻击他的人。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擅长使用Facebook以巧妙地避开传统媒体,向公众直接发布没有经过政治机器过滤、筛选的信息。特朗普正是选择了无限放大“身份政治”的白人至上主义,成功地激发了底层白人的委屈和不满,并不断向公众直接展示对非白人群体的对抗性信息,最终获得总统宝座。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学者福山撰写了《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详细论述美国的“身份政治”对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在所写的文章中也将特朗普的胜选归结为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
在这三大事件的影响下,“身份政治”在美国被赋予了“群体认同”的内涵。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美国人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做出不同的行为。
(二)特朗普操弄“身份政治”的表现
1.以“出生纸运动”为代表的首次对抗
实际上,在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时期,围绕“身份政治”就已经出现了首次对抗。2004年奥巴马带着“团结”的承诺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中,他向美国民众表示:“没有所谓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黑人、白人、拉丁美洲裔和亚洲裔的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奥巴马以“我们可以信赖的变革”作为竞选口号,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化,为种族之间的和谐带来了光明。但世事难料,在他的第一任期内种族问题却成了美国社会鸿沟的核心。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白人群体对奥巴马的愤怒日益加剧,甚至开始怀疑他是否是地道的美国人,在他们看来奥巴马的出生证明是通过手段伪造的,他实际上是一位肯尼亚公民。美国宪法相关条文规定不是美国公民就不能担任美国总统,由此引发了有名的“出生纸运动”。这引起了正在考虑参加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的关注。在特朗普的政治顾问班农的帮助下,特朗普将这一事件带入了公众的主流视野,他多次在公共场合责问奥巴马,“为什么不出示自己的出生证明?”“如果没在美国出生,你不能当总统,他可能没在美国出生……”。尽管在2008年大选的时候,奥巴马就向公众展示过与自己身份有关的相关材料,但针对奥巴马是肯尼亚人的质疑声音仍旧持续不断。为此奥巴马不得不向美国民众证明自己的美国身份,使事件平息。经历过“出生纸事件”后,奥巴马变得极其谨慎,几乎不对种族问题发表看法。在2012年2月26日晚,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马丁的黑人高中生在社区散步时被拉丁裔美国人齐墨曼开枪射杀而亡,但这名凶手最后却被无罪释放。马丁案在2015年还引发了轰动全美的南卡罗来纳屠杀案件。这两大事件中,奥巴马均未对种族问题发表过多言论,但身为一个黑人总统,甚至可以说就是靠着黑人的选票上台的总统,黑色族群希望他能发声。奥巴马任期内发生的重大种族案件显示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在衡量种族问题上的困难和复杂,稍有偏差就是立场错误,乃至引发社会冲突。
2. 特朗普突出“白人身份政治”的竞选策略
据统计,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超过60%的白人蓝领工人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将“白人身份政治”转变成为自己的竞选策略成为特朗普获胜的关键。
在这次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策略都带有明显的“身份政治”色彩。民主党将选票集中在社会边缘群体,共和党人则将目光集中在白人中下层选民并且将其描述为一个正在“受到威胁、歧视”的群体。同样的,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希拉里的支持者以女性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城市青年人、同性恋者、环保人士为主,她的竞选策略也旨在迎合这些少数族群的政治诉求,这反而在白人工人阶级那里产生了“希拉里会将工作机会优先给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的负面印象[8]。特朗普则凭借着对白人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吸引力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在竞选初期,特朗普打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标语投身于总统竞选活动中,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所提到的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美国,而是指一个基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群体为主的旧美国。在特朗普的数次竞选演讲中,他提到白人都会用“We”、“Us”来指代,而提到诸如墨西哥裔、拉美裔时则会用“They”、“Them”来指代。如在2020年的新墨西哥州竞选造势集会上,特朗普又一次打“身份政治”牌,公开向拉美裔选民发问:“你爱你的国家,还是爱拉美裔?”涉及具体政策方面,特朗普则将目前白人阶层所遇到的问题归咎于上层精英所做出的自由贸易政策、移民政策等。特朗普极力反对自由贸易,在其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重新进行北美自由贸易谈判,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工人获得更好的条件。为了防止就业岗位减少,他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了在美国本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特朗普宣布对将公司总部设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增加关税。在反对移民方面,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曾呼吁美国要对穆斯林彻底关上大门,他还把墨西哥非法移民描述为强奸犯,并一再强调这些移民抢走了原本属于白人民众的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和他们的孩子一同分享着美国的教育资源,提高了美国的犯罪率。上台后,特朗普则废除了之前的移民法案,甚至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方式筹集资金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同时拒绝接收具有恐怖主义倾向国家的移民。通过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和当选后的施政措施,不难看出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迎合对政府早有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一直以来自诩为民族的“大熔炉”,倡导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在多元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不同的群体都要求“平等权利”并在就业、教育等方面享受和白人群体一样的待遇。但全球化的加深和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认为自己是美国社会的主导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群体感到自己曾经的特权正在逐渐消失。诡异的是,以民主党为主的自由派打出的平权政策激发了白人群体的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而特朗普所采取的种种政策背后的白人化色彩能够帮助他们重新享有文化特权和身份优势,因而,这些白人工人阶级自然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仅如此,他们更是“白人身份政治”的基础。
3.“BLM”运动的典型案例
2020年5月,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的白人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的暴力执法,在美国六百多个城市引发了以“BLM(Black Lives Matter)”为主题的各类抗议活动,并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社会抗议活动,是非洲裔美国人追求种族平等的“身份政治”的强力表现。这些抗议活动引发的骚乱直接反映的是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对社会和政府的抗争,背后则暗含了黑人平权与白人至上两种运动之间的对抗[9]。尽管由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BLM”运动规模前所未有,然而特朗普却没有对白人种族主义做出批判,反而呵责这项运动人为地制造社会分裂,不断强化白人选民对他的忠诚度,以期第二次赢得总统大选。
2020年底特朗普输掉了竞选,导致美国总统的权力交接出现了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失序。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参众两院统计本次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的同时,大批“川粉”聚集在白宫外举行了“拯救美国”的集会。特朗普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拒绝接受败选的事实并声称这次的选举结果被“偷窃”、“更改”、“操纵”,煽动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之后,人群破坏了国会广场前的围栏并冲进了大厦,导致国会休会,议员匆忙逃走。虽然特朗普这次竞选总统落败,但他仍然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可见其仍然拥有庞大的选民基础。
总之,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的几年里,“身份政治”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新政治,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与美国社会的撕裂。
三 后特朗普时期“身份政治”对美国的挑战
(一)政治共同体能否继续保持统一
当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多个政治派别时,“身份政治”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都必然会威胁到政治共同体的统一。美国政治习惯性地把美国社会划分为对立的两个层次——共和党和民主党、红色州和蓝色州、左翼和右翼、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白人群体和非白人群体等[10]。这些对立层面之间的差异正在日益扩大,在短期内看不到双方和解与理念趋同的迹象。在政治发展中,身份标签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被标注出来,形成“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状态成为政党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在美国,民主党人的政策越发迎合少数族群和诸如同性恋群体等少数群体,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与之相对的共和党则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建立起了一个以白人为主的联盟。以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目光集中于种族歧视,强调加强对黑人、少数族裔、女性等群体权利的重视,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在种族问题上保持了沉默,重点突出了维护美国白人的权利。回顾特朗普的任期,美国的两党政治朝着极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政治共识愈发受到挑战,导致在社会内部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
(二)“身份政治”影响下的政策走向
2018年9月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外交事务》杂志采访时表示身份问题超越了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正在主导当今美国政治的走向,“身份政治”不仅成为解释全球事务的主要概念,也对国家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11]。
对于边缘和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所追求的“身份政治”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权利平等、反抗社会歧视。然而对于曾经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白人群体而言,他们倡导“身份政治”的背后,反映了对不断涌入的移民群体的无休止利益诉求的不满、对自身生存的焦虑和对现行政策的愤懑[12]。这些人中不乏一些移民群体的同情者、倡导弱势群体救助的支持者,但现在他们既失落、委屈又心中不平。于是,他们也开始倡导自己的身份认同,主张维护其所在阶层的收入、地位和荣誉。
在特朗普的任期内,“美国优先”战略背后表现出了激进的“身份政治”倾向。特朗普的种种对内对外政策均表现出了白人至上主义。这种白人至上主义不仅激发了中下层白人的身份意识也成功地将白人民族主义引向舆论中央。然而2020年坐拥7400万(在美国历史上得票位于第二位)选民的特朗普却输掉了美国大选,这些铁杆“川粉”在失去“发言人”时,不可避免地会重新面对制造业流失、贫富差距、移民大量涌入等问题。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外来移民会使白人群体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来自少数族裔的压力,身份认同感会日益得到强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的任期内,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失业率屡创新低,制造业就业人数回升,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以内,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19年出现较大收缩。拜登上台后如果能继续保持这个劲头,无疑是一个弥合社会分裂的好办法。
2021年1月21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他利用民主党在国会的优势,顺利推行其新政策。然而当前的美国内部对立严重,拜登要想弥合社会分裂就必须争取到相当一部分特朗普的支持者,否则拜登的政策难以在整个社会推行。依靠一党的力量在国会中推进某项政策议案,在一个不同党派理念严重对立的国家必然加深党派之间的分歧,甚至引起不同党派支持者之间的激烈冲突。
拜登的内阁成员超越了肤色、性别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执政团队。这或许能为更多民众带来被代表的政治效能感,但这样的组合也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白人、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于“我们是谁”的身份焦虑,形成“政治正确”的强烈冲突[13]。
2020年底,尽管特朗普败选,但是“特朗普主义”的民意根基仍然存在。在2021年4月29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一方面对现任总统拜登的政策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表示自己将在2024年继续参选并为参选造势,特朗普还表示现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可能会成为他的竞选搭档。四年之后,“特朗普主义”有极大的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回归美国政治生活。
(三)“身份”与“选票”的恶性循环
“身份政治”认同在美国两党主导的选举制度下,必然形成社会成员间的对抗冲突,加重群体内与群体外社会成员的冲突。“身份政治”正逐步将深层问题表面化,而美国的两党制则强化了各自的“身份”立场。2016年和2020年的美国大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两党竞选人的政策更多地集中于对身份认同的运用。运用“身份政治”便于政治家获得更多的选票,这样的正面效应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政客利用这一政治现象,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对于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而言,急需通过构建一种跨越身份认同的国家认同来扭转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与极化趋势。换言之就是在全美境内,无论是移民还是原有的白人、无论是非裔美国人还是亚裔美国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等都要跳出身份的小圈子,在身份圈子之外认可同一个美国文化,同一个美国政治,同一个美国身份,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反之,如果过分关注个体和政治身份的差异,则不利于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
四 结语
“身份政治”给美国带来了诸多问题,最突出的莫过于使美国人无法走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划分的小圈子,强化了个人主义,使单个的人退缩到自己的族群抑或是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小圈子里。以后的美国无论是在面对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是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共和党和民主党均需重视“身份政治”在美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当前的社会危机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即族群政治会破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但族群意识亦是人类作为生物而具有的群居本能的反映。如何既能促进民族融合,又能维持文化的多元,让不同的族群变得包容而不是对立,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