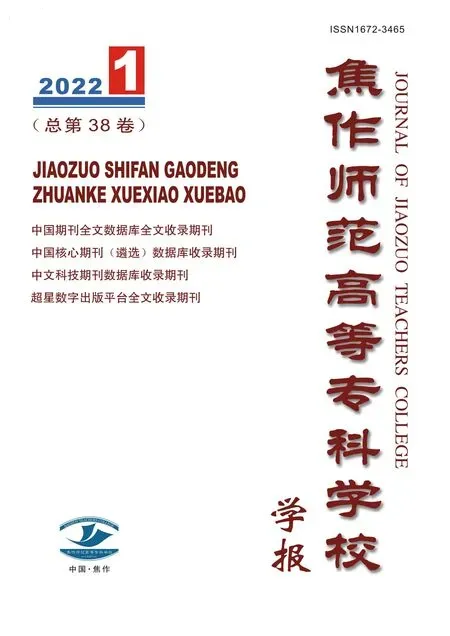许衡对“万物皆备于我”章的诠释
张小晴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万物皆备于我”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孟子》颇为难解的一章。许衡对此章尤为重视,所著《孟子标题》和《孟子通解》二书虽未见传本,但《语录》《阴阳消长论》《答仲叔家语亡弓论语予所否者》《观物》等仍保留着相关引述与解读。他在阐释“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时引入理气范畴,着重阐释后四句,因而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展开,具体探讨理气关系和“诚”“知行观”、变化气质等内容[1-4]。学界研究成果开显出许衡释论的多个面向,但以往研究大多引用部分诠解内容,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诠释《孟子》此章时本体与工夫相贯通的思维模式。从《语录》来看,许衡将此章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诠解“万物皆备于我”论述道德依据,“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的诠解涵括修养必要性、修养目标与成德方法。考察许衡对“万物皆备于我”章的诠释,关乎到其工夫论建构与孟子学思想的问题,对于显豁元代孟子学诠释的丰富内涵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通过爬疏许衡阐释“万物皆备于我”章的内容,将释论统串为一体,试图完整地呈现其整体阐述和诠释进路,进一步窥测其理学思想特色及时代意义。
一、“万物皆备于我”章的历来疏解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言语简略,颇为费解。汉代以来,许多儒者从各自的学术路径出发诠释此章。赵岐、程颢、张载、张栻、朱熹、陆九渊、王夫之等大儒对“万物皆备于我”章的诠解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其一,成人万事皆知,彰显道德知识的重要性。汉代赵岐从知识角度进行阐释:
物,事也。我,身也。普谓人为成人已往,皆备知天下万物,常有所行矣。诚者,实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实而无虚,则乐莫大焉。[5]
宋代孙奭延续赵说,将“以其外物为乐”和“以内为乐”区分为小乐与大乐,强调“不为物丧己”“有得于内”的大乐[5]。清代焦循进一步解说成人万事皆知的可能:
我亦人也,我能觉于善,则人之性亦能觉于善,人之情即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即同乎我之欲。[6]
换言之,成人“知识已开”,道德知识基本完备,能推己及人践行忠恕之道。
其二,“诚”的精神境界,凸显道德境界。程颢将“反身而诚”与万物一体思想相结合: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7]
依大程意思,“反身而诚”即与物同体之乐,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与张载“民胞物与”思想大致相同。张栻注重道德情感的类推能力,追求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诚能推己及人,以克其私,私欲既克,则廓然大公,天理无蔽矣”[8]。
清代王夫之对孟子精神境界做出反思,把孟子之乐的意涵扩充为身心政事交养之乐[9],认为孟子之乐与孔颜境界可以相提并论:
乃孟子于“万物皆备于我”之下,说个“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何等境界!愚意,即此与孔、颜无甚差异。[10]
这即将孟子的精神境界提升为天人合一的形上之乐。
其三,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为理本论张本。朱熹诠释说: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11]
概言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12]1749。他从“理”论证道德行为依据在我身上原本自足。我身上原本完备的理,在现实中受到气禀物欲的遮蔽,需要通过外向的格物穷理去认知和把握。“反身而诚,乃为物格知至以后之事,言其穷理之至,无所不尽”[13],经过格物穷理、积累贯通才能达到“反身而诚”的效果。
其四,万物皆备于我心,从心本体层面抉发。陆九渊将孟子学视为思想渊源:
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14]5
这是从心本体诠释此章,良知良能是其“本心”说的立论依据。陆九渊和朱熹都注重存在层面,但不同本体存在本质区别,格物方法亦不同。朱熹在《释格物致知》中评价说:
陆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这物事。[12]396
朱学的格物包括穷究物理,而陆学的格物为心上工夫,展示出二者修养路径的不同。
理学家着重从形上层面诠释此章。程颢等人探究精神境界,重点解读“反身而诚”之乐;朱熹和陆九渊从本体上立论,用力发掘“万物皆备于我”的依据,展示出本体和修养方法的不同。可见,“万物皆备于我”章的确难解,而对其解读也颇能彰显儒士的思想特色。许衡诠释此章的时间在元代初期。元初时代环境与宋代不同:一方面,儒士肩负着传扬和保存中原文化的使命;另一方面,蒙古对金与南宋的征服,引起金元儒者对宋末道学空谈性理风气和假道学现象的反省与批判[15]。针对宋末理学弊端,许衡主张为学返求《论语》《孟子》与《六经》,注重践履笃实。他探究“万物皆备于我”是为了寻找理论依据,从而建构起本体与工夫相贯通的诠释模式。
二、许衡对“万物皆备于我”的诠释
许衡以朱子学为依归,在理学范式下重新解读孟子学思想。在诠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时,他并未完全依照朱熹的解读路径,而是将庄子之说、朱熹理学、邵雍象数学、释氏论心等学说加以引证或阐发,会通儒释道思想。他试图从本体与心性层面找寻“万物皆备于我”的依据,为道德建构形上本体。
元至元三年(1266)冬,许衡寓居燕京崇天观著《阴阳消长论》,从阴阳之气入手诠解“万物皆备于我”。他引述庄子“一尺之箠”之说,指出每日将木棍截为两段,日复一日,不断重复,即使木棍变得细微不可见,但阴阳仍然存具于其中。他因而得出结论:
是知天下古今,未有无阳之阴,亦未有无阴之阳。此“一物各具一太极”,“一身还有一乾坤”也,孟子谓“万物皆备于我者”是也。第未得一无之数,沿而下之,以见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数,泝而上之,以见其元。安得如康节邵先生者从而问之。[16]253
在许衡看来,阴阳是一对范畴,阴阳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永恒规律,阴阳消长规律存在于每一事物的始终。“一物各具一太极”出自朱熹《太极图解》,“一身还有一乾坤”语出邵雍《观易吟》,许衡引述朱、邵之语阐发“万物皆备于我”,旨在说明阴阳二气消长的规律具足于我身,即自然规律在我身上完备无缺。阴阳之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质料,“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16]107。在论及太极与阴阳关系时,他将太极理解为太极之气,太极与阴阳是一元二气的关系,“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16]345。许衡通过论述万物、阴阳、太极、理的关系,建构起“道(理)→太极→阴阳之气→天地万物与我”的宇宙生成模式,阴阳二气是宇宙生成的重要中间环节。“沿而下之”,阴阳之气相合化生天地万物与我;“泝而上之”,阴阳之上存在“道”这个实理。“道”和“理”属于同一层次,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他从阴阳之气切入,通过上溯与下沿建构起宇宙生成模式,目的是建构一个统合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的思想学说,论述道德的可能性。
许衡引入心、性等范畴以探寻“万物皆备于我”的道德依据。他在最高本体层面延续朱学的理本说,坚持“‘性’,即是理”[16]173的说法,又在《语录》中作出补充和发挥:
释氏有所谓“如意宝珠”,有所欲为,无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是,善道亦在是。苟于此焉真积力久,其所欲为,无不如志者。[16]103
“如意宝珠”是佛教论“心”的概念,五代延寿在《宗镜录》中论及典故,大意是金翅鸟死后骨肉散尽,只有心保留下来,难陀龙王取此为明珠,转轮王得之视作如意珠。此珠是“真心”的象征,即“菩提心”,万类之中最为宝贵。此处虽未见“心”字,本心概念实则已经呈现,可见许衡重视心的地位与作用。在他看来,心形体虽小,但蕴藏着天地万物之理,“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过有六尺之躯,其大处同处,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16]94。人能与天地一般就在于心,学习圣贤文章不过是为了“求圣人之心”[16]72。许衡对心的看法与陆九渊有相似之处,陆九渊将仁义视为本心,“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14]13。许衡说:
试以斯二者体之,则世间何事不备于我?在君臣为义,在父子为仁,无不可者。正所谓“如意宝珠”也。[16]104
以仁义之心体之,则世间万事万物皆备足于我。从理论上来说,道德伦理在我身上完备无缺,以仁体之则物我兼该,以义体之则各得其宜,展示出提高心的地位的倾向。他将“如意宝珠”等同于“德性”,德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表现,是天赋予人的仁义礼智信。心与性不可割裂,心、性、天、理“便是一以贯之”[16]93,似乎可以当作是一回事。许衡对心、性、理的处理,看似没有圆融一贯,实则是他对朱子学做出的改造和发挥。
许衡从阴阳之气入手诠释“万物皆备于我”,试图从天人合一角度建构形上本体,目的是为了构设道德本体。通过“泝而上之”凸显道德的可能性,从理气关系论证修养的必要性,接着从理气角度诠解“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自然而然进入对修养路径的探究。他试图将道德的可能性、修养的必要性、修养方法与目标完整展现出来,建构起体用一贯的心性修养工夫。关于“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的诠释,进一步明晰了这一诠解路径。
三、“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
许衡将孟子此章诠解为连锁贯通的整体,“万物皆备于我”是成德依据,达到“诚”的境界须经由“反求诸己”“强恕而行”的修养过程。他从理气角度论述“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将修养工夫与心性本体联结起来,体用一贯,知行并进。在元初务实环境下,许衡主张通过“力行”使道德意识与道德法则发见于日用伦常之间。
许衡主张孟子性善说,人禀理成性,本性纯善无恶,但由于气禀不同导致现实个体的差异。气有清、浊、美、恶,因而衍生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差别;清美、浊恶的分数不等,所以修养境界有不同等第。“气,阴阳也,盖能变之物。”[16]123气不断变化,若纵于情欲,不加节制,清美之气会变为浊恶之气;若修养心性,克己复礼,浊恶之气则变为清美之气。因而,许衡从理气角度入手,论述变化气质的工夫:
“反身而诚”,是气服于理,一切顺理而行。气亦是善,岂有损于其间?“强恕而行”,是气未服顺,理当西而气欲东,必勉强按服,必顺于理然后可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为之际,或远于理,气未得平,必勉强其气,以从于理。人之不善,未合于理,亦在容恕,未庸遽与之争也。在事必勉强,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能强于为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则吾之仁远矣。[16]104
“反身而诚”是气受理的支配,气为清美之气,“强恕而行”是气与理逆反,必须勉强按服气,使之顺于理。至于具体的修养方法,《观物》一诗似乎粗略给出了答案,“万物备吾身,身贫道未贫。观时见物理,主敬得天真”[16]356。知识层面的探索亦有助于彰显道德实践主体的价值,但主要是通过道德层面的持敬工夫,最终达到至诚无妄的理想境界。在答复李仲叔的书信中(1)家藏本以《答仲叔〈家语〉亡弓〈论语〉所否者》为题将其按照书信收录到书状类,中州本、和刻正德本以《纪疑二事答李仲叔》为题名,中州本将其收录到杂著类。,许衡讨论了“反身而诚”的修养境界,“言来谕以‘反身而诚’,为颜子乐处,意极精切”[16]324。反求吾身,若能做到真诚无妄,到达颜子境界,这便是最大的快乐了。若未诚,则是气与理不服顺,须勉强践行忠恕之道,到达仁的道路,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张载曾言“既知之,又行之惟艰。万物皆备于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为近”[17],即持久地在行动上落实善道是艰难的。许衡则从人己双重维度解读“强恕而行”的内涵,自己处事接物不合乎道德规范,须勉强而行,去除气禀、物欲的遮蔽,以符合理;他人未能为善,则要推己及人,涵容宽恕。先自求己事,勉强行善去恶,践行善道,如果于此处真诚地积累且持久地力行,那么所想要做的事情,没有不如志的。“强恕而行”是有意识地确立自我修养,道德实践带有故意性,到“反身而诚”阶段“气亦是善”,道德实践主体从故意性中解放出来[3]。许衡舍弃了朱熹以圣贤之事与学者之事不同修养层次区分“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的诠释路径,开出以理气区分二者的解读方法,强调道德实践见证于生活与最终结果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即使是资质愚钝的人,只要真诚地追求和实践善道,“至功深力到,则与‘反身而诚’一矣”[16]104。虽然资质不同的人所走的路径和付出的努力存在差异,但是最终去处是一样的。
许衡将整章的释义落脚在“力行”工夫上。他通解《孟子》此章为“件件事至诚恻怛做将去,其心安,其气舒,俯仰无愧,其乐可知。此天下广居也”[16]103。真诚地积累知识,持久地践履善道,则能身心泰然,理气和顺。许衡尊信朱子学,将朱熹《或问》等书一一抄录,应当能关注到《大学或问》将“格物致知”作为“反身而诚”的重要前提条件。然而,他对格物做出新解:
朱子说,经文所言“致知在格物”者,是说人要推极自家心里的知识呵。[16]142
将格物理解为向内心求索,颇有心学色彩。他主张“知与行,二者当并进”[16]98,注重道德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促进、相互启发。在他看来,“强恕而行”阶段需要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身行为,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和提升道德认识,使道德知识逐渐内化为道德自觉,最终从故意性中解放出来,实现道德自由。易言之,通过持久的道德实践,使德性和良知良能彰显出来,心性本体的自觉在生活中发挥主宰作用,身心得到安顿,人的价值与意义便得以挺立。
许衡对“万物皆备于我”章的诠释,实际上含括他对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深刻体会。首先,许衡融合多家思想建构起关节完备的理论,彰显出道德的意义和价值。他对道德的重视于今仍有借鉴意义,易言之,将新诠释所开示的内容和当今文化语境相结合,能够启发当代道德建设。许衡融合多家思想来诠释“万物皆备于我”章,建构出新的心性修养学说,启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在赋予时代新内容的过程中能够被激发出生命活力。其次,他强调知行并进工夫,主张通过实践将道德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实现道德自由,这对于启发当代人的修身立德具有现实意义。修身律己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将正确的道德知识和主动的道德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提升修养境界,方能在繁杂的现代生活中坚守本心,自觉抵制物欲的诱惑。再次,持敬、反躬自省、知行并进的修养方式为道德提升提供了可行路径。在当代社会,以新时代道德为导向,通过反躬自省、知行并进等方法可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这也为德育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许衡对“万物皆备于我”的诠释,展示出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强调实践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凸显了道德实践的意义,具有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