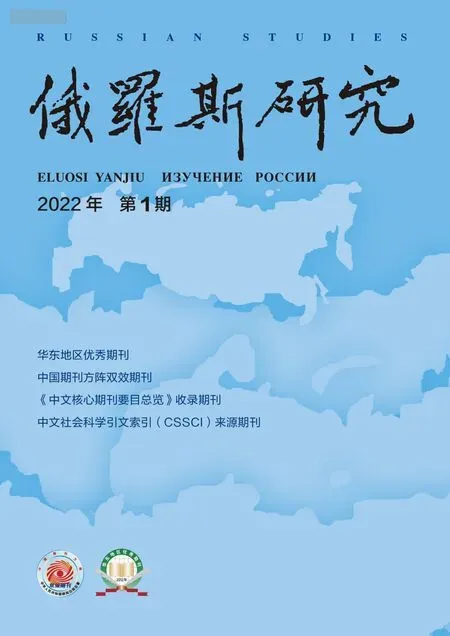中断还是反复
——“颜色革命”中的路径依赖*
曾向红 尉锦菠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为代表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抗议、游行示威、骚乱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社会运动不仅影响着各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也深刻牵动着世界政治形势的演变。社会运动对于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何一国会反复发生社会运动并导致政权更迭。本文尝试运用路径依赖机制及相关观点,通过比较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应对“颜色革命”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初步得出一国因社会运动反复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本文认为,不同国家应对“颜色革命”的不同策略,将形成存在明显差异的社会运动动员类型,这种差异经由路径依赖机制而得到固化,最终在特定国家形成导致“颜色革命”或中断或反复的不同互动模式。
21世纪以来,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骚乱等具有抗争政治特征的社会运动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来自社会运动的挑战。不过,社会运动对于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社会运动带来的众多后果之中,影响最大,同时也最受研究者重视的,是社会运动所导致的政权更迭。如果某国因社会运动多次出现非正常的政权更迭,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研究就具有重要价值。而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国家反复出现因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本文选取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在2005年、2010年、2020年三次出现大规模抗议并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作为主要案例进行研究。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尝试选择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机制切入,并引入乌兹别克斯坦作为比较案例,探索一国为何反复因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
本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颜色革命”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所发生的三次非正常政权更迭;第二部分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评述及对案例选择的解释;第三部分是运用路径依赖机制,尝试提出分析政权与社会运动互动的框架;第四部分是分析吉、乌两国应对社会运动时采取不同策略的原因;第五部分是不同应对策略所形成的“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如何得以固化;最后是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背景:“颜色革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三次政权更迭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发生在欧亚地区的以颜色或花朵命名、以“街头政治”的方式导致政权变更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后来随着中东变局(西方称作“阿拉伯之春”)等运动的爆发,“颜色革命”的内涵发生了扩展,泛指西方国家通过操纵某国内部抗议势力,结合非军事手段,建立符合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亲西方政权的行为。①Ieva Bērziņa, “Weaponization of ‘Colour Revol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2019, Vol.18, No.4, pp.330-343.
从2003年开始,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出现了以“街头政治”为代表的非正常政权更迭。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发动一系列示威活动,促使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成功夺取政权。由于萨卡什维利在抗议示威活动中总是拿着一枝玫瑰花抛头露面,该运动也被西方人称为“玫瑰革命”。“玫瑰革命”成为掀起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各国反对派望风而动,伺机夺取政权。在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尤先科的支持者聚集在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进行示威,抗议亚努科维奇选举舞弊。迫于压力,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进行重新选举。尤先科以52%的优势胜选。由于尤先科在大选中使用橙色作为其标志,这些抗议示威活动也被西方国家称为“橙色革命”。
2005年2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议会选举。以巴基耶夫为首的反对派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指责时任总统阿卡耶夫所属的政党在选举过程中存在舞弊行为,并在吉南部地区动员大批抗议者游行示威。3月24日,抗议者在比什凯克市中心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总统下台。傍晚,抗议者攻占了总统府,阿卡耶夫流亡海外。由于部分示威者手持黄色手帕或郁金香花束,此次事件也被称为“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政权的崩溃标志着“颜色革命”在欧亚地区的发展达到高潮。受“郁金香革命”影响,2005年5月12日,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爆发骚乱,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警察哨所和部队营房,并释放了500余名在押犯。①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安集延事件”的定性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该事件不在选举周期内爆发且手段具有暴力性,因此不属于“颜色革命”而是“恐怖主义”。但无论是俄美双方,还是国际社会,均倾向于从“颜色革命”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解读,认为“安集延事件”同样是抗议者通过体制外方式挑战政府权威,是“颜色革命”的延续。参见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48页。同时,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安集延的中心广场,要求卡里莫夫下台。此次骚乱很快便被乌政府镇压下去,武装分子与部分抗议者被捕,其余抗议者或被驱散或外逃至吉尔吉斯斯坦。
5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二次革命”。通过“郁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也由同样的方式被赶下总统宝座。2010年4月7日,因“祖国党”领导人被警方逮捕,反对派支持者在比什凯克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总统巴基耶夫辞职。数千名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4月15日,反对派成立的临时政府称巴基耶夫已经签署辞职声明。25日,巴基耶夫流亡白俄罗斯。2020年10月4日,反对派指责议会选举过程中存在贿选行为并于次日在比什凯克组织抗议示威。示威者攻占总统府和议会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在10月9日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迫于压力,热恩别科夫于15日辞职。
本文选取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如下:第一,所选择案例应满足出现两次及以上因为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的现象,否则不能被称为“反复”。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于2005年、2010年、2020年爆发“郁金香革命”“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①致使巴基耶夫和热恩别科夫政权垮台的两次事件至今没有形成广泛认可的称呼,例如,对2010年巴基耶夫政权垮台就存在“二次革命”“血色革命”“无色革命”三种命名方式,参见周明、李嘉伟:“21世纪初两次国际抗议浪潮的关联与比较——兼论作为中介的吉尔吉斯斯坦‘革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1期,第94页。本文按照政权更迭次序将2010年与2020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两次非正常政权更迭称为“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似乎通过抗议示威来推翻政权已经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固定”的权力交接模式。第二,该国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是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而非结果。因此,埃及与缅甸分别于2013年、2021年因军事政变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可以被认为不属此列。委内瑞拉、泰国等国家虽然反复爆发社会运动,但没有因此而导致政权更迭,也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
二、文献回顾与案例选择
(一)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对于一国反复因为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这一问题,学术界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成果。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当前学术界对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吉历次“革命”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历次“革命”爆发原因的探讨;二是将在吉发生的“革命”作为案例,纳入21世纪初波及欧亚大陆的“颜色革命”浪潮中进行研究,将“郁金香革命”②2003-2006年发生在欧亚地区包括“郁金香革命”在内的受到境外西方势力干预的非正常政权更迭,通常被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而发生在2010年的“二次革命”则因受到俄罗斯而非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背后的干预,通常不被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发生在2020年的“三次革命”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干预,通常也不被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与“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进行比较,以探讨“颜色革命”爆发的一般性原因及其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三次革命的分析大致相同,认为其爆发“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1. 经济问题。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认为,高度的不平等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①参见 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 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quoted from Steve Hess,“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Regional Protest Waves: The Post-Communist Colour Revolutions and 2011 Arab Uprising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6, Vol.51, No.1,pp.1-29.自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其处于贫困线及以下的民众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始终在30%以上,南部人口密度较大而且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比北部更多。巨大的贫富悬殊加剧了底层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进而导致了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但该解释的缺陷在于:为什么不满无处不在,但抗议不是无时不有?单一的经济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何吉尔吉斯斯坦反复爆发“革命”。
2. 部族问题。事实上,吉尔吉斯斯坦自转型以来始终处在“部族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中。吉政权更迭体现出南北精英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权力交接的特征。在“郁金香革命”中,出身于北方部族的总统阿卡耶夫被来自南方部族的反对派推翻;而在“二次革命”过程中,出身于南方部族的总统巴基耶夫被来自北方的反对派推翻。但值得注意的是,部族因素无法有效解释发生于2020年的“三次革命”。王林兵和雷琳指出,热恩别科夫延续了“二次革命”后在政府人事任命中“去部族化”的做法,在既没有谋求“家族专制”复辟,也没有鼓动“南北对立”的前提下,热恩别科夫政权却被推翻了。“在过去的政权更迭中,要么是‘北方反对南方’,要么是‘南方反对北方’,但为何此次变局却形成了‘南方反对南方’的格局?”②王林兵、雷琳:“从议会选举到政治变局——吉尔吉斯斯坦西式民主的危机”,《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8页。
3. 腐败。在吉尔吉斯斯坦,无论是寻求商业机会还是政府机构中的领导职位,都需要金钱,并与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③Jaimie Bleck, Igor Logvinenko, “Weak States and Uneven Pluralism: Lessons from Mali and Kyrgyzstan”, Democratization, 2018, Vol.25, No.5, pp.804-823.在2021年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中,吉尔吉斯斯坦在180个国家中排第124名。①“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ugust 10, 2021,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ountries/kyrgyzstan2004-2011年间,吉腐败感知指数从未超过2.3分(满分为10分),2012-2021年间,吉腐败感知指数从未超过31分(满分为100分)。②“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ugust 10, 202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貪污感知指數国外势力与本国反对派揭露这些腐败行为直接成了“革命”的导火索。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三次“革命”过程中,反对派或者境外势力所控制的媒体均通过“揭露”现任领导人的腐败行为而煽动民众进行抗议示威。
4. 外部势力干预。杨心宇指出,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实施的政府更迭计划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③杨心宇:“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的若干问题”,《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4期,第45-56页。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积极向吉反对派提供资金、技术、方法援助,并通过其所掌握的媒体机构对现政权进行“丑化”,煽动社会舆论,进而实现政权更迭。
将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革命”作为案例纳入“颜色革命”浪潮进行研究的成果,在承认以上因素对于“革命”爆发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替代性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关注政府与反对派的互动。大卫·雷恩(David Lane)认为,“颜色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一个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派,以及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政策。④David Lane, “‘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9, Vol.25, No.2, pp.113-135.而政府对反对派力量大小的估计与是否采取镇压措施,也极大地影响了“颜色革命”成功的概率。⑤Charles Sullivan, “Misruling the Ma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Cracking Down in Kyrgyzsta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9, Vol.47, No.4, pp.628-646.也有国内学者进而认为,“颜色革命”的成败“不是反对派或者政府一方的原因,而是受到两者之间互动的影响”。⑥曾向红、连小倩:“从反对派与政府互动差异看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3期,第63-84页。第二种解释是“颜色革命”的示范效应。既有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性在推动政治转型中发挥了强大的因果作用。⑦Steve Hess,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Regional Protest Waves: The Post-Communist Colour Revolutions and 2011 Arab Uprisings”, pp.1-29.“颜色革命”具有明显的扩散性。一旦一个国家的抗议活动获得成功,抗议策略就会通过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s)转移到区域内的相似国家,导致邻近国家也突然出现类似的抗议模式。①释启鹏、韩冬临:“当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130-155页。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小国很少受到学界关注,以上研究成果的出现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但以上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上述大部分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结构化的特征,往往将政权更迭这种重大的结果归于宏观层面的原因,强调是特定的政治或者社会结构塑造出的特定结果,而忽视了类似的条件导致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上述因素在爆发或者没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其他欧亚国家或多或少也存在,但其他国家并没有反复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乌、吉两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实矛盾、潜在的政治风险类似,且两国分别在2005年遭遇了“安集延事件”与“郁金香革命”的冲击,但两国日后的政治发展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与西方学者的预测相反,“颜色革命”浪潮衰退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局势保持着稳定,并于2016年卡里莫夫总统去世后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大众动员数据库(Mass Mobilization Data)②大众动员数据库(Mass Mobilization Data)是由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教授大卫·克拉克与圣母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里根采集编制的抗争政治数据库。旨在了解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抗争事件(包括抗议者的诉求以及政府的回应方式)。该数据库涵盖超过1万起发生在1990年至今的162个国家和地区的50人以上规模的抗议事件。所采集的数据显示,2005年“安集延事件”至今,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未爆发过大规模抗议示威。③包括爆发“郁金香革命”的2005年在内,吉尔吉斯斯坦共发生500人以上规模的社会运动46起,其中暴力抗议15起,抗议诉求则“五花八门”:抗议警察执法不公或者暴力执法2起,抗议物价上涨2起,土地权纠纷抗议1起,劳资纠纷抗议1起,抗议官员腐败5起,抗议本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或者追求民主41起。乌兹别克斯坦包括2005年“安集延事件”在内共发生500人以上抗议示威6起,其中暴力抗议2起,和平抗议4起。抗议警察暴力执法2起,抗议物价上涨1起,抗议官员贪腐1起,抗议政治进程(本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或者追求民主转型)2起。由此可见,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示威活动更加“常态化”,并且充斥着明显的“破坏性”。而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的次数极少而且很少附带有实现“民主化”等政治目的。但抗议示威反复爆发作为吉尔吉斯斯坦跨越15年之久的动态变化过程,仅仅用结构性的静态因素而忽视时间因素加以解释,常常会陷入“用常量解释变量”的谬误之中。因此,上述成果虽然指出了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革命”的诸多背景因素,但却难以对一国为何反复因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这一问题给出准确解释。

图1 吉、乌爆发500人以上规模社会运动频次对比(2005-2020年)(次数)
(二)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将乌、吉两国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因在于,两国都位于中亚地区且长期处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框架内。在独立初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且两国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故具有较高的可比性。①曾向红:“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第9-37页。而同样发生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并实现了政治稳定的格鲁吉亚,则在地缘位置、国家身份、道路选择等方面均与吉尔吉斯斯坦存在巨大差异,不太具有可比性。其次,本文旨在回答,为什么一国会反复因为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故重点在于解释“反复”这一长时段的行为,即在发生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吉尔吉斯斯坦反复爆发,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类似的情形。同样,在历史上同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且同为中亚国家、但没有发生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土库曼斯坦等国也不在比较的范围之内。在西方学者看来,乌兹别克斯坦长期限制市场经济发展并实行广泛的政治与宗教“压制”,这些在既有的理论解释中可以促成政权更迭甚至是内战爆发的因素,在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发生作用,①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19, No.1, pp.78-97.因此乌兹别克斯坦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反常”案例。探析乌、吉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助于解释这一问题,即为什么两国都遭遇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冲击,但乌兹别克斯坦后续实现了政治稳定,而吉尔吉斯斯坦却掉入反复爆发“革命”的泥淖?
与现有解释不同,本文认为,一国会反复由社会运动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在于:在一国的抗议历史上,当政权采取妥协的方式应对抗议示威,将会扩大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而这种政治机会会进一步增强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这种影响经过“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的过程逐步得以固化,最终导致该国政权与社会运动之间形成了一种一旦民众对政治现状产生不满,就诉诸社会运动推翻政权的互动模式。
三、理解“反复”:路径依赖机制中的关键节点与正反馈
路径依赖机制最早出现于经济学领域。保罗·大卫(Paul A. David)和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分别以QWERTY作为字母排序的通用式键盘与VHS制式录像机取代BETA制式录像机作为案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反常现象——一项并没有显示出更高效率的科技发明,在初始阶段的比较优势会使该成果比其他效率可能更高的后期竞争产品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且随着收益递增强化获得重要的优势地位,最终占有整个市场。②参见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 Vol.75, No.2, pp.332-337; Brian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1989, Vol.99, No.394, pp.116-131.这种被理解为涉及“正向反馈”的自我强化过程,就是路径依赖。
将路径依赖这一机制引入政治学领域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者认为,行动者偏好、权力关系和资源配置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和外部给定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并得到强化。①奥菲欧·菲奥雷托斯、图利亚·费勒提、亚当·谢因盖特:“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2期,第112-126页。当既有结构产生了收益递增,并对嵌入其中的政治行为体产生正向反馈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或偏离既有路径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认为,一旦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始步入某一条轨道,那么逆转这种轨道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与此同时,尽管其他的选择始终存在,但若干制度安排的确立阻碍了最初选择的轻易逆转。②Margaret Levi,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L.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n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9-41.换言之,事态发展的时机和次序至关重要,早期事件产生的因果作用将明显强于后续事件。
路径依赖分别涉及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与正反馈两个阶段,其中关键节点构成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关键节点的概念界定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科利尔夫妇(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认为,关键节点是“一个显著变化的时期”,它通常会在不同的国家(或其他分析单元)中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它被假设为会产生独特的制度遗产。③参见Ruth Berins Collier,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 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则在有关中美洲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将关键节点定义为在两个或更多选项中选择某一特定选项时的选择点(Choice Point),而这个选择点是由先前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马洪尼强调了关键节点④需要指出的是,马洪尼并不认为所有的选择点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仅仅是指对未来能够产生重要结果的选择点。但如何衡量所谓“重要结果”的重要程度,马洪尼则没有做出相应的说明。参见James Mahoney,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1, Vol.36, No.1, pp.111-141.与路径依赖过程之间的关联,“一旦特定的选项在关键节点处被选择,即使还存在其他选择,但要回到起始点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⑤James Mahoney,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111-141.乔瓦尼·卡波恰(Giovanni Capoccia)与丹尼尔·凯勒曼(Daniel Kelemen)在此基础上将关键节点定义为:“核心行为体对结果影响的可能性发生实质性提升的一个较短时间段”①Giovanni Capoccia, Daniel Keleme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2007, Vol.59, No.3, pp.341-369.,强调“节点”是一个行为体面临广泛选择的短暂时期,节点相比于所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其时间要短。而“关键”指的是行为体在节点处做出的选择,可能会比节点前、后做出的选择更能对后续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的30年内经历了6位总统。其中,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15年,而在2005年阿卡耶夫政权垮台以后,陆续更换了5位总统,平均每位总统的执政时间为3年,远未达到宪法所规定的任期。而且,其中两位领导人是因为大规模游行示威而被迫下台。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0年来只经历了两任领导人的轮替,且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简要回顾吉、乌两国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2005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在2005年,两国自独立以来长达15年的政治稳定局面被打破,由此开启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稳定发展,而吉尔吉斯斯坦则陷入反复的国内冲突当中并遭遇多次非正常政权更迭。
本文选择2005年作为关键节点有以下原因:首先,在持续时间长短方面,“郁金香革命”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安集延事件”更是只持续了三天,两者的持续时间相比于后续长达15年的政治动荡或政治稳定而言,可以被视为一个“节点”。其次,吉、乌两国政权在应对“颜色革命”时,同时存在“镇压”与“妥协”两种选择,且两种不同的选择都是由先前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三,在2005年之前或之后,吉、乌在任政府对于社会运动的不同应对,均未能逆转两国特定的政治发展“模式”,没有对两国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就此而言,2005年足够“关键”。
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的选择,将会通过正反馈锁定于特定的发展轨道。因此,对于“为什么一国会反复因为社会运动而发生政权更迭”这一研究问题,可以拆分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1)面对社会运动的威胁,特定政权在关键节点上采取的应对策略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采取这种应对策略?(2)关键节点上不同政权采取不同应对策略形成了何种“政权-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这种互动模式如何通过“正反馈”得以固化?
在某些情况下,政权崩溃取决于关键行为体在关键节点上所做出的决策和所采取的行动,这些决策和行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显著增加或者减少该政权走入特殊发展轨道的可能性。在竞争性威权(Competitive Regime)体制中,以领导人为代表的政权所做出的选择,往往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走向的关键。①这是西方学者对于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贬损性称谓,意思是,中亚国家表面追求民主,但实际上属于威权国家。参见Vanessa Ruget, Burul Usmanalieva, “The Impact of State Weakness on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Kyrgyzsta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7, Vol.40, No.4, pp.441-458; Vitali Silitski,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ac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Following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0, Vol.43,No.4, pp.339-350; Thomas Ambrosio,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Concepts, Dynamics,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0, Vol.11,No.4, pp.375-392.在面对“颜色革命”浪潮的冲击时,以吉、乌两国为代表的欧亚国家在多种应对方式中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继而导致两国在应对社会运动方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权-社会运动”间的互动模式,进而对两国政治发展轨迹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根据路径依赖机制的相关假定,可以发现,当行为体在关键节点上做出选择后,沿着所选择的这条路径而产生的结果一般会增加该路径的吸引力。这种累积效应开始以后,就启动了自我强化活动的强大周期,②[美]保罗·皮尔逊著:《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黎汉基、黄佩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页。而自我强化的过程即为正反馈形成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文假设:在2005年面对“颜色革命”浪潮冲击的关键节点,吉、乌两国应对抗议的不同策略选择对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影响,经过正反馈过程,被固定为两国民众与政权的互动模式,从而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反复发生“革命”而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稳定。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

图2 本文的分析框架示意图(笔者自制)
四、关键节点:2005年吉、乌两国对“颜色革命”的应对
当社会运动发生后,政权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来自体制外部的挑战。政权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不仅会影响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能够影响运动的结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政权对于社会运动所做出的镇压与妥协两种行为,都是此类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国家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划分为压制和促进两类,通过对两类手段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进而将抗议者的行为分为指令型活动、容忍型活动、禁止型活动三种类型。①[美]查尔斯·蒂利著:《政权与斗争剧目》,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0页。叶夫根尼·芬克尔(Evgeny Finkel)进一步将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细化为孤立、边缘化、分配、镇压和说服五种类型。②Evgeny Finkel, Yitzhak M. Brudny, “No More Colou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Colour Revolutions in Eurasia”,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19, No.1, pp.1-14.蒂娜·比沙拉(Dina Bishara)在镇压和妥协之外引入第三种政府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漠视(Ignore),即政府面对抗议毫无反应或者对抗议者持嘲弄、轻蔑的态度。③Dina Bishara, “The Politics of Ignoring: Protest Dynamics in Late Mubarak Egypt”,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5, Vol.13, No.4, pp.958-975.然而“镇压”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并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冲突研究中,“镇压”指的是政权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使用某种形式的强制性控制,而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对镇压行为做了限制公民自由和暴力侵犯人身安全的划分。④参见Christian Davenport,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Tyrannical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7, Vol.44, No.4, pp.485-504.在本文看来,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一致的,即使用暴力手段压制甚至消灭反对势力,并威慑其他潜在的可能被动员起来反对政权的行为体。
在“郁金香革命”与“安集延事件”中,吉、乌两国政权与抗议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如表1、表2所示。从2005年3月18日吉南部城市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之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阿卡耶夫政权不断选择对抗议者进行妥协:承认反对派的地位、与抗议者谈判、拒绝实施紧急状态、将政权拱手“送给”反对派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安集延事件”爆发的2005年5月12日,乌政权即已完全放弃向抗议者做出妥协,总统卡里莫夫直接选择了镇压,至5月14日,乌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了安集延市中心并开始追捕逃散的武装分子。

表1 2005年“郁金香革命”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与抗议者的互动过程

表2 2005年“安集延事件”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抗议者的互动过程
那么,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镇压的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呢?与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相似,早期研究政治镇压的学者认为,领导人诉诸镇压的形式来应对社会运动,源于领导人个人的偏执与不受约束,是一种“非理性”行为。①Mauricio Rivera,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State Repression: The Divergent Effects of Legislature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on Personal Integrity Righ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Vol.61, No.10, pp.2183-2207.而如今大多数研究则认为,镇压绝非因为某些领导人的“残暴”特质,而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当镇压收益超出镇压成本,或没有其他替代性选项且镇压成功率较高时,镇压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②Christian Davenport,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Tyrannical Peace”, pp.485-504.考虑到镇压的政治合法性、镇压所需要的物质力量、可选择的替代方案等因素,国家在采取妥协还是镇压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时,不仅取决于国家能力,还要考虑到政权的镇压意愿。
当政权既没有足够的镇压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镇压意愿,或者有足够的镇压能力但是缺乏意愿,抑或有强烈的镇压意愿但缺乏足够的镇压能力时,都会导致政权更倾向于采取妥协或者漠视的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而当镇压意愿与镇压能力两者兼具的情况下,政权更倾向于采取镇压的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吉尔吉斯斯坦属于第一种情况:政权既缺乏镇压能力又缺乏镇压意愿;而乌兹别克斯坦属于最后一种情况:政权的镇压能力充足且镇压意愿强烈。
(一)“郁金香革命”:为何阿卡耶夫政权选择妥协?
阿卡耶夫政权垮台之迅速,超乎吉民众甚至国际社会的预料。在“郁金香革命”发展过程中,阿卡耶夫政权瓦解的重要原因在于,吉强力部门的软弱与阿卡耶夫对反对派力量的低估。事后,阿卡耶夫也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没有重视巩固权力体系,特别是加强护法机构;二是在政权旁落的重要关头没有实施紧急状态。③孙壮志主编:《中亚五国政治社会发展30年:走势与评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66页。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开启了自身的民族国家构建,立国之初期待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禀赋、经验、意志及其世界观。④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页。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是一位物理学家而非政治精英,也是中亚地区唯一一个非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出身的领导人。故“他在苏联走向解体的民主化浪潮中却不乏追求民主的积极热情与主动性”。①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第45页。阿卡耶夫政权在经济层面实行全面且彻底的“私有化”,并且积极吸纳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在政治层面将追求“民主”作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目标。
首先,武力镇压将威胁阿卡耶夫政权本就不甚稳固的执政合法性。政治心理、政治文化或者意识形态一经确立之后,一般都具有持久性且易形成路径依赖。阿卡耶夫致力于构建西式民主制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沉淀为该国民众的政治心理,令部分民众认为本国具有相对于其他中亚国家更高的民主水平。相对于妥协而言,镇压无疑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但镇压还可能刺激其他行动者走向街头,使得反对者从涓涓细流演变成滚滚洪流。②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230页。2016年一项覆盖吉尔吉斯斯坦7个地区2个城市1004名民众的民意调查,衡量了吉民众对推翻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政权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民众认为“郁金香革命”与“二次革命”是合法的。同样,超过1/3受访民众认为两次运动都不应该受到政府的武力镇压。相比于阿卡耶夫政权,接近半数的受访民众对巴基耶夫政权的评价更负面,因为巴基耶夫在2010年4月试图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③Charles Sullivan, “Misruling the Ma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Cracking Down in Kyrgyzstan”, pp.628-646.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采取武力手段镇压社会运动的合法性低且结果难料。
其次,镇压能力取决于强力部门的能力以及文官政府是否能够掌控强力部门。中亚各国的军警系统继承自苏联。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军警部门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吉军事力量是中亚五国中最弱的,其规模也是最小的。在“郁金香革命”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军队仅有1万人,国家经济的困难大大制约了对军队建设的投入,造成军人薪饷很低,士气低落,逃兵现象严重。④杨恕:《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吉军内部腐败严重。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对男性公民实行义务兵役制,但大多数人会使用各种手段逃避兵役。在2007年春季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中,所有受访者都承认,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少有人会真正履行其军事义务。①Vanessa Ruget, Burul Usmanalieva, “The Impact of State Weakness on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Kyrgyzsta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7, Vol.40, No.4, pp.441-458.与军队相似,吉警察数量也严重不足,工资很低而且充斥腐败行为。
2002年,吉政府担心议员阿奇姆贝克·贝克纳扎罗夫(Azimbek Beknazarov)煽动反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对其进行了逮捕并提起诉讼。此举在其家乡阿克西地区(Aksy)引发了支持者组织的大规模抗议。2002年3月17日,警察在阻止示威的过程中开枪击毙了数名抗议者。阿卡耶夫政权起初对此次事件不闻不问,既没有与受害者亲属进行会面也没有出面道歉。政府的冷漠引发了抗议者的强烈不满,抗议活动迅速失控,阿克西地区要求为遇难者伸张正义的示威活动持续了数月之久。②Donnacha Ó Beacháin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Colour Revolut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0, pp.47-48.阿克西事件对阿卡耶夫政权与警察的关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阿卡耶夫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内务部长,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件的原因。该事件的调查结果将阿克西事件的责任完全推给强力部门,警察事实上被阿卡耶夫政权“出卖”了。一些警察发起了抗议并进行罢工,警察也在怀疑,如果继续发生此类事件,当警察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后,会不会被作为政权向示威者妥协的“替罪羊”而被送进监狱。而此次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则是时任总理巴基耶夫被迫辞职,并在日后的“郁金香革命”中成为反对派领袖。阿克西事件的前车之鉴,加上抗议者利用亲友和部族的人际网络来影响警察的行为,成功换取了强力部门的“中立”。③在2010年的“二次革命”过程中,强力部门则直接倒戈,向反对派效忠。据对政治人物卡西姆·伊萨耶夫(Kasym Isaev)的采访,吉安全部队将军米罗斯拉夫·尼亚佐夫(Miroslav Niazov)曾建议反对派领导人,应该从纳伦州和塔拉斯州开始动员。首先,当局需要时间将比什凯克的部队转移到这些地区。第二,在封锁了道路之后,就有可能将远离比什凯克的部队锁定在这两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国家都会被卷入到反政府的洪流之中。参见Kasym Isaev: Tret’a Qshibka-Katastrofa Dlia Suverennogo Kyrgystana,Tolgonai Osmongazieva, May 21, 2010, http://24.kg/community/74579-kasym-isaev-tretyaos hibka-ndash-katastrofa-dlya.html, quoted from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10, Vol.38, No.5, pp.589-600.吉强力部门力量弱小、腐败不堪且强力部门与政权“分裂”,共同导致了政权没有足够的能力对社会运动进行镇压。既缺乏镇压能力又缺乏镇压意愿,导致阿卡耶夫政权选择了对抗议者进行妥协。
(二)“安集延事件”:为何卡里莫夫政权选择镇压?
反观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执政伊始就把“政治稳定优先”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的目标,并极力主张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切制度和政策的立足点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自独立以来,卡里莫夫发表了数次演讲,详细阐述“稳定”作为民主和发展之保障的重要性。
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实施重大的经济或政治自由化。对卡里莫夫而言,如果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卡里莫夫拒绝了经济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范式,而是优先考虑自给自足,且认为经济现代化应优先于民主转型。卡里莫夫认为,“在建造新房子之前不要摧毁老房子”,“我们的人民应该吃饱肚子,穿戴整齐”。①参见Assylzat Karabayeva, “Leaders, Ideas, and Norm Diffusion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2021, Vol.6, No.1, p.30.政府保留了对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管制,追求工资的自给自足,只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②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pp.78-97.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改革同样稳健。卡里莫夫拒绝允许竞争性选举或有意义的政治反对派。③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1, pp.15-31.卡里莫夫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道路,谁也无法阻止民主的客观进程和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但民主的发展需要符合自身国情,反对派的民主理想与国家历史、传统文化与民族身份不匹配。
在卡里莫夫政权看来,所谓的“民主运动”也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所驱动的。2003年“玫瑰革命”掀起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浪潮之后,卡里莫夫政权将西方国家所谓“促进民主”的组织及其资助方定义为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威胁”。随后发生的“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也成了外国势力构成威胁的“证据”。④“Islam Karimov Excludes Possibility of ‘Colour’ Revolution”, op cit, Ref 38, quoted form Jone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1, pp.123-140.阿卡耶夫下台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也加入了对西方进行批评的行列。例如,《乌兹别克民族新闻报》的一篇头条文章指责美国煽动了中亚地区的不稳定。⑤Jone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pp.123-140.抗议示威被乌政府视为扰乱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威胁,政权具有强烈的镇压意愿。卡里莫夫将“安集延事件”描绘为“恐怖主义暴行”——政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是对恐怖分子“挑衅”行为的慎重反应,维护了法律和秩序,保护民众的生命免受伤害。①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pp.15-31.此举强化了镇压的合法性,同时也使得抗议者无法从中立的旁观者中获得支持。
另外,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重视军队建设,将军队视作维护国家独立的重要力量,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均居中亚五国首位。②孙壮志主编:《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第219页。卡里莫夫同时建立了庞大的安全机构,以对潜在的“威胁”进行威慑和消除。乌兹别克斯坦被认为拥有中亚规模最大的警察和内务部队,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掌握着管理国民警卫队和特种部队的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③Sarah Kendzior, “Recognize the Spies: Transparen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Uzbek Cyberspace”, Social Analysis, 2015, Vol.59, No.4, pp.50-65.凭借强力部门的控制,乌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应对“颜色革命”浪潮冲击的过程中,乌强力部门始终被牢牢掌握在卡里莫夫手中。镇压“安集延事件”,几乎没有引起乌政治精英,尤其是强力部门的反对。乌强力部门直接参与到国家资源提取与寻租活动中,将寻租利益置于行政部门之下,实现了政治精英与政权的“绑定”。卡里莫夫执政早期,向乌地方政治精英开放寻租渠道,通过允许寻租行为,来将地方政治精英与政权联系起来。1997年,乌政府出台法律,赋予了检察官、安全部门、警察、税务员监督和执行经济法律的权力。④Lawrence P. Markowitz, “Beyond Kompromat: Coercion, Corruption, and Deterred Defection in Uzbekist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7, Vol.50, No.1, pp.103-121.这些措施将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与寻租结合起来,使得强力部门深深地嵌入到政权中。政权对于强力部门和地方精英寻租行为的默许,使得强力部门与地方精英“背叛”现政权不仅无利可图,反而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某一政治精英的“背叛”行为会招致寻租利益链条上各方势力的反对。因此,在面对社会运动对于政权的冲击时,以强力部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展现出了高度的“团结”。既有镇压能力又有镇压意愿,这使得卡里莫夫政权能够对“安集延事件”进行镇压。
五、正反馈:“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的形成与固化
(一)吉、乌两国应对“颜色革命”的不同方式所造成的影响
在从事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政治过程与资源动员论者看来,如果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出于理性选择而参与社会运动,那么可被动员的资源多寡与政治机会的大小被视为左右社会运动兴衰的重要因素。与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所定义的政治机会结构①参见[美]西德尼·塔罗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不同,本文认为,政治机会不一定是那些能够影响政治参与、较为宏大的、稳定且不易改变的结构性条件。因此,“政治机会”这一概念的结构化取向,可能会导致此概念的僵化。在以往的“颜色革命”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政治机会”这一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任何可能影响到“颜色革命”成败的结构性条件均被列入其中,故削弱了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事实上,许多政治机会既不是先于社会运动存在的,也不是较为稳定的,而是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通过运动与政治权威以及外部干预势力的互动过程逐步产生的。
一般而言,国家面对社会运动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会创造出不同的政治机会,也会在短期内取得不同的效果。如果国家对社会运动做出妥协,一般会降低参与社会运动的成本,导致政治机会扩大,从而使得社会抗议者走上街头,激发社会动员;而采取镇压政策则会极大地增加参与社会运动的成本。相比于妥协为社会运动带来政治机会而言,镇压带给社会运动的更多是政治威胁,而非机会。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进一步认为,“相对剥夺感”等情感性因素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但这种“不满”需要转化为行动。任何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一般都需要两个动员过程:一是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ation),二是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ation)。前者意在凝聚共识,让外界接受和支持运动所持的观点;后者意在形成行动,即推动人们实际参与。②Bert Klandermans,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Vol.49, No.5, pp.583-600.
吉、乌两国均存在家族统治、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且这些矛盾没有得到执政当局的妥善处理。当民众认为自身诉求通过常规的政治途径没有办法得以解决时,就有可能选择发起或参与社会运动作为改善自身不利处境的一种方式。为了实现民众的集体诉求以及动员民众参与社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及其支持者首先需要建构出一套针对现实不满的替代性方案。回顾前文罗列的吉、乌两国政府与抗议者互动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共识动员层面,吉、乌两国的抗议者将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归因,认为各自国家和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分别源自阿卡耶夫与卡里莫夫的统治,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两位领导人的下台得到解决。这种主要框架①框架视角最初于1974年由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由戴维·斯诺和罗伯特·本福德等人引入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框架视角强调的是抗议组织者或支持者为了赋予抗议合法性而建构起来的话语框架,这些话语框架因为与抗议者所处的文化背景或者生活体验产生共鸣,能够极大地扩大社会运动的影响,甚至能够左右社会运动的成败。参见David A. Snow, E. Burke Rochford,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Vol.51, No.4, pp.464-481.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社会运动的潜在参与者能否获得“框架共鸣”(Frame Resonance),即社会运动的领导人或者支持者针对某个社会问题所做出的诊断以及解决方法,能否得到其他潜在参与者的认可与支持。②Robert D. Benfor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Vol.26, No.1, pp.611-639.在动员的过程中,少数坚定的政权支持者被动员起来反对政权或坚定的反对派被动员起来支持政权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动员的关键,是没有十分强烈政治动机的普通民众。能否动员居于多数的普通民众参与社会运动,往往会影响社会运动的成败。吉民众中“民主”观念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采取抗议示威手段表达政治诉求是合理的。而在乌兹别克斯坦,用抗议示威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很可能被描绘为“恐怖主义”。就将普通民众转变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而言,在乌兹别克斯坦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大得多,故其动员难度也要高得多。
在“安集延事件”的性质、政府进行武力镇压的理由、抗议者身份、死亡人数等问题上,乌官方的说法与西方媒体的说法大相径庭。与西方媒体所宣传的“安集延事件是一场大屠杀”相反,卡里莫夫对于这起事件经过的描述是这样的:2005年5月12日晚,武装的宗教极端分子闯入了安集延的一所监狱,并释放了被看押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成员。5月13日黎明,武装分子开始劫持人质,卡里莫夫召集军队前往现场平叛。在随后的对峙和冲突中,共有187人死亡。①Sarah Kendzior, “Poetry of Witness: Uzbek Identity and the Response to Andij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3, pp.317-334.面对西方媒体的诘难,卡里莫夫进一步将抗议者的行为定义为对宪法的颠覆,并指责媒体故意将所谓“和平示威者被枪杀”的错误信息传递到西方世界。卡里莫夫将自己的武力平叛行动与抗议者的行为进行对比,进一步凸显出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同时也针锋相对地构建出一套反框架,以对社会运动进行“反动员”(Demobilize)。
首先,卡里莫夫强调抗议者是“恐怖分子”,故总统动用军队进行平叛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是为了保护无辜民众免受“恐怖分子”的伤害。其次,卡里莫夫指责抗议者的行为是不“民主”的——抗议者试图获取政权,但不是通过选举这种符合宪法的形式,而是采用暴力手段攻占政府大楼等并不“民主”的行为。最后,卡里莫夫强调自己是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抗议者的行为未经人民的合法授权,也违背相应的国际惯例。②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pp.15-31.卡里莫夫在“安集延事件”中建构出一种“反恐”和“平叛”叙事,以反击西方制造的抗议者行为的“民主”叙事,从而将抗议者的框架边缘化。而在行动动员层面,特定人群的集体行动形式主要是习得的,在数量和范围上也是有限的,是变化缓慢的,是适应了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的。
抗议者倾向于从本国的抗议历史中进行学习,③Alex Braithwaite, Jessica Maves Braithwaite and Jeffrey Kucik, “The Conditioning Effect of Protest History on the Emulation of Nonviolen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2,Vol.52, No.6, pp.697-711.而当局最初应对抗议示威的对策将会极大地塑造抗议者的学习行为。面对镇压“杀一儆百”的效果,“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得抗议者更不愿意直接参与社会运动,转而使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卡里莫夫政权的高度压迫性也解释了该国社会运动的高度破碎化。④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pp.78-97.如果当局有过妥协的历史,抗议者参加社会运动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要更低,在不会招致镇压的情况下,抗议者往往会继续参加社会运动,最终形成一旦对政治现状不满,动辄参与社会运动的“怪圈”。
综上所述,吉、乌两国政权针对社会运动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图3 吉尔吉斯斯坦抗议者与政权互动模式示意图(笔者自制)
(二)不同“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的固化
政权对社会运动进行妥协或者镇压所形成的互动模式,是如何得到固化并沉淀为一种政治心理的?在新的互动模式出现之后,既可能被固化也可能被消减。如果这种新的互动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接受并且得到内化,那么新的模式也将进入到“正反馈”的过程。在政治领域,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运用政治权威增加权力不对称的可能性等相互关联的特征,将影响到行为体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的选择能否进入“正反馈”过程,进而形成路径依赖。①[美]保罗·皮尔逊著:《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第36-48页。

图4 乌兹别克斯坦抗议者与政权互动模式示意图(笔者自制)
首先,参与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人们在决定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会仔细权衡收益与成本,唯有经过一番艰苦的动员,社会运动才能招揽到足够多的参与者。同时,基于“理性人”假设,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每个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都会有搭便车的欲望,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①参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大多数试图影响政治议程的社会运动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努力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还要面临遭到镇压的巨大压力,这将导致参与者一旦做出错误选择,将承担高额风险,所以参与者往往倾向于根据对他人行动的预期来不断调整自身的行动策略。
回顾吉、乌两国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可以发现集体行动所发挥的作用。“郁金香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动员过程截然不同。“郁金香革命”的动员模式是各种政治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协调行动,在“庇护”网络和部族的支持下,通过为潜在的参与者提供物质和精神激励,从而较好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郁金香革命”开始时,反对派集中精力动员政党、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然而,这些资源不足以有效和全面地动员地方民众。之后,反对派通过地方各级的人际关系网络和部族力量来推进动员。2005年的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些对选举组织方式不满的领导人和议会候选人。这些不满的领导人开始积极动员他们的支持者,其中大多数是亲戚、朋友和老乡。然而,“二次革命”不是反对派精心动员的结果,而是民众自发的集体行动。与持续一个多月的“郁金香革命”相比,“二次革命”短短两天就结束了。反对派并没有进行诸如架设扬声器、公开发表演说、散发反政府传单等传统的动员手段,而新闻媒体对于警察枪杀抗议者的新闻激起了民众的义愤。对巴基耶夫政权心怀不满的人群自发手持棍棒、石头,甚至是从警察手中夺取的枪支加入到抗议示威中来,要求巴基耶夫辞职。后续的过程和“郁金香革命”相似,抗议者再次攻占了总统府。巴基耶夫逃亡到南部的贾拉拉巴德州,后出逃至白俄罗斯寻求庇护。②Kathleen Collins, “Kyrgyzstan’s Latest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1, Vol.22,No.3, pp.150-164.
回顾吉尔吉斯斯坦两次“革命”的动员过程可以发现,在“郁金香革命”的演变过程中,政权在面对反对派的压力时毫无作为,参加抗议示威的成本较低,相反在一些地区不参加抗议示威反而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遭到当地社会排斥、失去部族长老或者地方政治精英的庇护)。事后来看,当时的吉政府好比一座破烂的房子,只要轻轻踹上一脚,整个建筑就会轰然倒塌。以至于在5年后的“二次革命”过程中,不需要反对派精心动员民众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少民众也会自发加入到推翻现政权的抗议示威队伍中来。与“郁金香革命”时期“追求民主”相比,“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中抗议者的诉求更加碎片化——抗议物价上涨、反对腐败、抗议执法不公、反对特定的部族或者政治人物等等,而这些碎片化的要求最后都汇聚成一个诉求——政权更迭。相反,“安集延事件”很快就遭到镇压。卡里莫夫政权通过镇压的方式传递了一个信号——政府无法容忍类似的行为,更不用说是一场“革命”了。在经验层面也是如此,“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极大增加了发起或参与反政府活动的成本,故乌兹别克斯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政权导向型”的社会运动。
其次,广泛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以及可能获取的资源。既有的政治制度往往由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进行支撑,且清晰地释放了行动者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信号。这种影响所产生的规训效应显然是持久的。①Richard Rose, “Inheritance before Choice i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 Vol.2, No.3, pp.263-291.“郁金香革命”中以反对派为首的抗议者,至少通过组织起来展现出似乎具有比被推翻的阿卡耶夫政权更大的“权力”。长期的体制薄弱伴随着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往往构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由外国资助者扶持的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形成了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与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其他欧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拥有欧亚地区最活跃的“民间社会”。当民间社会团体利用抗议和抵制来表明自身的政策偏好时,国家不但无力镇压,而且其维护“民主”形象的动机也使公民能够对其提出要求。而经过“革命”成为执政者的原反对派,由于执政合法性不足,故会以鼓励“民主”来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例如,通过“郁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曾表示,“革命”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及其追求自由、真正的生活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吉前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也表示,2005年3月24日发生的“郁金香革命”是一场“人民革命”。①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第137页。
与吉尔吉斯斯坦“发达的公民社会”相比,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20世纪90年代,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来自西方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与此同时,乌本国非政府组织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安集延事件”结束后,乌政府于2005年6月成立了新的非政府组织协会,要求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隶属于该协会。仅在2005年8月,大约有200个非政府组织因不被允许重新注册而停止活动。②Donnacha Ó Beacháin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Colour Revolut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pp.169-172.与非政府组织的萎缩相比,国家的渗透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卡里莫夫政权选择与“玛哈拉”(Mahallas)③“玛哈拉”是乌兹别克斯坦地方自治管理的最小机构。“玛哈拉”在乌兹别克语中有单元、社区之意,指一个社区、街道、楼层群体的居民交互关系的整套系统。“玛哈拉”的中心是民选产生的、由德高望重者领导的“玛哈拉”委员会。参见孙壮志主编:《中亚五国政治社会发展30年:走势与评估》,第223-226页。等传统的社会机构进行合作,逐步完善国家管理体制。“玛哈拉”的存在,使得乌政府能够实施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措施,也使国家能够对民众的诉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④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pp.78-97.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无法负担全民福利,“玛哈拉”给政府提供了更多关于个人福利需求的信息,政府根据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再分配,合力化解了大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此同时,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或那些可能从事颠覆政权活动的人都会被“玛哈拉”的工作人员及时通报给强力部门,凡此种种,极大增强了乌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
第三,政治权力的不对等。当若干行为体处于可以对其他行为体施加压力的位置时,权力的运行可能是自我强化的。政治权威往往会被用来强化和巩固已有的政治优势。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能力低下的主要表现是缺乏法治、无效的税收制度和普遍的腐败等。①Jaimie Bleck, Igor Logvinenko, “Weak States and Uneven Pluralism: Lessons from Mali and Kyrgyzstan”, pp.804-823.吉政府很难对政治精英、官僚和其他政府雇员进行有效监管。尽管政府进行了各种改革,但治理能力没有得到系统地提升。外部援助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创造其他类型收入的能力有限,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导致吉政策“更容易受到援助者对民主化要求的影响”。一旦使用武力镇压社会运动,显而易见就会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进而面临援助停止的风险。由于西方援助者往往只满足于竞争性选举的进行和所谓的“言论自由”原则,②Vanessa Ruget, Burul Usmanalieva, “The Impact of State Weakness on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Kyrgyzsta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7, Vol.40, No.4, pp.441-458.吉历任领导人通常只需要营造社会多元化的假象即可,从而确保外部援助源源不断从西方流入。
与过分依赖国际社会的吉尔吉斯斯坦相比,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实施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较好。“安集延事件”发生后,乌兹别克斯坦拒绝了美国与欧盟关于对该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要求。欧盟以乌当局血腥镇压平民为由,先后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武器禁运与政府官员旅行禁令。美国则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对乌进行制裁,包括逐步停止经济援助,在援助项目中附加保障人权、实现政治自由化等要求,冻结乌相关官员的海外资产等措施。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卡里莫夫政权采取终止合作的方式进行反抗。乌政府关闭了汉纳巴德军事基地,同时取缔了索罗斯基金会等一批西方在乌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终止了与美国的“准盟友”关系。
卡里莫夫在采取雷霆手段平息“安集延事件”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社会的管控。自“安集延事件”以来,相关的乌兹别克语网站的数量激增。事件本身“骇人听闻”,加上相当多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在事件发生后流亡海外,只能通过互联网手段发泄不满并对当局进行抨击。③Donnacha Ó Beacháin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Colour Revolut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pp.157-158.2007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要求所有网站和博客都必须向当局登记,以加强互联网管制。与此同时,卡里莫夫政权也在全社会加强舆论宣传,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对于“安集延事件”的界定凸显了以下几点:(1)就如在吉尔吉斯斯坦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和武装分子”主要是为了利用此次机会推翻政府;(2)年轻人的思想“中毒”了;(3)武装分子受到其他国家的指使;(4)抗议者错误地认为安集延民众会支持他们;(5)抗议者的总目标是推翻宪法秩序,试图建立“哈里发国”。①Sarah Kendzior, “Poetry of Witness: Uzbek Identity and The Response to Andijon”, pp.317-334.相较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多元化程度较低,大多数民众接受卡里莫夫所提倡的国家主义观念。卡里莫夫为乌民众提供了稳定与秩序,因此在历次总统大选中,总能获得极高的支持率。
如下图所示,吉、乌两国在关键节点,即应对2005年“颜色革命”之类的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对后续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不同的影响经由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运用政治权威增加权力不对称等路径,导致两国政权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的选择进入正反馈过程,从而形成路径依赖,继而使得“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被锁定在特定的轨道上,即吉尔吉斯斯坦反复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而乌兹别克斯坦不再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

图5 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不同路径示意图(笔者自制)
六、总结与反思
本文尝试通过运用路径依赖机制的相关观点,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颜色革命”及之后的政权与社会运动互动结果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在应对“颜色革命”的关键节点上,由于国家能力与镇压意愿的不同,两个国家分别采取了妥协与镇压的不同策略。这两种不同的策略扩大或缩小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使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产生了差异明显的政治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两种差异通过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运用政治权威增加权力不对称等路径,产生了“正反馈”效应,最终导致路径依赖。这或许可以解释,2005年以来,为何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三次政权非正常更迭,而乌兹别克斯坦却有效地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依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所进行的案例选择有可改进之处。本文选择了位于中亚地区的吉、乌两国作为案例,没有选择位于其他地区的案例进行比较,也没有选择某一国家政权更迭频繁与实现政治稳定的不同时期进行比较。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选择偏差。事实上,无论是在“颜色革命”还是其他抗议浪潮中,我们都很难找到这样的案例。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局限于分析吉、乌这两个特定的国家,学界可以在本文的基础上选取其他案例进行进一步验证。其次,本文在界定政权对社会运动的应对策略时采取了简单的“镇压”和“妥协”二分法,并没有对其他策略进行分析,也没有考虑这两种策略的交叉组合运用。事实上,如果考察两种方式的组合运用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本文分析的是政权所采取的策略对社会运动动员过程的影响,不意味着本文认为来自政权的镇压或妥协就是决定社会运动发生与否及其带来何种结果的唯一因素。结合其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或许可以收获更多的启示。最后,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研究资料相对匮乏,以及笔者没有掌握吉、乌两国的民族语言与通用语言,因而本文对两国的研究仅限于尽可能多地参考业已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这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对相关问题的把握。期待未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针对本文的问题和观点进行修订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