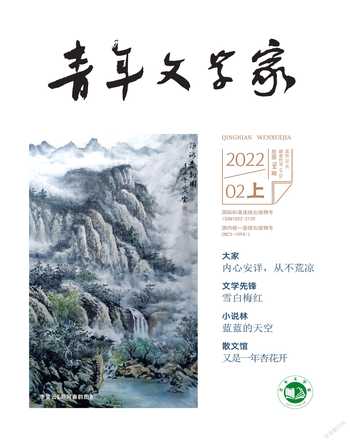时空变化下木兰故事的中外差异比较
于弋洋



《木兰辞》是我国北朝民歌,“乐府双壁”之一,讲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其高超的写作技巧与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进行改编。其中,豫剧《花木兰》与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下称“电影《花木兰》”)为重要代表。豫剧《花木兰》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片,戏剧大师常香玉主演。常氏刚柔并济的唱腔与耐人寻味的唱词结合,使得此部戏剧在当时脍炙人口、广受好评,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仍是不可多得的精品。电影《花木兰》上映于2020年,由刘亦菲、甄子丹主演,上映后毁誉参半,在内容、形式上都颇具争议。
本文选取三部作品,既从封建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步建立时期,以及现代进行时间上的比较,也从全球化的视野比较不同地域的木兰故事,进而对其背后的内涵进行分析,展现木兰故事的时代价值。
一、木兰故事的忠孝主题、反战思想与女性话题
《木兰辞》的主题不止一种。“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写出了木兰对长辈的爱护,是“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极言木兰为国家征战的热情,宣扬的是为家为国的“忠”;“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刻画了边疆的苦寒与战争的残酷,其反战思想不言而喻。
叶露教授认为,女性主义号召男女平等、平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男权为主导的北朝社会让一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劳动女性拥有这一思想无疑是牵强的。而且木兰最后梳妆打扮的情节更是说明诗歌的主旨即在颂扬作为女性也应有“忠孝”的品德,与女性主义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却可能并非如此,虽然《木兰辞》是北朝时期的民歌,时代决定了木兰不可能具有与现代完全一致的女性主义思想,更何况木兰从军并非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并非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父亲、为了国家。但是,她身为明明可以躲在男性身后的封建时代女性,却能站出来承担男性的责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他人所迫而是她自己的意愿。这样的“自己决定”是具有极高的时代价值的,是能证明她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觉醒的。
木兰从军的重要桥段就是男扮女装。这个行为是很明显的“去女性化”过程。在古代,即便是有相同的能力,但只要性别为女,就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机会。于是,花木兰披盔戴甲,扮作男性实现了忠孝。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忽视两性之间的差异,两性也不可能共同持有行为主体权力,女性主体的重塑不能依靠模仿、伪装甚至是同化为男性来完成,必须尊重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差异性’表达的重要性”。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花木兰化装成男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对价值的评判恰恰还是用男人的标准,更可悲的是世界上没有成功的、不同的原则,要么就是不平等的,要么就是平等而同一的、拒绝差异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木兰辞》中“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是否给女性真正实现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呢?
木兰没有完全被男性建立并追求的价值标准所诱惑,她也对自己的女性身份自豪和喜爱。因此她跟随自己的内心,选择了用回归家庭、穿回女装这种方式完成自己的终极追求,这种行为关乎于个人选择而非仅仅回归传统女性身份。木兰回归家庭并非选择成为和其他被男权社会所压迫的妇女一样的家庭主妇——即便是选择成为家庭主妇,只要是自己的选择,也不算是被压迫。而是选择回归家庭,拒绝迎合如男性所认为的成功,进入传统男权社会中实现价值的名利场。无论她接下来选择什么,只要是遵从她自己的内心,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给新时代女性实现自我提供了重要参照。
豫剧《花木兰》同样有着忠孝观念与反战主题,这在唱词中有多处体现,但是又与民歌《木兰辞》和电影《花木兰》不同。
在剧中,花木兰的父亲收到军帖后的反应是与电影一致的,都是非常坚定地决定自己前往。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在送别时嘱咐木兰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但花木兰对此的不同回应展现了豫剧与电影在忠孝观念上的细微差别。在刚收到军帖时,豫剧中的木兰唱道:“恨敌寇犯边关侵我乡邻”,从邻居、家乡到敌人入侵,将家国联系了起来。这与中国家国同构的传统是一致的,无疑潜藏了国家父权制的文化想象和审美倾向。送别时说:“咱今日可不把旁人来恨,恨只恨突力子残害黎民。”矛头直指外部威胁,对于不合理的征兵制度这一内部矛盾一笔带过,表示理解。征兵制度当然不至于无情到让年迈的老父亲前往战场,但是其中必然会有为小家、为大国牺牲的无奈。这些牺牲并不能怪自己的国家,要怪就只能怪发动战争的人。这个情节与民歌《木兰辞》的反战思想一脉相承,但是又加上了自己的时代注脚,用通俗的文艺作品形式实现了政治宣传的目的。
电影《花木兰》继承了传统花木兰故事替父从军的内核与木兰抗击外族侵略者的事实,其忠孝双全的观念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电影却对“忠”进行了淡化,更多聚焦于个人与家庭。其中,个人与家族的放大与国家的缩小无疑受到了西方价值观中个人主义的影响。在电影开篇就有女孩用婚姻为家族带来荣耀的论调,奠定了影片重视家庭的基础。木兰得胜归来,她的家乡公开赐予她荣誉,这从实际上证明了女人也可以用其他方式为家族带来荣耀,这些情节无疑都是立足于家族的。皇帝赐予木兰的剑上,除了有家族传承的剑与军队中反复提及的“忠、勇、真”之外,又加上了“孝”,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家庭在电影《花木兰》的重要地位。与中国强调“家国同构”不同,西方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着爱国主义,却未将家庭与国家联系起来,他们崇拜英雄,但没有中国人所崇尚的“国是大家”的思维建构。因此,电影虽然有展示家庭、展示国家,但其中的联系并不深刻,不可能像豫剧《花木兰》那样直接唱出“恨敌寇犯边关侵我乡邻”的唱词。
二、作为女性的花木兰
《木兰辞》本身篇幅很短,但是寥寥数语就对木兰的形象進行了立体的勾勒。“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静一动,展现了木兰上得战场,下得厅堂的文武双全的形象。替父从军的决定自然体现了她的孝心,东市、西市、南市、北市的采购更是凸显了她娇憨的女儿家情态。“旦辞爷娘去……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则是展现了她虽然思念父母但是为了国家不得不疾速前往前线的矛盾心理。在战争结束,封赏之时,“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又契合中国思想中的功成身退的道家内核。总体来说,木兰的形象立体生动、栩栩如生。
豫剧《花木兰》中,在穿戴好男子装束后,木兰出场不复落落大方,而是娇羞无比,动作声音也更加温婉,远不如要求上战场时的大义凛然,木兰穿上了男装反而更有传统语境下的女性气质。在木兰回乡、元帅前来为女儿提亲的情节中,木兰换上女装,与相熟的同伴一起面见元帅,却是不再如军中一般自然,而是掩面害羞,一步三退。无论身份是男子抑或女子,木兰都是磊落的,她勇敢坚定、泰然自若。而在变装后,无论是回归本身的性别抑或扮成男子,她都产生了羞涩、不好意思的情绪,这里可以看出,让她害羞的并非她的性别,或者说性别被社会塑造的普遍形象,而是“变化”本身。这个情节突破了对社会性别的塑造与界定,肯定了木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性格特点,淡化了其性别属性。
另外,豫剧《花木兰》增加了一个“刘大哥”的角色,在与他的对话中,木兰的形象更加丰满。作为同样应征入伍的准士兵,刘大哥在途中抱怨犹豫、贪生怕死,甚至认为女子做的事远不及男子多:“思爹娘想妻子愁上眉尖”“为什么倒霉的事都叫咱男人来干?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等等。花木兰先是针对其贪生怕死,不愿为国效力进行批驳:“刘大哥再莫要这样盘算,你怎知村庄内家家团圆?边关的兵和将千千万万,谁无有老和少田产庄园?若都是恋家乡不肯出战,怕战火早烧到咱的门前。”从家国情怀、集体主义劝解他,展现了极为浓厚的中国特色,木兰的爱国精神可见一斑。另外,她又反驳刘大哥“女子享清闲”的论调,认为男女分工不同,但都是为国做贡献。即便普遍认为是男人的职责,如打仗,也有很多女子担当起了相关责任,建功立业。因此,最后得出结论“谁说女子不如男”。这让木兰身上的女性主义光辉更加璀璨。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成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私有制是导致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在封建男权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根深蒂固,这是“天然”的,因此处于古代、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男子是不会像刘大哥一样将自己与女性进行比较。换句话说,之所以刘大哥会抱怨,其实是男女平等观念的渐入人心与女性主义的悄然兴起。在救亡图存、反封建等政治力驱动下,在劳动力的需求下,在女性呼吁中,我国较早确定了男女平等的地位。但因为这是由男性从政治层面推进的,将妇女问题与阶级问题糅合在了一起。因此,这无疑会带来妇女平等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这种平等的地位所赋予女性的权利以及其所对应的义务,只能在封建思想的缓慢消解与选择性的忽略中步履维艰地深入人心。正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到位让“刘大哥们”对此提出质疑,而木兰从不同分工都是做出贡献以及女性也在逐步进入传统男性领域等方面对其进行反驳,充分彰显了女性主义以及对女性承担起相关责任,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呼吁。虽然“谁说女子不如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与男性作对比,“表达出了以男性为参照话语的‘女子不如男’的集体无意识”。在第三波女性主义消解女性概念的思潮中这或许是不彻底的,但是这无疑是给了女性更多进入被男性侵占的社会领域的期待与鼓励。
在某些情节上,电影《花木兰》太契合现今的女权主义,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太取巧。
首先,电影中媒婆提出“好妻子”所需要的品质是“安静”“优雅”等,在军营对理想女性的探讨中,其他人对妻子的期待也只是身材、外表等内容,这些都让我们期待木兰对女性品质的回答。木兰说,自己心中的理想女性却是勇敢、幽默、机智的。这是很明显的打破女性被塑造的固有形象的例子,而且木兰选择的女性特点也并非是所谓的“男子气概”,是吻合女性去性别化的诉求。另外,花父告诉木兰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让她隐藏能力,做大众眼中的普通女子;在军中,她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份,试图用男性的躯壳获取男性的认可;巫女仙娘同样让她认清自己的位置,却是让她回归有特殊能力的女儿身。在这来来回回的“认清位置”中,木兰完成了从回归到突破社会性别的过程,这也就是影片中所强调的“真”。她完成了性别的传统建构、解构与重新建构,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契合了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
在感情戏份的安排上,与木兰有朦胧感情的是和她一起进入军营、一同成长的陈洪辉。陈洪辉一开始还能与花木兰有相当的武艺,但是随着木兰“气”的增长,他渐渐比不上花木兰,甚至在与敌人大战中需要木兰救他。但是影片的聪明之处在于,并没有让花木兰成为性转版的“王子拯救公主”:陈洪辉的武力也随着训练逐渐增长,会帮木兰解围,给木兰建议,并非等待“女王子”拯救;而木兰也并非“拯救”,她在救出陈洪辉后悄然离去,并不以此为根据发展恋情。这里从某种程度上遠离了“隐性父权制”的话语,影片通过减少爱情戏份,不再用爱情置换成长对于人的意义,爱情关系不与角色成长纠缠,感情不再掺有崇拜,让木兰的成长更为独立,更侧重于展现木兰作为“人”而非“女性”的一面。
电影《花木兰》努力从“去女性化”走向“去性别化”,试图从单纯的男性身份、女性身份转变为单纯作为“人”的中性化。木兰脱下盔甲回归女性的时候,只是将头发披散开来,身着朴素的宽袍,她的脸庞依旧不施粉黛、略显粗糙甚至有战争中不可避免染上的灰尘。她的回归并未如传统印象之中的女性一般有着精致妆容,身着凸显身材、花团锦簇的裙装,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性别的状态。这无疑既释放了性别角色解放可能的空间,又警示了超越性别身份的重重困境。
三、剧情安排中的中西差异
情节的一个很大不同是电影《花木兰》中,木兰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要出征,而中国的《木兰辞》和豫剧《花木兰》都是有告知父母后,辞别父母的情节的。
“询问”这一情节其实是有些复杂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情节有父权的因素。我国古代对女子的规范“三从四德”中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要求,即便是为了父亲、家庭、国家,但是还是要询问其意见再行动。豫剧《花木兰》继承《木兰辞》的篇章结构,告知父母自己的想法并与他们告别的情节还被拓展开来,成了戏剧中篇幅非常长的一部分。花木兰从给父母讲从前的巾帼英雄的故事,到与父亲比武证明自己的能力,再到“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不如自尽的威胁,让父母最终含泪同意。从这个情节我们是能够看到木兰父母对国的忠诚与对女儿的爱护。虽然最后还是让木兰代父前往,这只是下下策,父母不愿但无奈的态度,这更让情节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电影中对“询问”的省略更多有着对木兰本身觉醒的暗示。影片要表明花木兰并非一个事事都要征求父母意见的“妈(爸)宝女”,而是一个有着自我意识,且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独立个体,这与美国亲缘关系并不像中国那样紧密,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彰显有着紧密关系。
另外,三者对木兰从军前后以及返乡这三段主要情节的篇幅分布并不相同。
《木兰辞》注重从军前与返乡后的描写,对战争只是用了六句三十个字概括,可谓是精简至极。豫剧《花木兰》继承了《木兰辞》对征战过程的俭省笔墨,只是增加了木兰通过宿鸟惊叫推测有人偷营的情节。这无疑对木兰机智、勇敢、细致入微的人物形象塑造有着重要作用。电影《花木兰》与中国的两部作品不同,影片竭力压缩了从军前与返乡后的情节,将重点放在从军中的情节。三部作品对战争过程的详略不同显然与作品主题的不同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作品的主题放在了忠孝观念上,木兰本身的变化并非作品的重心。因此,最能体现花木兰蜕变的从军过程被略写。另外,中国的作品一是诗歌,一是戏剧。诗歌讲究凝练,要生动详细地描写战争的场景并不容易;戏剧重点在主要演员上,舞台背景不可能常换,演员也不可能太多,因此战争场面的展示用流畅的花枪表演代替,没有花样频出、拳拳到肉、血肉模糊的感官刺激,因此也没有必要占过多篇幅。而美国电影中的从军过程被详写,这样安排有更多丰富的情节可以填充,大场景的变换更容易吸引大屏幕下的观众。另外,影片重点在于木兰的个人成长,一是对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彰显,二是作为迪士尼“公主”系列的其中之一,必然将重心放在人物的塑造上。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思想观念庞杂,“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花木兰给予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尤其是为未来女性的价值实现与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通过对中外木兰改编作的梳理,也能从不同角度彰显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这对于作品背后的文化研究有着极高价值。
2190501705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