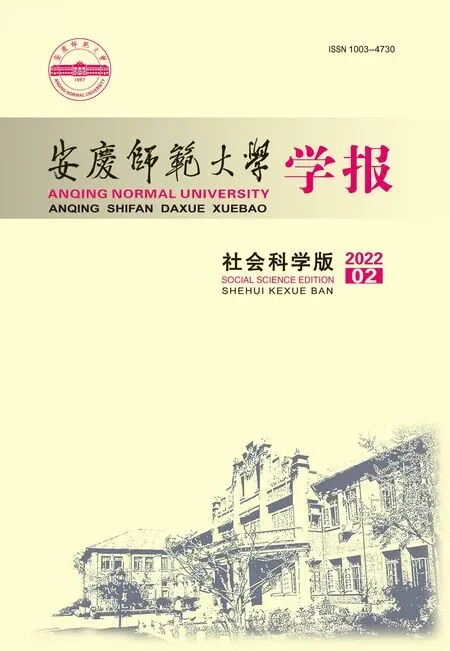戏曲经典生成的再思考
汪 超
《桃花扇》和《长生殿》作为清代戏曲的经典作品,本期两篇文章围绕二者展开经典性的再思考。戏曲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既有自身价值的完美呈现,又有各类“衍生品”的参与赋值,其中包括序跋、题词、译介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完成对戏曲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再度认可。
围绕文本批评而生成的序跋、题词等资料,一直被视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受到历来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最为突出的前有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后有郭英德、李志远《明清戏曲序跋纂笺》。戏曲序跋文献被不断发掘与纂编,使其从戏曲文本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研究,其文献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美学价值等也被重新发现,代表性著作如罗丽蓉《清人戏曲序跋研究》、李志远《明清戏曲序跋研究》等。
序跋、题词在展现出自身的批评价值的同时,还参与到戏曲作品的流传过程,成为作品不断被接受的“推手”,也是完成经典生成的重要“助手”。《长生殿》所演绎的李杨爱情故事,是古代戏曲较为常见的题材,已经成为经典故事得以流传。而要完成经典戏曲的定性,还需经历舞台演出的考验与文本批评的臧否,其中序跋、题词的价值就被凸显出来。作者张建雄梳理《长生殿》创作、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轨迹,来重现其经典性的构建过程,挖掘序跋、题词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对李杨故事的创造性改编、对经典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对艺术价值与经典情节的提炼品评,而这又与题词作序者的时代与性别、身份与动机各异,对其内容及文化指向的充分探讨,也为戏曲文化学的研究提供经典案例。
戏曲文本的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同样是助推其经典生成的重要因素。自上世纪初开始,西方戏剧被不断引入国内,中国古典戏曲也开始远播海外,开启了中西文化在戏曲领域的互译与互动。然而,与《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海外的“盛名”,以及西方经典戏剧在国内的“适应”相比,中国古代戏曲的“出门”则要坎坷得多。
中国古典戏曲作品的“西渐”,伴随着国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译入”和国内学者的“译出”,他们从各自文化背景和翻译视角出发,通过译介的传播方式对戏曲经典的生成实现他域思考。此际,海外代表有伯奇、宇文所安等,国内代表有张光前、许渊冲等,他们共同推动古典戏曲作品实现多语种版本的呈现,为海外传播与多元接受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中,美国汉学家白芝英译《牡丹亭》与霍克斯英译《红楼梦》获誉较高,二者共同代表了戏曲小说翻译的最高成就。而白芝还与陈世骧、阿克顿合译清代另一部戏曲作品《桃花扇》,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具有划时代意义并应引起学界重视。作者李震选取“译者行为批评”的本土译学理论,是对西方“译者主体性”观点的借鉴与跨越,虽然也是基于译者主体为中心展开批评,但是弱化了“能动地改造”和“过度地变动”原文。所以,“译者行为批评”牵涉到“译内”和“译外”两个维度,前者基于“忠实”原则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研究,后者基于“影响”因素对文本接受进行研究。这也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路数,代之以一种动态的“求真-务实”评价模式,从而构成白芝别具一格的翻译策略。
可见,白芝借助英译《桃花扇》等古典戏曲作品,在“务实”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学的“真色”,既生动再现中国作家的特有情感表达,又有效兼顾海外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这种积极探索的成功“路数”有助于中国文学有勇气“走出去”,同时又有信心“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