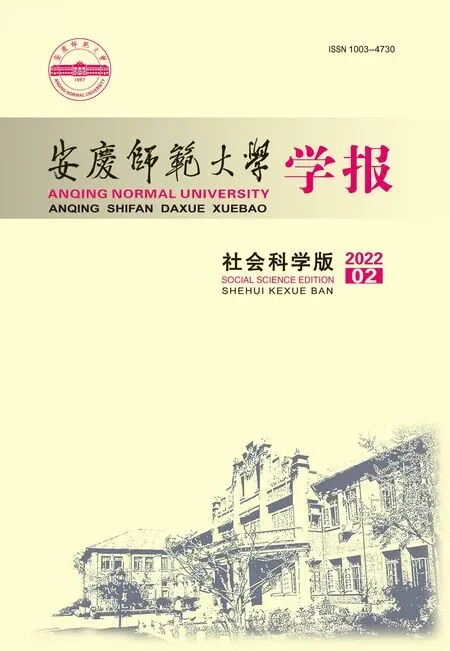论潘军小说近作《知白者说》的叙事特色
黄晓东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潘军的中篇小说《知白者说》发表于2018 年。小说情节很吸引人,至少很吸引我。但是在第一遍阅读的过程中也有些许迟疑和停顿:这究竟是小说、散文,还是当下所谓的“非虚构”?总体而言,《知白者说》仍然保留着潘军早期创作中的诸多艺术特色,譬如:叙事的戏剧化特征、散文化的“东拉西扯”、偏爱第一人称叙事、一如既往的愤世嫉俗、留存着先锋叙事的余韵等等,只是他讲故事的手法更加成熟老辣,对生活及人生的思考及评价更加深刻、果断,当然始终未变的则是他的愤世嫉俗。本文将结合对潘军早前小说创作历史的“钩沉”,对《知白者说》的叙事特征做一个归纳,并对小说的主题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一、叙事的戏剧化
《知白者说》主要讲述了“我”与主人公沈知白二人之间的故事。故事主要集中在二人的几次交集上:第一次交集,是恰逢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我”作为中文系的大学生,写作的剧本《孔乙己》被省话剧团看中了,而省话剧团的团长正是沈知白。沈知白看“我”是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就想免费拿到这个剧本并占有著作权。结果这个“诡计”被“我”和同学王兵戳穿,最后只好买下了这个剧本。第二次交集是“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而沈知白此时要晋升为文化厅副厅长,于是再次找到“我”,因为“我”是组织面试沈知白的命题人。第三次是沈知白想要出演话剧角色,从而和作为编导的“我”之间的一些纠葛。最后一次交集,是沈知白作为厅级干部,因为腐败被“双规”坐牢六年,出狱后因为在超市偷窃,被打残废后坐上轮椅,而“我”恰好目睹了沈知白被打的惨烈场景。
文中故事的交集在叙事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戏剧化特征。首先,是叙事场景的固定化与封闭化。小说叙事的所有场景几乎都限定在城南茶馆的一个包厢内,这也不免让人想起老舍的三幕话剧《茶馆》,正所谓“小茶馆就是大社会”。茶馆里发生的几段故事也折射出了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以及人物命运的转折,《知白者说》亦是如此。其次,戏剧化的特征还表现为对上述几次人物交集的细节化、细致化的叙述及描写。小说中叙事的细节化,具体到了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这导致了二人每次交集的场景,因为这种细节化叙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画面感,让读者感觉到每一次交集发生的故事,都可以成为话剧的一幕,而且这每一幕“话剧”的情节则也相对完整。不仅如此,小说的人物描写和人物之间的对白亦给人剧本化的感觉,因为对白设计得都很有张力。
具体以二人的第一次交集为例来分析。“我”应约来到城南茶馆见面。叙事过程中,我们能感到剧本化的镜头在推进:城南茶馆的中式建筑风格;茶馆大门上的回文对联“趣言能适意,茶品可清心”[1];茶馆内部古旧的陈设,四壁挂着30 年代的明星老照片和老式的月份牌美女,楼梯转角处还搁着一台带大喇叭的电唱机,颇有民国风情。接下来,戏剧人物开始出场:话剧团的李科长和话剧团的刘倩,以及摆谱装大人物,假借有事,故意延迟露面的团长沈知白。再接下来,是细致完整的一问一答的人物对话,甚至包括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这些都可以看作剧本写作的要素。这第一次交集如果将写作的手法略加转换,将故事要素按照剧本形式列出,就可成为戏剧的一幕,完整独立而又封闭。后面几次交集的写法大致都有上述特征,这种对场景细节化、戏剧化的写法,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犹如置身剧场看演出,读小说犹如看话剧,很是过瘾。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小说对沈知白的同事兼情人刘倩的描写很有意思,说刘倩等待沈知白的到来时,每听到包厢外的声音,就“像猫一样扬起了下巴”[1]。这种神态描写在小说中至少出现了三次,形象地写出了年轻女性的期待以及柔媚,很是传神到位也极富戏剧的画面感。小说如果拍成话剧或影视,女演员就要揣摩如何“像猫一样地扬起下巴”,因为这是“剧本”对人物神态的规定。写女性,是潘军小说写作中拿手的地方之一,《知白者说》中刘倩这个形象,贯穿始末,就让小说增色不少。对此,后文还要论及。
这篇小说戏剧化的特征,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两处:一是“我”在听说沈知白被“双规”后,通过王兵之口,对沈知白的被捕以及审讯场面所进行的想象性描写。正常情况下,小说中在此处可以一笔带过,亦可略写或不写。但是作者再次形象传神地进行了想象、补充,叙事极富画面感。其实这可看作是剧本写作中的补白性叙述,它可以使剧本在情节完整的同时又极具画面感。原因还是细致化、剧本化的写作。还有一处,是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作者写到了“画面的幻化”,把正在超市盗窃的沈知白幻化成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这也是影视中常见的镜头,因为影视通常以剪辑等技术为手段,更能轻松便捷地将此表现出来。小说最后写到,通过超市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晚上,录像显示的时间是2017年1月17日20点13分零5秒,西装革履的沈知白,顶着一头梳理整齐的白发,步态优雅地走进了那家小超市。……20点47分11秒,这个人现在停到了摆放花生米、蚕豆、凤爪、鸭胗等小吃的货架面前,顺手拿起一包蚕豆,这时,他的嘴动了,似乎在说着什么——从口型上看,他是在说‘多乎哉?不多也’。接着,他又神经质地猛一回头,再张开细长的五指,形成倒扣的碗状来护着另一只手里的蚕豆,继续喃喃……”[1]这种细节化,画面感,戏剧影视化的写作手法,产生的戏剧化的特征,读者一看即知,仿佛就是为影视剧的拍摄做准备。
戏剧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设置。小说写作经常会写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但戏剧中更多会具体地落实到人与人的冲突。“我”与沈知白的几次交集,其实也就是二人之间的冲突与较劲,在冲突之中刻画出人物性格,最后,性格决定了人的命运的走向。第一次见面是为剧本的版权之争。第二次是为了升迁,二人之间的较劲。第三次是为了拿到演出权,多方进行的角力。故事通过多次较劲,刻画出了沈知白的性格——自私,贪婪,心胸狭窄。这些性格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潘军在早年的小说中就善于设置人物冲突。譬如在小说集《小镇皇后》中有一个短篇叫《别梦依稀》,儿子是组织部长,父亲是乡长。儿子的官比父亲大,儿子要到父亲的乡上去考察。首先我们看到了官级大小上的矛盾,接下来的矛盾是父子反目,儿子和父亲已经多年不相认了,因为父亲当年酗酒对母亲家暴。小说就是在这样富有戏剧矛盾的情境下展开,让小说充满悬念。小说集中还有一篇《教授和他的儿子》,设置的也是父子矛盾冲突。桀骜不逊的儿子和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之间缺少理解和沟通,他拒绝父亲的帮助,按照自己意志去行事。上述戏剧冲突的设置所产生的悬念,往往能使小说叙事突破了平实,让读者对小说情节的发展充满期待,故事的可读性也大为增强。
二、“东拉西扯”与“第一人称”
潘军的小说不少都具有散文化的特征。《知白者说》也是如此。让我们对此来寻找原因,或者说做一个“钩沉”。小说文本的散文化跟潘军早年从事大量先锋小说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作家的写作习惯和叙事风格经常会或多或少的保留下来,这点不可否认。在当年的先锋小说写作中有一个重要的叙事特征就是“东拉西扯”,说的理论一点,也可以叫做文本语言的游戏化。另外这种东拉西扯也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严重的“东拉西扯”,它们完全无厘头的游离于故事之外。当然,先锋小说中有不少文本它们本来就具有故事情节淡化的特征,也就是没有故事。所以这种严重的“东拉西扯”在整个文本中往往显得并不是很扎眼。形成这种文本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先锋小说作家有一种文本自恋在里面,他们经常完全忽视了读者的感受,忽视了故事的可读性和故事情节。当然这也是先锋小说后来最终没落,小说重新走向现实主义,并且开始关注生活的一地鸡毛的重要原因。我们以小说《流动的沙滩》为例,来看看潘军当年的“严重”的“东拉西扯”,然后再来看看《知白者说》中对这种东拉西扯风格的遗留及其意义。先来看《流动的沙滩》,这部中篇小说通篇没有情节没有故事,在先锋小说流行的时代,无故事无情节的“东拉西扯”在大部分先锋作家那里都有尝试,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时尚。我们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段:
《流动的沙滩》是一部关于思想的妄想之书。书名出自上面那句法国人的话是很显然的。我不懂法语。电视里法语教学节目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它的书写形式和英语德语差不多,用的还是古罗马人遗下的文字;其次是它的发音没有脾气,软软的。据说对情人说话用法语最恰当。我不怀疑这点[2]。
提到先锋小说,大家都会想起马原《虚构》中最有名的一句“元叙事”: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我叫马原。后来诸多先锋作家多有模仿,小说中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后来成为叙事策略之一种,也就成了大篇幅的“东拉西扯”。作者借此在文本中跟读者透露自己的创作意图,跟读者商量打算如何安排文本中人物的命运,等等。潘军的小说中也有很多此种“元叙事”。上面引文及下面的段落皆是如此:
还必须说明,《流动的沙滩》不是我的作品。它的实际作者是一位看上去还算健旺的老人。在不远的一个夏日黄昏里,他以不披露姓名为条件向我谈起要撰写这本书的计划。我们谈了很久,但他只是说了书名。……我已经说明《流动的沙滩》是老人计划要写或者正在写作中的书[3]。
在先锋小说没落之后,小说思潮重回现实主义的“新写实”思潮。潘军的小说写作也开始比以前注重讲故事,努力讲精彩的故事。但是先锋的叙事特征有意无意的保留了下来,也许是写作习惯的保留,抑或是写作中的一种惯性。我们来看潘军1998 年写作的小说《和陌生人喝酒》,潘军对自己的这篇小说还是颇为自信的,在出版的《潘军文集·第二卷》前面的彩页中,就放置了该文本的手稿照片。当然小说写得也确实很精致,我们以此为例来说明“东拉西扯”的妙用。小说讲述了“我”经常遇到一个陌生人,一起坐地铁,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陌生人请我喝酒,喝酒的同时陌生人开始给“我”讲述他和自己老婆的故事,讲述夫妻二人如何相识,如何结婚又如何分手。小说先是讲述了自己和老婆如何在电梯里相遇相识,女孩子头上有个纸屑,然后陌生人提醒了她,女孩子脸红了拿下了纸屑。后来两人就认识了并开始交往,并结婚了。在这里,本该继续的故事却忽然打住,潘军插入了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东拉西扯:
一九九七年秋天这个晚上我和陌生人一起喝酒,听他说话。我感觉他是在满足诉说欲,我这个外省人是最好的对象。但我也发现,在某些方面他有点闪烁其词。他的话断断续续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从来没想过,这可以写成一篇小说。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们再次在那个地铁车站相遇时,我才意识到这已是篇现成的小说。这样我便有权力改变一下叙述角度与方式。小说不要求以法律为准绳,但你眼下读着的这篇小说却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我有必要做出这种申明,再往下写[4]。
在大段大段地插入“我”自身的故事,以及与陌生人故事无关的“东拉西扯”之后,“我”再次遇到了陌生人并一起喝酒,然后陌生人开始讲述有人神秘地给自己送了一张电影票,自己进了电影院却远远发现自己座位的隔壁坐着自己老婆。然后悄悄退了出来,然后夫妻互相猜忌离了婚。故事忽然又打住了,留下了悬念,又开始了“东拉西扯”。最后,小说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没解释谁送的电影票,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叙事的停顿、设置悬念等叙事技巧的运用,这些叙事策略也使小说的的故事更为丰满。
这种当年先锋小说中留存下来的特征,在《知白者说》中仍然表现的很明显。
虽然更为简洁,属于使用了并不严重的“东拉西扯”,但是叙事的套路还是一样的。尽管故事较上述所引之前的那些作品,叙事显得更为单一。小说《知白者说》一上来,就是“非虚构”地总结“我”的一生。直到第二自然段的结尾,才开始提到同学王兵的儿子要结婚,自己参加婚礼来到犁城酒店住下来。酒店对面是城南茶馆,小说开始切入正题,这两段就用了六百零六个字。所以也让人产生小说为“非虚构”散文的一种错觉。在整篇的叙事中,完整的故事也就是我和沈知白的几次交集,被这种不算严重的“东拉西扯”隔开,让故事变得不连续,不停的产生停顿,造成悬念,是一种叙事的“留白”,也使故事变得更有张力。
潘军的小说还有一个当年延续下来的特征就是喜欢用“第一人称”“我”叙事。《知白者说》亦是如此。《潘军文集·第二卷》中收集了他早前创作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共收了八篇。分别是:《白色沙龙》《省略》《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爱情岛》《情感生活的短暂真空时期》《三月一日》。这八个中篇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在先锋小说中,“第一人称”可以用来元叙事,可以用来解构小说。作者经常要向读者讲述构思的过程,之后往往又要解构自己的创作,这些不用第一人称是很难进行的。正因为“第一人称”叙事具有如上的灵活性和可塑性,所以先锋作家们都对其情有独钟,潘军更是如此。但是,在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中,“第一人称”叙事相对于“第三人称”叙事而言,最重要的和最明确的一点变化,就是叙述者必须部分介入作品,而成为其中的一个人物,同时又是叙述者。这样读者便不能期待叙述者向他展示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全部真相。一个部分成为小说人物的叙述者在逃避了“第三人称”的叙事职能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叙事空间。
《知白者说》中,“第一人称”叙事使故事变得有亲切感,读者往往有一种代入感,同情人物“我”的命运。另外故事也是随着“第一人称”视角一点点推进,剥开。“我”的视角决定了故事的发展和推进。例如,“我”和沈知白直接的交锋结束以后,沈知白的命运对“我”来说,也是不可知的,“我”最终通过王兵之口,知道了沈知白的坐牢和被打。“我”通过刘倩之口,知道了沈知白和刘倩之间暧昧的情人关系,以及沈知白对她的不负责任和玩弄。“第一人称”使叙事更加灵活,也可以让叙事者自由地抒发感想,对故事中的人物做出评论。当然也更容易设置悬念,因为“我”只能通过别的渠道知道其他人物的命运,故事的展开及人物命运的展示都是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既控制了故事的节奏,又保持了一种神秘感。
三、“男女问题”及沈知白形象的意义
潘军的小说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男女问题”的描写很有特色,也很有趣味,《知白者说》亦是如此。潘军曾经借助小说人物之口说:“实际上我和别的作家大致差不多,比如每一自然段开始得空出两格不写。我当然也需要构思,需要在人物之间走来走去,需要风景、性和眼泪。”[5]191也就是说,“性”是潘军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小说《知白者说》中,涉及到的“男女问题”主要是沈知白与刘倩。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刘倩的叙述,二是对刘、沈二人之间关系的叙述。文中对刘倩单个形象的叙述,如前文所述,让整篇小说增色不少,也让人读起来饶有兴趣,也使小说有了烟火气和生活味。人都有七情六欲,而那些“大人物”和名人在此方面可能更加引人关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潘军小说中经常写出了“我”的性心理。《知白者说》中“我”对刘倩与沈知白的关系一开始表现出了羡慕、嫉妒的心理。这是作为大学生的“我”,其人物心理的一种真实的刻画与描写:“这个瞬间我有些冲动,觉得身边要是有刘倩这样的一位女朋友,一定会很幸福的。正这么想着,女人的下巴又像猫一样扬起,我这才听出外面响起的脚步声。”[1]而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刘倩再次出场,这里有一大段刘倩对沈知白的控诉:“刘倩说到这里就哇地哭开了,情绪已经完全失控,说姓沈的太欺负人了,骗了她二十年,她为他离婚,为他堕胎,为他鞍前马后地伺候着,可是他一直就在欺骗她。”这时的“我”,与当年不同,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幸灾乐祸,以及对刘倩的一种厌恶,这种心理和“我”对沈知白的厌恶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心理相对于爱屋及乌来说,那应该叫“恨屋及乌”了。文中还有对沈知白常年不在家睡觉的描写,说沈知白家的席梦思一边已经塌陷,一边还完好无损:“王兵还谈到一个细节,差点让我笑喷。沈家的席梦思已经买了十多年,现在是女人睡的一侧已经塌陷,而属于男人的一侧还是鼓鼓的——这个男人在家根本就待不住啊!”[1]
潘军在《知白者说》中对“性”的描写如上所述。这些描写主要是为了刻画沈知白形象而设计,也相当生活化。我们把潘军此前的小说中关于“男女问题”的描写做一回顾后,我们发现,潘军对性描写是节制的,没有围绕这些大做性爱文章,就像他在《流动的沙滩》中说的那样:“我不喜欢也不希望任何人在我的笔下做爱。我的卷面总是清洁的。”[5]210潘军小说中偶有的性爱描写也显得得较含蓄。这种对性描写的节制首先和潘军一贯对性描写持所持的观点有关,他认为“西方比较注重性意识而东方比较注重性行为,把性作为对心理的刺激和心理的调料放进文学里”[6]137,“我们民族对待性一是功利和实用,二是心理上带有动物性,这些已经渗入到一些作家的意识和作品里,拼命的去写诸如性饥渴、性扭曲。”[6]139在《我不认为贾平凹是小说家》一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过度性描写的反对,“我对贾平凹书里的性描写也很反感,……性可以写得很干净,也可以写得很脏很丑,我觉得贾平凹的性描写趣味比较低级,读起来很不舒服。”[7]其次这也和潘军的创作思想有关,他的小说一贯不追求以“性”取胜,早年他对小说形式上的实验和创新更感兴趣;当下,在内容上我想他可能更多的关注故事本身,关注如何写好人物,写好故事,如何通过故事和人物来表现当下社会的关注。
上面谈的主要是小说的叙事特征和艺术特色。这篇小说其实必须要谈的是沈知白和孔乙己之间的关系。小说中作者明显的想把沈知白比喻成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在于沈知白盗窃以及被打残废这个情节的设计,尤其是沈知白向孔乙己的幻化,具体见前文所引。大多数读者可能和笔者一样,都怀疑这个情节的过于生硬,因为一个厅级干部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到小超市偷窃小商品。但是,据笔者向潘军先生本人求证后,他向笔者透露,沈知白某种程度上是个“非虚构”的人物,其因盗窃被打残废,这一情节也是“非虚构”。也就是说沈知白被塑造成现代孔乙还真不是巧合。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个醉心于科举,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迂腐的没有觉醒的读书人,其下场也很惨,这个评价应该符合鲁迅塑造孔乙己形象的初衷。那么在潘军的创作意图中,沈知白应该也是个迂腐的读书人,他追逐名利,没有原则,自私自利地谋求一条向上的通道,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还有一点,在鲁迅的笔下,孔乙己是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按理说,穿长衫的人按照身份地位应该坐着喝酒,但是由于真实的经济、社会地位等原因,却又不能坐着喝,因为孔乙己穷到了要“偷书赊酒”的地步,这是一种尴尬。所以在小说中,沈知白把“我”的剧本做了改编,孔乙己想坐下来喝酒却被人从后面抽走了板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酒洒了一地。也就是说在鲁迅那里,孔乙己想坐着喝酒而不得,沈知白亦是如此,这正是作者潘军想表达的。在《知白者说》的结尾,潘军这样写到:“我给犁城的王兵去了电话,问他这两天是否去骨科医院瞅了一眼?另外,我托他捎去的一箱小瓶装的虎骨酒是否送到了沈家?王兵说刚从医院回来,但只是远远瞅了一眼。沈知白现在可以自己转动轮椅了,王兵说,正喝着你的虎骨酒。他终于可以坐下来喝酒了。”[1]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了潘军想要说的:沈知白们都想能够坐下来喝酒,但是,如果跑错了地方,就可能被打骨折,去喝虎骨酒。这应该是小说《知白者说》的题旨所在。正如潘军自己在《坐下喝酒》一文中所指出的:“人生原本就是一台戏,区别是按谁的剧本演。沈知白是天生的演员材料,他本该立足于舞台,却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别的场子,想要更加的风光体面,仿佛任何空间都是属于他的舞台。那会儿他大概忘记了,别的场子,自己是不能随便坐下来喝酒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