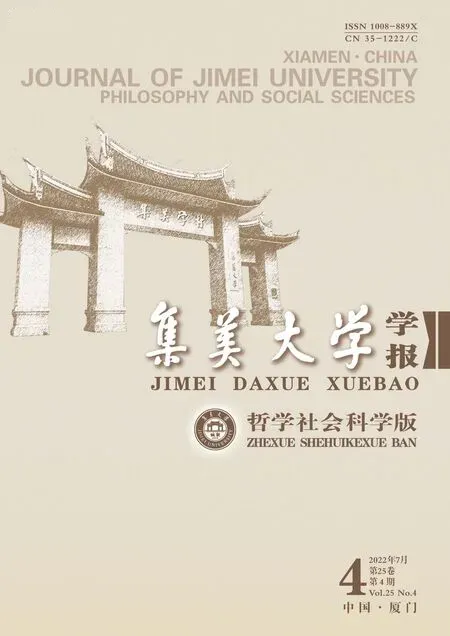金子光晴的上海经验与世界观的变化
李秀烈,崔洛民
(韩国海洋大学校 国际海洋问题研究所,釜山 49112)
一、近代日本思想与上海
上海从19世纪中叶开始步入国际性租界城市的行列。《南京条约》之后,上海于1843年开埠,先后划定了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到1870年左右,这里基本具备了近代都市的设置要素,往返西欧的邮轮、西洋建筑、道路和桥梁、煤气灯、医院和学校、跑马场和公园等纷纷涌入这座都市。在由日本出发的定期航线开航之前,日本人去西欧必须经过上海。因此对于造访这里的近代早期日本人而言,上海这座近代都市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准西洋的体验。不过,当时访问上海的日本人仅限于部分官员、商社职员和妓女。
上海和近代日本关系的密切化是从日俄战争之后开始的。当时日本的纺织业首先正式进入上海。随着日本企业的大规模进入,1907年设立了上海居留民团。日俄战争结束的1905年,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人比5年前增加了4倍,达到约4 300人,而到1909年就超过了8 000人。之后,由于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在中国的地位显著上升,上海虹口区已被视为一个“日本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日侨人数突破1万名,把英国侨民甩在了后面。
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的增加也意味着访问者的人数在激增,其中兴起于1910年的观光产业使得日本人到访上海变得更加容易。由日本邮船、东洋汽船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共同出资组建的日本交通公社(JTB:Japan Tourist Bureau)先后开发出连结朝鲜、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观光路线,也因此涌现出了当时多种多样的中国旅行指南书籍。这一结果使日本人造访上海更加普遍化,主要路线大致分为2条:一条经由朝鲜、中国东北地区;另一条从长崎、神户和横滨等地搭乘直达汽船。进入1920年代以后,从长崎搭船到上海只需26个小时,这和当时从长崎坐火车到东京所用时间差不多。另外,上海是当时日本人唯一不需要旅券(即护照)就可以前往的外国都市。
在近代日本,没有一个外国的城市像上海这样,有如此多的日本人到访过并留下很多记录。从梦想着捞财致富的流浪者,到跟随民间资本进出的人群,还有与日本对华政策有关的大陆浪人、军人和政治家,以及与新闻业有关的当时屈指可数的文人、知识分子等等,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访问上海,并且用记录留下了他们的体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关上海的档案无疑是这些在历史经纬中诞生的产物。
然而,在这些保存至今的众多有关上海的记录当中,至今仍具有反思价值的作品到底有多少?想到这个问题便不免令人悲观。且不说村松梢风仅仅对上海的“奇形怪状”感兴趣,偏执于关注上海的“魔都”特质,就连在当代日本被誉为“中国通”的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等人,虽然笔下描写的上海表现出对于古典中国的喜爱之情,但是其中也充满了对现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极度厌恶和嫌弃。芥川抵达上海码头的第一印象就是“不洁本身”。他印象中“嘴里蹦出的具有最初纪念意义的‘中国语’”,就是甩开车夫时撂下的“不要”这句话[1]12-17。谷崎的描述也是类似情况。1926年,谷崎第二次来到上海,他乘坐画舫沿水路逆流而上,在观赏江南风景中感受传统中国乡愁的同时,还讲到了被革命所包围的中国内战状况,在他看来内战只是妨碍自身旅行的“革命骚动”[2]50。这些记录者只字不提中日之间存在的政治矛盾,以及由此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苦痛和困扰,而强调上海的奇形怪状或者渲染对于古典中国的乡愁,就像中国史研究者野村浩一所说的“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3]47,这些作品也不例外。
访问上海的近代日本文化人一般的态度可分为2种:(1)半故意地无视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2)对中国社会混沌和奇形怪状持有偏执性喜爱。不过,事实上其中也存在通过来自上海的经验实现思想转变的人物。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他的行动就是可贵的事例,在紧迫的政治状况下,他站在两国文化人之间交流的前列,显示出了文化的力量,尽管只是一时的;还有武田泰淳和堀田善卫,他们目睹了战败(对中国而言是光复)前后上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实体和现代中国的现实,以此为基点展开战后思想活动;再有尾崎秀实等受到上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启发而觉醒,并投身其中。这些思想家所具有的价值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值得回顾和反思。
以上海经验作为方法,用焕然一新的视角去看待人类和世界,金子光晴(1895—1975)毫无异议是这些思想家当中的一员。金子光晴是战时极具批判立场的诗人,发表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和欧洲文明的几首诗,二战以后也批判了日本的天皇制及其产生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封建体制。众所周知,他的一生饱经沧桑,他不受制于任何意识形态,秉持独立的立场去凝视和批判日本以及世界,有着特异的个性。迄今为止对金子光晴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他的战时反战诗和战后作品,对于成为他思想形成过程中重要转折点的上海和东南亚经验,并不太重视。然而,在金子光晴的思想当中,把上海和东南亚经验说成几乎是决定性的重要契机也不为过。固然,在上海遇到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给金子光晴的中国认识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是,成为其思想上更重要转机的则是他在上海亲眼目睹到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摆脱所有人际关系的限制,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些苦力仅凭唯一的“肉体”日复一日地苟且偷生,他们的存在体现的是利己主义(egoist)或者无政府主义(anarchist)性质的上海人生活的象征。金子光晴将自身的状况和苦力们的生活重叠起来,获得了透彻的利己主义视角。之后,金子光晴从这一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控诉东南亚的现实,批判近代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很早就在法国抒情诗的唯美主义诗歌世界当中开始创作活动的金子光晴,重生为一位新的诗人。
二、作为“避难所”的上海
在近代日本,上海所具有的意义因为明治维新这一转机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研究者刘建辉曾经将其整理为从“近代国家的‘起爆剂’”转变为“距离最接近的‘乐园’”[4]9-10。即,作为西方信息的窗口,同时也是实际感受“文明”的冲击以及中国半殖民地状况的空间,上海一度敦促着日本的国家觉醒,而近代国家成立以后的上海则被视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自由”新天地,是“浪漫”的对象,充满“冒险”机会的地方。对于这种变化,刘建辉作了如下论述: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上海,对于作为“国家”的日本而言,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但是,对于众多的梦想“脱离日本”的日本人来说,这个混沌的都市,确实是一个距离最近的“避难所”,而且是距离最近的“乐园”。另外,明治以后, 实际上有大量的日本人渡航来到上海,这些人当中,除了一部分是政府和军部派遣的大陆扩张的推进者之外,大部分人在这块土地上所要求的,是它与“内地”不同的“近代”的存在方式。也可以说, 上海起到了一种能够与日本的现实相对比的“装置”的作用[4]10。
梦想着“脱离日本”的人将上海视为“避难所”或者“乐园”。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国家,随之而来的日本社会的倦怠感扩大了上海的这一意义。也不妨可以认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上海事变”(亦称“八一三”事变)以后日本对上海的独霸。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社会经受着战后不景气的折磨,在这样的社会上仍然盛行着“要不还是去上海试一试”[5]13的半自嘲式的对话。
金子光晴或许可以说是近代日本逃避型上海体验中最为典型的人物。不可否认的是,成行于1928年11月的金子光晴访沪带有作家逃离无产阶级文学开始抬头的日本文学界而亡命的一面,但是,他外出游历期间,其夫人森三千代出现外遇的问题以及为解决生活困苦而表现出来的个人逃避更为强烈一些。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上海行与在大言论社资助下以准公派资格前往上海的文人,或者为发掘创作题材而去上海的文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此时此刻,第三代路虎发现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中型SUV,4.8米的车身长度配合上仅用直线和直角勾勒出的轮廓,它所具备的阳刚气质让SUV概念重新回归到了原点。而车厢内也不再是英国汽车品牌所惯常使用的那种略显传统的布局和设计风格,液晶显示屏,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的旋钮的存在除了在视觉上增加了不可忽略的科技感之外,更暗示了其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全地形潜力。
然而,金子光晴“没有任何计划,也不抱任何希望,仅只为了远离日本”[4]而渡海抵达上海,那里有着与日本“截然不同的伦理道德”。在那里,金子光晴感到“前面挡住去路的墙壁坍塌了,墙上出现了一个窟窿,外面的空气一下子涌进来,那份带劲儿的解放感”[6]68。
1928年11月,当金子光晴拖着一个旅行箱、两只手提箱抵达上海时,因为夫人的外遇和生活困苦等个人危机,看不到作为一位诗人的未来,困扰重重,如同中野孝次所描述的正陷入“在完人意义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穷途末路”[6]293。上海以“敞开生疥癣后落下疮痂的巨大胸怀”[6]144迎接了这种状态下的金子光晴夫妇。金子光晴是这样表达他当时所感受到的上海魅力的:
阴谋、鸦片和卖春的上海混杂着大蒜、菜油、煎药以及腐烂物等磨人的味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体臭充斥其间,这令人难以忘却的味道的魅力把人抓住不放,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即使回到日本,短时间内也不能从那时的氛围中摆脱出来[6]69。
这样的上海描写很容易让人一下子想到对暗黑的上海表现出偏执性喜爱的村松梢风的《魔都》,不过,在金子光晴的上海论当中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看都找不到异国趣味,或者“文明和野蛮”“先进与落后”之类的二分法思考方式。他由上海那里获得的“解放感”是从所有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给他带来的平安快乐的感觉。身处穷途末路的金子光晴勇敢地只身“逃离日本”,他在“无政府主义乡村”上海品尝到解放的快感,并逐渐被其魅力所征服。金子光晴感受到了变化,他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体内长出了白色的根”,它“钻入(上海)石阶的缝隙中去,渐渐无法动弹”。究其原因,金子光晴认为在于自身“先天的无政府主义”[6]193-195气质。上海人的生活“是一种顽强而倔强的利己主义者和乐天派,不会对未来的重大规划感到发愁”[7]24,金子光晴把自身的处境投射到了上海人的这种生活境界上。在金子光晴看来,上海的苦力们正是象征性地体现上海人作为利己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生活的存在。
任何国家的失业者、流浪者也不会遭遇到如此难以想象的程度被孤立和个人化。任何国家的劳动者也不会遭遇到连牛马也不如的早晚奴役,而习以为常地带着牛马一样的禀赋去劳作。完全杂七杂八。 即使他们也有出于利己主义防卫而建立的琐碎集团,但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国家或结社之类组织的力量一点也帮不上忙。他们是纯粹的虚无主义者。他们降临人世间,就只是在不可计数的死人当中熬过饥饿、传染病和严寒酷暑,最终活下来的一个人。更甚于此的是他们随时都处于饥饿当中。他们深陷于无可复加的非自然贫富差距当中,充当了英国侵略主义的末梢部分,摆脱不了终身不见天日的命运[7]75。
金子光晴如此表述道,“我们觉悟到了在日本内地时始终无法感受到的‘我一个人’的事实。只我一个人……自身完全成为自身的中心”[7]76。金子光晴从苦力身上获得的这种视线,如同泷本和成所指出的一样,“与其说是人道主义的视点,不如说是从他们那里(发现了)人要活下去的残酷性”[5],并且把自身的现实重叠到了这些苦力的生活上。他看到连“很早便敞开心扉交流的”郁达夫等知识人也把苦力当作“像狗一样要撵走”的对象。这种态度给他带来冲击,这是所谓“东方人的半开”[6]152的批判在顽强而倔强的利己主义同质感上的代表。
上海是利己主义者火热的生活空间,在那里不能从任何组织或者团体得到保护,每日苟且偷生,“就像说的那样啃噬着自己的生命过活”[6]151。金子光晴认为“再没有像(上海)这样日子好过、心情也舒适的地方了”[6]194。对于有着这样认识的金子光晴而言,他发现“文明对野蛮”或者“先进对落后”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正是这一点才是金子光晴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上海访问者的决定性的界线。
三、遍历东南亚
1929年5月,金子光晴从上海出发前往香港,同年12月在新加坡登上驶向马赛的游轮,在此期间他遍历东南亚各处。整个旅程包括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三宝珑和马来半岛全境,之后再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他返回日本的途中,再次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马来半岛旅行,最后于1932年5月抵达日本神户。
金子光晴游历东南亚最主要的目的是攒到赴欧的旅费。尽管这样,他在东南亚所看到和感受到的现实带来对近代西欧文明的新认识,使他成为重生的诗人。金子光晴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马六甲街景:
从广东或者福建来的华侨,马来、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原住民,以及身体细长的印度人等在大街上穿梭往来,摩肩擦踵,汗淋淋的肩膀和手臂,汗液里沤着恶臭。洋车(译者注:人力车)用长长的棍棒毫不留情地扒开人群,在其间飞奔。长鸣着警笛粗暴开车的是那些有地的土豪,或者脸庞泛红而又倨傲的欧洲旅行者,还有看上去像是带着狐狸面具一样眼角上提、心怀诡计的日本旦那(译者注:带有“主子、老爷”的意思,当时东南亚对经营种植园或者矿山的日本人的称呼)。从葡萄牙开始,再到荷兰、英国,就算世上变天了,也不过是行径越来越大胆而已。原来有着主人面孔的支那人把土地和房子置于优先考虑的对象,原住民则没有栖身之地。原住民和印度劳动者在冷夜的沥青地上衣不遮体地熬过长夜[8]206。
在东南亚流浪,金子光晴目睹到的是作为统治者君临殖民地的文明国度,以及受欺压呻吟着的原住民社会。“虚张声势而又狡猾的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犯下的罪恶擢发难数”[9]111。荷兰人“横霸”爪哇,在他们的“高压强制”下,“爪哇人的筋骨”[6]284都被累断了。
在榨取原住民社会这一点上,金子光晴的祖国日本也不例外。森波浪(Sembrong)江两岸散落着橡胶农场,那里的“旦那”们“在漆黑的凌晨,天还没亮就起来到浓雾笼罩的橡胶园巡视一圈”,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读读书、打打网球、捉捉麻雀,游手好闲地”[9]23打发日子。橡胶农场就像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空间,“有钱有枪”的“旦那”们在那里就是“王侯”,是“神”[7]162-163。金子光晴从这些东南亚的现实中解读出了日本“东洋鬼”(当时汉语圈社会使用的对日本人的蔑称,其中就有“日本鬼子”。金子光晴将其用来作为对日本人的自称)的嘴脸和近代西欧文明的伪善。没过多久,他一面直视“眼前因榨取和强制劳动而疲敝的人类样品”,一面重读“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熟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8],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也正是在这时,诗再次“回归”金子光晴。
金子光晴很早就追随法国抒情诗的唯美主义传统开始从事诗歌创作,而上海利己主义者火热的生活现场和东南亚帝国主义横行压榨的社会经验,促使他脱胎换骨成为新的诗人。日后,他对自己的早期作品所做出的评价“难以重读”[10]122,并不是单纯表达“谦虚”的修辞,而是带有与前后诗歌世界截然不同的意义。发表于1935年的《鲛》是这样揭露西欧文明实体的:
海上的鲛,/肆意滑水浮游。……鲛,并不猛然大咬一口。/这是肚子饱啦。//这些家伙的肚子里塞满了人,以至于都冒了出来。/消化好了,圆鼓鼓裂开的一只手臂,/咔嚓咬断的大腿根,/像小枕头似的躯体。/鲛现在,“什么也不需要”,眼睛眯成一条缝,/连连打着瞌睡。//超越想象的斗鸡眼。隐忍而又残忍的家伙。/鲛聚集在马拉卡南宫 (Malacanang)丹戎不碌港(tanjungpriok)的白色防波堤外。……鲛。/这家伙没心脏地在世上阔步,惨无人道的混蛋。//我们为了得到基督徒和香料来到这里。/达·伽马(Vasco da Gama)从印度登陆时说过这句话,/我们为了得到奴隶和掠夺来到这里。/这样说也行。/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巴达维亚修建炮楼/史丹福·莱佛士爵士 (Sir Stamford Raffles)钳制住新加坡的关门,为扭断暹罗、日本和中国的手而建立了牙城。……这些家伙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友情,是和平,是爱社会。/这些家伙随后出来结成纵队。/那是法律。是舆论。是人的价值。/该死的!所以我们又被一缕一缕地撕碎了[11]145-164。
这篇作品再度收入1937年日本人民社出版的诗集《鲛》当中。在该书的《序文》里,金子光晴证实是在“南洋旅行中”完成《鲛》的,并且阐明“除了实在是令人愤怒至极的事、想表达轻蔑或者有想嘲弄的事情以外,以后不再从事诗歌创作活动”[11]110。把这句话倒过来琢磨一下,可以反过来证实金子光晴对于文明国度在东南亚的伪善和暴力是多么的愤怒。
1930年,时隔10年金子光晴再次到访巴黎。然而,他却“不由自主地冒出疑问‘这一文明到底是什么’,巴黎弥散着往日看不到的虚无感”[12]205。“西方”作为“明亮自由的另一个世界”[10]37,曾一度是日本社会闭塞性的参照点,也是憧憬的对象。不过,金子光晴目睹了文明国度榨取和伪善的现实情形,在他看来巴黎不再是“花都”。金子光晴已经看到了“英国在海峡殖民地和印度对当地人的压榨以及荷兰政府在爪哇长期施行强制劳动的历史”。他“无法原封不动地从表面上接受”文明国度所标榜的“正义”[10]192。他第二次到访巴黎唯一的收获只是“弄清楚了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我的故乡”[12]210。
巴黎不是一个做美梦的地方。安息吧,巴黎。在睡梦中,如果像蜷曲着身体的狗一样睡着,这样就够了[12]263。
金子光晴以这样的方式向巴黎作了诀别宣言,之后以“异邦人”[13]107的方式度日。
四、结 语
在近代日本,上海是“西方”和半殖民地中国共存的二重体验空间。整饬的城市设施和华丽的殖民地特色建筑物是近代都市上海的象征,而同时并存的鸦片窟和卖淫窑子则暴露出中国旧社会阴暗且沉重的现实。上海的这种二重状况,反过来说,也是“自由”从上海生发出来的基础。在国际性租界城市,上海尽管受到国民党的高压钳制,自由还是存在的。这自由就是因为上海被列强瓜分占领的现实,即这里是帝国主义矛盾巨大的结点,所以产生出带有矛盾性的自由。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们集合在国民党势力够不到的租界,这就是因为列强瓜分割据格局下悖论式诞生的自由在上海仍然存在。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的日本文化人到访上海的热潮,其成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海所具备的矛盾自由。金子光晴出于作家的使命和个人生活的困苦而决然逃离日本,在上海他一方面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交流,另一方面从日复一日从事体力劳动的底层民众生活中获得彻底的利己主义视点。此后金子光晴展开的对近代文明的批判就是以这些生活者视点为基础的思考。金子光晴思想的经历由上海出发,可以作为帝国主义矛盾下诞生的租界城市也开放了“脱帝国主义”可能性之空间的一个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