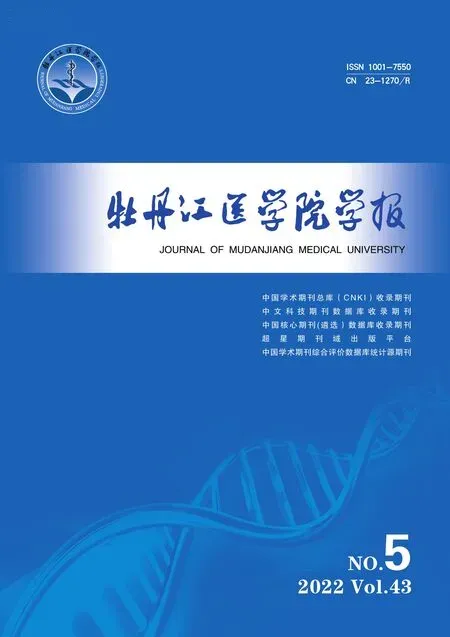围术期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研究进展
张慧慧,周子昊,鲁卫华
(1.皖南医学院;2.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 安徽省危重症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全世界每年约进行2亿多例大型外科手术[1]。围术期肺损伤是患者术后恢复期最常见的并发症,其中以ARDS最为严重,其在心脏手术发生率高达8.1%,导致术后死亡率的明显增高[2]。在重症监护病房的相关试验数据显示,低潮气量和呼气末正压(PEEP)通气的使用可改善ARDS的预后[3],由此引出ICU广泛使用的ARDS相关肺保护通气策略,近年来在围术期麻醉中肺保护通气的使用得到推广,本文就围手术期肺损伤相关机制及保护性通气策略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围术期肺损伤的机制
目前关于围术期肺损伤的定义包括肺部炎症、气体交换受损、放射学异常和呼吸衰竭等在内的一系列疾病,出现上述任意结果都可认为已经产生肺损伤,最近已将临床产生的肺部相关并发症合并称为围术期肺部并发症(PPCs)并达成共识[4]。虽然不同形式的围术期肺损伤的发生率各不相同,但肺损伤的发生被认为与机械通气有关。已有研究证明肺部炎症反应可发生在所有机械通气患者,且炎症反应程度与呼吸机的设置有较大联系[5]。机械通气引起的呼吸机肺损伤主要继发于肺萎陷伤、容积伤、气压伤、生物伤等。PPCs的发生率与手术类型相关,在非胸心外科手术中约2%~39%,而胸外科手术中为14%~59%[6]。其他因素例如术中体位改变、手术方式的选择、腹腔镜手术的压力、手术操作创伤、体外循环和缺血再灌注损伤等也可增加PPCs的发生率。
1.1 萎陷伤萎陷伤主要由肺不张引起,肺不张的发生是由于肺实质受压、肺泡内气体吸收和表面功能受损所致。由此可造成许多不良生理反应,包括肺内分流、肺顺应性降低、肺血管阻力增加和对炎性肺损伤的易感性。这种易感性不仅局限于某一肺不张区域,临床数据显示,炎症在正常通气区域肺不张可长达数天[7],炎症反应的持续存在加剧了PPCs的发展。
1.2 容积伤低和高的肺容量通气均可引起肺损伤。低容量通气时,肺处于不均匀性扩张状态,可发生肺不张肺损伤,产生上文所述萎陷伤。高容量通气时,局部肺泡过度扩张,产生较高的肺泡内压,肺泡内压超过肺泡表面的张力,即可出现肺泡损伤,进而破坏肺泡-毛细血管屏障,促进局部产生炎症反应,从而导致蛋白质移位和水份进入肺泡腔[8]。由此而知,高容量通气时所产生的并发症如肺泡破裂、气胸、纵隔气肿和皮下气肿等,并不是因为高容量通气引起气道压力变化导致,而是由于局部肺区域的过度膨胀,产生较高的肺内压引起。
1.3 生物伤指肺损伤后产生的肺泡炎性损伤、凋亡和纤维增生过程,其最终导致肺顺应性降低、缺氧和肺纤维化。以上所述损伤可通过直接(通过损伤肺泡各种类型细胞直接引起肺损伤)或间接途径(将这些转导到上皮细胞、内皮细胞或炎症细胞引起各种细胞内介质释放到肺,从而间接引起肺损伤)发挥作用,为肺纤维化的发展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生物伤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呼吸系统,损伤还会引起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使介质、脂多糖和细菌等进入体循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TNF-a、IL-6、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a、肺源性脂溶性介质等已经被证实在机械通气肺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9],以上细胞因子可通过肺泡毛细血管屏障释放到肺泡腔和循环,从而导致肺部促炎细胞因子在体循环中的水平增加,使炎症反应逐渐向非肺器官传播损伤,进一步促进MODS的发生。
1.4 其他因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最严重的围术期肺损伤。其显著特征是在疑似肺损伤后7 d内发生缺氧性呼吸衰竭,并伴有肺水肿的影像学证据。尽管ARDS与呼吸机相关肺损伤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特征,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ARDS诱发的肺损伤通常不是由于机械通气本身引起[10]。围术期还有许多其他潜在原因导致ARDS的发生,例如肺炎、败血症和吸入性肺炎创伤、输血、失血性休克、烧伤和吸入性损伤及手术相关因素如手术类型、手术部位及术中体位等。
2 围术期肺保护性通气策略
机械通气策略是围手术期肺损伤的主要防治措施,包括潮气量、PEEP的设定和肺复张手法等的使用。目前,不同研究对“围术期肺保护”的定义有很大差异,其涉及的呼吸参数调节包括以下内容。
2.1 通气模式与容控(VCV)模式相比,压控(PCV)模式具有快速输送潮气量,可同时设定的最大气道压力避免气压损伤的优点。目前为止,有关术中使用PCV与VCV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Li等[11]在关于PCV模式在胸外科单肺通气的研究显示,在单肺通气(OLV)期间使用PCV较VCV模式可降低患者吸气峰值压力,改善OLV期间的肺气体交换和肺力学以及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性。而Bagchi[12]在对超过10万手术患者的大型数据库研究中却发现使用PCV模式与PPC的增加相关。到目前为止,多项研究已经检验了PCV与VCV相比的效果,然而,就已经公布的数据没有明确说明支持或反对某一特定机械通气模式的优越性,关于在围术期应如何选择通气模式仍值得进行研究。
2.2 吸入氧浓度(FiO2)术中使用高吸入氧浓度(FiO2)是常见的做法,特别是在气道插管和拔管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围术期使用高FiO2,以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13]。另一方面使用较高的FiO2(>80%)也会导致肺泡吸收性不张,增加PPCs发生率。在对接受非心胸手术患者进行的一项大型分析报告显示,术中FiO2的增加与术后肺部并发症(PPC)的发生率及30 d死亡率之间存在剂量依赖性关联[14]。Cohen等[15]通过设定FiO2为80%与30%,验证FiO2为80%是否会增加PPC发生率,结果发现二者发生PPC并无明显差异。尽管上述的研究能够在临床诱导和苏醒之间选择最佳吸入氧浓度提供一定的指导,但关于如何平衡高浓度吸入氧的益处和风险仍是麻醉医生经常面临的临床难题。
2.3 潮气量低潮气量的使用可能是肺保护策略中最广为人知的组成部分。Futier E等[16]在关于腹部手术术中潮气量的研究中发现,低潮气量可以减少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Needham DM在ICU的另一项实验显示,在常规的临床实践中,ARDS患者及时坚持使用低潮气量与提高生存率相关[3]。然而这一系列关于低潮气量通气的研究中大都包括使用至少5 cmH2O呼气末正压(PEEP)的措施。调查显示,使用低潮气量和零或低PEEP仍会使肺部炎症发生率和30 d死亡率增加[17]。由此可知,低潮气量的单独使用并不能减少术后PPC的发生,其可能只是作为术中肺保护通气(IOLPV)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2.4 呼吸频率(Respiratory Rate,RR)目前临床上术中RR的设定多基于呼气末二氧化碳(PET CO2)进行相应的调整,且常通过提高RR以避免高碳酸血症的发生。Santer P等[18]在关于评估术中RR和术后PPC之间关系中发现,接受机械通气的非胸外科手术的患者,术中使用高频率通气与PPC的发生显著相关。RR的增加可使吸呼比、胸内压、吸气流量等发生相对应的改变,这些改变都会导致循环肺张力和肺压力的增加。此外,高频率通气可增加死腔量,从而可能导致肺损伤。
2.5 吸呼比一些研究将延长吸气/呼气比(I∶E)与机械通气常用的1∶2进行比较。延长的I∶E比值增加了平均气道压力,并同时降低气道压力峰值。延长吸气时间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有益的效果,包括增加肺顺应性、PaO2、降低肺泡气动脉血氧分压差和减少炎症标志物[19-20]。但目前仍缺乏相关证据表明一个特定的I∶E比率有明显的益处,我们仍可以通过监测氧合、肺顺应性等参数来个体化优化单个患者的吸气时间。
2.6 呼气末正压(PEEP)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PEEP已经被证实在预防术中肺不张有效。Spadaro S等[21]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腹腔镜手术中接受5 cmH2O PEEP的患者与未接受PEEP的患者相比,氧合情况明和肺顺应性更好,术后肺不张发生率降低。在PEEP存在的情况下,使用设定的潮气量时,肺泡压力升高,有利于使塌陷区域的肺组织得到更好的复张。另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发现,12 cmH2O PEEP并不优于2 cmH2O或更低PEEP,两组间PPC的发生率几乎相同[22]。综合以上与既往ARDS的相关研究,可以合理地推断,对于大多数手术人群而言,高PEEP在术中的使用并不是必需的,但对于存在肺不张或伴有肺损伤的高风险患者可以考虑使用。在为病情复杂患者决定机械通气方案时,麻醉医生仍需要考虑血流动力学波动带来的风险。最近的一项生理学研究发现,采用滴定最佳PEEP方法不仅可以改善腹腔镜手术中的氧合和肺力学,而且可减少血流动力学的波动[23]。而近年来关于如何滴定个性化PEEP的方法仍在探究,我们发现目前围术期肺部超声的应用正逐渐增加,这项技术在未来也许可成为用来辅助滴定术中个性化PEEP的有效方法。
2.7 驱动压驱动压定义为平台压和呼气末正压(Plat-PEEP)之间的差值,因其与肺静态顺应性相关,目前被看作是一种可将潮气量设置到满足正常肺功能大小的方法。Amato MB等[24]在对3562名ARDS患者的机械通气相关数据分析显示,驱动压的降低增加了ARDS患者的生存率,而并非既往认为的使用低潮气量和呼气末正压。驱动压代表了肺实质在每个通气周期中承受的循环应变,根据患者的呼吸系统顺应性调整潮气量,与跨肺压直接相关。因此,设置通气参数以降低驱动压有助于改善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的预后。这些说明,在使用肺保护措施时,即使在肺健康的患者中,驱动压变化也可能使患者面临呼吸机诱导的肺损伤和发生PPCs的风险发生变化。
2.8 肺复张策略在麻醉诱导后可暂时性使用肺膨胀法(维持气道压40 cmH2O,持续20~30 s)来逆转术中肺不张。肺复张的生理效应是通过增加跨肺压,以打开未充气或充气不良的塌陷肺泡,从而改善氧合和肺顺应性的过程。但最近相关数据表明,当复张手法仅作为常规通气的辅助手段,与腹腔镜手术期间的低潮气量、中等PEEP通气策略的使用相比,并没有给病人带来意料中的效益[25]。由此我们猜测肺复张操作可能在打开塌陷肺泡,改善机体氧合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气压伤。与低潮气量通气相似,肺复张措施可能也是肺保护通气(IOLPV)的一个组成部分,临床上仍需麻醉医生在权衡相关利弊后决定是否使用。
2.9 围术期无创通气围术期无创通气包括通过面罩施加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压力支持通气伴或不伴正呼气末正压通气等。在全麻诱导前应用无创通气可显著改善氧合,而术毕拔管后使用无创通气与呼吸系统并发症的风险降低有关,但与气管拔管后再插管和意外ICU入院的风险无关[26]。由上可知,决定围术期是否使用无创通气应首先考虑引起患者呼吸衰竭的原因,肺不张可能较肺炎、外伤或ARDS患者获益更多。
3 结语
围术期肺损伤是一种严重的肺部并发症,可由损伤性机械通气引起或加重。尽管关于ARDS的相关研究已经引导现代麻醉实践向使用小潮气量方式改变,但对部分肺保护通气原则仍存在争议,其中包括对血流动力学影响和高碳酸血症的担忧,以及健康肺的患者是否可以从中获益。目前,在围术期一般人群中使用肺保护性通气的证据还不明确,由于PPCs在低风险患者中发生率较低,假设采用某种通气策略将PPCs发生率降低50%,则需要超过4000名患者的样本量,这需要大样本多中心试验。鉴于围手术期患者死亡率非常低,证明IOLPV可导致生存获益的试验更为困难。随着医学的发展,围手期机械通气的未来主要涉及个性化管理。基于PBW(理想体重)的个性化潮气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采用,目前许多临床研究都围绕着滴定“最佳PEEP”平衡维持呼气末肺容量,同时避免肺过度膨胀来开展。因此加强机械通气肺损伤的相关机制研究可为临床制订合理的机械通气方案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