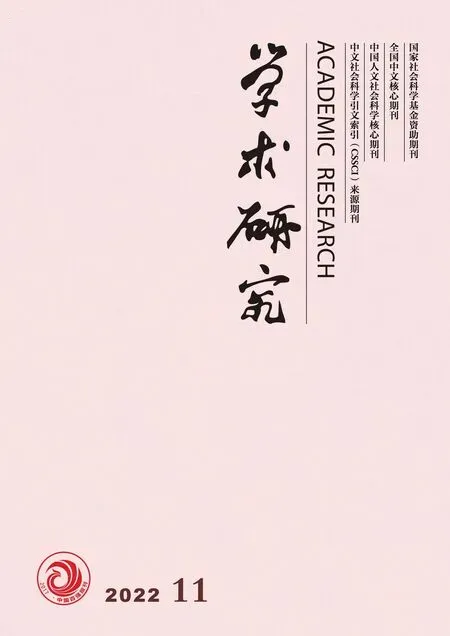跨文化自觉与民族电影的主体性问题
周安华
如同其他大众视觉传播形式,21世纪的当代电影也被纳入全球化话题,在一种整体性框架和美学层面遭遇审视和质询。然而,电影在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值得关注,美国学者乌尔夫·赫德托夫特称其“充满悖论和张力”。他特别强调,电影全球化的表现格外复杂——“有些是民族或地域造成的异质现象;有些是地球村及其消弭民族特征所代表的同质倾向;还有一些则倾向于在接受跨民族文化过程中,在它自身的精神视野、自身的理解与行为方式内,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进行重新诠释和再造”。①[美]乌尔夫·赫德托夫特:《处于文化全球化和民族诠释之间的当代电影》,一匡译,《世界电影》2003年第1期。在上述三者中,笔者认为同质倾向更具代表性。也就是说,在深度国际化甚或全球化话语甚嚣尘上的历史现场,讨论一国电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电影及其传播,人们大多会从“适应性”角度,探究其“普遍性”蕴含,分析其融入世界影坛的可能性及正确途径。似乎只有不断修正自身的主旨、题材和范式,使民族电影成为大国镜像的“渐近线”,成为国际电影市场的“宠儿”,才有真正的水准,才是所谓“跨文化”电影和国际范儿电影。
那么,问题就来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电影一直身处与欧美电影互动的情境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影坛甚至出现不少直接改编自好莱坞的电影如《香衾春暖》等,为什么在众多中国观众眼里,依然是费穆《小城之春》一类深具传统气质、尽显东方美学神韵的电影成为翘楚,而致力于好莱坞化的那些国产电影并未成为历史标杆,反而遭致很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与此相应,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代末,当西方大片如《侏罗纪公园》《泰坦尼克号》等风靡一时,中国影坛迅速出现了美式大制作电影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它们气势足够“恢弘”、场面足够“华丽”,视觉奇观化明显,却并未引起欧美影坛一丝的骚动,就连本土观众也纷纷对之退避三舍。这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这说明,百年中国电影最根本的绚烂,并非一味模仿国外电影之作,而是沉入民族文化之河,以鲜明的地缘文化符号,凸显本土精神和情趣的中国风影像,是以中国故事描述中国国情,表达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电影。这里就凸显出在开放观念之下,在世界电影潮流中坚持民族电影主体性问题。
一、民族“自我”和“个性”:电影主体性之本
电影主体性首先与民族性息息相关,无论哪个区域哪个国度哪个时代的电影生产,都是特定地域的民族生产,也是一种民族性生产,都包含着地缘、历史和传统的厚重元素和丰富编码,留有深刻的种族记忆和族群印记,充溢着地方性、民俗性视觉符号。伦敦大学教授裴开瑞认为:“民族性不但在我们这个跨国时代里依然生生不息,在跨国电影研究中 ,它同样是一个有着长久学术生命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把民族性这一概念及其表现方式视做可变的而不是绝对的话,那么民族性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还越发普遍了。民族性不再以一种单一的面目出现,而是变成各种不同的观念,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①[英]裴开瑞:《跨国华语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抗与主体性》,尤杰译,《世界电影》2006年第1期。由此可见,民族电影主体性建构在绵长而酣畅的民族性土壤上。
电影主体性包含电影的“自我”和“个性”,蕴含独特的电影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反映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是一国电影在吸取与拒绝、纳入与清除、化合与分离博弈中的知性把握、敏明自省,也是逐步确立自身现代性电影观念、美学气质与艺术根性的一个能动过程。它本质上是一国电影真正的情志与魅惑所在,是所谓国族电影之“吸引力”根源,同时,也是一种对绝对电影霸权的反抗姿态,是在动态过程中高高竖立的民族电影的幡旗。即如我们谈“印度电影”“韩国电影”甚或“亚洲电影”,谈“挪威电影”“芬兰电影”甚或“北欧电影”,事实上我们是被其别开生面、与众不同的面貌和样态所吸引,为其所包含的强烈而自主的电影创造力所折服,从而确认其绵延于银幕的“印度性”“韩国性”以及“亚洲性”“北欧性”。
显而易见,无论南美还是东亚,民族主体性都与出色的电影创造如影随形,都彰显着电影的地方经验和区域情怀。维罗妮卡·加里博托在《“标志的虚构”:2000年后第二代电影中的阿根廷近代史叙述》中,以加斯东·比拉文的《禁锢》为例,说明它是如何揭示意识形态紧张关系的,他“将 2000 年后的第二代(阿根廷)电影读解为政治对抗的场所”,并且认为“通过儿童或青少年视角表现历史”具有一种“有效性”。②[美]维罗妮卡·加里博托:《“标志的虚构”:2000年后第二代电影中的阿根廷近代史叙述》,黄钧妍译,《当代电影》2016年第9期。阿根廷本土电影导演、编剧费南多·索拉纳斯回应称:“我们的真理就是新人通过挣脱所有压迫他的缺陷而建立起来的自我,这是颗威力无穷的炸弹,也是生活唯一真正的可能性。在这项尝试中,革命电影人以他颠覆性的观察、感性、想象和实现来冒险。诸如国家历史、战士爱情、人民觉醒等伟大的主题,都在去殖民化的镜头前重生。”③[阿根廷]费南多·索拉纳斯、奥克塔维·赫蒂诺:《迈向第三电影:关于第三世界电影解放的发展经历与感悟》,王伟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以此新世纪阿根廷电影凸显了青春政治维度的民族主体性。
韩日电影也如此。“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时期的特点,是从大叙事到小叙事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媒体研究中的回应就是从广播(broadcasting)到窄播(narrowcasting)的转变,就是精品销售而不是杂货拍卖的时尚,就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边缘性成长的视角。”④[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韩国电影贯以小叙事见长,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被用来指喻韩民族命运,以及思考东西交汇碰撞的半岛现状和未来,这就在主体性层面反映了利奥塔所说的边缘性成长问题,也揭示了韩国电影的价值侧重。比如在金基德影片中可以看到许多与社会疏离的无根的人,《真相》中饱受凌辱的画师,视世界为野兽牢笼;《雏妓》中的珍花不知从何处而来,最后进入一个原本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家庭;《坏小子》中的善华在被迫沦为妓女以后,她的家人和她曾经“心爱的男友”竟没找过她。直视现实的个体命运,勾勒其生活样态,主动折射底层社会的困窘,使韩国电影“以小博大”,每每获得关照弱者和折射历史的贴近感。在叙述南北对抗、兄弟杀戮的惨烈主题时,这种“韩式镜像”也无处不在。韩国首部“粉丝电影”《隐秘而伟大》表现北方5446部队派遣特工元柳焕到首尔“潜伏”的主题,影片一改韩国谍战片《实尾岛风云》那种酷冷、凝重基调,而用惯常的世俗喜剧手法,将温暖的百姓生活光影描述出来。影片以第一人称叙事,作为间谍的元柳焕具有双重人格,他心中交替回荡着两个声音——对母亲的思念(杂货店生活的隐喻)和对“祖国”的忠诚(战士责任所在);他也始终盘桓在两个世界——善良、热心、真切的“敌人的”贫民区邻居、店主们和他们的戏弄取乐、真情灼照,和来自北方的“党和同志们”冷飕飕的考验、审查乃至追杀,不同环境、身份和境遇撕扯着这个英武少佐(杀人机器)的心,曾经的战斗信念如坚冰一点点融化。可以说,《隐秘而伟大》通过喜剧化的场景处理,笑中带泪,大幅度耗散了一贯的南北题材固有的拼死相搏等对立叙事惯性,而从人性视角赋予双方更自然、更深邃的骨肉相依、同胞亲情元素,由此更深刻地灌注了韩国新电影的民族主体自觉以及南北方作为同一族群的深层文化认同。
二、贯通电影和本土文化间的血脉
中国民族电影的主体性,可谓是中国电影成长史的“弱项”,也是电影精神长期孱弱的深层和内在的反映。一百多年中国电影演变史,被太多的“模仿史”“致敬史”占据了篇幅,不惟电影故事、影像、镜头,就是堂皇的民族“电影理论”,也常常是域外某个电影学说的转译或转述。如“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电影理论著作”——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年上海华先商业社图书部)就是日本著名电影学者归山教正代表作《活动写真剧的创作与摄影方法》的译述,两相对照,几乎是照搬。而中央电影摄影场导演陈鲤庭的理论著作《电影轨范》,其英文“母本”则是斯波提斯伍德的《电影语法》,也属于编译成果。直到20世纪50年代,郑君里在理论上提出“破自然照相”,民族电影理论才与欧美的“照相本性”说形成了明显疏离。就电影创作而言,20世纪20年代,“鸳蝴派”固然在言情片、古装片和武侠片类型上有拓展,《玉梨魂》《空谷兰》《啼笑因缘》《美人计》《盘丝洞》《木兰从军》《火烧红莲寺》《儿女英雄传》等作品也有一定的现实语义和较好的观众缘。但是,受好莱坞通俗剧影响,更多的“鸳蝴派”电影体现的是受市民青睐的言情小说、里巷文学与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匆迫媾和,是为商业利益折腰的结果,多在低俗和喧闹的场景上着力。由此都市银幕上演了一出出光怪陆离的艳情、神怪电影风潮,其时的神怪电影《西游记·盘丝洞》《古宫魔影》以及“飞剑道术”片《大侠复仇记》《半夜飞头记》《荒江女侠》《大破九龙山》等等,都因传布“宿命论”“迷信因果”而受到人们的抨击。当时就有观众呼吁电影检查委员会“取缔”神怪武侠片或剑侠片,认为其对中下层社会的思想教育有害无益,甚至会加重他们思想上的“不良与俗鄙”。①小痴:《应取缔神怪的剑侠影片》,《华东日报》1931年3月9日。诚如美国学者尼克·布朗在《社会与主体性:关于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中所说,20世纪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通俗娱乐文化如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无可争辩受到了西方影响,②[美]尼克·布朗:《社会与主体性:关于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吴晓黎译,《世界电影》1998年第4期。而彼时中国民族影坛一系列作品的迎合与渲染、浅斟与低吟,也确实很快拉低了现代话剧建立起来的现代性话语,和剧烈震荡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进入新中国,民族电影工业迎来了生机勃勃的发展历史。相比而言,此前活跃的商业电影形态此时已被红色革命电影所取代。在冷战背景下,中国电影延续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念,以革命战争电影为主调,塑造了一批为缔造工农革命政权赴汤蹈火的“人民英雄”,一批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的艺术形象,如《上甘岭》中的连长张忠发、《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白毛女》中的喜儿、《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等等。这些艺术形象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贴合时代的味道和气质,发掘了共同性的政治伦理的价值……成为新中国罕见的一种‘公民教育文本’”。③周安华:《过去性:新中国政治电影的文本叙述——“老三战”电影创作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其显现出苏联电影持续而强烈的影响。新中国初期的译制片主要是苏联电影,1950年《团的儿子》中的小红军伐尼雅,1951年《夏伯阳》中的传奇英雄恰巴耶夫等,都在当时的国产片中留下了清晰的影子。《渡江侦察记》《董存瑞》《党的女儿》《战火中的青春》《鸡毛信》等中国战争片都以苏联电影为“范本”,而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唯一指针。194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同一版发表陆定一《欢迎苏联电影》、茅盾《美国电影和苏联电影的比较》等四篇文章,热切宣传苏联电影,视苏联电影为“教科书”。从1949年到1962年,我国共引进苏联电影421部,苏联电影迅速进入中国大江南北、城市乡村。这些都在观念和美学上促使了国产电影的嬗变,这种嬗变包含着艺术和技术的某种提升,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电影“自我”在相当程度上的缩减甚至消泯,它们使国产电影在价值导向、艺术趣味以及生产形式上逐渐趋向“联共化”“左翼化”“政治功利化”,为其后电影的“高大全”人物模式埋下了最初的伏笔。这是自好莱坞电影广泛渗透中国银幕之后,外来电影再次全面影响中国银幕,虽然一个是通过市场力量,一个是通过意识形态渠道,但它们都对中国民族电影的主体性营建、对鲜明的电影“中国性”生成构成了较大的消解和直接的挑战。
审视中国电影的百年追求,我们几乎是在好莱坞电影、苏联电影持续的影响下发展和推进电影生产的。因为缺乏民族自信,畏惧技术创新,我们时不时模仿外来者,时不时纠结于电影本体的找寻、艺术方法的高端以及电影技艺的炫酷,希望能由之取得与时代、与他者一致的先进性,但我们较少关注源于自身传统和审美习性的民族电影伦理、电影美学的构建,疏于打通电影和本土文化之间贯通的血脉。由此,一旦政治风向、商业风气和文化潮流发生改变,本土电影随即开始追逐下一波的“热点”“卖点”,力图在新的历史时尚和财富比拼中获得成功。
三、“影以载道”:中国电影精神与美学之砥砺
电影是影像的现实和历史。植根于中华大地,蕴含五千年文明,携裹古老东方哲学、宗教和艺术的情愫,中国电影应当是别具风格的“这一个”,应当富含主体性的构成,时刻凸显本民族的镜像理念和艺术风致,并在映射现实和揭示人生时独辟蹊径。但是,在现代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的学界反复强调的不是中国电影的“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即民族电影和西方现代电影之间的共同性——相对于主体的一种“他者性”。这种膜拜心态忽略了国情和历史要素,也让中国电影的现代性进程完全受制于世界“主流电影”的观念、节奏而在可有可无的处境上徘徊。众所周知,好莱坞电影虽然也负载社会思考,但其“梦工厂”的文化定位,令其更侧重于电影想象和故事的完美构建,而欧洲艺术电影源于近代人本哲学,更多从经验的视角、个性的视角来确立自我观察的眼光,触摸人性人心,两者本质上和中国民族电影的主体能动性有着巨大的不同。
早期中国电影的有识之士就强调电影要积极弘扬本土民族精神。佩娟1929年在《大公报》发表《电影与民族的精神》一文称,与竭力发扬民族精神的德国、美国不同,“中国的影剧,是否尚保存固有民族的精神,已经成为疑问,更谈不到发扬固有民族的精神方面了”。①佩娟:《电影与民族的精神》,《大公报》1929年8月6日。而佚名说:“我们认为中国制片界,根本就不必为‘媲美’而模仿洋大人,尤不可放弃自己的精神,而投降到它们的拜金旗下。”②佚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剧本》,《大公报》1929年3月5日。华菲则认为:“能推动时代的是无数个有善良向上心脚踏实地勤恳真实的人。我们要宣扬一切能忠实描写小民的苦痛与希望的作者,因为歌颂英雄的时代已过去了,人民世纪中平凡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③华菲:《评〈万家灯火〉》,《重庆晚报》1948年10月30日。美国学者尼克·布朗也强调中国电影是有民族个性的。他认为这些“区别性要素特征”相当明显,包括“善恶对立的形式的系统化、电影的情感作用、它的戏剧性模式与演出方式、它将个人塑造为牺牲品的方式、它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正义问题的方式”。尼克· 布朗举例说,“西方的情节剧理论如此青睐核心家庭及偏爱对于‘主体性’、‘性别差异’的私人领域的心理分析性解释,实际上它忽略了形式产生意义的更广阔的社会环境”,而中国则不同,比如谢晋的《芙蓉镇》,观众“将《芙蓉镇》作为情节剧和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化阅读应该密切联系政治时代和政治文化,影片正是植根于其中,而不是西方批评的课题性的简单摹写”。他指出:“与第五代对政治角色重新塑造的许多激进影片相比,《芙蓉镇》以颇不相同的方式置身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地平线上。谢晋不偏不倚地留在汉文化可辩识的地带,和社会主义生活观熟悉的轮廓与课题性之中,同时继续阐述一种道德话语,它密切活动在失望或愤世嫉俗的大众化情感与具有政治可能性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空间”。①[美]尼克·布朗:《社会与主体性:关于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吴晓黎译,《世界电影》1998年第4期。而这正是谢晋作品也是中国情节剧的独到之处。
从主体性角度看,真正的中国电影从不以一种梦想构建或者个性认知的方式来面对和选择电影艺术的价值,而更多是以对社会性的深刻理解和挖掘,即所谓的“影以载道”方式,来标明电影创作者的责任和身份,实现国族电影的价值追求。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主体性特征,它也是百年中国电影深度现实主义融合了诗意和家国意识的体现,从《一江春水向东流》《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到《野山》《秋菊打官司》,再到当今的《钢的琴》《我不是药神》《烈日灼心》《心迷宫》《少年的你》等等,它们以低姿态触摸生活之弦,贯穿着深刻的社会洞见、细腻的人心描摹,而背后却熔铸了自觉而浓郁的家国情怀、生命情怀,由此建构了国产电影精神与美学之砥砺,也成为别有洞天的民族原创影像的标志。
与此相应,我们的先锋实验电影和文艺电影,在恍惚和迷离的历史空间勾勒个人的心绪感受,也与唐宋以降中国诗词歌赋的感伤、悲秋之情,以及生命旅程“不如意事常八九”的“错过”“伤别”“苦痛”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时代的画屏上展开耐人寻味的国人故事书写。《城南旧事》《苏州河》《长江图》《无问西东》《路边野餐》,都站在不同时空,通过一个个独特的情境,寄寓了对特定历史的审视思考,隐含着多变现实的隐喻和一代人的文化焦灼,其非线性镜像背后埋藏着个体以及民族的心灵感受、生存感悟,隐含着创作主体对历史的一种“光影重构”。正如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杰姆逊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提到的,所谓的怀旧电影从来就不是过去那种对于历史内容的再现,相反,它是通过带有独特风格的内涵,以虚拟的意象传达一种“过去性”。显而易见,仔细去揣摩,《钢的琴》等国产片源于现实的艰辛与阵痛、起于生存危机的僭越,与伯格曼的《野草莓》、塔尔可夫斯基的《镜子》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等那种超越现实而深具普世意味的精神性探索和真理叩求,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蒙太奇拼合的日常记忆、历史片段以及梦境还原几乎和每个生命个体、和具体的生活形态无关,而是直指哲学本体世界。
四、当代民族电影主体性与现代性营建
当代优秀的国产电影已蕴含某种主体性,在相对宽松的创作氛围下,对时代变革的透彻感悟,体现在作为个体的电影导演及其作品上,就生发出当下中国电影现代性的魅力。近年国产电影在商业类型片和艺术电影两方面斩获颇多,这与四十年改革开放,与本土导演自我意识觉醒、人文情怀渐丰有密切关系。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反对同化的惯例和仪式,拒绝遵循权力性话语的框架规定,其反身性现代性及自省自觉几乎随处可见。在2013年的《致青春》里,小女生郑微无视官本位、无视权力社会的自由与奔放,让现在的“规制和习得”显得尴尬,也凸显了中国现象级电影的主体性自觉。在2015年的《冈仁波齐》里,导演以民族志立场叙述了一个朝拜圣山的故事。当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和叔叔、临盆孕妇、贫困屠夫、残疾少年等朝圣者,在静谧的月夜安营扎寨集体诵经祈福时,观众感受到久违的怀揣希望的美好,也看到了市场、金钱和权力之外的特别力量——一种偏执而自我的生命选择,主动、坚定而可贵,富含主体意义。正是它让这帮衣衫褴褛的人们笑对艰险,长驱2000多里去仰望神山,重温祖辈流传下来的信念。甚至在2019年新主流电影《夺冠》里,连连夺冠,赢得全中国人民喜爱的郎平回答西方记者关于“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在乎输赢”提问时的回答——“因为我们内心还不够强大,不够自信”,也异乎寻常地敏锐,有一种正视自己、直面差距的非凡主体勇气。
作为兼具社会性挖掘和历史隐喻的所谓“双重性文本”,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在另一个层面体现出民族电影的一种主体性,即尊重生活事实,关心普通人的底层情怀,而非居高临下的权力主义、商业主义、票房主义,始终坚守一种平等对话立场,用电影和当下对话,和普通人对话。它以民族词典中的热词“江湖”展开,不仅有味道,也有视界。江湖从来都是族类、口味、故事的替代语,当然也代表动荡以及人性检阅、云淡风轻的岁月。在传统的民族叙事文本中,只要提到江湖,就会让人充满想象和期待,静待一个具有鲜明丛林法则的奇幻空间扑面而来。贾樟柯深谙民族精神与传统血脉的“江湖”,并以之构建自己的现实故事,寻求故事背后的人性拷问,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由此,《江湖儿女》序幕,棋牌室里众人打麻将与谈天,其中的暗战、斗法体现出了江湖的味道。里屋的斌斌虽然只是一个江湖小头目,身边只有些许跟班,但他是在用江湖的方式解决问题,这让观众对江湖充满了猜想。《江湖儿女》前半部分在讲男人的故事,而后半部分则讲女人的故事。有意思的是,贾樟柯先扬后抑,在影片最后,让我们最终明白,其实这个故事和男人无关,导演讲的不是“江湖儿女”,而是“江湖女儿”。影片真正的唯一的主角是赵巧巧,导演在这个女人身上融合了中华文化元素中的大爱与大义,展现了江湖的本质——道义、信用和对过往美好事物毫不迟疑的坚持。这种颠覆性的叙述,显示了贾樟柯以及当代民族电影的主体立场。显然,这种深植于文本的主体意识带有鲜明的“反叛”性。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采用“移动的”叙事,讲江湖行走的故事。观众跟着主人公巧巧棋牌室现身、煤矿拔电源、舞厅见二勇、二勇家慰问、出席葬礼、嗜血街头、出狱上船,随着剧情延展,人物命运轨迹逐步清晰起来,当代诸多社会阶层的“状态”也或明或暗呈现出来。由于抛弃简单浮面的情感戏、紧张剧烈的冲突戏,而将视线集中在中下阶层民众的日常现实,影片镜头获得了醒目张力(如底层社会葬礼的艳舞表演等),导演以其客观真实性,深挖国民性之弊。影片地理与空间选择也具有符号隐喻性,公交车、麻将馆、歌舞厅等场景细节的现实构建,从大同到奉节再到大同的空间和时间转换,导演由之实现对完整国情深入普遍的揭示。
在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语境下,伴随知识信息的跨国界传输、艺术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包括电影在内的媒介艺术,其主体性建构的意义愈发突出和重要。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主体性是民族电影赖以生存和借力擢升的基石,是获得跨文化认可的前提与基础。从精神和气质、内涵和风格上充分涵养中国电影主体性,确认国族镜像的本土话域、人文理趣和审美情态,是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在视听新媒体时代,在普遍的跨文化生产、跨媒介传播的新历史场域,人文生态和客体都已深刻改变,任何因循守旧的所谓“主体坚守”,都意味着内蕴消解、本体失能和竞争失势。只有破除固有藩篱,从当代性视角寻求主体建构的突破,才能在观念、底蕴与方法论上彰显自身主体话语的先进性,形成与当代强势文化的有效博弈。因为,21世纪的电影主体性,与迅速变化的媒介主体形成了“对抗”,这使更多的人力图在更广泛的知识和社会框架内分析和整合艺术创作。特别是当代电影主体性出现某种“不稳定性”,观众和作品陷入了复杂纠缠,“被历史化、政治化所遮蔽的艺术家隐藏的思想和感情问题”就特别值得关注。①Susan Best, “Minimalism, Subjectivity, and Aesthetics: Rethinking the Anti-Aesthetic Tradition in Late-Modern Art”,Journal of Visual Art Practice, 2006, 5(3), pp.127-142.显然,充分认识移动交互媒介主导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主体性的变异,在以跨文化自觉对话世界的同时,积极尝试民族电影主体性的调适与充盈,使其更具内涵和张力,是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