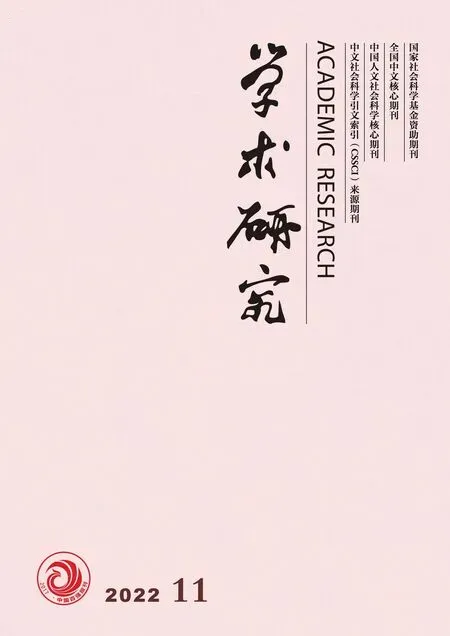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与文明力较量*
余 露
在今日的历史教学科研体系中,世界史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系统,与中国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这并非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形,其他国家或者只有国别史,没有整体意义上的世界史,或者有世界史但以本国为中心,而中国的世界史却不包括本国,主要是各个外国的历史或者国际关系史。因此,世界史的范围、内涵和功能,常常引起学界的讨论,是否包括中国、如何与国别史和外国史区别开来、是否具有以及如何承担探索人类大同的功能,是其中的关键。①较有代表性的有向荣:《世界史与和谐世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黄洋:《建构中国立场的世界历史撰写体系》,《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徐浩:《什么是世界史?——欧美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诹议》,《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王大庆:《“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学术研讨会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刘小枫:《世界历史意识与古典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年第1期。要解开纠缠不清的困扰,探寻清季“世界史”观念的最初渊源和内涵旨趣,不失为有效的途径。
先行研究已大体勾勒出清末以来西洋史、万国史、世界史著作译介和传入的基本情况。可是除少数例外,一般均将西洋史、万国史、世界史等量齐观。②参见刘雅军:《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世界历史观念》,《历史教学》2005年第12期;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缪偲:《从“万国史”到“世界史”》,《人文论丛》2014年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学术研究》2015年第8期;王艳娟:《〈万国史记〉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邢科:《〈东西史记和合〉与晚清世界史观念》,《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其中李孝迁于其著作第1章“清季汉译历史教科书”中专列一节“西洋史、万国史的翻译与‘世界史之观念’”,三者分别而言并敏锐注意到“世界史”主要是作为观念存在,尚未形成学科体系,亦未出现本土著作。如果只是作为探究清末国人域外历史认识的方便名词,不妨一视同仁。若要追究各自内涵外延的差异,尤其是“世界”这一重要概念的影响,就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原本是佛教概念的“世界”,在19世纪后期逐渐落实为指称地域上的全球,同时兼具其他复杂意涵,认定相当主观,大小虚实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共通性则是推崇和学习西方的强烈价值取向。完成语义转变的“世界”一词,成为表达近代中国对外观念、人我关系和未来方向的重要词汇,①相关研究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桑兵:《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余露:《虚实互用:洋务运动时期的“天下”、“地球”与“世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变动中的紧张:甲午前后中国人的“世界”意象》,《暨南史学》2019年第2期。并被用以多种名物,“世界史”即其中之一。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主要依托外来的译著,至于本土,既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的著述,亦未形成体系化的学科,但相关讨论仍透露出大量的信息,既是近代国人面向世界的重要一环,也制约了其后世界史的属性、定位和旨趣。从思想史而非学科史的角度,将重心从整体的清末以来西洋史、万国史、世界史传播发展情况,聚焦到具有特殊性的“世界史”上来,结合近代中国“世界”观念的发展,考察“世界史”认知的产生与意旨,可以在历史中呈现“世界史”与西洋史、万国史的不同内涵,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一系列关乎近代中国基本方向与命运的思维取向。
一、统合东西洋史与以西洋史为“世界史”
以名词勾勒历史的弊病之一,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1876年公布的同文馆课程中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等名目,而后人追述时却统统成了“世界史地”。②参见《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美]毕乃德:《同文馆考》,傅任敢译,均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1、203页。在将“各国”理所当然地置换为“世界”之际,后起的“世界史”作为集合概念产生的意义荡然无存。实则当时更为通行的指称是西洋史、各国史、万国史等。虽然考察对象相近,实质和内涵却相去甚远,所以有学人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只有西洋史,并没有世界史。③杨令侠:《杨生茂先生与世界历史教学》,《历史教学》2016年第16期。不过,凡事都有从无到有的渊源流变,早在清季十余年间,国人就有大量关于“世界史”观念的讨论,不仅是他们认识域外历史的重要积累,更深刻反映近代中国认识和走向世界的艰难探索。
“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外国史、西洋史等概念的比较中存在的,时人常常不惮笔墨仔细辨析各自的异同。而这种分辨意识,最初是受到日本影响的结果。
目前所见国人关于世界史的最早讨论,是1899年王国维为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作序时提出,历史分为国史和世界史,前者叙述一国,“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不过东西洋文化的交流尚不充分,于是暂时只能“大别世界史为东洋史、西洋史之二者,皆主研究历史上诸国相互关系之事实,而与国史异其宗旨也”。王国维关于世界史包括全体且注重联系的看法,其实来自桑原骘藏本人的认识,所谓“东洋史者,专就东方亚细亚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而言之,与西洋史相对待,盖世界史中之大半也”,④王国维:《东洋史要序》,[日]桑原骘藏:《东洋史要》,上海:东文学社,1899年。即以世界史为东西洋史之统合,二者缺一不可。
1901年4月,《译林》第2期开始连载六条隆吉、近藤千吉《世界商业史》,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明确标明“世界”史类作品在中文世界的出现。作者自称该书立意在于通过探寻商业之兴废盛衰,使人养成实业思想,从而富国强兵,还特别论述商业史与其他历史尤其是文明史的关系,称“商业与文明关系最重”,“文明之所由起,即商业之所由始,商业之发达,即文明之进步”,甚至呼吁“商业即文明、文明即商业之念”。⑤[日]六条隆吉、近藤千吉:《世界商业史》,《译林》第2期,1901年4月18日。商业与文明如此紧密相连,可以说,一开始国人的世界史印象,就跟实利、实力相联,同时又被赋予了文明的内涵。王国维着意指出的各国联系,在此有了更具体的落脚点。
不过,桑原骘藏和王国维所强调的另一面即世界史必须包括世界诸国全体,只能显示东亚人心中的世界史应该如何,在现实中未必如此。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的论说就进一步从理念和现实的紧张出发,明确道出“世界史”之“世界”的主观性和实力底色:“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他同时强调“西人论世界文明最初发生之地”本包含中国。“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虽然,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①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1页。以文明力是否够强作为能否置身于世界史之列的凭据,所以中国排除于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也就是说,世界史的地理属性并非主导,社会属性才更重要。
王国维是在特定的标名东洋史的著作中展开对世界史的讨论,《译林》刊载的《世界商业史》是翻译过来的个别著作。1902年,梁启超《东籍月旦》则是针对其时日本史学的整体情况进行分别和议论的。在他看来,此时的“世界史”不仅作为一个门类存在,而且作为一种标准被用来点评各种著作。梁氏将日本历史之书分为八类,“一曰世界史(西洋史附焉),二曰东洋史(中国史附焉),三曰日本史,四曰泰西国别史,五曰杂史,六曰史论,七曰史学,八曰传记”。他指出:
日本人所谓世界史、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欧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国、俄国而亦不载,他更无论矣。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以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②《万国通史》追求 “总挈万国之大事,发明世界之全体”,对于“一国之形势虽具,征之世界之全体而不见其轻重”,则不予录之([日]天野为之:《万国通史·自序》,吴启孙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故梁氏有此说。此在日本或犹可言,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也。近年以来,知其谬者渐多,大率别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而著真世界史者,亦有一二矣。
在此梁启超清晰表达了对欧洲人撰写的世界史的排他性以及日本照搬套用的不满,不过他没有意识到在欧洲、日本和他本人之间,所谓世界史并非统一概念。西文原词与日文翻译以及梁启超的使用,不能一概而论。在逐本点评中,梁启超仍然不免混淆概念与事实的异同,他肯定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之《万国史纲》和箕作元八、峰岸米造之《西洋史纲》两种“据历史上之事实,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来”,可是同德国布列著《世界通史》、矶田良编《世界历史》、长泽市藏著《新编万国历史》、天野为之著《万国历史》、下山宽一郎著《万国政治历史》、辰巳小次郎与小川银次郎合著《万国史要》、今井恒郎编《万国史》诸书一样,“以欧巴罗史而冒世界史、万国史之名”。对于坂本健一“东洋、西洋合编”之《世界史》上卷,梁氏谓其“真可称为世界史者”,“可以识全球民族荣悴之大势”。又肯定松平康国著《世界近世史》名副其实,“盖真属于世界,东洋西洋并载者也”,对于高山林次郎著《世界文明史》亦承认其“叙述全世界民族文明发达之状况”,“可以增学者读史之识”。③梁启超:《东籍月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473-477页。
梁氏区别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正涵盖全球,这一点恰恰来自他所肯定的“真世界史”——坂本健一的《世界史》。蠡舟生在该书序言中称:“此书名曰世界史。以往所称之世界史或万国史,大抵限于泰西范围,普遍认为アルヤ外之民非人也,欧美以外之地非国也。”这与中国过去视四裔为夷狄如出一辙,是“因己所需,以明己为任”的狭隘之见,“从不占理”。当下“世界一体,南极以北、北极以南、东西互通融合之宿命已无法避免”。该书“兼论东西洋古今之事,以不负‘世界史’之名”,且简明扼要指出“世界史起源于国际性交涉,遂注重政治变动”。④[日] 坂本健一编:《世界史》上卷,东京博文馆藏版,1901年。综合推断,序中的“アルヤ”当为雅利安,即梁启超所称的阿利安。
结合梁启超的论述,蠡舟生所批评的“限于泰西范围”的所谓世界史或者万国史,应该包括此前欧洲人所著和当时日本人编著。实际上,欧洲普遍被认为开始脱离历史神学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俗世界史——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简称《风俗论》),不仅包括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并且给予相当高的评价。①《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et sur les principaux faits de l’histoire depuis Charlemagne jusqu’à Louis XIII)曾在 1753 年以“世界简史”(Abrégé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为题出版,该书是对博舒埃世界史将历史事件归为神的意志的反动,开启世俗世界历史的先河,西文指称世界史的至少有world、universal两个词。参见[美]沃格林:《革命与新科学》,谢华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40页;[德]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5、121-135页;[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也就是说,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人,带着马可波罗式的印象,相当高看中国等东方民族。弃而不论既非从来如是,也非天经地义,而是西方殖民势力侵占到亚洲,西方文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东方文明之后的情形,是殖民扩张时代的产物。而后者,显然才是日本人以及受到日本人影响的梁启超等中国人关注的重点,他们念兹在兹世界史是否真正涵盖全球,是否给予东洋或者中国应有的地位,恰恰是对殖民扩张时代西方在一元文明论之下排除东亚和中国于“世界”之外的反抗。
同样是在1902年,梁启超肯定为名副其实“世界史”的另一著作——松平康国编著的《世界近世史》由上海作新社出版发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世界史著作,对于中国人的世界史观念起到了近乎定型的作用。松平康国在该书绪论中分别国别史、列国史和世界史,相对于国别史“详一国之变迁”,列国史“明列邦之情势而比较之”,世界史则须具有“考宇宙之大势、遍征人类之命运”的功用。松平康国强调如果所记载的只是“五洲万国之事实,而无相通之脉络,与相关之条理,则亦不过为国别史之集合者而已”,是不足以称为世界史的。他认为列国史虽然“固与搜集多数国别史为一丛书者之体例不同”,但其主体仍然“局蹙于世界之一部,而无关于全局”。世界史则不然,“其主体在全局,而不限于一部,凡立国于大地上者,必考其如何成立、如何推迁、如何进化,人类之家族,如何冲触、如何结合、如何有情智、如何营生活,且归宿于如何之方向,是世界史之本分也。然必先知关系于世界全局之大事,而后揭明大事与大事自然之因果,是又世界史所当择之体裁也”。在他看来,“今日刊行于世之万国史,其名固为世界史之别称,其实能脱列国史之体裁者,盖寡也”。松平康国还论道:“夫人必有世界之观念,而后可为世界史。”具体而言,希腊人的世界史观念兴起于罗马征服四方扩张版图之后,日本人则在明治维新之后,而其编述却多依据“以西洋为主体”的“西洋之成书”,既然如此,“直谓之欧洲史而已,直谓之西洋史而已,于世界乎何有”。但是对于此种以西洋为世界的取向,松平康国是相当认可的。他甚至旗帜鲜明提出“世界史即西洋史”,因为世界交通发展、人类交往频繁、民族关系紧密、学术技艺进步、“政体法制略趋向于大同而渐近于真理”、“干戈玉帛利害射及于域外”等等,无不于西洋见之。就土地和人口言,“欧洲固不足以雄视世界,而境遇与实力之足以动世界大势者,则断断乎莫欧洲”。所以欧洲无愧为“世界史之中心点”,这是由事实决定的。不过是过去的事实,松平康国还是希望将来世界史之中心可以移到东洋。②[日]松平康国编:《世界近世史》,作新书局译,上海:作新书局,1902年。
1903年1月8日,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所办的《大陆》紧紧跟上,刊出《近世世界史之观念》一文,直接讨论作为观念的世界史。该文主体论述几乎完全照搬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的绪论,偶有文字区别,但将论述的立场由日本转为中国。两国近代命运的相似性是沟通的天然基础,也便于日本人相关观念的传播。该文最后提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国土之发现、交通之开张”是近世史的开端,“局面之阔大与世态之错综”是近世最大的特征,两半球“自有影响相应痛痒相关者”。由此“演出世界之历史者,不可不普及于全世界”。当下列国并立,大并小、强吞弱之事难免,但世界史“必以世界为一国,人类为一族”,“五色人种,虽智愚相分,利害不同,而博爱主义,将驱天下而归于大同矣”。③《近世世界史之观念》,《大陆》第2号,1903年1月8日。
有意思的是,前述被梁启超认可为“真世界史”的三本著作,专讲近世的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和侧重文明的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都很快在中国有了译本,倒是最纯粹的坂本健一的《世界史》未见译本,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其只有上卷以及篇幅较大等原因,内在地可能还是由于“近世”和“文明”更贴切国人的现实关怀。在日本人的影响下,梁启超等中国人的“世界史”认知包括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在理念上要求范围涵盖全球,二是在实际中又不得不承认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世界史的主体乃至全部就是西洋史。①汪荣宝编纂的《史学概论》在世界史的认知方面,几乎完全照搬松平康国的看法,一方面强调世界史的全局性,一方面承认西洋有左右世界大势的实力,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表示认可(《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10期,1902年11月14日)。二者对立统一的关键在于,他们都强调世界史不只是客观的、静态的、地理概念上的囊括全球,还必须注重国家与国家间的紧密联系,②邓实亦认为历史应该是“有机团体相翕应相维系而起也”,而不是事实材料的集合,所以他反对 “称世界各国历史之集合者为世界史,西洋各国历史之集合者为西洋史”,而强调必须“于世界各国间有密切之关系,始可谓世界史,于西洋各国间有密切之关系,始可谓西洋史”。邓实辑:《光绪壬寅(廿八年)政艺丛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719页。而联系是需要实力的,实力又被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这一状况与“世界”一词落实到地域指称的进程和情形恰相吻合。大体而言,“世界”一词在洋务运动时期开始零星被用于指称地域上的全球,甲午战后迅猛发展,1900年前后压倒此前的“天下”“万国”等概念,成为指称全球的最主要词汇。源自佛教的“世界”一词原本具有虚幻的时空双重涵义,具有极强的伸缩性,而国人对域外的认知,又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和势利感(印象最深的是欧美等几个有数国家的强力),而不是一般性地客观认识全球。两相结合,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主观性极强,可大可小,寄托着效法西方、融入世界的价值判断与追求,也承载着冲破西方中心观的文明一元论,向“世界”证明东亚和中国自有文明,完全有资格屹立于世界的艰辛努力。而这些高度凝聚在清季国人的“世界史”认知中,形成区别于同类概念的独特内涵:相对于同样注重全体的万国史,它还强调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动态,动态中又产生了厚此薄彼的轻重取舍;相对于同样突出重点的西洋史,它又强调必须名副其实囊括所有,更加开放,开放中体现出后进国家的艰难与坚持。
二、厘定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总体而言,1900年前后,在日本人著作的启发下,梁启超等具有新视野的中国人,开始在传统史学范畴之外思考“世界史”应该如何书写。大要有三:一是视野上扩大至全球,这是最基本的层面,也是“世界”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二是强调世界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而非简单的各国历史的叠加,这是更加动态和本质性的要求;三是注重各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这是“世界”主观性的反映,也是由第二点延伸出来的现实考量,折射出当时激烈的国际竞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方面是有关“世界史”观念的讨论、辨析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学科建制中,此时外国史地的内容已经出现,但并未取得世界史、世界地理之名。1895年上海强学会章程中用的是“万国史学”之名。③《上海强学会章程》,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页。1898年初,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率队到日本考察教育,归国报告用的是“本国、外国历史”这样明确人我之分的名称。④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己亥(1899年)夏四月刊本,第2页。1901年蔡元培考察全国各级学校课程撰成《学堂教科论》,在“普通学级表”中,历史、地理均按本国、外国展开。⑤《学堂教科论》(1901年10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8页。按中外分别历史地理,在当时乃是主流。张之洞、刘坤一筹设文武学堂,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规划学科时,均属此种方式。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张之洞、刘坤一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设文武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附章程)》,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773、791页。1902年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章程学规中则是分别为万国历史、中国历史。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章程学规》,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992页。同年公布但未实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寻常和高等小学堂的史学均按中国朝代展开,并不及国外。中学堂的中外史学按外国上世史、外国中世史、外国近世史、外国史法沿革之大略展开。奇怪的是,中外史学只有外国,可能是预设小学已经将中国史学习完毕。高等学堂的政科和艺科中的中外史学按中外史制度异同、中外史治乱得失、中外史治乱得失商业史展开。①《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8.15)钦定小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钦定中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钦定高等学堂章程》,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164-167、375-376、562-563页。1903年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史地指称在延续《钦定学堂章程》的基础上,稍稍出现一些新情况。经学科大学周易学门科目的补助课中出现“世界史”,文学科大学九门当中有万国史学门,却反而在中国史学门科目、中国文学门科目的主课中出现“世界史”,进士馆课程中也出现“世界史”。②《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奏定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定进士馆章程》,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2、779-780、785、866页。“世界史”终于现身于朝廷的制度设计中,但限于师资,并未实施,只是虚悬。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世界史”观念的讨论是无足轻重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是观念层面的讨论,反而不受具体现实的束缚,更能撬动时人对于“历史”和“世界”的思索。梁启超曾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学》中,给历史下定一个界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从范围和视野上当然不可能局限于一国。“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正是梁氏指陈的旧史一大弊端。求公理公例的目的,在于施诸实用,规划将来。梁氏的构建中,史学的意义显得重大、现实而又紧迫,不仅面向过去,更要探索未来,③关于公例公理观的各种表现及其与进化论和对未来态度的影响,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0-261页。关心的乃是中国的地位与前途。梁氏提倡新史学的最终关怀在于“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④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01-504页。这一点恰与他在前一年的《中国史叙论》中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提出的“世界之中国”时代界定相呼应。⑤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319-320页。已有学人指出,梁氏《新史学》试图“重新界定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寻找联结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新思路”。⑥[奥地利]苏珊·魏格林-施维德齐克:《世界史与中国史: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普遍与特殊概念》,《全球史评论》第3辑,2010年12月,第4页。且看梁氏的论述:
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
梁氏还在此一一点评何者可为“世界史之主人翁”及 “世界史之正统”。⑦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13-517页。根据李孝迁对梁氏该文与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的对照,原书只有“世界史之民族”的表述。梁氏不仅将民族改为人种,还变换出“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二元对立关系,⑧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74页。紧张感更加凸显。
1903年2月,《大陆报》从第3期开始连载《世界文明史提纲》(实为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同年有上海作新社译本),特别强调文明史应该“究明社会发达之真相”。《大陆报》称赞其“诚为文明进步时代所不可阙之善本”,堪为欲求文明进步者之圭臬。《新民丛报》第36号广告则称通过该书可以识“去野蛮而进文明”之途径。文野之辨是时人关注的重点,且多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4月,何负在《经济丛编》连载《世界交通史略》,其实是1902年世界各国间的外交活动大事记,按日期排列,与今日意义上的世界交通史迥异,却恰恰反映当时观念。作者称其鉴于“吾人既生于无日不争之世界,又处争而不胜之国”,为免坐以待毙,“图所以补救既往而防拒未至”而编是书。⑨何负:《世界交通史略》,《经济丛编》第23、24期,1903年4月12、26日。12月,镜今书局推介德国布勒志的《世界通史》,称“生乎今世界而不知环球之大势者,谥之曰盲。知环球之大势而不能寻其起原,探国家兴亡之轨道,究人群进化之阶段者,亦无以促文明而应时变”。⑩《镜今书局新出要书》,《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2月19日。
英国人器宾的著作原名“欧洲商业史”,日本人永田健助翻译时改为“世界商业史”,并解释道:欧洲虽不包括万国,但欧人却将文明商业遍布世界,东洋亚洲则停滞不前,“非日进不止者,不得为文明之真主义”,在此意义上,“商务沿革,成为一种世界开化史”。1904年,中国人许家惺在跋中特别解释道,“是书西名The History of Commerce in Europe,日译原名欧洲商业开化史,专述欧洲各国商业之历史。以各商业国位置论,固在欧洲,然其势力所播,则遍及世界”,因此“不啻为世界商业史”。许氏最后提到,日本人读该书“愤其国不列于商史”,于是奋起改良工艺、振兴商业,他希望中国也应该有此一愤。①[英]器宾:《世界商业史》,[日]永田健助原译、许家惺重译,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1904年。外国史刺激国人奋起,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史亦激发国人明确自身地位。是年5月起,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连载《中国历代的大事》,后改名《中国史略》。他强调中国人要首先晓得三件大事:“中国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中国人在世界上算什么种族”,“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的”。②三爱:《中国历代的大事》,《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4年5月。
1905年,梁启超撰写《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认为广东“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鸡肋而已,但“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③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第57页。视角不同,意义迥异,在世界中定位中国或者其中一部分,逐渐成为一种时代关切。1907年,吴渊民摘译国内外史家之说编纂《史学通义》,旗帜鲜明提出读史之目的,“一言以蔽之曰,在明中国之位置而已”。这显然“非徒读本国史所可能也”,而需要“读东洋史,所以求明中国在东洋之位置也,读西洋史所以求明中国在世界之位置也”。④吴渊民:《史学通义》,《学报》第1号,1907年2月13日。11月,《北洋法政学报》刊出《中国纸币起源考》,认为中国纸币的历史“可谓世界经济史上最可注意之现象”,⑤《中国纸币起源考》,《北洋法政学报》第44期,1907年11月。该文转自《大同报》第2号。可算是一次具体的计较与努力。
在世界(史)中厘定中国(史)的位置,文明是最重要的视角和尺度。1907年,濑川秀雄在其专为中国学生翻译的《汉译西洋通史》中鼓舞中国人在“今世界趋势合东西文明为一”,“百般事业皆一新其面目,划一新时期”的大势下,变“亚细亚东部之支那”为“世界之支那”。⑥[日]濑川秀雄:《汉译西洋通史》,东京:富山房,1907年。濑川秀雄在另一版的序中更明确呼吁“熟读西洋史,览其文化发展之次序,国民隆替之状态,及欧美现时之大势,俾确知日本所处世界之位置也”。⑦[日]濑川秀雄:《西洋通史》,章起渭编译,傅运森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这样的意识对于相同境遇又更等而下之的中国人,有着很强的感染力。1908年,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编辑的《学海》在东京创刊,其序称“尝读世界文明史,谓吾黄河扬子江文明实为最古五大文明之一。文明者何,学而已。学者何,学为人而已。阅人而成时代,积人而成社会。……吾辈幸生是邦,应有舍我其谁气概,使后世修世界文明史者,大书特书谓吾由最古之黄河扬子江文明一跃而为最近之太平洋海文明”。⑧《学海序》,《学海》第1期,1908年2月。
连带起来的,是国人对于对外观念的反思和“世界”观念的呼吁。本多浅治郎的《西洋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作为高等教科参考通用书编译发行。中国的译者在序中说,“竞争为进步之母”,希望警醒国人争胜于世界。译者认为不论是闭关锁国时代的“以为吾国以外无世界,即有人类亦等夷狄”,还是甲午庚子以后慑于强变而“日事崇拜外人”都不可取。“排外既失睦邻之道,而媚外亦为蠹国之媒”,总之都是因为“于世界知识有所未谙,以无世界知识之国民,形成无世界知识之国家,而欲与世界列强同立于二十世纪竞争之舞台,宜其日受侮辱而未有艾也”。因此,在五洲交往紧密的时代,养成世界知识迫在眉睫,而“欲有世界知识,要非读西史不为功。盖史也者,研究人群之进化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也”。批判过去的中国史家只局限于一部,而“西史则求人群之真象,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之文野而观察之”,呼吁读者积极探求公理公例,养成世界知识,助力国家振兴。⑨[日]本多浅治郎:《西洋史》,百城书舍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1909年,《申报》为李提摩太《万国历史汇编》广告,称该书“譬黑夜之灯光,既导人避泥滓,且俾人遵循大路而至所欲至之室。中国昔为文明首出,今退居他国后,其必求日跻也明矣。而是书实开导中国左右世界之力,与万国同底太平也。予日望之矣”。①《书万国历史汇编后》,《申报》1909年1月14日第6版。这些著作虽非名世界史,却与“世界”观念紧密相连,不仅体现出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换关系,更强化了“世界”观念和“文明”视角给国人带来的压力与动力。
在以世界(史)厘定中国(史)的位置的大潮下,关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1902年,陈怀对多数著作“高标其大主义以示于人曰世界史”不以为然。他从追究世界之始终说起,在他看来:“世界特民之世界耳,故世界远矣大矣”,“欲举世界而析之而又析之,以至于其世至近,其界至小”。“世界者,积民而成者也”,而方志正是“纯乎其为民史者”。因此,他宣称“子言世界史,毋遽远证之古也,先观于今方志可矣”,“毋遽外征之五洲之大,环球之广也,先观之今方志所载之民事可矣,所谓其史至琐其史至简者也”。他认为“世界之事,又必自近之远,自细之巨”,方志最小,但“自一方以至于十而百而千而万,积至小之地以达之于其大,积至寡之民以达之于其众,而居然一世界史之主人翁矣”。②陈怀:《方志上》《方志下》,《新世界学报》第7期,1902年12月。陈氏之意,显然是不必舍近求远,与其高谈世界,不如从身边的方志做起。如果说这还只是达至世界的路径不同,章太炎则更进一步,他强调“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主张经是最初的历史,是不能废的,如果中国史可废,西洋史亦没有什么用处,③章太炎:《国故论衡》《经的大意》,《章太炎全集》第5、14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7、105页。则是强调中国史才是基准所在,不可舍本逐末。在文明力较量下厘定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是弱势、被动的一方,陈怀和章太炎的论述则更强调中国的先决和本体地位。
三、结语
清季十余年间,有关西方历史的著作,乘着日本的东风,源源不断被译介过来。在西洋史、万国史等名目之外,“世界史”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和主观性,引起国人持续的关注和讨论。面对西方以文明之名、依据国家实力排列世界次序,从而排除东洋于世界之外,以西洋史等同于世界史,近代日本人表示相当的认可和接纳,同时又强调世界史理应包括世界全体,并注重彼此联系。同处东亚、面临类似境遇、文明更为悠久的中国,延续日本人的界定和思路,在围绕“世界史”观念的讨论中,直逼中西文明力较量的根本问题,表现出传统大国面临前所未有变局的无奈、艰辛与坚韧。
或许正由于浸润了诸多理想与现实、称谓与内涵、现在与将来的矛盾纠缠,清季的“世界史”基本停留于观念和认知的层面,而未见具体实在的本土著述和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但相关的观念讨论十分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其后世界史学科的属性、定位和旨趣。更重要的是,由于“世界史”认知是中外交流冲突的时代产物,其影响也必然溢出学科之外,而有着更为深远的干系。
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世界”,历史成为归纳公例、探究世界公理从而指导现实、规划未来的工具,“世界”则是抵拒西方文明偏见、强烈要求占据一席之地的目标,后者深深的时代烙印尤其值得注意。“世界”观念在近代中国的重大影响,几乎都在“世界史”的问题上得到体现,而“世界史”这样一个具体的依托,又使得“世界”观念之于近代中国对外观念、自我定位和未来规划上的影响更加深入、实际和强化,二者相辅相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促使时人思考中国在世界的资格、位置和前途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既面临是否够资格进入世界的问题,也面临着其历史能否进入世界史的问题。作为新环境的“世界”,与由此激发出的新的有关“史”的观念结合而成的“世界史”,深深地拷问着中国是否具有文明的根本性问题,既让国人沮丧,也让国人奋发。就此而论,清季的“世界史”认知,对于中国而言,更多是一个关乎立国之本的思想史问题,而非一般性知识扩充的学科史问题,对于世界而言,则是能否超越一元化文明观、实现文明多样性的深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