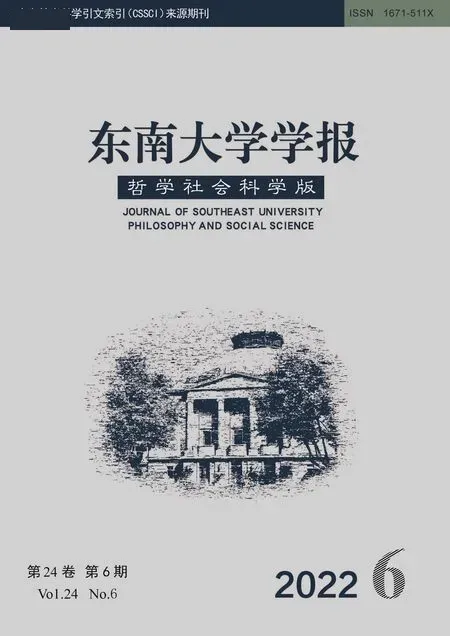维尔纳·松巴特的“精神”概念:帕森斯最初的理论社会学志趣
王 珩
(西北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海德堡大学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德文原稿于2018年末至2019年初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1)Uta Gerhardt,Parsons’,verschwundene Dissertation. Eine wahre Geschichte,Parsons, T.: 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3-24.。这份稿件此前被认为早已在辗转中丢失。帕森斯1924年前往欧洲,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功能主义人类学,1925年来到海德堡大学,开始用德文撰写关于维尔纳·松巴特和马克斯·韦伯的博士论文。1927年,他以先行提交的论文主体部分参加答辩,并以最优等成绩(summa cum laude)通过答辩。1928年末至1929年初,帕森斯将论文整理成为两篇英文稿件,发表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期刊》上(2)Talcott Parsons,“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28(36),pp. 641-661;1929(37),pp. 31-51.。这两篇英文稿在1929年被海德堡大学作为学位论文底稿接收,而之前的德文原稿就再也不曾露面。直到在哈佛大学帕森斯档案遗存中被重新发现之时,它已经在箱底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不为人知的岁月。
在今天看来,这篇标题为《松巴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概念》的论文,在各个方面都相当合乎人们对20世纪初博士论文的认识。它聚焦于整理和评述一种现有学说的主要内容。在简短的引论(第一章)和介绍研究现状(第二章)之后,论文分别以约40页的篇幅论述了松巴特(第三章)和韦伯(第四章)这两位当时在学界极富盛名的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而后以它们为基点,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做出简短的评述(第五章),最后以简要的对比和评价结束全文(第六章)。然而,这篇博士论文在平实的文面与合乎标准的体例之下,潜藏着充满张力和革新精神的思想。作为一篇对帕森斯博士论文密集的文本分析文章,本文致力于阐明它在理论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所代表的鲜明立场,提示它年轻的作者具有的内在力量和精彩纷呈的精神世界。
一、“一种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在社会学专业语境中提及“资本主义精神”,会自然地将它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工作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是维尔纳·松巴特的原创概念。围绕这个话题,两位先驱之间曾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松巴特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原则,即“精神”,看做每个时代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基础,精神生活和实践理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思路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论述的基本结构。韦伯在1904/05年写就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承认松巴特贡献的同时,也表达了不同的见解。韦伯注意到松巴特“精神”学说的伦理意涵,同时指出松巴特将这种动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出的行动者对外部环境良好适应的产物。他进而指出松巴特的方案所没有涉及到的现实才是他自己的研究兴趣的核心(3)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p. 46-48.。对此松巴特在1913年出版的《中产阶级——现代经济人的精神史》,以及诸如《奢侈与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相关研究当中,推出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发端的学说,并且在之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修订中,有意识地引导读者注意到他对“精神”概念的澄清。他表明自己拒绝对“精神”赋予任何玄学色彩,不回答“自然法则”这一类抽象问题,而一切历史的规律也必须回溯到人们具体的意识生活当中。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开篇最显眼的位置,松巴特隐晦地指出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容易误导人们产生具有玄学色彩的认识(4)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pp. 6-7.。
帕森斯1925年来到海德堡之后,很快将注意力投放到这两份不同的“资本主义精神”方案当中,心无旁骛地走上了属于自己的社会学道路。他在关于“资本主义”众说纷纭的学术和世俗观点中,发现了“精神”学说这种独特的方案。它一方面远离古典经济学所基于的功利主义原则,拒绝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做出一概而论的抽象预设。松巴特和韦伯都曾指出,经济活动并不总是具有理性的动机,并且“理性”的含义是丰富的。在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总体思维中,这种现实的多样性构成了独特的研究兴趣:一种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个体”,其发生应当被视为独一无二的过程。另一方面,放置在当时德国学界主流范式的背景中,“精神”学说同样有别于早期制度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模式。它将一种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再归因于其组织形式本身,而是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上,并且将它的组织形式反而看做后者的产物。帕森斯注重“精神”理论包含的能动性视角,认为它不能被看做社会现实的附属物。相反,精神构成了人们经济行为的框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了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就是资本主义时期”(5)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29.。
帕森斯论文的第二章综述部分介绍了经济学历史学派中有代表性的作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和体制的研究。这一章的行文方式大约是这样的:某作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如下基本观点,其中某些见解给我们带来了新颖的认识。然而,这种学说归根结底不能被看做充分界定了经济生活的本质范畴,因为它只涉及某种“外在的特征”,而完全没有包含任何“精神”的要素。这种露骨的表述体现出这位青年学者的辨别和否定意识。他毫不含糊地澄清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志趣,以及自己对什么事情不感兴趣。这让我们回过头来看清他在只有两页篇幅的简短引论中表明的基本立场。帕森斯的工作并不寻求完备地涉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所有理论方案,因为这全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进一步指出,自己甚至不关心论文是否能够得出一个恰当的“资本主义”概念。他所关心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个议题当中如何包含了“一种重要的东西”,并追问它的具体内容(6)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2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他优先选择讨论这个话题,即在彼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中,“资本主义”概念最容易为我们呈现出什么是“精神”的实质。
二、松巴特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立场
“精神”的意涵在其可以追溯到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的意义上,具有三个层面。首先,它最常见的意义指的是一种意识的状态和它所包含的精神气质;其次,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构造,它以自身作为媒介,确立自身存在的基础,并依靠其自为的性质维系自身与总体现实的关联;最后,它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将自身客观化,成为一个实现的过程。松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学说在构造上合乎上述精神概念在经典意义上的结构,它同样具有三个层面:意识层面的“思想品质”(Gesinnung)、自我意识层面的“组织”(Organisation)和作为实现过程的“技术”(Technik)(7)Werner Sombart,Die prinzipielle Eigenart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Werner Sombart,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Band I,1925,pp. 1-26.。与彼时常见的研究范式将经济体制的组织形式作为客观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相比,松巴特理论的显著特点在于它的思辨性,他试图“让经济生活成为一种活的东西”(8)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39.。松巴特将这种意图表述为“不要破坏了维系经济生活的活性的精神纽带,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包含一切的力量呈现出来”(9)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Erster Band: 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2. Aufl.,1916,p. 24.。这种“发生系统论”观点有别于将社会现实看做自然或者可类比于自然的客观过程的见解。对社会现实的研究在松巴特(与马克斯·韦伯共享)的观念中被看做历史的科学。世界呈现为一个由内而外的现实,行动者在历史中不仅顺应潮流和听从命运的安排,他的行动也在从内部塑造着历史的形态。就经济生活而言,它所呈现的组织形式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核。而作为“历史的个体”,它的法则也仅仅适用于系统内部。经济体制的生命力是由行动的力量维持的,一旦精神的内核崩塌,系统就无法继续维持自身,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体”,即不可拆分之物。松巴特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社会具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形态,而随着其精神的消散,它也将无可挽回地消亡,并且不会再次重演(10)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XIII.。
在松巴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经济史中的特殊地位是由它的精神气质决定的。精神气质体现为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维度:它的目标设置(Zwecksetzung)和它的经营方式(Wirtschaftsführung)。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两个维度上不同的表现,松巴特发展出一套西方经济制度的发展阶段理论。前资本主义经济,即土地私有经济和手工业经济阶段,经济活动原则上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为导向,以“传统”的方式运行,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则以“盈利”为目标,遵照“理性”的要求运行(11)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41-45.。
这种传统与现代生产方式的二分法,构成彼时经济史和社会学者共享的知识背景。然而,松巴特在这里仍然展现了他细腻的用心。他说:“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生活中一切操心和辛劳都围绕着活生生的人。”(12)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Erster Band: 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2. Aufl.,1916,p. 31.作为传统经济原动力的“需求”,不仅意味着个体行动的具体动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淀在风俗和习惯之中,被群体赋予规范性意义。换言之,“满足需求”成为经济生活的制度化目标,而“人的需求”脱离了具体的人,成为主导人们生活的原则性力量。它在生活世界中塑造了一种规范性意识,成为被个体所内化的“精神需求”,我们可以用直观的例子说明这种观点。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各种时间表和周期性当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节律既是“自然”,又不是。它们在人们的实践意识中显现为自然或本性的要求:自然要求人们在春夏季节耕种,而到了生育年龄就需要嫁娶和繁衍后代。然而这些依托“自然”概念的规范性意识,事实上包含着更多对当事的个体而言难以认识到的抽象的“人的需求”:前者比如统治者对食物储备作为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关注,后者比如长辈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而在意识中产生对后代更加热切的精神需要。在这种观点中,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就显得不再如“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奔忙”那般单纯。
相较于韦伯,松巴特眼中的传统生活更加富有“精神”的意涵。在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中,传统主义的行动策略是被无意识动机所占据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立面。《新教伦理》提及的在提高计件工资的诱惑面前反而降低生产效率的劳工和永远只会依靠习惯从不改进做事方式的德国和波兰姑娘,是缺乏“精神”要素的传统生产方式的代表。而对于松巴特来说,传统主义本身构成一个“精神”的问题,以满足需求为导向的生活基于人们对自身的需求在观念中的认识。松巴特通过揭示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对贵族式生活的“需求”,以及平民阶级对生产物质资料的相应“需求”,说明了等级制度的运作方式,也间接说明了这种制度内在的稳定性的根源:生活建立在朴素的“持存”概念之上。人们并非总是处在物资匮乏当中,却一直处在精神上的物资匮乏当中。
松巴特对旧时代的经济社会生活做出了合乎其本质的描述。他的经济史研究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寻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雏形,以及能够代表其“精神”的社会群体。与马克斯·韦伯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与传统经济之间在逻辑上的断裂不同,松巴特孜孜不倦地寻找两者之间具有连续性的线索(13)Klaus Lichtblau,Johannes Weiß,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Geist“ des Kapitalismus,Wiesbaden,Springer VS,2016,p. 18.。另一方面,在传统经济作为“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比照下,潜藏于其中的“精神”要素呈现为对人类本性的要求史无前例的背离。松巴特眼中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带有一种“自然的芳香”(14)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42.。“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人,就是自然的人,是如上帝所创造出的那样的人。”相反,现代社会的经济人是“完全颠倒的”(15)Werner Sombart,Der Bourgeois.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menschen,Leipzig und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13,p. 11.。在对这一部分简短的总结中,帕森斯暗示这个到目前为止运转良好的理论体系即将面临一场灾祸,这种自带芳香的朴素的自然观念正散发着浓郁的不纯正的气息。他用Aroma这个词的双关意(芳香和香精)暗示了它人造物的属性。领主、地主和家长用自己生活的困境编织而成的网,造就了无所不在的统治秩序的整体。这也是为什么相应的被统治阶级——武士、农奴和小孩,在古德语中都用同一个词(Knecht)来表达的原因。这些旧时代社会生活的真相,恰恰是松巴特的理论带给我们的重要认识,而不是他应当用“自然”的概念去试图文饰和掩盖的事情。
三、实践意识的朴素同一性的瓦解
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在松巴特看来在于(目标设置上的)盈利原则和(经营方式上的)理性主义,“精神”的概念要求它们是彼此相应的。在传统经济生活中,这种同一性体现为“人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和调节经济行为的主要机制。而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经济行为与人的需求脱钩,目标设置和经营方式的统一必须在原初同一性已然瓦解的实践意识中重新建立起来。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其核心任务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发生。
松巴特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位是“企业”,其不同于以“个人”为单位的传统经济的关键性质在于“劳资分离”。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生产资料不再由劳动者而是由少数资本家所掌握,而占有资本意味着掌握设置目标的权限。相比之下,无产者只能通过形式上自由的契约进入生产关系当中。其二,劳资分离带来了某种特定的分工,即管理工作与生产操作的分离,它伴随着企业运营各个环节上的专门化进程而逐渐加深(16)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43-44.。松巴特发现——这也是他理论的关键阶段——上述的两个劳资分离的维度分别在自身当中实现一种客观化和匿名化的进程。后者,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愈加依赖科层制的结构和功能,而逐渐脱离(在早期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家的个人权威。前者,企业的目标设置也越来越多地听命于资本的利益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企业遵照它的本质,发展成为一种愈加务实的、以盈利为固有目标的抽象统一体。它所根植于的并与之相应的社会现实就是“市场”。市场抹消了一切存在者“质”的差别,将它们换算成可以用“数量”表达的普遍形式(17)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Erster Band: 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2. Aufl.,1916,p. 321.。
行动与对象的同一性在传统社会的语境中呈现为生活的两极性,它反映在早期社会学典型的思维方式当中:现实既与主观行动相关联同时又是客观的。松巴特对这一类社会现实的内在逻辑有敏锐的洞察力。在传统经济生活中,他揭示了“人的需求”在社会关系中被客体化而产生普遍和制度化的约束力,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资本”就属于这个关键的环节。它是企业在行动中所采取的“务实取向的基础”,代表一种行动的逻辑,而不是对象物的概念(18)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45.。资本没有“自然”的属性。“想让资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这种看法纯粹是一种玄学。”(19)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7.资本增殖的“欲望”从根本上必须被理解为经济系统内部相互关联的目的性和手段目的理性的产物。对于松巴特而言,“精神”是行动者的精神——在劳资分离的背景下它仅仅是指企业家的精神,并且只有行动者的精神才是能够解释体制创造性的根源。但同时,这种“精神”与它在之前所有经济制度中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让企业的目标设置和经营方式呈现出在外部条件面前的自我强制。松巴特意图在资本主义精神当中呈现这种两极性,他解释一种为行动主体所持有的精神,它的核心特征在于受到客观力量的决定,并且自行开始遵从客观的逻辑。
虽然资本主义精神已不复有自然的属性,但它通过模仿自然来重构自身:重要的是构建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同一性,而这一过程又建立在行动主体与自身的原初同一性之上。松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析实质上就是在阐明这两个问题。对于后者,“企业家”(人格化的主体)将自身等同于以行动原则定义的抽象存在,即“企业”。企业家以自己全身心的付出维护企业的利益,由内而外地贯彻以盈利为目标的理性化经营方式,并以此获得主客观现实的同一性:主观等于客观,因为主观成为客观——生活就是一部记录盈亏的账册。这种特质被松巴特看做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创造性”(从内部产生的实现自身的力量)。对于前者,企业作为行动者不是简单地面对一个既定的外在现实,而是它自身在行动中造就了一种系统化的现实。行动造就的现实完美地合乎行动的内在本性,让行动在其中得以源源不断地实现和再生产自身的原则。松巴特指出,这个在以盈利为原则的行动中被创造出的世界,与自然生成的生活世界相比,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倒置。他用“财富”和“权力”在因果关系上的反转来揭示这种系统化现实的逻辑。权力不再(如传统社会那样)是获得财富的先决条件,相反,有能力生产财富的人同时可以从中生产出权力(20)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46-48.。
如果上述的两种同一性构造是“精神”概念的全部真相,松巴特的理论就是无可挑剔的。它令人疑惑的地方在于这种两极性在行动者主观世界中的统一。为什么企业家能够做到全身心地为客观的利益服务,甚至为此不惜过上一种压榨自己的生活?韦伯指出这种对待自己的残忍方式从自然理性的角度看显然是非理性的(21)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 54.,松巴特自己也指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具有一种本身不合目的性的“任意的”性质(22)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29.。诚然,这种精神被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造就了作为现代西方文明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但这种动机却不能因此从它造就出的现实中获得根据。恰恰相反,它如何扎根于现实当中,面对现实的要求,才是“精神”的概念真正必须关注的事情。
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行动者令人费解的主观动机,松巴特对比了企业家从资本主义早期到成熟时期具有的不同面相。它从起初充满幻想和冒险冲动、被攫取和征服的欲望所驱使的海盗精神,逐渐转向公务人员在经济管理中日渐成熟的对生产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最后演变为企业家取代一切世俗生活追求的客观化盈利取向。与海盗的冒险精神和公务人员的务实精神相比,企业家追逐利益的原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反而丝毫不以对现实的兴趣和关注为前提。“如果想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就必须对企业的兴隆怀有欲求,无论这种欲求最初是被对权力的追逐、对利润的贪求、抑或大干一场的冲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所驱使。而企业的兴隆事实上单纯意味着获利。”(23)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0.松巴特指出,正是因为这种“欲望”脱离了与现实的原始关联,它才获得了一种原则性地位和永无止境的性质。这是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理性的盈利目标”的本质特征,它不同于以往所有时代人们对利益非理性的追逐。
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体制让个体必须完全凭借自己的行动为自己负责,这也让个体彻底暴露在充满与之对立力量的周遭环境当中。个体与带有敌意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模式,也就是竞争,成为私有经济的精神基础。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和创造力也正来源于此。获利的动机作为经济生活的目标,与生存的危机感关联在一起,上升为一种原则和精神的需要:企业必须不断地努力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这使得企业的目标获得了“永无止境”和“以自身为目的”的性质——这正是“持存”这个在西方社会诞生于近代的思想给人们的实践理性带来的新的内容(24)Dieter Henrich,Die Grundstruktur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H. Ebeling (Hrsg.),Subjektivität und Selbsterhaltung,Frankfurt a. M.,Suhrkamp,1976,pp. 97-121.。它们的结果是我们都熟悉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理性的盈利目标中被客体化。人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发生了倒置,经济活动不再从属于人的需求,反而是人成为它的手段(25)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1.。
我们看到,松巴特将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对比,以期得出后者的本质特征。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诉诸一种霍布斯式的社会哲学。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脱离人的需求的“客观化”盈利目标之上。而支撑这种目标的力量,正是人们在泛化的敌对当中保全自身的原始本能。它脱离传统经济活动所回应的一切具体需求,作为抽象的“持存”动机塑造了人们的实践意识,成为制度化的“精神”需求。松巴特解释传统经济的图式此刻完美地在他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再现出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创造力”,推动它发展并赋予它活力的那股积极的力量,正是丛林法则给人们带来的难以抗拒的恐惧,以及人们出自本能的逃生欲望。就这一点而言,松巴特甚至比霍布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霍布斯尚且认为,人类社会的归宿在于其终将走出自然状态,而松巴特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建立在运转良好的自然状态当中。这种精神在最极端的意义上接受和认同对它产生强制的外在力量,并且将它转化为从自身出发对自身的强迫。帕森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这个“企业家精神”学说一方面强调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强调目标的客观化和行动受强迫的性质,而两者在松巴特所依据的经验现实中表现为完美的因果关系。
与企业家在为生存所迫的斗争中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的行动者精神相应,资本主义精神的另一半在松巴特的眼中合乎逻辑地体现在市民阶层(劳动者)节俭自律的受动者精神当中。这一“精神”的核心品质,即“适应”的意愿和能力,将普通人的生活塑造成为有原则的“经营”和“商业道德”。市民阶层管理自己生活的方式,与企业家管理企业的方式是相仿的。市民的生活同样以收支平衡为原则,支出永远不得大于收入。这种节俭不再被看做下层民众的窘迫状态,而是被视为遵从理性原则的生活方式。节俭的道德的适用范围从金钱拓展到时间,以至于生活中的一切对象。它最彻底的表述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篇关于“时间就是金钱”的教导。帕森斯特别指出,这篇松巴特和韦伯都十分重视的著名文本在两人那里分别得到了不同的理解。富兰克林所宣扬的这种在字面上以“唯利是图”表述自身的生活方式,在韦伯眼中反而透露出浓厚的宗教式信念(26)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 33.。而在松巴特看来,这种美德仅仅是由生活经验造就的,是适应的产物。市民生活所贯彻的道德,在各个方面以对客观标准的“遵守”为核心理念:诚信意味着遵守诺言和契约。明晰性要求对生活的账目化管理,它在生产活动中又体现为行动严格遵照目的性和计划性,以既定目标作为唯一的取向。遵照这些原则构建出的生活,其本身成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关联性整体。它不再奉行除商业道德以外的任何道德,唯一衡量其价值的方式就是转换为收支。帕森斯指出,这种精神很容易退化为功利主义,人们不再追求美德,而只需要追求在行动中被看做具有美德(27)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2.。
毫无疑问,松巴特如实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鼎盛时期人们的精神气质——节制、耐劳、守信、规律、冷静、均衡,所有这些品质塑造了一个时代成功者的形象。然而,松巴特对于这些品质的由来和社会基础却持有类似婆罗门教的观点:它体现为一种社会分工的原则。企业家是这个社会整体现实的头和躯干,而市民阶层相当于社会的手和脚。帕森斯这样表述松巴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创造性毫无疑问在于企业家,……而市民阶层造就了一种有序的现实,让企业家得以在其中施展。”这个整体性现实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莫过于市民阶层的生活同样被塑造为(将自己当作自己的企业,一切以收支来衡量,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经营”,并且它同样呈现出不以人的自然需求为依据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性质,帕森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市民化”(28)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3.。诡异的是,统治者(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内化了被统治者的道德,自己成为自己设置出的统治原则的对象。帕森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市民化”带来了“市民精神的客观化”。企业家反过来将企业设置为他的主人,赋予它人格和人的品质。“企业家精神”转化为“企业精神”,后者意味着进取精神和创造力,前者必须节俭和操劳。
四、帕森斯对松巴特“精神”学说的接纳和批判
从帕森斯的博士论文对松巴特“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份早年的研究在其日后的理论工作中留下的印记。首先,松巴特的“精神”概念扎根于行动中的主客同一性思想,与观念论哲学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意识、思维和气质,精神不仅意味着文化现象,它的社会学意义更多在于行动的同一性诉求在系统中的展开。帕森斯日后的理论构建呼应了松巴特以“精神”为核心的系统概念。行动与世界建立关联的逻辑环节构成了帕森斯“系统”理论的核心要素。其次,帕森斯分享着早期德国社会学通行的理念,在社会现实作为行动产物的意义上,赋予其独特的现实性。社会学关注人们的主观意识,比如经济行为的动机、目标设置、对生活方式的营造、道德观念以及宗教信念,正是由于他严肃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在于探究客观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源,帕森斯之后五十余年的社会学生涯坚守着这种思想传统,并且在与主导美国学界的量化研究不同的意义上倡导将社会学视为严格科学的理念。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帕森斯的理论工作关于社会现实的整体性观点。他在十年之后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引论部分就澄清了自己将研究对象视为不可拆分的有机体的基本立场(29)Talcot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8,p. 47.。这种观点极易在社会学创立初期的学者当中得到回应,而放置在作者的生年,却逐渐表现出与时代的格格不入。非但如此,帕森斯要求自己的理论工作呈现出对社会总体现实的描述和解释。这种学术风格无论是在内容、形式还是(不合时宜的)篇幅上,都与维尔纳·松巴特的工作遥相呼应。
然而,即便对前辈的工作充满敬意和钦佩,帕森斯也在对资本主义精神内涵的认识上与松巴特保持着清晰的距离。文面上对学术权威必要的隐晦,合乎体例和期望的表达,以及作为非母语者在修辞能力上的限制,都没有能够阻碍这位时年23岁的青年学者呈现出他鲜明的立场。松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是既定的生产方式“被客体化”的产物(30)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4.。他将生产者看做棍棒底下的孝子,无论是市民还是企业家,其生活都不再有丝毫内在的成分,道德意识的唯一表征是顺从,以此完美地遵从压抑自我适应规则的价值观。帕森斯揭示了松巴特关于“企业家和市民精神”的学说在规范性意识的问题上所包含的问题。现代社会思想正是以人们发现和揭露这种以“顺从”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的虚伪性质为开端,它构成了康德、黑格尔一流的伦理学说的原始动机。
帕森斯的批评呼应了马克斯·韦伯对他与松巴特在理论志趣上的差异做出的辨别。韦伯在《新教伦理》中隐晦而尖锐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与手工业生产保留在个体身体记忆中的劳动方式形成反差的“劳动的客体化”进程,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那种日后社会学所熟悉的惯习场域相互嵌套的解释图式,并不适用于韦伯所关注的特定历史时期。这种主客同一性的起源才是韦伯眼中“资本主义”这个议题中所包含的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松巴特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关注引向经济理性主义(ökonomischer Rationalismus),亦即依靠精密的计算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韦伯指出,他将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理性”意涵置换为一个“合理化进程”(Rationalisierungsprozess),也就是在现实因素面前对自身做出的调适。松巴特的视角催生出一种精妙通透、影响深远且毫无疑问的观点。看穿这种观点的欺骗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该理论的根本误区。松巴特区分需求取向和盈利取向的经济活动。韦伯指出,如果“需求”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需求,那么需求经济与传统主义经济就是相对应的。但如果将“需求”的概念回溯到它在心理上的普遍意涵,那么所有在形式上采取现代企业组织,而事实上被自身的生存所驱使的经营行为,本质上也是需求取向的。韦伯审慎地提醒读者将被松巴特归入盈利取向的某些企业从这个归类中分离出来。他以此隐晦地指出,将求生存的需求看做企业盈利导向的动机的观点没有对两者做出实质上的区分(31)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p. 46-49.。
帕森斯在这一章的总结部分指出了松巴特的“精神”学说具有欺骗性的根源。“松巴特将他的研究工作投入到现代资本主义当中,并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研究了当今西方世界经济社会秩序的历史发展进程,从中总结出在其间产生的欧洲中世纪封建体制,并以此作为对立面,反过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独特性。”(32)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63.换言之,松巴特始终站在一个中世纪农民的立场上批判现代社会。他试图依靠传统生活中人们的实践理性建立在需求调节上的朴素同一性,为自己的批判立场构建基础。然而他自己的学说本身,却已经揭示了传统主义并不是精神自然发展的产物。松巴特用“抽象的目的”来表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理性的特征,这一批评却在同样的意义上适用于传统经济,并且根源于传统社会的结构当中。行动动机系统地建立在外在要求之上,服务于制度化的他人的需求,精神在其中无法获知自身的意义。正如松巴特所揭示的那样,企业家的主导性地位的前身正是领主的权力,而劳动者从屈从于领主的需求,到开始自主地为市场的需求操劳,也就此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松巴特没有认识到从中世纪传统社会到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或包含某种质的飞跃,从中会有全新的东西产生,并塑造了从未有过的现实的形态。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接受和理解现代社会对个体的要求,也就是帕森斯在引论中提及并且一直在寻找的那种“重要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无论在哪个时代,精神都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然而到了现代,它却开始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的原因。
有一种观点可以看似合乎情理地维护松巴特的精神学说。松巴特或许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让我们从根本上不可能具备认识到“精神”概念实质的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精神才会显露出它的意义。松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的写作动机建立在作者早年与马克思的学说深厚的渊源之上,其学术生涯的特定时期有充足的理由持有这种立场。帕森斯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讨论了这个议题。在他看来,松巴特可能赞同,并且自己或许具有这样的直觉,但他同样没有领会“精神”在马克思的思想背景中的含义。帕森斯指出,马克思的学术观点包含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基本方面,而松巴特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渊源恰恰体现在,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认同后者的立场。其一,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是由“生产力”这种客观力量推动的,而松巴特眼中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就在于它会在人们的实践意识中作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呈现出来。其二,马克思同样积极地认同行动者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个体并不因为生活在依照客观规律发展的历史中,就失去了参与历史的能力。新的社会形式是必然会到来的,并且在同样的意义上,它也是在人们不懈的斗争中被带来的。帕森斯指出,在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面前,唯意志论的思维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同样体现出强大的力量(33)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61.。松巴特赞赏马克思独特的理论贡献:他发现了生产关系背后活生生的人。而松巴特自己对企业家和市民的精神的关注也印证了他对此的认同。
松巴特认为他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可以有效地缓和马克思的思想中客观力量的决定性和主观力量的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他意图揭示主观的行动(企业家精神)如何通过自身构成了客观现实的基础,从而有效地中和了唯物史观在形式上必然具有的外在决定论。他在主观精神与客观历史规律之间构筑了一座“因果关系”的桥梁,却恰恰因此拆毁了它们之间原本固有的“辩证关系”的纽带。事实上,马克思的学说毫无保留地同时赋予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独特的现实性,并不试图通过将它们相互还原来缓和两者的矛盾。正是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中,它们获得了统一。松巴特通过中和唯物史观的意义来塑造“精神”的概念,却因此反而陷入了深刻的教条主义当中,从中得出了一种彻底被物质现实所决定的精神概念。松巴特在对待“矛盾”的问题上的中世纪立场(消灭矛盾)和他对辩证思想的不解,造就了他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历史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现实的关注,构成了他在学术道路上前进的动力。然而,站在更高的“发展”的视角上,他也辨认出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并从周遭世界矛盾深重的状况中获得了对未来乐观的态度。松巴特将资本主义时代看做一种历史进程中短暂的病态,他得出的结论同样带有深厚的中世纪色彩:“我们只能绕过和背离它,来寻求一条拯救之路。”(34)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XXI.
帕森斯最后总结道,在“仅仅作为对我们时代的经济生活的呈现”的意义上,我们要“承认”松巴特的贡献。他在表述中自如地运用着隐藏和彰显的辩证法,“承认”透露出主观立场与对象在表面的一致之下所掩盖的深刻对立,同时也表达了将对立面包含在自在与沉默当中的自知。“我们相信,松巴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完成了将马克思带给他的灵感发展为理论的工作。”(35)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62.松巴特没有做到这件他有理由相信的事情,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走上这条道路。松巴特的贡献在于“描述”,而作为一种关于精神的(合乎个体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他的学说早已崩塌。松巴特对“精神”概念的理解与这一理论传统中几位开拓者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没有共同点。
五、新的契机
帕森斯在社会学理论教科书中通常以一个死板守旧的老头的形象出现。虽然他的学说对现当代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人们还是宁愿将他归于经典理论家。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将他看做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守护者中的最后一位。帕森斯的理论工作方式带有浓厚的旧时代遗风,他具有非凡的雄心和强硬的作风,将理论社会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来操作,并且诉求对总体社会现实的把握和理解能力。这种惊人的思维方式戏剧性地将他同时放置在美国社会学界两股对立的主流思潮(人文主义和量化研究)的对立面上。还未等到他去世,他的同行和学生就埋葬了这股传统,认同它的人今天已经是真正的少数派。
在人们对帕森斯学说的总体观感中,他被看做社会学保守思想的大本营。帕森斯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可以用来彰显这种思想的脉络。至1937年完成并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被人们理解为以“社会秩序是怎样实现的”这个霍布斯式的问题为出发点,并且由“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伦理动机所推动(36)Alvin W. 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pp. 335-336.。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波理论思潮,即在这个意义上将自己置于帕森斯思想的对立面。他们倡导不要忽略了(相较于理性)在现实中具有更多决定性作用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广泛的冲突。这些视角都对“秩序的维持”的理论动机投以怀疑的目光。帕森斯的理论方案被看做康德式先验主体论的社会学版本:社会现实必然地建立在人们先验的规范性意识当中,它是一切社会行动的基础。在20世纪中叶各类解放运动开始兴起的美国,持有这类命题就无法避免被看做一个守旧的道学家。1951年出版的《社会系统》所开创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和帕森斯自己的姓名永远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部关于总体性社会现实的逻辑结构的理论方案,它关注系统建构的先验范畴和它在经验世界中的自我维持过程。依照之前的那种观点,这种理论不仅关注秩序的形成,而且将一切社会现实的要素全部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秩序概念当中,这种做法让人们感到窒息和本能的抵触。
帕森斯的博士论文德文原稿(1925/26)的现身带来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这位先驱走上社会学道路的原始动机。由这种(此前仅为少数学者私下持有的)兴趣所推动的理论工作,在近几年来事实上已经逐渐展开。人们开始理解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中包含着一种隐晦的“最终之物”,它既不能被还原为“外在条件的决定性力量”,也不能被等同于“行动的目的论纲领”,并且同样不能从“规范性意识中”得到充分的理解。人们认识到它超越经验意识的本质(37)Jens Greve,Talcott Parson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The Social System,Senge, K.,Schützeichel R. (Hrsg.), Hauptwerke der Emotionssoziologie,Wiesbaden,Springer VS,2013,p. 256.,并且开始尝试用前所未有的方法来界定它。笔者在此简要地讨论两个有代表性的方案。
哈罗德·温策尔(Harald Wenzel)早先关于帕森斯行动理论的论著包含他对其中一股强大的内在力量参与的直觉(38)Harald Wenzel,Die Ordnung des Handelns. Talcott Parsons’ Theorie des allgemeinen Handlungssystems,Frankfurt a. M.,Suhrkamp,1990.。这种直觉与帕森斯早年对“精神”概念的执着是相应的。在之后的研究中,温策尔发现帕森斯前后期的思想之间呈现出一种断裂:后期的系统理论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性来源的理解,已经脱离早先秩序理论的思维,它诉诸一种源自主体自身的凝聚力(39)Harald Wenzel,“Jenseits des Wertekonsensus. Die revolutionäre Transformation des Paradigmas sozialer Ordnung im Spätwerk von Talcott Parsons.”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2002(4),pp. 435-436.。然而,在温策尔(以及当代社会学者典型)的思维中,“规范性”在范畴上已然退化为纯粹的外在力量,因此他随即将约束主体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动的权限交付予“媒介”。这种解读可以被看做是对哈贝马斯提出的“精神作为媒介”理论的拓展(40)Jürgen Habermas,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Philosophie des Geistes“,Jürgen 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Frankfurt a. M.: Suhrkamp,1969,pp. 9-47.。这样一来,温策尔虽然认识到用保守主义思想来衡量帕森斯的理论有缺陷,却仍然预设它作为其早期工作的动机,这让他自己重构帕森斯整个学术生涯连贯思路的尝试反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汉斯·约阿斯(Hans Joas)研究了帕森斯晚年对一些本源问题的探寻,并指出其(极少引起读者注意的)关于宗教的思考事实上贯穿他所有时期的理论工作(41)Hans Joas,“Das Leben als Gabe. Die Religionssoziologie im Spätwerk von Talcott Parsons”,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2002(4),pp. 505-515.。帕森斯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修行生活以及他们关于生死的意识保持着联系,他也从未让实践本身过多远离它的本源。这种理论思维对于约阿斯本人来说,只需推己及人就很容易理解: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价值(Wert)在根本上与行动和世界的关联(Weltbindung),亦即创造性有关(42)Hans Joas,Die Entstehung der Werte,Frankfurt a. M.,Suhrkamp,1996.,它要回答的远不止“规范性意识怎样促成了秩序的产生”这一类的世俗问题。他就此提出帕森斯将秩序的稳定性看做分析的参照系而并非自身价值的谨慎观点。套用哲学上常用的对立范畴,人们一直认为帕森斯关注“有效性”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一直在探寻“发生”这件奇妙的事情。从这里入手可以进一步揭示帕森斯的思想不为人知的深度。约阿斯在自己早期对行动理论的研究中,就将帕森斯的论题作为其揭示行动创造性维度的理论工作的开端(43)Hans Joas,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Frankfurt a. M.,Suhrkamp,1992.。他却没有从帕森斯本人的方案中着手做这件事情,而是将任务留给了我们。
帕森斯这篇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博士论文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线索,他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澄清了自己对松巴特建立在“精神”概念基础上的经济史学说的见解。后者致力于说明一种现实秩序的可能性和它在历史中的形成过程。《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最初的版本即在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对“秩序”问题的关切(44)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Erster Band: Die Genesis des Kapitalismus,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 Aufl.,1902. p. 3.。松巴特以同一性构造为出发点,发展出涵盖广泛社会现实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理论。这种“精神”的构造最终在他人的期望(传统社会)和客观现实的要求(现代社会)中找到自身的根据。这印证了社会学在当代持有的“社会同一性”的出发点,并抹杀了行动从自身出发的同一性诉求(作为“理性”的原初含义)的现实意义。帕森斯在他的博士论文讨论松巴特的部分,隐晦地对这种总体思路表达了无可争议的拒斥态度,他对被外在现实所决定的精神概念没有任何兴趣。《社会行动的结构》讨论松巴特的篇幅萎缩到只有讨论韦伯篇幅的四十分之一,这一残酷的现实印证了帕森斯最初的动机和志趣。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我们再要从“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论题出发来理解帕森斯的学说,就不得不有所顾忌。这种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行动的结构》的途径。虽然它有令人望而生畏的篇幅,但仍然很容易辨认出,直到1937年《社会行动的结构》出版完成,帕森斯一直在关注一件事情。他的博士论文所展现出的强大的集中力,这一次蔓延到长达十年的工作周期中,所有的阶段性成果都指向这种唯一的关切,并且它和之前的博士论文具有深刻的连续性。用帕森斯自己的话说,这些工作是关于“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学成分”。然而它们背后的“问题”,那种他一直在寻找的“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却仍然值得我们去追究。它让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进而更加完整地认识到这位作者鲜活的思想。这篇论文致力于揭开这样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