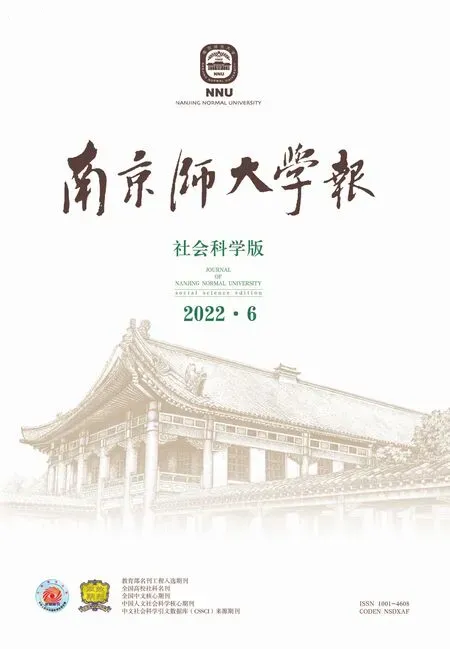古汉语全称量化用法析义
刘梁剑
汉语的量词表达极为丰富。表全称,可用“所有”“一切”“全部”“任一”等,古汉语则有“皆”“凡”“遍”“周”“尽”“悉”“兼”“各”“每”等。表存在,可用“有些”“某些”“若干”等,古汉语则有“或”“有”等。在早期的汉语逻辑学文献中,英语中表全称的“all”曾被翻译为“全数”、“皆”(艾约瑟《辨学启蒙》,1886年)、“凡”(《辨学启蒙》;傅兰雅《理学须知》,1898年;严复《穆勒名学》,1903—1905年,及《名学浅说》,1909年):表存在的“some”则被译为“分数”、“有数间”(《辨学启蒙》)、“有”、“某”(《理学须知》;《穆勒名学》,《名学浅说》)。
以下,考察古汉语全称量词的量化用法。
一、 全称、存在及其他
古汉语常用的量词有“皆”“兼”“或”“多”“莫”“无”等。(1)古汉语的量词自然不尽于此。可参见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London and Malmoe:Curzon Press,1981,第二章。该章关于量词用法的详尽讨论直接刺激了本文的思考。下引此书,若干中译参考了万群、邵琛欣等的译本(《古汉语语法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刊),谨致谢忱。大致可归入三类:全称量词,存在量词,广义量词。
全称量词有“每”“兼”“皆”“遍”“泛”“周”“各”等。试举例如下:
“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下》)
“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
“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
“周爱人。”(《墨子·小取》)
“物各从其类。”(《荀子·劝学》)
“或”是典型的存在量词。如:
“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孟子·梁惠王上》)
“莫”“无”是表否定的全称量词。“多”则可归入广义量词,它既非全称量词,又有别于存在量词。如:
“各顾其后,莫有斗心。”(《左传·成公十六年》)
“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史记·高帝本纪》)
“诸侯多有谋伐寡人者。”(《孟子·梁惠王下》)
“多”也可以表示存在量化,但用法有别于存在量词“或”。“诸侯多有谋伐寡人者。”(《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谋伐寡人的诸侯超过二人。(2)《马氏文通》举例:“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释曰:“‘多’者,观者中不止一人也。”(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5页)不妨用集合的方式加以刻画:多x(A,B)↔|A∩B|>2。其中,A表示“x是诸侯”,B表示“x是谋伐寡人者”,A∩B表示A与B的交集,|A∩B|表示此交集的元素个数。
“诸侯多有谋伐寡人者”不同于“多数诸侯谋伐寡人”。后者可以形式化为:多数x(A,B)↔|A|>|A∩B|>|A∩¬B|>0。其中,¬B表示“x不是谋伐寡人者”。也许可以想到另一种可能的表达式:多数x(A,B)↔|A|>|A∩B|>|A-B|。其中,A-B表示由诸侯所组成的集合A与由谋伐寡人者所组成的集合B的差集。(3)张晓君即把“大多数人都有恋母情结”中的“大多数”的真值定义为:大多数E·(A,B)⟺|A∩B|>|A-B|(参见张晓君:《广义量词理论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页)。这一表示法,似乎预设了A>B。经语义解释之后,则是预设了谋伐寡人者都是诸侯,也就排斥了诸侯之外的人是谋伐寡人者的可能性。前面一种表达式没有比较A、B集合的大小,也就无此预设。
“莫”“无”表示否定的量化。“相人多矣,无如季相。”这是说,于所相多人中无人优于季相。“各顾其后,莫有斗心。”“莫”者,无人也。有意思的是,“莫”恰好与前面一句中的“各”形成对照。“各”者,所有人也。如果说,“各”为全称肯定量词,则不妨将“莫”称为全称否定量词,二者表示相反的质。如果将“各顾其后,莫有斗心”两句中主词“各”“莫”分别换质,可以得到以下表达相反意思的句子:“莫顾其后,各有斗心”。
我们也可以用集合的形式刻画全称否定量词。如,将“诸侯多有谋伐寡人者”中的“多”替换为“莫”,得到以下命题:“诸侯莫有谋伐寡人者。”可以形式化为:莫x(A,B)↔|A|=|A∩B|=0。各符号的定义如上。
处理广义量词“多”的技术也可以施之于存在量词与全称量词。如,“诸侯或有谋伐寡人者”可以形式化为:或x(A,B)↔|A∩B|>0。又如,“诸侯皆谋伐寡人”可以形式化为:皆x(A,B)↔|A|=|A∩B|≤|B|。如果“诸侯皆谋伐寡人”是一实然断定,即预设“诸侯”存在,则需要修正集合为:皆x(A,B)↔0<|A|=|A∩B|≤|B|。各符号的定义如上。
下面的考察聚焦于古汉语全称量词。
二、 位置和辖域
在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或英语中,量词一般居于名词之前并对之施以量化。易言之,量词以紧跟其后的名词为辖域。相形之下,古汉语的情形比较复杂。以上举诸例来看,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姑名之曰:顺辖、跳辖、逆辖。
跳辖,量词的辖域为“跳过”动词之后的名词。常见“量词+动词+名词”的句式中,量词用在动词之前,却对动词之后的名词起到量化作用。如:“兼爱天下之人”,“兼”辖“天下之人”;“遍爱人”,“遍”辖“人”;“泛爱万物”,“泛”辖“万物”;“周爱人”,“周”辖“人”。逆辖,量词紧随所辖名词之后。如:“万物皆备于我矣”,“皆”辖“万物”;“物各从其类”,“各”辖“物”。与跳辖与逆辖相对的是直辖(顺辖),此时量词紧居于所辖名词之前。如:“每事问”,“每”辖“事”。《马氏文通》已指出:“‘每’字概置于名先,‘各’字概置于其后,间或无名而单用。”(4)马建忠:《马氏文通》,第78页。直辖(顺辖)在现代汉语中为通则,于上述用例中却仅一见。何莫邪注意到,“诸”“群”“众”等表复数的量词也往往直接放在所修饰的名词之前。(5)C.Harbsmeier,“Language and logic”,in J.Needham(ed.),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7,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23.
综上,全称量词中,“兼”“遍”“泛”“周”为跳辖,“皆”“各”为逆辖,“每”为顺辖。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逻辑量词理论对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处理之后,量词的辖域从词项转为命题(带有空位的命题),直(顺)、跳、逆辖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就消失了。如:“每事问”“泛爱万物”“物各从其类”可以统一形式化为:∀x(Fx→Gx)。相应于“每事问”,Fx表示“x是事”(太庙之事),Gx表示“(孔子)问x”。(当然,Gx也可以改写为H(a,x),表示“a问x”。其中,a=孔子。)相应于“泛爱万物”,Fx表示“x是物”,Gx表示“(圣人)爱x”。(“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为《庄子·天下》述惠施学说。就其为社会道德政治理想而言,不妨把缺省的主词补充为“圣人”。)相应于“物各从其类”,Fx表示“x是物”,Gx表示“x从其类”。
三、 主体量化与客体量化
传统的演绎逻辑把命题分为四类,所谓A、E、I、O,即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特称否定。其中的“全称”“特称”从量上着想,更确切地说,从主词的量上着想,而在宾词方面没有量的表示。(6)金岳霖已指出这一点,并介绍了哈蜜敦(Hamilton)主张宾词也要有量的表示,并依此将命题分为八种(金岳霖:《逻辑》,《金岳霖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17页)。A命题,更完整的说法,应是全称主词肯定命题,E、I、O可类推。然而,何莫邪提醒我们注意,考察古汉语中的量词,不能不注意到“subject quantifier”和“object quantifier”之间的区别。(7)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49.考虑到所讨论的用例不限于传统演绎逻辑所处理的主宾式命题(形如“S是P”),我们且把“subject quantifier”“object quantifier”译为“主体量词”“客体量词”,而非“主词量词”“宾词量词”。
“皆”“各”为主体量词,即,“皆”“各”所量化的名词在语法上处于主词的位置,从语义上讲则是动作发出的主体。“物各从其类”,物都从其类;“万物皆备于我”,万物都为我所备。后一句为被动句。(8)《庄子·齐物论》:“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 何莫邪认为:“这句话里的‘皆’量化的是一个前置宾词(而古汉语中的‘各’显然从来没有这种用法)。”(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79)不过,依“万物皆备于我”之例,不妨将“万物皆照”理解为被动句“万物皆照(于日)”,如此,“皆”仍被理解为主体量词。此外,何莫邪所讲的“古汉语”主要是汉代之前的文言。如果“古汉语”的范围稍作拓展,可以找到以“各”量化宾词或客体的用例,如:“不可者,各厌其意。”(《史记·游侠列传》)各厌其意,满足每个人的意愿。马建忠释:“‘各’在宾次,而位先动字。”(马建忠:《马氏文通》,第79页)当然,这里的宾词“其意”并没有前置。“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则是主动句,“皆”量化主词“人”。(9)亚里士多德区分“每一个人都是白的”和“人是白的”,认为,“‘每一个’一词,并不使主词成为一个全称,而是对命题给以一种一般性”,因此,前者是“关于一个全称主词的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后者则非。(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0页)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解,“物皆从其类”的“皆”也具有将“物从其类”普遍化的意味。依此,“皆”作用于命题,而不是作用于作为主词的词项。存在量词“或”也是主体量词。“或百步而后止”,有些(士卒)向后逃了百步才停下来。
“兼”“每”“遍”“泛”“周”为客体量词,即,“兼”等所量化的名词在语法上处于宾词的位置,从语义上讲则是动作加诸其上的客体。“兼爱天下之人”,爱所有天下人;“每事问”,问每事;(10)钱穆:“祭事中礼乐仪式,乃及礼器所陈,孔子每事必问,若皆不知。”(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6页)“遍爱人”,爱一切人;“泛爱万物”,爱一切物;“周爱人”,爱所有人。《马氏文通》已指出“各”“每”分别位于主、宾次,从我们所讨论的量化角度则是分别量化主体、客体。《论语·公治长》:“盍各言尔志。”马释:“‘各言’者,‘每人言’也。‘各’字单用,而在主次。”(11)马建忠:《马氏文通》,第79页。《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马释:“‘每’合于‘事’,‘事’在宾次,而位先焉。”(12)马建忠:《马氏文通》,第79页。
依照传统演绎逻辑,可由A推出I。这是基于全称主词与特称主词之间的关系。那么,是否可能建构基于客体量化关系的逻辑推论?试建构以下推论:“兼爱人;楚人某,人也;故,爱楚人某。”“兼爱人”可表示为∀x(Fx→Gx)。其中,“Fx”表示“x是人”,“Gx”表示“爱x”。如果把“楚人某”视为“x”的一个值,则“爱楚人某”可以理解为∀x(Fx→Gx)的一个实例:x=楚人某,F楚人某→G楚人某。因此,可由“兼爱人”推出“爱楚人某”。
但是,能否由“兼爱人”推出“爱盗砳”呢?关键在于以下说法是否成立:“盗砳,人也”。换言之,如果“兼爱人”的量化表达式为∀x(Fx→Gx),那么,“盗砳”能否被视为“x”的一个值。对这一逻辑问题的回答,关涉到伦理学的相对性,或者说不同的伦理学预设(仿照蒯因“本体论的相对性”“本体论预设”等说法)。如从告子的角度看,“生之谓性”,盗砳,生而为人。从孔孟的角度看,一方面,盗砳,非人也;另一方面,盗砳,人也。孔孟讲人禽之辨。人皆有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盗砳,无恻隐之心;盗砳,非人也。这是就显性现实而言。易言之,“盗”标识了其“非人”的特性。另一方面,人皆有恻隐之心,盗亦有恻隐之心;盗砳,人也。这是就潜在可能而言。从施爱者的角度看,“盗砳,人也”提供了爱盗砳的合理性根据。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爱的力量,那么不妨说,通过“爱”,揭示了盗砳作为“人”的面向。爱,彰显了某个体隐于“盗”这一显性标识之下砳的“人”的存在可能。如果相信爱的转化力量,那么不妨说,爱盗砳的行为蕴含着激发砳的人性面向的可能,从而蕴含着将此个体的显性标识从“盗”转化为“人”的可能。就此而言,“爱盗砳”的行为竟然可能反过来证成从“兼爱人”推出“爱盗砳”的合理性。不妨做一类比:乔治娶了玛丽女王,玛丽女王是寡妇,但我们不能因此毫无歧义地说“乔治娶了寡妇”,因为正是乔治的“娶”使得玛丽女王从寡妇变成了有夫之妇。
“周爱人”“周乘马”在《墨子·小取》中的语境如下:“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也。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也。’”(13)王国维对此的解释:“此墨子自主张其兼爱说:‘爱人’指无人不爱,而‘不爱人’指不兼爱者,非指兼不爱者也。‘乘马’之例反是。乘马不待其人全乘于马上,然后谓之乘马。‘不乘马’必俟其下马后,方可谓之不乘马。此由一家之学说及一时之习惯立论,非纯由名学上观察者也。”(王国维:《周秦诸子之名学》,《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燕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21页)“乘马不待其人全乘于马上”,王国维此解似误。“周”之全称,施于客体即马,而非施于主体即乘马者。又,“一时之习惯”者,约定俗成者也。这里涉及“周爱人”“周乘马”与其否定形式之间的关系。寻绎《小取》之意,“爱人”与“乘马”表面相似,而深层逻辑则不同。“爱人”,省略了全称客体量词,实际上说的是“周爱人”;“乘马”,省略了存在客体量词,实际上说的是“乘某马”。与之相应,“爱人”的否定式“不爱人”即“不周爱人”,“乘马”的否定式“不乘马”却相当于“周不乘马”。何以如此?乘马=乘某马,用量化式表示:∃x(Fx∧Gx)。其中,“Fx”谓“x是马”,“Gx”谓“乘x”。不乘马,则为:¬∃x(Fx∧Gx)。试加演算:¬∃x(Fx∧Gx)→∀x(¬Fx∨¬Gx),∀x(¬Fx∨¬Gx)→∀x(Fx→¬Gx)。对“∀x(Fx→¬Gx)”进行释义:对于所有x来说,如果x是马,那么不乘马。这正是“周不乘马”。“周不乘马”不同于“不周乘马”,后者的量化式为:¬∀x(Fx→Gx)。经过量化分析,可以看出,“周不乘马”之所以不同于“不周乘马”,是因为二者所包含的全称量词的辖域不同,否定词的辖域也不同。
四、 整分之别
不难想到一个问题:上述《小取》讲“周爱人”的地方,可以换成更具有墨家色彩的“兼爱人”吗?毕竟,“兼”“周”的量化用法很接近,都是以跳辖的方式对客体做全称量化。何莫邪已注意到这一点,并由此观察到“兼”“周”另一种细微的差别:“周”作为逻辑客体量词只是指称全体,“不带一丝言外之意”(free from all connotations);而“兼”不仅指称全体对象,而且同时意味着对象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14)参见: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51; C.Harbsmeier,Language and Logic,p.122.
又如,前引《孟子·尽心上》的用例:“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我们也不免纳闷,孟子既以辟杨墨为己任,此处何不径用“兼爱”,却偏偏说个“遍爱”。何莫邪指出,孟子此段论辩的要点,在于“无不爱”和“遍爱”的差别,“兼”“遍”都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无不”的同义词,且孟子于此用“遍”而不用“兼”,实有深意焉。至于深意何在,何莫邪说得不甚明确。(15)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56.试绎之如下。
仁者“急亲贤”,因此不是“遍爱”,但并不能由此就否定仁者“无不爱”。换言之,“无不爱”是无所不爱,强调的是,就爱的对象而言,囊括一切,无所遗失。但“无不爱”对于如何爱无所言说,因此,无论是尧舜的爱由亲贤始,还是墨子的爱无差等,都可以说是“无不爱”。孟子强调了儒家的仁爱和“无不爱”不冲突。仁者,爱人;爱人,无不爱,周爱。(“周”与“无不”相当。)但另一方面,孟子又突出了仁爱与“遍爱”的对立,强调“遍爱”否认“急亲贤”。这意味着,“遍”隐含了无差别之意。何莫邪已指出,“‘遍’并非仅仅意味着‘一切对象’,而是意味着‘一切对象(彼此无别)’,‘一切对象(无论来自何处)’”(16)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55.。不过,依照常识,墨家用“兼爱”强调了爱无差等;如此,“兼”也隐含了“一切对象(彼此无别)”之意。如此,前面何莫邪关于“兼”的解读便不完整,须将此义补入方可:“兼”指称全体对象,同时意味着对象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且进而强调需要无差别地对待之。如此,可回过头来说明孟子何以用“遍爱”而非“兼爱”:“遍爱”的“无差别”义能够跟“急亲贤”形成鲜明对照,而“兼爱”语义复杂,其中的“对象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义项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语义干扰。
由上述比较可知,“周”“遍”“兼”的量化还有整分之别:“周”“遍”指向量化对象的整体,“兼”指向整体内部的差异。《马氏文通》以“皆”“遍”为约指代字,而以“每”“各”为逐指代字。(17)杨树达《词诠》则以“每事问”中的“每”为指示形容词(解惠全、崔永琳、郑天一编著:《古书虚词通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9页)。这里涉及量化词的词性问题。何莫邪给出一个“最重要的一般性观察”:“在希腊语中,量化的办法是通过类似于形容词的语词(如相当于‘所有’的‘pantes’,相当于‘每一’的‘pas’);而在汉语中,主导性的策略则是运用类似于副词的语词(如‘皆’‘兼’‘尽’‘周’‘汎’‘泛’‘悉’‘各’‘遍’)。”(C.Harbsmeier,Language and Logic,p.121)实则,词无定类在古汉语是常见的现象。我们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讨论“皆”“各”“兼”“遍”等量化词,至于它们的语法词类归属则无关宗旨。从逻辑的角度看,“约指”“逐指”之分已有见于整分之别。概言之,全称量词之间又有整分之别:“皆”“遍”“泛”“周”重“整”,其语义焦点在全部元素的整体,而“每”“各”“兼”则重“分”,其语义焦点在整体内部的差异。
进一步看,“每”“各”“兼”亦有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罗素、蒯因对英语中全称量词“any”“every”的分疏颇有可观之处。罗素分析了“每个人”(every man)和“任何人”(any man)之间的差异,认为它们指称不同的对象。(18)B.Russel,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0,pp.60-63.罗素的分析还涉及“所有人”(all men)、“一个人”(a man)和“某个人”(some man)。“所有人”指称人1,与人2,与人3,……与人n;“一个人”指称人1,或人2,或人3,……或人n,这里的“或”意味着,没有一个选项是必选的;“某个人”指称人1,或指称人2,或指称人3,……或指称人n,且某个特定的选项是必选的。推衍罗素之意,“每个人”指称人1,和指称人2,和指称人3,……和指称人n。“任何人”指称人1,或人2,或人3,……或人n,这里的“或”意味着,无论选择何种选项都无所谓。蒯因也论及全称量词“任何一个”(any)和“每一个”(every)之间的“神秘”差别。他构造了两个句子:“如果每一个人都捐款,我都会感到惊讶。”“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捐款,我都会感到惊讶。”如果借用罗素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两个句子之间的差异。有一个说话者默认的集合A,包含元素a1,a2……an。“每一个人都捐款”,说的是,a1捐款,且a2捐款,……且an捐款。“任何一个人捐款”,则说的是,a1捐款,或a2捐款,……或an捐款,至于究竟是a1捐款,还是a2捐款,抑或是an捐款,无关宏旨。
蒯因则引入了量化分析。用“Fx”表示“x捐款”,“p”表示“我会感到惊讶”(x在p中不自由)。那么,以上两句可以分别形式化为:∀xFx→p,∀x(Fx→p)。这样一来,“每一个”与“任何一个”之间的差异就得到了刻画:虽然它们都可以处理成全称量化,但其辖域是不同的。“每一个”的辖域较窄,而“任何一个”的辖域较宽。(19)蒯因:《逻辑方法》,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132页。蒯因在另一处还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评论:“量化分析有助于澄清思维的一个原因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不太具有欺骗性的用语代替那些似是而非的名词‘某物’‘每物’和‘无物’(以及它们的变形‘某人’‘每人’和‘无人’)。”(蒯因:《逻辑方法》,第158页)
罗素、蒯因析义甚精,量化分析的技术在澄清日常语言用法方面起到了不小作用。这对于我们考察“兼”“各”“每”之别不无启发。
“每”字的语义和“every”相当,只是古汉语中的“每”主要用于量化客体,而“every”则无此限制。“每”将所涉全体逐一指之。船山《说文广义》:“每,本训草盛出土也。草盛非一种,故借为分类历言之辞。但一种则有一种之形性,但一事则有一事之条理,但一人则有一人之措置。分而言之,每,各别也;合而言之,每每,皆类也。故每为分别,每每为频繁。”(20)王夫之:《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第九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374页。汉语中的虚词“皆有所本”,所本(即源初的实词义)既殊,“同为语助,而用之也殊”;易言之,源初的实词义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虚词的用法,即“所以助语成文之理”。(21)王夫之:《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第九册,第56页。对虚词做词源学考察,通过回溯其实词义明其用法,船山得出不少有启发性的见解。当然,语词的意蕴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虚词亦然。词源学考察,一方面不能穷尽虚词的意蕴,另一方面也可能做出一些牵强的解释。如船山释“即”字:“即,本训即食也。徐锴曰:‘就也。’即食者,食不以饔飧之常,随便辄食也。食不以时,故从卩,欲使节之也。就者,就便之意,便则就之,故相迩曰相即。就便者无待,故无所待而急应曰即。即日者,就此日也。即事者,就此事而言之也。两相就则合而为一,故二名同实曰某即某,展转相借尔。”(王夫之:《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第九册,第400—401页)船山《说文广义》的体例,乃是“先列《说文》本义,再列从本义转为某一义,或转为若干义,以广《说文》所未备”。(童第德:“点校说明”,见王夫之:《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第九册,第403页)船山释“即”,从《说文》所讲的“即食”本义出发,整理出“就”“相迩”“无所待而急应”“二名同实”等词义链条。船山用“A义,故B义”的句式,强调从A义转出B义是合乎逻辑的。然则,语义的发展是在语词具体使用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往往掺杂了偶然的非理性的“杂质”。再者,推衍本乎《说文》,如果《说文》错了,那么,推衍的起点也就错了。段玉裁便不认可《说文》的“即食”训义,认为“即食”当作“节食”:“‘即’,当作‘节’,《周易》所谓‘节饮食’也。节食者,检制之使不过,故凡止于是之词谓之即,凡见于经史言即皆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段玉裁将“即”的虚词义理解为“止于是”,并且解释了如何从“节制”这一实词义转出。我们未必能马上用段玉裁之说否定王船山,但至少可以看到不同解释的可能性,从而提防一种可能的情形:合乎逻辑的语义推衍只是主观上“合理”重构的结果,未必能复历史之实,亦未能尽历史之实。
“各”似乎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词,或可勉强用两个英文词相结合,译为“every different”。“各人”,指称人1,和指称人2,和指称人3,……和指称人n;并且,人1、人2、人3……人n之间存在差异。引入量化分析,“物各从其类”可以刻画为:∀xFx∧∀x∀y[x≠y→¬(Fx↔Fy)]。其中,“Fx”表示“x从其类”。相形之下,“物皆从其类”的量化形式为:∀xFx。由此,便不难看出“各”比“皆”多出来的意涵。
由于“各”比“皆”多一点意涵,从“各”出发还是从“皆”出发思考等同关系,亦将有细微的差别。如果着眼于“皆”,如:“物皆同于己。”(所有事物都是与自身相等的。)则相应的量化式:∀x(x=x)。如果着眼于“物各同于己”思考等同关系,则有量化式:∀x(x=x)∧∀x∀y[x≠y→¬(Fx↔Fy)]。其中,“Fx”表示“x=x”。“∀x(x=x)”之所以还跟了一个冗长笨拙的式子,只是因为,还需要深入到“x=x”的内部,彰显因x取值不同而导致的“同于己”方式上的差异。“物皆同于己”,着眼于“己”在不同时空中保持不变的同一性(identity);“物各同于己”,着眼于一“己”有别于另一“己”的独特性(uniqueness)。勉强以别之:前者,重个体;后者,重独体。
如上所论,“兼”指称全体对象,同时意味着全体对象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且进而强调需要无差别地对待之。全称、个体间差异性、无差别,三个义素兼而有之。如果译成英文,就有必要把三者都表达出来,摆到明面。“兼爱”通常的英译有二,或为“universal love”(普遍之爱),或为“impartial love”(无偏私之爱),似乎都未能尽“兼”字之蕴。(22)另一个问题,则是“兼爱”之“爱”是否应该译为“love”。葛瑞汉认为,“universal love”这个译法既太模糊,又太富于感情色彩(参见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3页)。亦可参见[新加坡]赖蕴慧:《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刘梁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60—61页。《庄子·天下篇》言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相当于也只是从“普遍”(universal)的角度把握墨子兼爱,不免有偏。何莫邪把“兼爱天下之人”翻译为“He loves 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equally”(23)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53.,这就遗漏了他曾强调的对象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或许,“兼爱天下之人”可译为“He lovesallthe peopleequallydespite of theirdifferences”。尽管知道客体的差别而无差别地对待之。相形之下,倘若是“仁爱天下之人”,则需要译为“He lovesallthe peoplerespectivelyin accordance with theirdifferences”。仁爱者,爱有差等,理一分殊,对待客体的方式需因客体而异,采取与客体的独特性相宜的方式。易言之,儒家“爱有差等”之仁爱蕴含着以客体为中心的伦理学主张。(24)关于以客体为中心的伦理学,以及相关的道德铜律等,可参见黄勇:《道德铜律与仁的可能性》,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概言之,“每”重元素个体,“各”重元素独体,“兼”则强调了尽管元素间存在差别却须无差别地对待之。
五、 结语:事上明理考量词
哲学的工夫之一,在于辨名析理。辨名析理的工夫,首先在于考察实词所表达的概念。不过,如以汉语做哲学,则须注目于虚词在汉语(尤其是古汉语)中的特出地位。辨名析理还需要一番出“实”入“虚”的功夫,即,练就一副听虚词的好耳朵,听出不同的虚词如何将义理进行不同的分环勾连,听出不同的虚词各自在达意上的精微之处。(25)参见张靖杰、刘梁剑:《虚词、句式与做哲学:以王弼〈老子指略〉为中心》,《江海学刊》2020年第6期。
在虚词之中,又有一类小词(particles)值得专题考察。小词即逻辑学所讲的逻辑词,包括联结词如“非”“或”“与”、模态词如“必”“可”等。小词虽“小”,其用甚大。它们撑起了思维的框架子。架子虽虚,却是虚以待物而有其大用。
小词中有一类量词(quantifier),如汉语中的“所有”“有些”,英文中的“all”“some”等,或为全称量词(universal quantifier),或为存在量词(existential quantifier),现代逻辑则用“∀”“∃”等符号加以形式化。(此“量词”或可称为“量化词”,以区别于用在数量之后表计量单位的量词,如“一本书”中的“本”。)在西方的思想脉络中,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量词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从皮尔士、弗雷格、罗素到蒯因、Barwise、Keenan、Westerståhl,现代量词理论不断翻新,新的量化技术的引入也帮助澄清了一些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量词理论呈现出多样性,哲学家对量词的理解、对量词表达式的解读方式、相应的本体论立场等都不尽相同,彼此间意见的分歧与争论层出不穷。莱布尼茨曾设想,发明一种普遍的、没有歧义的语言,可以把意见的争论转化为数学式的演算,从而做出准确的对错判断。现代逻辑的发明,似乎让逻辑学家相信已经实现了莱布尼茨的梦想,找到了那种解决问题的普遍语言。然而,现代逻辑内部的争论让我们看到,如果有一套普遍的算法,的确就能用计算解决是非争论;但在此之前,我们要确定怎样的算法是普遍的算法,是非争论重新开始;为了解决是非争论,需要找到另一套(也许更高阶的)普遍的算法来进行裁决;但在此之前,我们要确定怎么的(也许更高阶的)算法才是普遍的算法;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一事实帮助我们从逻辑学家的“甜梦”中清醒过来,(26)康德说,在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或普通人看来,永久和平只是哲学家“甜蜜的梦”(康德:《永久和平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7页)。且反其意而用之。可以顺便一提的是,引用西方哲人的思想而用其反意,冯契“智慧说”已是先例。培根《新工具》在批评的意义上讲,“人类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易言之,人类理解力本应是干燥的光。冯契暗引培根,则从正面主张理智并非干燥的光。看清以下现实:世界归根到底——即,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是算不清楚的,因世界生生不息而人类心智有限之故。(27)晋荣东反思现代逻辑隐含的封闭世界假定:“世界的可变性、人类知识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表明,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但迄今为止逻辑学家通常都是把开放世界理想化为封闭世界,并用基于封闭世界限定的逻辑来处理开放世界的问题。”(晋荣东:《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反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37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逻辑学家的理想:世界还是可以想办法算清楚些的,而逻辑便是有效的办法,哪怕是“之一”。
在操作层面,量词理论的成就启发我们,像西方现代逻辑学家那样事上明理:对汉语的量词做专题考察,从汉语的量化实践出发,提出相应的量词理论,以解决或澄清一些哲学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的“石”不是西方逻辑学家所提出的某种现成的量词理论,这里的“玉”也不是某种现成的量词理论可施于其上的汉语言语实践。如果直接取西方现成的某种量词理论对治汉语量词,难免出现一般性的以理限事的“理障”,或者说,缺乏逻辑理论(logica docens)和逻辑实践(logica utens)之间的反思平衡。但除此之外,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因中西语言的结构性差别而造成的理与事睽。对于后者,不少中西方学者已经从逻辑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等角度提醒我们慎思,西方语言逻辑之理是否合乎中国语言逻辑之事。(28)兹举三例。顾有信(Joachim Kurtz)在《中国逻辑的发现》一书的反思部分指出,现有的关于中国逻辑史的书写,渗透着现代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预设。其中一点,则是以亚氏《工具论》为逻辑典范,努力在中国发现“逻辑”。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继续用力追逐理论碎片,而是仔细审视辩论实践,并试图恢复它们所体现的隐含和明确的有效性标准”(顾有信:《中国逻辑的发现》,陈志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38页)。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在《古汉语语法四论》导言中指出,无论是弗雷格、罗素,还是乔姆斯基,他们“在讨论人类语言的方法上,都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它们似乎都没有认真重视不同的自然语言之间深刻的结构差异”(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2)。马蒂尼奇为《语言哲学》中译本作序:“我是带着颇有点儿惶恐的心情来说这些哲学家对理解‘语言性质’作出贡献的,因为,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们都是依据其仅仅关于英语的知识来作出关于一切语言的论断。”(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页)就量词问题而言,何莫邪写道:“我们可以问,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量化直言命题是否都可以轻松自然地用古汉语表达出来。反过来,我们必须追问,古汉语中一切微妙的量化模式是否都可以轻松自然地用古希腊语表达出来。或者,更一般的问法:我们在现代逻辑中找到的量化策略仅适用于某些语言如希腊语,抑或具有普遍性,亦适用于像汉语等迥异的语言?”(29)C.Harbsmeier,Language and Logic,p.120.理事之间的反思平衡在这里加入了跨语际的要素:源自西方语言的逻辑理论和汉语的逻辑实践之间的反思平衡。
事上明理始于事。研究汉语量词,第一步,“不要想,而要看!”(30)[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页。何莫邪以此作为研究古汉语语法的方法指南(C.Harbsmeier,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p.15)。不是找到某种现成的量词理论加以依傍,而是回到汉语言语实践本身,综观(uebersehen)量词的种种用法并加以整理。(31)维特根斯坦:“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75页)。这些日常语言的用法往往复杂微妙、丰富多彩,非通常的逻辑形式所能穷尽。那么,它们算不算逻辑的用法?换个问法:从逻辑的观点看,比通常的形式逻辑“多”出来的用法是值得专题研究的珍宝,还是应当滤去的渣质?蒯因可能会同意后一种看法。他比较了三个例子:“琼斯在这里并且史密斯不在。”“琼斯在这里但是史密斯不在。”“琼斯在这里尽管史密斯不在。”三个句子的意义显然有所不同。“并且”,平实的并列;“但是”,有所对比(如希望史密斯在);“尽管”,似乎传达出一种看到反常现象的惊讶之情(如平时琼斯与史密斯孟焦不离)。但是,三个句子都可以无差别地翻译成合取式p∧q,其中,“p”表示“琼斯在这里”,“q”表示“史密斯不在(这里)”。蒯因将此称为修辞和逻辑之别。“‘并且’‘但是’和‘尽管’意义之间的区别是修辞的而不是逻辑的。逻辑记法,不涉及修辞上的差别,可以统一表达合取。”(32)蒯因:《逻辑方法》,《蒯因著作集》第2卷,第50页。不同于蒯因,斯特劳森可能会说,比通常的形式逻辑“多”出来的用法值得深究;而且,为了把这类研究纳入逻辑学,我们还得为之正名,如称之为“日常语言的逻辑”(logic of ordinary language),以有别于狭义的形式逻辑。(33)P.F.Strawson,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London:Routledge,2011,pp.230-232.当然,我们也不妨把斯特劳森所讲的“日常语言的逻辑”简单地称之为“广义逻辑”。广义逻辑注重日常语言用法中比形式逻辑多出来的东西。广义逻辑并不拒绝形式化,对量词的广义逻辑研究也要充分利用量化分析的技术。如有可能,将蒯因视为修辞之别的东西加以形式刻画,从而将包裹在日常语言中的丰富意蕴清晰地分析出来。如以上蒯因所举三例,为了刻画三者之异,我们可以把隐含的命题表示出来。且用“r”表示“希望史密斯在”,用“s”表示“琼斯与史密通常在一起”。如此,分别用“并且”“但是”“尽管”联结的三个句子可以依次表示为:p∧q,p∧q∧r,p∧q∧s。如此,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句子表达了三个不同的命题。当然,这样的形式刻画可能仍然显得外在,如要进一步揭示p、q、r、s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能就要深入命题内部,运用谓词逻辑的技术把三个命题的差别刻画出来。
事上明理,始于事而非终于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的“石”,乃是西方逻辑学家事上明理的研究方法,这里的“玉”乃是某种新的量词理论(从不系统的观点到成系统的学说)。理想的情况下,新的量词理论,对汉语量词的用法具有解释力,对基于西方语言实践的量词理论有所检验、回应、补足、修正甚至替代,且以汉语量词现象为线索,思考其中关于人与世界的独特观察和理解,从而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与世界有所助益。一言以蔽之,事上明理考量词,于量词观其日用,析其逻辑,明其逻辑之理,兼明逻辑之外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