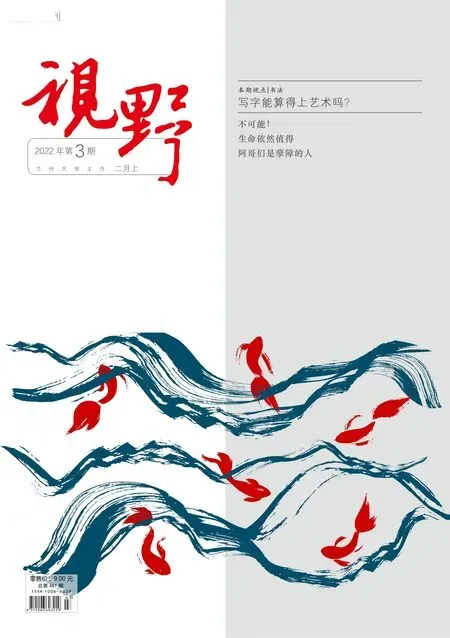他好像一下子老了
/三三

那年夏天,父亲再一次提出教我学游泳。
“你看——”一天,他用手指敲打着手里的报纸,指着上面一则海难新闻对我说,“当海上发生危险时,除了勇气与希望,还有什么能让人存活下来?”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迫不及待地自问自答道:“没错!就是那些会游泳的人!”说完,他忧心忡忡地瞧着我,仿佛正看见他的小女儿在海水中苦苦挣扎。
自七岁第一次学游泳起,又一个七年过去了,我还是没学会游泳。我一站到水里就眩晕、恶心,除此之外,我还能找到诸如此类这样一沓不下水的理由。然而,想到假期漫长而烦闷,那一个个长长的下午闷热难捱,以及柜子里那件漂亮的还未上过身的孔雀蓝新泳衣,我决定试一试。
头天晚上,我把那条新泳衣同一副黑色游泳镜放进包里,叮嘱父亲走时带上。而我将在妈妈一尘不染的家里度过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后,只等父亲那辆半旧的蓝鸟在楼下按响喇叭时飞跑下楼。我知道妈妈会站在窗口向下张望,当汽车缓缓驶离时,她会凌空冲着我们的背影,更确切地说是冲父亲喊上一嗓子:注意安全!半是训斥,半是叮嘱,还有一丝预支的愠怒,就像他们离婚前一样。
一路上,带点咸味的海风从车窗灌进来,吹拂着我们的脸,父亲像年轻人一样吹着口哨,而我则一边翻看着漫画一边狂吃零食,还没到海滩,我已经消灭掉半个西瓜、三个番石榴和一小袋甘草瓜子。
父亲严肃地提醒我注意车内卫生,并摸出一只塑料袋用来装那些果皮纸屑。终于,我吃累了,抹了抹嘴巴,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父亲顺手把那只袋子扔到后车座上,路过检票口,它又被父亲一把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
转过一片季雨林和一块蛋糕般的仙人掌田,蓝汪汪的大海像幅画卷一样徐徐展现在眼前。长条形的海滩上,条纹伞和沙滩椅在那里排成一排。一个穿着料子很少的泳衣的女人像只细脚仙鹤一样踱着步。一群套着游泳圈的小孩撒着欢尖叫着冲进大海,其中最小的那个又被海浪送回到岸上。
这就是生活,我想。我感觉生活开了个口子,一股凉爽的风正从那里呼啦啦吹进来。我已经隐约看到沉闷的假期向我露出了一丝美妙的微笑。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美妙了。
在靠近沙滩的地方,父亲让我先下车,而他要把车子开到远处咖啡馆后面的停车场去。他随手递给我一个袋子,那里面装着他给我带来的泳衣和泳镜,并指着旁边的更衣室让我换好后等他。我打开车门准备下车,可是,我的一只脚刚刚落地,另一只脚还在车里,他已经发动了汽车。我尖叫了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那声尖叫那么响,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子,把那个下午分成了两半。
等我睁开眼,我看到父亲蹲下来,惊慌失措地看着我,他身后的蓝天蓝得令人目眩。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子,好在是在沙滩上,我的膝盖上只稍微擦伤点皮。
父亲连声问着我:“没事吧?没事吧?”并命令我在沙滩上走几圈给他看看,这才放心地开车离去。
当我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时,我不知道,一件更让人郁闷的事正等着我呢。
我打开那个袋子,里面竟然没有找到我的游泳衣,而是一大堆果皮纸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刚才,父亲扔掉的那个袋子根本不是垃圾,而是我的游泳衣!我重新系好袋子,拎着它就出来了。
父亲见我还是穿着刚才的衣服,问我为什么还没换上游泳衣。我什么话都没说,把手里的袋子递过去。他疑惑地看着我,打开了袋子,探头朝里瞧了瞧。“糟糕!”他低声嘟囔了一句,拎起袋子,急匆匆地向检票口走去。
当海风送来第一缕清凉,太阳移向西方第一棵椰子树的时候,父亲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大汗淋漓,手里忽闪忽闪地提溜着一个袋子,敞开的衣襟像鸟儿的两只翅膀一样扑棱着。
“快拿去换上!”他揩了一把额头上的湿津津的汗,把手里的袋子递过来。
我又回到更衣室,准备换上游泳衣。当我把手伸进袋子,跟随我的手出来的,不是我那件漂亮的孔雀蓝泳衣,而是一团皱巴巴团在一起的红布头。那是我小时候的游泳衣,我八岁至九岁的两个夏天,穿着它在海滨浴场的浅水里扑腾。
怎么回事?明明昨天晚上我把准备好的孔雀蓝游泳衣和一副游泳镜装进包里,让父亲来时带上,现在怎么会变成另一件呢?我拿着它就冲了出去。
父亲挠挠头皮,“你给我了吗?噢,我把这事忘了……我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件。”他冲我摆摆手,说:“将就着点吧!一会儿天一凉,就游不了多长时间了。”我苦着脸看着他:“爸,这么小,怎么穿?”他伸手扯了扯那红色泳衣,像扯牛皮糖一样把它扯成一个长条:“怎么不能穿?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好孩子,将就一下吧。”说着,他不耐烦地把我推进了更衣室。
我只好穿上了那件儿童时期的游泳衣。那巴掌大小的一块布料,让我的整个后背露在外面,凉飕飕的!而它胸前绣上去的那只加菲猫,当时曾引起好多小朋友的艳羡,现在看上去却是那么恶俗不堪,一只眼睛还被我抠掉了!
在墙上的镜子里,我看到我十三岁的身体紧紧地包裹在那件又小又旧的游泳衣里,我使劲地扯了又扯,才勉强盖住我结实的小胸脯。我无比气恼,忍了又忍,终于还是流下羞愤的泪来。
我踩着白色的细沙,向海边走去,低着头,看脚窝陷落,在起脚的那一刻被沙子重新填满。我希望海滩上的人看在我不看他们的分上,也不要看我。
父亲已经游了一圈回来了。他站在水里,像以前一样张着两手等我下去。带盐的海水顺着他的脸颊,流过他桥墩般健壮的躯体,一下一下拍打着他的大肚皮。从七岁到十三岁,父女俩一年一年重复着相同的游泳课程,没有一点长进。
我站在那里,任凭水里的父亲怎么招手和呼唤,就是站着不动。我昨天就准备好的,和那条孔雀蓝泳衣放在一起的游泳镜,在这时我没法不想起它来。
我低头看着奶油般的浪花顺着海滩涌上来,一下一下地啄着我的脚。我对父亲说:“我得戴游泳镜。”从第一次学游泳,我就习惯了戴游泳镜,对我来说,游泳时它和游泳衣一样都必不可少。
父亲抬头看了看日头,它已走到第二棵椰子树的树梢。一只带斑点的海鸥飞掠过他眼前,嘎地嘲笑了一声,飞走了。
父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走上岸来,“在这等着,别动。我去买游泳镜。”
海滩上到处都是人。那些浑身湿漉漉的游泳的人和滴水不沾的不游泳的人,所有人的脸上都是那么无忧无虑,一副快乐度假的样子。只有我无比沮丧,双臂交叉环在胸前,极力遮住我的胸部和那只一只眼的加菲猫,不让人们看到它们。对我来说,这个下午和这海滩已经受到损害,无论如何也跟他们的不一样了。
这都怪他。他总是这样,丢三落四,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脑子里像缺根筋一样。
当我还是两个月大的婴儿时,一次趁母亲一不留神,他喂我吃了一颗黑提子,差点结果了我的小命。我的小脸憋得都紫了,嘴巴张着却发不出声音。幸亏当时串门的邻居手疾眼快,她把我像个沙漏似的倒拎起来,在我后背上一顿猛拍。我吐出了那颗完整无缺的黑提子。我用小手触摸了一下死神的大翅膀,又回来了。
两岁时,他和我玩“扔高”游戏。我一次一次地被他抛向空中,又一次一次地降落下来。我咯咯地笑着,看着天花板近了,倏地又远了……不知怎么他回了一下头,没接住正在降落的我。我被重重地摔在地上,顿时没了声音……
三岁时,他把我驮在肩上,我两手抓住他的两只招风耳玩骑马。我用小腿使劲擂着他的胸膛,他则发出一连声欢快的马的嘶鸣。这时,院子里的一个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应声就往外走。可是,他忘记了门框高一米九,而他有一米八,忘记了我还坐在他的肩上。只听“咚”的一声山响,我一头撞在门框上,顿时,额上隆起个大包,鼻子血流如注。
五岁时,父亲骑车带我和弟弟去博览会,弟弟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我坐在后车座上,在街的转角处,他远远看到一个久没见面的老同学,忙紧蹬两下,打算下车寒暄。他一抬腿,一脚就把我踢下了自行车……
七岁生日那天,他带我去书店买书,结完账,他把我丢在那儿,自己一个人回家了。我像所有走失的孩子那样恐慌和无助,感觉大祸临头。我张着两手,小声哭泣着,从一楼找到六楼。那天傍晚,当我被民警送回家,一进家门,我就看见我的父亲,翘着二郎腿,正悠闲地喝茶呢。
……
这一笔笔的血泪史,本来我早已经忘了,因为这个下午一连串的郁闷与沮丧,它们又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有时候,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爱我,是不是存心那样做。
我可怜的妈妈,她从他那里所遭受的这一切肯定比我们多。两年前,她终于忍无可忍,和他离婚了。
我越想越气越委屈,泪水在眼睛里打着转。突然,我想报复他一下,我做了他十几年的女儿,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这还是第一次。我决定把自己藏起来,吓唬吓唬他,让他满世界找去。
在一棵椰子树底下,我用沙子把自己埋了起来,连同我身上这件又小又旧的加菲猫游泳衣。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看到它了。
大海在阳光下闪光,沙子暖烘烘地包围着我,耳边传来海浪拍打海滩的声音。我的眼睛睁不开,不知不觉迷糊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半个小时或者几秒钟,一阵嘈杂声传来,我睁开眼,不远处的海滩上,一个男人张着两手飞奔着。他向前跑,再向后,然后又再向前,像个癫狂的猴子似的,在海滩上乱窜,抓住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人,问人家:我的女儿,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女儿?
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
现在,他抓住了一个穿橘色制服的海滩救护员的胳膊,指着波浪翻滚的蓝色大海,大声叫喊着:我的女儿不见了,快救救她!说完,他放开救护员,朝前奔跑了几米,准备跳入大海。海滩救护员抓住他,看上去像在询问他详细的情况。在他们周围,人越来越多,还有更多的人从远处的海滩上朝这边过来了。
我远远地看着人群中的父亲,又气又恼。看来,不能再这样藏下去了。我决定提前结束对他的惩罚。如果这样下去,接下来,指不定他还会出什么洋相呢。我叹了口气,从沙子里站起身来。
我站在人群外喊了他一声,父亲怔了一下,迟疑着扭过头来。他的生活从此改变了。只见他两眼通红,脸颊扭曲,像个小丑。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一个成年人这样失态。人们随着他的视线也转过头来。我闭了闭眼睛,心想,但愿永远也不要有第二次。
父亲冲过来,一把抱住了我,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我还以为你被大海冲走了,你不会游泳……”他紧紧地抓住失而复得的我,仿佛稍一松劲,我就会被大海吞掉。
父亲一头汗水,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一只扣子还系错了。他乱糟糟的头发向上支棱着,露出了发根的白色。父亲真禁不起折腾,他好像一下子就老了。
忽然,我羞愧起来,不敢抬头看他,恨不得再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