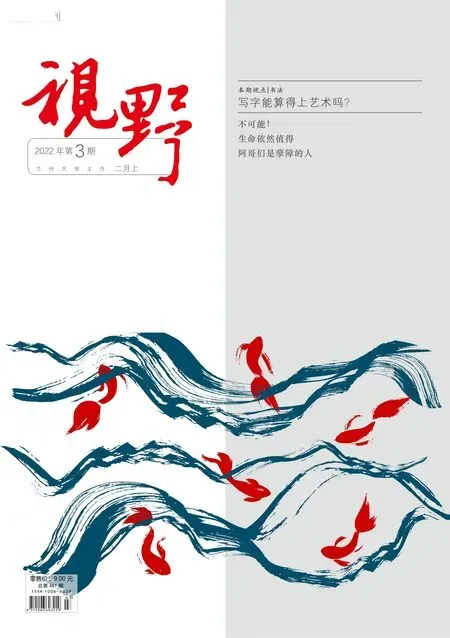不可能!
/[美]Paul J.Steinhardt译/任愚

不可能!
这话响彻了整个大报告厅。而我刚讲完一个关于一种新型物态的革命性概念,这是由我和我的研究生Dov Levine共同发明的。
加州理工学院的这间报告厅里坐满了来自各个院系的科学家。讨论本来进行得相当顺利,但就在最后的人群鱼贯而出的时候,响起了一个熟悉的、高调的声音:“不可能!”
我闭着眼也能认出这个另类的、低沉沙哑的、带着明显纽约腔的声音。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科学偶像,传奇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顶着灰白到肩的头发,穿着他一贯的白色衬衫,脸上带着让人放松戒备的、狡黠的笑容。
此时费曼已经因其发展了电磁现象的首个量子理论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在科学群体当中,他已经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他有一种特别顽皮的幽默感,还因其精心设计的恶作剧而“臭名远扬”。但当涉及科学的时候,费曼一直是毫不迁就地实在并总是严酷地评判,这使他成为科学研讨会上特别唬人的存在。谁都可以料到,一旦他听到什么在他看来是不明确或者错误的东西时,他就会直接打断并公然向演讲人发难。
所以,当费曼在我演讲开始之前进入报告厅并坐在他习惯的前排位子上时,我就敏锐地意识到了他的存在。在演讲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用眼角余光小心翼翼地瞥他,时刻等待着任何可能的爆发。但是费曼一直没有打断我,也没有提出质疑。
“物理X”
演讲结束后费曼上前与我对质这个事儿,恐怕会吓到许多科学家。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差不多十年前,我还是加州理工的本科生的时候就十分有幸跟费曼一起亲密工作,我对他只有仰慕和爱戴。费曼通过他的文章、演讲和躬身指导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1970年当我作为新生第一次进入校园的时候,我打算学习生物或数学。中学时我从未对物理产生什么兴趣。但我知道每个加州理工的本科生都要求修两年的物理课程。
我很快发现,很大程度上拜那个教科书,也就是《费曼物理学讲义》(卷一)所赐,新生物理难得邪门儿。这本书不像是传统教科书,而是基于费曼在1960年代做的一系列有名的针对大一新生的物理学报告而整合起来的精彩文章。
不像我曾经接触过的任何其他物理课本,《费曼物理学讲义》从不拘泥于阐释如何解题,这使得尽力完成繁难的课后作业既费时又费力。不过,那些文章提供了更有价值的东西——费曼本人思考科学的方式的深刻洞察。一代代人从费曼讲义中获益。对我而言,那段经历完全是一种启蒙。
几周过后,我感觉我被洗脑了一样。我开始像物理学家一样思考,并且热衷于此。就像我这代人里的许多科学家一样,我很自豪地将费曼视为我的英雄。我打消了我原本学习生物和数学的计划,而决定加倍努力地专攻物理。
我还记得在我大一阶段,有几次我鼓足勇气在报告会前向费曼打了招呼。在当时要再有其他举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是到了我大三的时候,我室友和我不知怎的就鼓起勇气去敲他办公室门,询问他能否考虑教一门非正式课程,每周一次和像我们这样的本科生见面,并回答我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我们跟他说整个课程都是非正式的,没有作业,没有测验,没有打分,也没有课程绩点。我们知道他是对行政事务毫无耐性的离经叛道之人,也希望这种随性能吸引到他。
十年前或更早些,费曼开过类似课程,但只是针对大一新生并且每年只开一个季度。现在我们请求他做一整年同样的事情,而且对所有的本科生都开放,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可能追问更多深入问题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我们建议这门新课程名为“物理X”,就像他之前的课程一样,让所有人都清楚它是完全脱离书本的。
费曼想了片刻,出乎我们意料,他回答:“Yes!”所以后面两年里,我和室友连同其他一些幸运的学生一道,每周和费曼一起度过一个美妙而难忘的下午。
“物理X”一直这样开场:他进入报告厅,询问谁有问题。偶尔,有人想问一个费曼刚好是专家的话题。自然而然地,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驾轻就熟的。然而在其他时候,很明显费曼之前从未想过这些问题。我一直觉得这些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有机会目睹他头回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思考和解决的。
我清楚记得我问过一些我觉得有趣的问题,即使也担心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是很无聊的。我想知道:“影子是什么颜色?”
在报告厅前头来回走了一会儿后,费曼开始兴致勃勃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抽丝剥茧。他发起了一场讨论,关于影子中的微妙层次变化,关于光的属性,关于颜色的感知,关于月球上的影子,关于月球上的地球反照光,关于月球的形成,等等。我听入了迷。
在我大四的时候,费曼同意作为我的研究课题的导师。现在我能更近距离地目睹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了。我也体验了没有达到他的期待时他的尖刻口吻。他常用诸如“疯了”“笨”“荒谬”“愚蠢”这样的词语来批评我的失误。
这些刺耳的话一开始很扎心,使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学习理论物理。但我发现费曼并不像我一样把这些严厉的批评看得那么重。往往紧接着,他就会鼓励我尝试不同的方法,并邀请我在取得进展的时候再来。
费曼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些最激动人心的科学意外可以从日常现象中发现。所有你要做的就是花时间仔细观察事物,并问自己好的问题。他还影响了我的信念,就是没有必要像许多科学家那样,迫于外部压力而局限在科学的某一领域。费曼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但凡有好奇心指引,那么摸索各个不同领域也都是可以的。
轨迹
我在加州理工的最后一学期,我们的一次交流是特别值得回忆的。我在解释一个我提出的数学方法——可用来预测超级球(Super Ball)运动行为。这是一种弹性超强的橡胶球,当年风靡一时。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超级球每次反弹都会改变方向。我想要预测超级球在一系列放置成不同角度的平面上的弹跳行为,这又增加了一层难度。例如,我计算了它从地面弹到桌子底下,再到一个倾斜平面,然后到墙上的轨迹。这些看似随机的运动根据物理定律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我给费曼看了我的一个计算。它预测我扔出超级球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弹跳,它会正好回到我的手中。我递给他论文,他扫了一眼我的公式。
“这不可能!”他说。
不可能?我被这个词吓了一跳。这是从他嘴里蹦出的新词儿。不再是“疯了”或者“愚蠢”这些我有时已有预期的评价。
“为什么你觉得它不可能?”我紧张地问。
费曼说出了他的考虑。根据我的公式,如果有人从某一高度释放超级球且让其带转儿的话,这球是会回弹,并且是以一个与地面很小的角度弹向一边。
“这很明显不可能,保罗。”他说。
我瞧着我的方程,发现我的预测确实表明这球会回弹,并取一个很小的角度。但是我不那么肯定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它看起来是反直觉的。
我现在已经身经百战,敢于反驳了。“好吧,”我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实验,就让我们在你的办公室试一把吧。”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超级球,费曼盯着我给它一个转儿并丢出手。十分确定,这个球精确地以我的方程预测的方向弹射出去了,以一个与地面非常小的角度弹到一边,这正是费曼觉得不可能的方式。
一念之间,他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他没有考虑到超级球表面非常高的粘性,而这会改变旋转对球轨迹的影响。
“好蠢!”费曼大声说,用他有时拿来批评我的一模一样的语气。
经过两年的合作,我终于确切知道我一直怀疑的了:“愚蠢”只是费曼的一种表达,用于任何人也包括他自己,是作为盯住一个失误从而不会再犯的一种方式。
我也意识到,当费曼用“不可能”的时候,不必然意味着“不可实现”或者“荒谬”。有时候它意味着:“哇!这有一些神奇的东西,与我们通常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相矛盾啊。这值得去搞搞清楚!”
准晶
所以11年后,当报告之后费曼以一种诡笑走近我,并开玩笑地声称我的理论“不可能”的时候,我十分清楚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报告的主题,一种被称为“准晶”的全新的物质形态,与他认为是正确的原理相冲突。所以它是有趣的,也值得搞搞清楚。
我在桌上设置了一个实验来验证该想法,费曼走上前来,他指着它们并要求:“再给我演示一遍!”
我拨动开关开始演示,费曼一动不动站着。他亲眼目睹,见证了科学上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原理被明确地违背了。这一原理是如此基本,他在讲义中也讲述了它。事实上,这些原理近200年来一直被传授给每一个年轻的科学家。
但是现在,我在这儿,站在理查德·费曼前头,解释这些长期存在的准则是错误的。
晶体不是唯一可能的具有有序原子排布和点状衍射图案的物质形态。现在存在一个大量可能性的新世界,它们有着其自身的准则,我们称之为“准晶”。
我们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摆明这些新材料与通常的晶体有何不同。两类材料都包含一组在整个结构中重复的原子。
晶体中的一组原子以规则的间隔重复,就像五种已知的图案一样。然而,在准晶中,不同原子组以不同的间隔重复。我们的灵感来自一种被称为“彭罗斯拼图”的二维图案。这类图案非同寻常,它们包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拼块,并且以两种不可公度的间隔重复而形成。数学家称这样的图案为“准周期的”。因此,我们把我们的理论发现命名为“准周期晶体”,或者简称为“准晶”。
我为费曼做的那个小演示可以证明我的观点,仅用一束激光和一张准周期图案的照相投影片。我按费曼的指令打开激光,将光束对准,这样它通过投影片投到远处墙上。激光产生了如X射线穿过原子间的通道一样的效果:它产生了一个衍射图案。
我关上顶灯,这样费曼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墙上那些雪花样的点状图案。它不像任何其他费曼曾见过的衍射图案。
正如我在报告当中做的那样,我向他指出,最亮的点形成了同心的十元环。这闻所未闻。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斑点形成了五边形,这揭示了一种被认为是在自然界中被绝对禁止的对称性。更仔细的观察揭示了斑点间的更多亮斑,以及越来越多的亮斑。
费曼要求更仔细地看那个投影片。我打开灯,把它从托板上取下递给他。投影片上的图像缩得如此之小以至于很难看清细节,所以我也递给他一张拼图的放大版,他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在激光前头看。
接着的一段时间在静默中过去。我开始感觉自己又像是一个学生了,等待着费曼对我想到的最新荒诞想法作出反应。他盯着桌子上的放大版,将投影片重新塞进托板,自己打开激光。他看来看去,一会儿盯着桌子上的放大印版,一会儿抬头瞧瞧墙上的激光图案,重又低头看放大版。
“不可能!”费曼最后说。我点头同意并笑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一种最高赞许。
他回望向墙壁,摇着他的脑袋。“绝对不可能!这是我见过的最惊奇的一件事儿。”
然后,不再说什么,费曼兴奋地盯着我,脸上堆着狡黠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