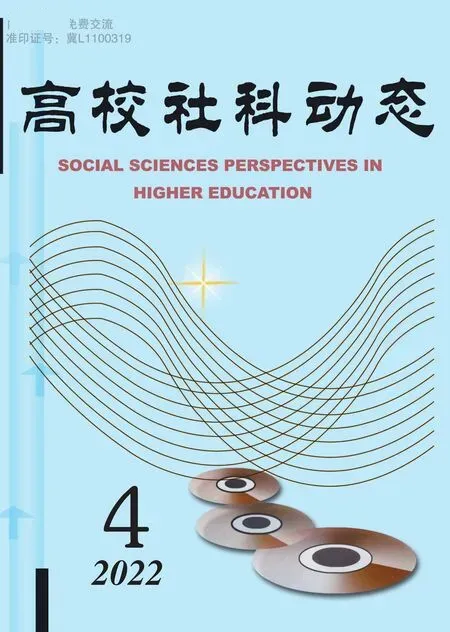寻找与失落的错位 反抗与服从的矛盾
——杨月月与陆文婷形象新探
张春晓
(河北衡水中学,河北 衡水 053000)
《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和《人到中年》是谌容的重量级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杨月月和陆文婷在当时影响很大,塑造得较为成功,但是细究起来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杨月月身上存在着自我价值寻找与失落的错位问题,而陆文婷身上则存在着反抗左倾和认同左倾相矛盾的现象。
一、杨月月:寻找与失落的错位
《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的主人公杨月月和丈夫离异之后,并没有沉沦。她在招待所拖地板、洗衣服,从而找到了自我。这部作品试图表现中国女性由于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从而进行寻觅的艰难历程。作品发表之后,评论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写出了东方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的,这篇作品是提出了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作品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结论是令人失望的。杨月月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她的丈夫步步高升,她可以成为一个省委书记的夫人,成为书记的后勤部长。但杨月月有自己的追求,她宁愿离开自己的丈夫也不愿成为丈夫的附庸。她最后在招待所干勤杂工,工作相当勤奋负责,受到大家的好评。但是,笔者读了这部作品之后,认为杨月月这一人物身上存在寻求与失落的错位。首先,她失去了爱情,但是她并未寻找;其次,她失去了发挥自己才干的环境,她也没有寻找;再次,她把一切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表现了强烈的母性意识而几乎没有妻性意识与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太高的评价是不恰当的。杨月月在失去丈夫之后,她没有积极地抗争,而是在等待。她是依靠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依靠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依靠成全丈夫的爱情转移来确立自我的地位,并以此保持内心的自我平衡。她以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所形成的不变心理来应付眼前所发生的万变,她通过自律来达到自助,通过忍耐而形成自己的心理优势。她被丈夫抛弃时不是怨恨丈夫的无情而是反省自身的问题,这样,这个人物形象便打上了道德自我完善的印记[1]92。杨月月并没有找到自我。如果说杨月月的自主意识是从拖地板、洗衣服中体现出来的话,那实际上用不着进行寻找了。因为她原来就是拖地板、洗衣服,只不过一是在家庭,一是在招待所而已。
杨月月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形成她对苦难的认同,在这种认同的背后隐含了某种悠久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有一种强烈的母性意识。她失去了爱情,但她并不去寻找,她用苦难的工作代替了爱情的寻找。她在儿子身上寄托了全部的希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杨月月除了属于苦难的事业,就是属于儿女,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少之又少。她缺乏从道德意义上向自我意识转变的勇气,她向世俗靠拢向原来的位置上回归,以此获得心灵的宁静和道德的自我补偿。但是道德上的守成妨碍了她的寻求,她的宁静成为一种自欺。她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试图寻找自主意识是根本不可能的。她的诚挚忠贞形成她对未来的真诚期待,这种期待主要是寄托在儿子身上,一旦儿子犯罪的真相被她知道之后,她的精神支柱便突然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这篇作品并无太大的意义。杨月月寻找与失落的错位说明作家认识上的拘囿和困惑。
二、陆文婷:反抗与服从的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谌容的创作登上了一个高峰,这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人到中年》创造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当代中年女性的典型。这部小说既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全部情节在女主人公陆文婷的昏迷与半昏迷的生病状态中时断时续地展开。在这里,回忆与现实、梦幻与事实、幻想与真象、意识与潜意识、心理时空与物理时空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冲突,又互相融汇为一片烟雨空濛的精神巨流。三组诗的意象,构成一篇交响乐章,三次鸣响在陆文婷的心灵深处。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从她灵魂的底蕴抽出的无数缕激情的纽带,交织成一片漫天铺地的情感网络,也成为作品结构的线索[3]。从陆文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在20世纪50年代浪漫主义气氛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素质——孺子牛精神。她在艰苦搏斗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也仅是普通一兵。她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计报酬,无间歇的精神磨损,超负荷的体能消耗,使她做出了最后的牺牲。她看似弱不禁风,但她是真正的强者。在“文革”中,她为了给中央某副部长焦成思做手术,同红卫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坚毅刚强、温文尔雅同野蛮残暴进行了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她焕发了青春,用高度的责任心和无私的奉献以及无邪的职业道德,同马列主义老太太进行了斗争。
《人到中年》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中国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职业妇女的双重负荷问题、家务劳动社会化问题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年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由于左倾思潮的猖獗,使我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断层。老年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环境中非死即伤,又由于自然的法则,幸存者也都是年纪高迈,新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培养出来。因此,中年知识分子便成为科教文卫战线上的中坚力量。他们肩负着振兴祖国科技的重任,由于人才奇缺,他们个个都是超负荷地运转,一个人担任几个人的工作。他们上有老人,下有子女,工资待遇极为菲薄,住房条件拥挤不堪,身体素质可堪忧虑。因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人到中年》通过主人公陆文婷命运的折光,把这些问题放在社会大转型的主潮中加以检视,这些问题都是新时代诞生过程中的矛盾和分娩阵痛的延伸。陆文婷性格的构成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这类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社会矛盾,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
《人到中年》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之后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人到中年》的巨大成功既是社会的要求,又是作家才能的表现。尽管《人到中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但如果我们把目光移注到陆文婷内心世界的深层,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指出:陆文婷的精神世界是明净的、高尚的,却又是单一的、单薄的。她虽然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虽然有人的七情六欲,但充满了普通人的英雄气概[1]94。至于她灵与肉的剧烈冲突,在作品中是无法找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怀疑意识及孤独感,她是没有的。她的好友姜亚芬对她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刚有一点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就要打下去?以后,再开这种会,我不参加,以示抗议!”陆文婷回答说:“何必呢!再开一百次批判你,我也参加,反正手术还得我们做,我回家照样钻研!”姜亚芬问她:“这么批你,你不觉得冤么?”陆文婷回答说:“我忙得昏头转向,没有时间想它。”[2]陆和姜的这段对话,表现了陆文婷内在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既是她对苦难的一种曲折抗议,又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形式,显示出她体验到了苦难而无法(也不想)摆脱苦难的尴尬处境。她的形象,不仅渗透了传统的文化因子,而且形成了她的潜意识与无意识。这之中还渗透了她接受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在她身上存在着《班主任》中谢惠敏的某些因素。在她看来,对左倾进行怀疑,这是一种“邪念”,要忠于革命,忠于事业,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必须抑制自己的“邪念”。但当左倾思潮把个人的自尊剥夺殆尽的时侯,她仍对之愚忠。这种表现一方面说明她具有美好的品质,另一方面则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重成分——奴性成分。
陆文婷对左倾思潮反抗的方式是沉默,这种沉默在行动上表现出一种服从,又在服从中表现出她的优秀品质。但笔者认为个人品质的优秀,并不是思想上的先进。当然陆文婷并没有成为左倾思潮的俘虏,但她也没有成为左倾思潮的怀疑者。作家对陆文婷沉默和认同的歌颂,便说明作家对左倾思潮的认识是肤浅的,批判是无力的。这篇作品用主人公肉体的精神重负表现了左倾思潮的盛行与对知识分子的伤害,用主人公的沉默与认同表现了左倾思潮的根深蒂固。与此同时,作家又赞扬了主人公的无思和对苦难认同中的劳作精神,这说明作家在创作这个人物时也是矛盾的、纠结的、无奈的。
三、结语
除了这两部作品之外,谌容影响较大的作品还有《懒得离婚》《错,错,错!》《人到老年》《永远是春天》等。这些作品都善于提出严肃的社会问题,都擅长塑造贴合时代的人物形象,但是由于时代环境和自身成长经历的限制,谌容在解决问题方面不够理想,在塑造人物方面也存在着价值观陈旧、人物内核相矛盾的现象。不过我们对作者不能求全责备,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局限。谌容在80年代初就能深入女性的内心去剖析女性的灵魂,通过女性的命运展示女性的生存困境,并呼吁整个社会关注女性的婚姻问题、事业问题以及自立自强问题,已开风气之先,并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