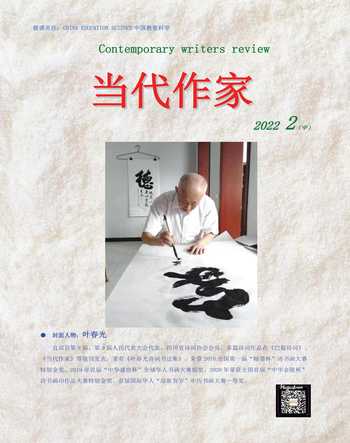煮俩饺子过元宵
1978年春节前夕,我带新婚正度蜜月的妻子春贤,回到农村老家过年。大年初一早上,全家人吃过团圆饭,母亲就叹息一声,对我说:“人常说,树大要分杈,娃大要分家。你弟兄三个哩,谁过了事(指娶过媳妇)就把谁分出去单另过日子。咱穷家也有穷打算,早早各想办法过光景吧。”我爹在一旁附和地点点头。既然是父母之命,我这个当娃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当天就一没唤舅舅分家,二没请中人作证,由我妈主持,分给我一只铁锅一摞碗,两双筷子两碗面,带着这些吃饭的家什,夹着两副铺盖,我俩立马从爹妈住的院子搬回老宅院那三间老院居住,算是重立门户安了家。那几天,来串门闲玩的我那帮子发小好友们,都打量着我这“极简版”的新婚新居,逗趣之余略带戚然。我却朝他们大度地一笑:“五八年大跃进时侯有句口号: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以外,都是祸害。咱比那时侯强多啦!”一席话把妻子和大家都逗乐了。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剁肉洗菜,蒸包子煮饺子,欢度元宵佳节。这天一大早,妻子春贤对我说:“咱妈昨儿个送来一块豆腐半棵白菜,我给咱包顿饺子。你先出去转转、逛逛,赶中午回来咱吃饭。”
那天上午,我出了门,先去爹妈那儿唠了一会家常,接着又到村里老舞台下去看村人打花鼓扭秧歌,最后又被几个发小拉着一块玩扑克。正在玩得高兴,我无意抬头瞅了一眼这家墙上挂的电子表,急忙扔下手里的扑克牌,边往外小跑边说:“哎呀,都快到中午十二点半了,我得赶紧回去,春贤等我一块吃饺子哩!”
一进屋门,只见春贤倚在门边痴痴发呆,锅边的风箱被抽开了盖板,倒扣在地,白面包的饺子洒得七零八落,灶门下躺着两只死老鼠……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忙问春贤,春贤先是气鼓鼓地半天不答腔,好大一会儿才噙泪说出原委:上午我出门以后,她就在屋内和面剁菜,包了一箅子豆腐白菜馅饺子。快到十一点左右,她等我等不着,便关上屋门去寻我。先到爹妈那儿,妈说我走了一会儿了;再到打花鼓那里去问,人们说见我在此呆了一小会,后来不知去哪儿玩去了。那时还不兴带手机,她当时又新嫁我村,人地两生,实在不知我的踪影,只好返回家中去守侯。一进门就把她吓了一大跳,只见一大一小两只老鼠从放饺子的箅子上惊慌地逃窜,而箅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两只饺子!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可恶的老鼠,趁她出门来祸害了。到底它们把饺子转到哪儿了?春贤气得在屋里屋外寻找,最后一拉风箱拐儿拉不动,干脆把风箱盖板一抽,才看见里面有一大堆饺子,还慌里慌张窜出两只老鼠,被恼怒万分的春贤当场抬脚踩死一个,用檊杖打死一个……“大年十五的,咱吃个饺子都吃不成,真是倒灶咂啦,命真真瞎呀!”春贤说罢,眼圈一红,淌下热泪。我心中一阵阵歉疚、后悔:要是我上午不出去闲跑,屋内老有人,老鼠就不会钻了空子祸害人!眼下,可该怎么安慰自己的爱人?猛然,仔细打量箅子上“劫后幸存”的那两只饺子,我先是托腮沉思,后是哈哈大笑。春贤忙问我:“你笑啥哩?气憨啦?”我说:“有啥气的,別看是老鼠捣乱,糟塌了咱一顿饭,可你已经惩罚了它们,有啥伤心生气的?况且——”我指着箅子上仅剩的那两只饺子说:“人常说年下见老鼠,是送福哩。你看它们糟塌咱饺子,故意留下两个,是不是有啥寓意?”“啥寓意?”我朗声一笑:“这是不是象征着咱夫妻二人,成双配对,今后就连吃饭都永不分离呢?”春贤一听到这,“扑哧”笑了。我趁势拉她起身,我俩一起,打扫了屋内垃圾,扔掉了死老鼠,重新点火做饭,把那两只饺子下锅煮熟后,连汤舀出,泡块冷馍就大葱,吃了一顿別有滋味的元宵饭。坐在风箱板暂代的“饭桌”前,每人端一碗只有一只饺子的“十五饭”,我们边吃连聊,情意绵绵……我们回忆起:初次相亲时的四目相对,握尺为证;结婚时添置了必需品后,我俩身上仅剩五块钱,只买了半斤喜糖一盒烟招待亲友……“眼前这点苦这点难算什么?只要心里有巴头,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用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的话来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俩共同商定,今天吃的这顿特殊的十五饭,出去对谁都不讲,免得父母着急,旁人笑话。“出门都把嘴一抹,谁知道谁吃了啥?”春賢说罢一笑,我朝她深情地点点头……
时光已过四十余年,元宵佳节又将临前。此刻,正在海南三亚寓所颐养天年的我们老俩囗,抚今追昔话当年,再次重温那句话:“只要心里有巴头,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熖山!”永做时代追梦人,幸福日子不断头!
2022.2.7写于三亚寓所。
作者简介:
宁水龙,山西省稷山县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原稷山县作家协会主席,现仼稷山后稷文化研究会会长,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3862500338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