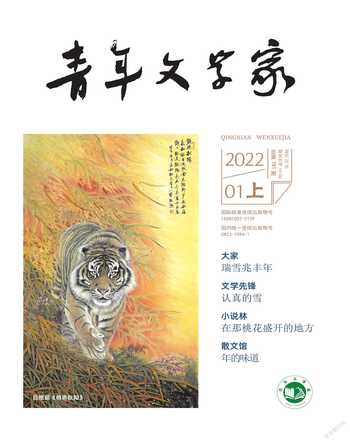终其一生,他想成为一块真正的石头
田丰源
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早晨,他,一个壮年,手里拿着一把小锤子,像一个地质专家,在石头沟村的西山坡,候山脉:看树、看草、看土、看风水,寻找大自然留下的不起眼的宝藏。
次日,他带着水葫芦、饭包和铁家伙,挖掘山脚。拨去参差不齐的毛发,剥开绿色的皮肤,去掉纵横交错的白色的血管,剔除远古时代留下的健壮的肌肉,裸露出坚硬而白章的骨骼。
白昼与黑夜的切割口,是他进出山的必经之路。他进山的第一锤,就砸碎了大山的宁静。钢钎与石眼的碰撞声,密密麻麻,在山间回荡。他一声呐喊,像惊雷,山摇地动,大大小小的乱石在空中飞舞,如密集的流星雨,清空了山谷葱翠的鸟鸣,落下一支支石质的乱箭,血洗树木花草—蕾不能开放,瓣无法闭拢。
他站在悬崖峭壁上,在山鹰的眼睛里,就像一只趴在骨头上的蚂蚁。二锤,从裤裆抡起,过头顶,过后腰,锤头抛出的弧线大过山峰。落下,铁撑子瞬间入骨三分,应声炸开一条薄薄的缝,石块脱离了母体。
他用的工具有两种。一种是铁质的,比如大锤、二锤、手锤、钢钎、铁撑、镐头、铣头;另一种是木质的把,比如锤把、镐把、铣把。
他的工具消耗也有两种。铁质的被石头磨钝、磨矮、磨瘦、磨小;木质的,则被折断。废掉的工具分类成堆,保存在东房里,足足有千斤。他喜欢看着它们,用坏的工具都卸过他的力,浸入他的汗,有的锈迹斑斑,有的留有掌纹、带着血丝。
他的乳名叫石头。模样跟石头一样,身高肩宽,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黑脸,大鼻子、大嘴、大眼,头发如疯长的山草。他最富有的两样东西—泉水般的力气和白色的石粉。他全身是白色的,石头的颜色,他很像一块喘着气的石头。
他开采的石料,边角分明,大小均匀,没有三尖子八棱,清一色。垒出的石头墙,清一色到顶;盖出的房子清一色,半个村的土屋改建新房也清一色。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给了石头。石头也给了三间青石房,還有他要的衣食无忧。
山体凭空被他撕出一个口子。留下的坑塘,是山的伤口。绿色的胸膛,裸露出五脏六腑。从塘底向上看,只有半个蓝天,半个太阳,半个月亮。那半个,隐藏在他双手托起的悬崖峭壁里。一棵倾倒的松树,一根连着陡峭,松针落光,如过火的枝头长满悲伤。
后来,县里搞山体生态恢复。他留下的石塘坑回填了土,栽上树木及花草。最深的地方顺势建了一个微型湖泊。夏天积攒雨水,积攒一片蛙鸣。他突然感觉很难过,天天跟着工程队出义务工,他想抚平内心深处的忧伤。
再后来,他老了。头发、胡子、眼眉都白了,石粉白。石头最后真的改变了他的面容。他每天上山游弋,义务去看管那片修复的山林。但是,他感觉还是不能弥补对大山的亏欠。
有一天,他带着生锈的铁家伙,在已修复绿林的石塘坑的上坡,又开始挖土、掘石。不几天,就有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坑塘。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墓穴。
他终其一生,想成为一块真正的石头。
3374501908255
——一款接地电阻测量钢钎的研制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