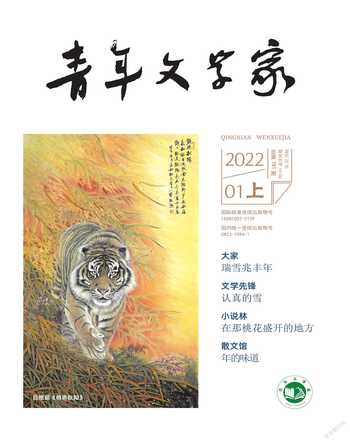年的味道
张宏丽
年是行走在春运路上冗长的思念,年是披一身霜寒推开家门喊妈时的暖,年是父母烹炒出的一桌桌的香甜,年更是新桃换旧符时心头的期盼……
在我的心里,年始终是儿时那段难舍的追忆。腊月前后,母亲的手就日夜忙碌起来。烀豆馅、蒸豆包、织毛衣、纳鞋底、做新鞋、接棉裤脚……一进入小年,父母的身影更忙碌了:扫棚、擦玻璃、拆洗被子、做被褥、做棉衣……那年月,每一个家庭主妇都是一台智能缝纫机。到了年根儿,劈柴、烀肉、做年夜饭,年的忙碌终于到头了。感觉这年的每一个细节里,都浸满了父母辛劳的汗水。年的味道,其实是生活的味道。生活常常是未雨绸缪撑起的那把伞,更是风雨兼程里共渡的船。所以,这年的味道是生活的辛劳。
父母的辛劳换来的是孩子们期盼里的快乐。趁我们三个都在,父亲抓来一把糖块拿给我们,我们分清各自的那几块偷藏起来,悄悄品尝年的香甜去了,还不忘体贴地往母亲嘴里塞一块。过年最少不了的是温暖了。一到年底,父亲就到亲戚家买一袋子煤回来,那炉火终于燃起来了,白花花的木头柈也在灶坑里旺起来了,火焰贪婪地吞噬着木柴,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烧旺了。“油滋啦”(即猪油渣)的香味勾得我们姐弟围着锅台直打转,再看一眼仓房大缸里屯的年货,好富有的知足感溢上来了。年夜饭终于端上桌了,五花扣肉、拆骨肉、小鸡炖酸菜粉、凉菜,那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了。一年的空肚子终于被油水撑得饱胀了。饭后,水瓢里的冻梨从冰坨里掏出来,咬上一口,水灵灵、酸甜甜。最让我们自豪的是,正月里,父亲偶尔露一手他的厨艺:酥白肉、溜肉段、锅包肉,每年能吃到一两道这样的菜,足够我们在同伴面前显摆了。看着我们开心,是父母最大的欣慰。年是孩子们满足了嘴巴,又绽放在脸上的欣喜。
年是父母巧手打扮出来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年是孩子们盼来的那件新衣裳,年是我们手中燃放的烟花……年画、福字、春联、财神,把老屋打扮得熠熠生辉。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父亲将烧热的水盛满大水缸,让我们陆续跳进去洗澡,母亲则挨个儿给我们搓泥球,把我们洗成白净的新孩子。大年初一,我们穿上新衣服,男孩子去拜年,女孩子聚一起赏新头花。秧歌的鼓声“咚咚咚”响在我们的心头,俊俏的小媳妇儿踩着高跷,穿红挂绿扭着酥腰打头排,那模样和装扮简直赛天仙,扛釘耙的八戒和撑船的老汉走在最后,走两步还倒一步。惹得淘气的男孩跟在后面偷放小鞭,吓得女孩子们直躲,生怕崩坏了新衣裳。在困难的年月,年的味道,是父母用勤劳的双手为我缔造的“新”。
在困难的年月,最难得的是那份好心气儿。为了经营这份好心气儿,陆续成长的我们不知道父母吃了多少苦。对新一年的祈望常常在父亲的烟圈里盘算,对好日子的盼望在母亲的织针里穿行。我们躲开正月里的忌讳,仿佛就能讨得新年的好彩头了。在粗茶淡饭的家庭,撑起一份好心气儿,就是给孩子们一片快乐无忧的天!支撑这一切的,不正是父母对我们成长的殷切希望吗?其实,年的味道,更像是为我们编织梦想和呵护成长的那颗苦涩的心。
儿时的年,成了萦怀在年根儿里的追思。如今,什么精美的糖果再也吃不出儿时的甜蜜,任山珍海味也品不出儿时年夜饭的香。这年牵扯着我的记忆,也锻炼出我们勤劳的品质,更滋养着我们的好心气儿。是好心气儿盘活了好生活,父母们在年的盘活里佝偻了腰身,而我们则走进厨房,为父母的健康快乐盘活,为下一代的成长盘活,为一年年的期望盘活。这品不完的年的味道被一代代传承、更新,这年复一年的中国年……
3852500338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