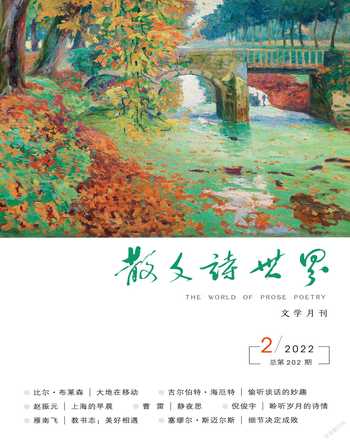慢性病
林晓波
一
单眼皮并不好看,也没有浓眉压堂。小眼睛聚光,提升了我的辨识度:遗传的不是母亲的美丽,而是林氏家族祖传的基因。
自称为高级动物,还不如猫头鹰。在黑夜,人的眼睛不能发光:黑,就是黑。
其实,看不见的东西很多,因为四周隐藏得太深。
说我目光短浅,是因为近视,是因为看不清远大的前途。直到戴着变色的眼镜,我才看清花花世界的媚眼和鸡眼。再把梦想快递到平原,遭遇一场沙尘暴。古老的骆驼静静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在沙漠深处远望。眼睛容不得一粒沙子,宽广的沙漠包容了眼睛:一滴眼泪,在大海中多么渺小,在沙漠中多么重要。
说老眼视野模糊,不是白内障。远视眼让我看不见近处的风景,却看见远处的老祖坟。站在高处,还能看见诗的远方:沙漠上,有数不清的眼睛,绿莹莹的。弯腰俯首,看见沙漠下,干尸的眼眶里,生长多少不死的胡杨。
说我还有散光,看不准自己的穴位和针眼,却要为谁萦绕光环镶嵌虚线。老光在朦胧诗里看见几个月亮,几个老妻。她们活跃在反光镜中,青春在招手,向我们跑来……突然,就停下了。
在老地方,看见一辆破车的警示灯在闪:看不见的尘埃,飞起又落下。
要看见更多隐私,必须紧闭眼睛。
二
百灵在合唱中,能听见自己的啼鸣,是不容易的。乐器在合奏中,能听到自己的颤抖,是不容易的。在市场的交响中,能听见你的呼唤,是不容易的。
隔离时期,真想听听你的笑,你的咳嗽,你的呓语……
半夜,死寂。
一道虚掩的门,等待敲门的声音。快要腐朽的木头,长出无数的耳朵。
围墙外,夜行的汽车在摇晃在发气。谁听见加油的音响,谁又听见刹车的声音?小心!转拐处有坑,差点撞上送葬队伍。谁家的葬礼,如此浩浩荡荡?在亲人的哭喊声中,谁听懂唢呐残缺的叫喊和铜管吹出生锈的歌声?
我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却不适合听风声:老天为我们制造又一场秋雨,亲爱的宠物们在纷纷逃避。围追,堵截。究竟发生了什么?冬至,也听见猫在叫春,蛙鼓悠扬。
前进的灯多么明亮,后退的灯被熬得通红。这就是新一轮疫情期。
三
以一张老相片为证,你看我小时候的丑像:流鼻涕,横着抹。
鼻炎,可以遗传。这才是林家的后代,也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姊妹。说真的,小时候有个绰号就叫“林四鼻浓”。
非虚构故事发展,就有一个小游戏:你的小手绢,正好揩我的花脸。
因为鼻子不正常,口音不容易辨别:地方土语,鼻音太轻太重。说普通话就不标准,就不能朗诵,更不能主持。
鼻炎严重的时候,通道堵塞,出不了气好难受。医生说,我患的是过敏性鼻炎:对什么过敏?原因嘛,自己想:比如鸟语花香,体香四溢,千呼万唤始出来,你为我细细地喷点外国香水。
此时,我失去嗅觉。
长在方正的脸上,就会异军突起。鼻子挺立,还有点骄傲:稍不留神,就碰一鼻子的灰。
过敏,不是过分敏感。
天气异常,暗香浮动,废墟上混杂更复杂的气味。没有特殊的嗅觉,就不如一只导盲犬,或搜救犬。
有时,也想得美:在敏感特区含苞欲放,谁潜伏在花丛中?抚摸一朵花,人的天性也能感觉到红润、细腻和意味深长的,痒。
其实没人,我只能自己摸自己的脸。摸自己的深浅皱纹,抚一个人的山川河流。左手,右手,无论怎样搓,也抹不平遗传的掌纹。意外的是:摸到人类必经之路的陷阱,暗器戳穿了我的掌心。
于是,多了一个心眼。
四
关节炎,成为落后的气象站,不能发出绿色黄色红色警报。
天呀,表情依然丰富,总是一脸苍茫:万里无云,或乌云密布。
天气变化,还有一只留守的候鸟,在阅读我们的病历:慢性病,风湿痛。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就是痛。骨骼错位,骨质分裂,神经更痛。
活了几十年后,听到的还是那句老话:人间的路不好走。无数次跌倒,无数次爬起来,已老得直不起腰来。就像一个屡教不改的问号:人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早年的隐患潜伏在关节,一直都在蠢蠢欲动。天气变化,就频繁活动,伺机报复。
口无遮拦,就是一个洞。这个无底洞填了几十年,也没有填满。
禍从口出:已记不清吃下了多少小菜,也欠了多少条飞禽走兽的命。好在有点味觉,还记得生命的味道:酸甜苦辣。
想起这些,我就饥饿难耐,却感觉到一阵阵胃痛。想起这些,我就说不出话来。总感觉喉咙被什么刺卡住,咳出了眼泪,咳出了鲜血……
咳嗽,就是非常时期的警报。
3780500338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