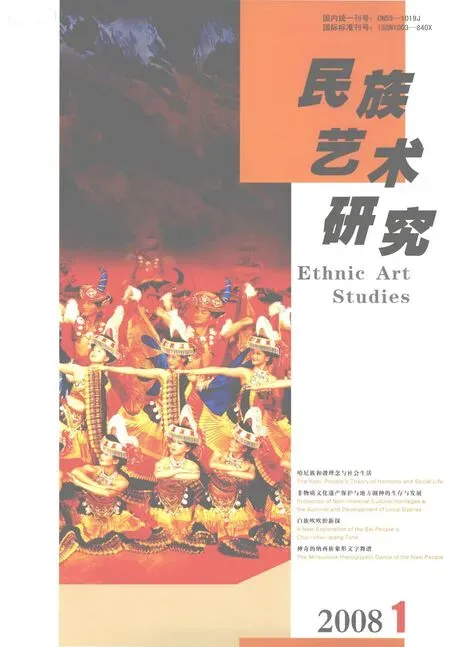历代“绘事后素”注释新解
马 悦,陈 星
“绘事后素”是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的观点,原文如下: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①[春秋]孔子:《论语·八佾》,载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7—160页。
虽然孔子是以绘画之事作比喻谈礼的重要性,并非就绘画艺术谈个人见解,但“绘事后素”历来都是中国画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命题,有关它的注解与辨析亦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这使得“绘事后素”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论题。
一、“绘事后素”注解中的“先素”与“后素”之争
历史上有关《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的注解颇多,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前人的基础上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也。②[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郑玄认为“后素”是指在描绘色彩的工序上应先使用其他颜色,最后再将白色画在这些颜色之间,从而形成清晰的纹理,“素”释义为白色。此后这一观点一直被沿用。
自北宋开始,学者们重新注解“绘事后素”,对以往被沿用的郑玄的解释产生了新的理解。邢昺在自己的《论语注疏》中不仅认可郑玄的解释,还引用了《考工记》以进一步佐证郑玄的观点,确切地说是佐证他自己的观点:
案:《考工记》云:“画绘之事,杂五色。”下云:“画缋之事,后素功。”是知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章也。①[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 —论语注疏》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显然,邢昺在色彩工序问题上沿用了郑玄的解释,不仅如此,他又以《考工记》原文来确立郑玄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尽管郑玄本人并未表明自己的解读是基于《考工记》。北宋官员陈祥道并不认同郑玄的说法,在他为《论语》作的注解中说:“倩盼,质也。有倩盼,然后可以文之以礼。素,质也。有素质,然后可以文之以绘。”②[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卷2,左周校,《钦定四库全书》经部8,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51页。不同于郑玄和邢昺,陈祥道认为女子的“倩盼”是首先需要具备的素质,在此本质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施行礼教。同理,在绘事上,应当先有一个较好的基底,然后才能在其上进行描绘,此处“素”理解为素质。北宋哲学家杨时对“素”的理解与陈祥道一致,他同样认为:“甘采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杨时以甘可以调和众味、白色之上可以描绘其他颜色这两件事来分别作比喻,实则说的是较好的素质对于学礼之人是基础且必要的。这里的“素”仍含素质之意,但具体理解为素白,因为杨时指出了绘画上白色作为底色的道理。
直至南宋,朱熹沿循陈祥道的思路,并吸收了杨时的观点,在二者基础上对“素”作了更具体的注解:
倩,好口辅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朱熹认为绘画需先有“素地”,这是颜色得以描绘的前提,那么这个“素地”到底是指什么呢?此处“素”被理解为“粉地”,朱熹保留了“素”作为白色的这一层意思,并将它与“质”相结合,也就是白底子,正如绘画的开始首先需要一张洁白的画纸,然后才能在其上绘出五彩颜色。由此来看,若说陈祥道的“素”是指一种相对抽象的审美性的话,杨时则指出了“素”具体的物质性层面,那么到了朱熹这里,“素”已经基于前人抽象的审美理解和具体的物质性启发,在内容上更明确、内涵上更丰富了。需注意的是,朱熹同样引用了《考工记》作为自己的参考,却和邢昺的理路完全相反,可见二者对《考工记》的理解并不相同。至此,有关“绘事后素”的注解呈现出一种分歧,即分别以郑玄和朱熹二人的说法为代表。从他们的解释看,郑玄确实是“后素”,而朱熹实则是“后于素”,也就是“先素”,问题的焦点就在于是“先素”还是“后素”。
元明时期,有关“绘事后素”的理解往往沿用了朱熹的说法。明朝张居正就在绘画工序上认同了朱熹的说法,他认为:“如今绘画之工,必先有了质素的地,然后加以各样的彩色,是素在于前,绚在于后。”⑤[明]张居正:《四书直解》,王岚、英巍整理,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清朝以后,考据学的兴盛使得学者们重新反思“绘事后素”的注解歧义问题,不论是基于郑玄、朱熹二人所处年代距离孔子时代远近的考量,还是二人对文本原意的还原度,学者们多认可郑玄的解释,尤其是他们认为宋人在解经时存在误读和主观理解的问题,并重新考察了《论语》《考工记》和《礼器》三者中有关“绘事后素”的说法,力图回到原初语境中探讨“绘事后素”,由此也展开了从郑说与从朱说的争论。清人凌廷堪和全祖望分别是“从郑说”和“从朱说”的代表,然而全祖望认为朱熹虽然对《考工记》的内容有所误解,却并未误解《论语》本义。
近代以来,这一争论仍未中断,钱穆、伍蠡甫等人皆是从郑说的代表,钱穆认为:“古人绘画,先布五采,再以粉白线条加以钩勒。或说:绘事以粉素为先,后施五采,今不从。”①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0页。钱穆是从绘画工序上明确表示不认同朱熹解法的。伍蠡甫则认为:
总的意思是,先用五种颜色,涂成若干的面,因为面和面之间不免交错、重叠,所以再用白色线条界画清楚,把面和面之间的界限加以修整,显得更有纹理,到了这时候也就获得“后素功”了。又因为白色较易融化,须等五色绘好并且干了,才可加上。换句话说,“缋”(绘)指涂颜色,“画”指以素色(白色)画线条。
……“缋”产生的面,被动地反映客观现象;“画”产生的线条,则主动地综合主观和客观,体现了……意和笔的主从关系。②伍蠡甫:《伍蠡甫艺术美学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伍蠡甫虽沿用了郑玄的基本意思,但他重新加入了对绘画创作方法的思考,赋予了“绘事后素”一个新的注解维度。丰子恺、李泽厚则是从朱说的代表,丰子恺认为:“‘绘事后素’,就是说先有白地子然后可以描画。这分明是中国画特有的情形。这句话说给西洋人听是不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画……不必需要白地子的。”③丰子恺:《绘事后素》,载陈星主编、刘晨编《丰子恺全集17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11》,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丰子恺是立足于中国画的传统解读,并且他深知中国画中“素地”的特殊审美意趣。李泽厚的理解是:
“礼”如是花朵,也需先有白绢(心理情感)作底子才能画也。总之,内心情感(仁)是外在体制(礼)的基础。④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4—95页。
李泽厚亦是沿用朱熹的基本意思,但他的侧重点放在了对儒家思想中仁、礼关系的分析上。也有学者认为郑玄遵循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并不是完美的,需要以“礼”来规范,所以是“后素”;朱熹遵循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善的,正像一张无瑕的白纸,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所以是“先素”。⑤李庆本:《强制阐释与跨文化阐释》,《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二人在读解时皆存在主观预设的问题,所以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总体来看,有关“绘事后素”的注解之争,主要呈现出两种观点:或是以经典为参考,将其简单地看作是工艺美术流程中的一个先后问题,实则是为了寻找符合孔子儒学思想的解读;又或是以孔子的儒学思想为依据,通过哲学的思辨推论何种解读更准确。其实不论是这两种角度中的哪一种,所追问的都是孔子的儒学思想,而不是“绘事后素”。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儒学思想成为了“绘事后素”唯一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绘事后素”的注解虽然在郑玄的“先素”说和朱熹的“后素”说中出现了分野,但是实质上被争论的并不是“绘事后素”本身,而是隐含在其背后的孔子的儒学思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儒家经典文本在字义训诂和义理阐释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虽然字义训诂与“汉学”二者并非必然对等,但是主张字义训诂者必然反“宋学”,而主张义理阐释者必然反“汉学”,此为事实。⑥吴根友、孙邦金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913页。那么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先素”与“后素”之分究竟是否符合孔子以素喻礼的儒学思想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二者都是将承载孔子儒学思想的文本作为论述依据的,只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角度,那就是字义训诂和义理阐释。虽然这会导致二者在阐述思路上的不同,但并不会影响符合孔子思想这一前提。显然,孔子在这段对话中意在强调礼之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郑玄和朱熹二人虽是以不同的出发点理解孔子的“绘事后素”,但无论是“先素”还是“后素”,二人实则殊途同归,他们的解读都符合孔子重“礼”的本意。
值得一提的是,伍蠡甫从绘画创作的角度为“绘事后素”开创了一种新的读解方式,即通过绘画的技法与美学思想的结合给出全新的解释。至此,围绕“绘事后素”展开的争论,所思考的内容其实早已突破探究孔子原意问题的局限。丰子恺更是将“绘事后素”置身于中国画传统中解读,甚至与西洋画传统对比探讨,使得“绘事后素”得以逸出原有语境,同时也面向其他绘画传统,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画的范畴。所以对于“绘事后素”的思考,如果纯粹只是探讨孔子原意,则往往会忽视对“绘事”本身的关注;若仅仅只是将其放置在儒学经典和思想的领域中,又会使得对“绘事后素”的理解陷入单一化的层面。其实不论“绘事”所指是工艺美术还是绘画艺术,都不可忽略“绘事”本身对于理解“绘事后素”的重要意义。从“绘事”的角度探讨,也必然会为“绘事后素”的读解创造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
二、“先素”与“后素”是《考工记》中不同的工序
虽然说“绘事”在孔子那里是作比喻之用,但世人在争论“先素”与“后素”的问题时仍离不开“绘事”本身,尤其是“绘事”过程中的工序问题。何以郑玄与朱熹二人都引用了《考工记》,却得到完全不同的解读呢?难道确实如清人全祖望所说,是朱熹误解了吗?《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记载手工业技术的文献,其中对设色工序的记载颇为详尽。设色的工序较为繁复,共分为“画、缋、钟、筐、巾荒”五个工种,这五个工种都与练染工艺密切相关,这些工序的解说具体通过《画缋》《钟氏、筐人(阙)》《巾荒氏》三篇来记述。首先是《画缋》篇:“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五采备谓之绣……凡画缋之事,后素功。”①闻人军:《考工记译注》第11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从原文即可看出“画缋”工序同时包括绘画与刺绣,并且强调颜色的搭配。《钟氏、筐人(阙)》篇:“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②闻人军:《考工记译注》第11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钟”是指给羽毛、丝、帛等染色的工艺;而“筐”条文已缺,可能是记载印花的工艺。《巾荒氏》篇:“巾荒氏湅丝。以涚水沤其丝,七日……以栏为灰,渥淳其帛。”③闻人军:《考工记译注》第12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巾荒”是指练丝、帛的工艺,主要用水练和灰练的方式。显然,制作一件精美的服饰,在工艺上按逻辑顺序应当先是巾荒,通过精炼的方法使丝绸布帛变得柔软洁白;其次是钟和筐,对柔软洁白的布料进行染色和印花;最后是画缋,通过颜色的搭配在已经印染好的布料上进行描绘和刺绣。
从目前出土的汉代考古文物和造纸术的发明时间来看,纸质绘画在当时并不是常态,所以郑玄所指的绘画,并非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纸上绘画,而是指在已经精炼和印染好的优质丝绸布帛之上进行绘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丝锦袍将印花和彩绘方法相结合(如图1),完整地呈现了当时的“画衣”传统⑤印花敷彩纱丝的制作工序是在敷彩之前先用镂版印花模子在素净的丝绸上印好枝蔓,然后再进行彩绘。如用银灰色勾画出蓓蕾,用棕灰勾绘苞叶,再用粉白勾绘。先秦“画衣”属皇后专用,但这件汉代墓出土文物采用了同样的工艺。参见张竞琼、李敏编著《中国服饰史》,东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那么结合《考工记》的内容,可以知道郑玄的注解是对应了画缋这一步,他在制作工序上理解为“后素”完全没有问题,一来白色本身容易被其他颜色污染,二来白色可作最后勾勒花纹之用,素作为“白色”这层意思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此一来,似乎朱熹的“先素”是错误理解《考工记》所记载的“画缋”之意了?

图1 马王堆汉墓出土印花敷彩纱丝锦袍湖南省博物馆藏④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官网,http://61.187.53.122/collection.aspx?id=1361&lang=zh-CN。
其实再次翻阅《考工记》中关于设色工序的记载,就会知道首先是“巾荒”,其次是“钟”和“筐”,最后是“画缋”。而在整个过程中,涉及到“素”的流程并非只有最后一步“画缋”,还有第一步“巾荒”,因为“丝和丝绸必须经过精炼,它们种种优美的品质和风格如珠宝的光泽,柔软的手感,丰满的悬垂态以及特有的丝鸣,才能显露出来,才能染成鲜艳的色泽。”①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如此看来,陈祥道所说的“素”正是指“素质”,这与丝绸精炼的过程是对应的,正如需要丝绸呈现出“种种优美的品质”,绘画也需要一种优质的载体。而杨时所认为的“白受采”,将素作为“白色”来理解,也是与丝绸的精炼和印染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素白的优质丝绸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染色。毕竟洁白的画卷上才能更好地展现色彩原本的瑰丽姿态,不会让色彩因画卷的底色而在视觉上发生改变。那么吸收了二人观点的朱熹,将素理解为“白底子”也就可以理解了。从整个设色工序来看,“白底子”正是呼应了那被精炼后洁白质优的丝绸。朱熹的理解恰恰是因为他关注到了第一步在整个设色工序中的重要性,所谓的“先素”,在此基础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从设色工序的角度来理解“绘事后素”,“先素”和“后素”并不意味着对错,而只是就分别立足于整个工序中的不同步骤而言的。
由此,朱熹虽然在设色步骤上与郑玄关注的不同,但是其解读也是成立的。所以,如果从《考工记》与绘画的角度来看“绘事后素”的注解,郑、朱二人在解读上的偏差,并非是因为某种知识认知上的不同,而是这一问题本就蕴含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技法和媒材等发生变化后,又能够在注解上给予“绘事后素”更多创新的可能。
三、绘画的技法与媒材的变化赋予“素”新的内涵
在绘画问题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郑玄对“后素”的理解基于当时的媒材和技法都是成立的,而朱熹身处的南宋时期绢画亦是非常普及的。也就是说,以丝帛绢布为媒材作画对于郑玄和朱熹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一种作画方式。那么,二人在绘画设色程序的解读上有所不同,显然并非是媒材引起的,更有可能是因为绘画技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里或许应当对绢画技法上的一些特点有所考量。
从当时的一些团扇作品(如图2、3)看,白色颜料确实是最后叠加上去的。一方面是因为花朵本身即为白色的,需要多次叠加才能获得洁白的颜色效果;另一方面这也是白色用于最后调整画面的一种功能,这与郑玄所说的“后素”在方法和目的上并无二致。所谓“后素”这一方法或也可说是对前人设色技法的沿用,但是至宋代,这一技法已然不是绢画设色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中国古代传统绢画的绘制首先进行白描勾线,然后再上色。相对于郑玄所处的汉代,宋代绢画的上色技法已经有所发展。绢画在设色过程中极为讲究步骤,尤其是在绘制工笔画时,第一步往往需要先做好打底工作,用白粉在画卷上打底正是一种常用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调剂一下明度,特别是某些浅色的花和枝叶,都可以根据需要,薄薄地打一层粉底,然后着色。”①袁志权:《国画基础》,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事实上,白粉不仅可以用于正面打底,还可以在描绘人物、花卉等形象时于画卷的背面进行托色。所谓托色也就是上色时需要在绢画的背面先做一层底色,尤其是当画的正面用了一些较浅的颜色时,往往会在其背面先涂一层白色的底色,然后再于正面进行多次晕染,以保证画面颜色呈现出干净鲜艳的效果。当然,“有的花着完色后,还可以用白粉提染……使花朵显得更加鲜艳,更有精神。”②袁志权:《国画基础》,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那么,从这一设色步骤的技法特点看,则完全可以理解朱熹为何会提出“先素”的说法了。

图2 宋佚名《夏卉骈芳图》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② 图片来源:《宋画全集》第1卷第8册,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其实,除了绘画技法的发展,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纸逐渐成为绘画的主要媒材。郑玄所处的汉代纸上绘画定然不多见,但南宋时期纸质绘画早已普及,媒材不同,观念和技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按照当时的绘画思维,在白纸上作画,又何须最后用白色描绘花纹?白纸底色已然洁白,甚至设色时的粉底也可免去,一张质地上乘的白纸成为了关键。那么对朱熹而言,他必然需要重新考量“后素”在步骤上是否仍适用于纸质绘画。
南宋时期纸上绘画已然是常态,在其上描绘五彩颜色时不一定需要最后再用白色勾勒,因为在纸本上画家可以凭借巧妙的留白来表现合适的内容,尽管这对画家的技法、构图和审美观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梅花的设色为例,在绢上(如图3)和在纸本上绘制(如图6)设色方法就完全不同,绢上梅花的花瓣需最后用白色多次叠加,但纸本上可以预先将白色的花瓣部分勾画后空出来,透出纸张本身的白色即可。媒材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绘画方法,但是涉及到画面构图中的改变,往往并不会受媒材的限制,留白的构图方式正是一种审美观念的体现。艺术家丰子恺在《绘事后素》一文中曾谈及中国画构图中的留白:“请看中国画,大都着墨不多,甚或寥寥数笔,寥寥数笔以外的白地,决不是等闲废纸,在画的布局上常有着巧妙的效用。这叫做‘空’,空然后有‘生气’。”⑤丰子恺:《绘事后素》,载陈星主编、刘晨编《丰子恺全集17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11》,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时期山水画家,他们的作品在构图上就体现出了这种“空”的“生气”。马远和夏圭的作品在构图上多呈现出“一角”和“半边”的特点,马远的《水图》(如图4),一共有12幅小图合为一长卷,集中表现江河湖海中水的多种形态特征,在构图上较为简单,基本都是遵循着“半边”的构图法则,内容集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多是空白。夏圭的《松溪泛月图》(如图5),前景是松树局部的精细刻画,稍远处是一叶扁舟和泛舟之人,中景已经没有多少笔触;整张画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前景中,或者说是画面的左下角,留有大量空白处。正因为这种构图上的留白,马远在描绘近处水的形态时得以保留远处水的一望无际之感,而夏圭在留白处反而营造出更空阔的意境,这正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①[清]笪重光:《画荃》,[清]王石谷、恽寿平评,吴思雷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可见,画家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借助媒材的特质创造出了新的绘画方式。这或可以说明,媒材的改变已然为绘画的技法和观念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可能。这也意味着,绘画中如媒材、技法、观念等诸多因素的改变,都会为“绘事后素”的读解提供新的可能。

图3 宋佚名《折枝花卉图》(局部)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③ 图片来源:《宋画全集》第1卷第8册,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图4 马远《水图》(局部)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③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1卷第4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31页。

图5 夏圭《松溪泛月图》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④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1卷第4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图6 佚名《百花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②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1卷第7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如果细看朱熹在自己的注解中所引用的《考工记》内容,就会发现他已经为自己试图重新解读“绘事后素”作了铺垫。朱熹所引用的那句话是“绘画之事后素功。”并且他只引用了这一句内容,而这一句中有两个关键词,那就是“绘画”和“后素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朱熹将原文中的“画缋”二字改为了“绘画”二字,在意思上必定是与原文不同的,那么他将这两个字进行替换是引用错误还是有意为之呢?显然,朱熹并非是错误引用了《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虽然“缋”通“绘”,但“缋事”却并不等同于“绘事”,这一转换,意味着朱熹在读解“绘事后素”时,是将其置于绘画的层面中考量。至此,不得不再次提及郑玄所讨论的“绘事后素”,因为细读原文会发现他所讨论的对象其实也是“绘画”,而非邢昺所引用的“画缋”。由于郑玄也是在绘画的层面里读解“绘事后素”,所以他们二人所讨论的对象是相同的,那就是绘画中的“绘事后素”。“画缋”问题涉及的主要媒材是丝绸布帛,且多以设色或刺绣的方式表现,是更具综合性的工艺美术。而“绘画”涉及的媒材则绝不仅仅是单一的丝绸布帛了,它的媒材更加丰富,表现方式更为多样,同时还会不断被赋予各种艺术观念,是一种专门的艺术门类。这意味着原先的“素”在朱熹的时代则需要面对新的媒材、技法和绘画形式,整个绘画艺术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仍是基于《考工记》解读“绘事后素”,对朱熹的时代而言,彼时“画缋”中的“素”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此时“绘画”中的“素”了。此时的“素”虽仍是主要指白色,但是素白的内涵却变得丰富了。素白不仅是具体的一种物质色彩,如白颜料和白纸,它还可以是一种抽象的审美色彩,如画面中内容丰富的空白。
之所以“素”在内涵上能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绘事后素”能产生“先素”与“后素”的读解,正是因为绘画艺术的时代环境在不断改变。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朱熹所面临的情况,正是需要将“绘事后素”重新放在当时的绘画艺术语境里来解读。他的解读在绘画艺术的技法上必然会与前代《考工记》中的设色工序有所重合,所以对《考工记》的借鉴是必要的,但是亦有大量新的内容是《考工记》无法涵盖的,因此他给出了新的创见。
结 语
尽管围绕“绘事后素”注解产生的争辩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在以孔子的儒学思想为前提的情况下,对于“绘事后素”意涵的辨析更多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纠结于“先素”还是“后素”则是因为对孔子谈论“绘事后素”时的作者意图的不断追问。事实上,孔子的真实意图,我们早已无从得知,留给我们的唯一可以确证的只是文本,这就意味着在读解上具有更多的阐释空间。如果只是从孔子的儒学思想入手进行学理上的推论,则必然使得孔子的儒学思想成为唯一可以解读“绘事后素”的依据。但是“绘事后素”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演变过程中,已经逐渐脱离了孔子儒学思想的限制,不论是工艺美术、绘画艺术还是其他艺术,亦不论是采用画布、画纸或其他材料工具,它早已独立成为一种在不同的门类艺术和不同艺术媒介中皆有一席之地的美学思想。可见,“绘事后素”具有跨门类性和跨媒介性,它所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宽广的,绝不仅限于儒学思想。正是因为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同门类艺术的特点和媒介不断变化的综合作用,赋予了“绘事后素”一种时代性,致使其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内涵,在每一时期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 民族艺术研究的其它文章
- 电影共同体美学与中小成本电影发展
- 徽州纸马的地域特征与艺术要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