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如何讲故事:“巨洞探险”与电子游戏的跨媒介起源
王洪喆
格雷厄姆·纳尔逊(Graham A. Nelson)是一位英国数学家、诗人,同时是电子游戏社群Inform 系统的创建者。在一九九五年的小册子《冒险的手艺》(The Craft of the Adventure )中,纳尔逊将电脑角色扮演和冒险游戏的起源回溯到一位生于一八二0年的混血黑奴—斯蒂芬·毕晓普(Stephen Bishop)身上。作为也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探洞者,毕晓普毕生都在肯塔基州喀斯特地区的猛犸洞(MammothCave)担任向导。猛犸洞,是迄今为止被人类所探测过的最长的地下洞穴系统;而黑奴毕晓普和这座猛犸洞的故事,也堪称现代洞穴探险史与现代电子游戏起源的奇特交汇。
猛犸洞发现于十八世纪末,据传说, 猎人约翰· 霍钦(JohnHouchin)在追逐一头受伤的熊时,偶然发现了洞穴的入口。洞口处蝙蝠密布,在美英战争期间,这里的蝙蝠粪被密集开采,溶解到硝酸盐中以提取硝石制造火药。战争结束后,随着硝石价格的下跌,洞穴一度归于沉寂,直到一具木乃伊的发现。
商人纳乌姆·沃德(Nahum Ward)在一次闲聊中得到了线索,于一八一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早上与两名向导进入猛犸洞,以寻找一具传说中的木乃伊。他在探险日记中写道:“……当我到达占地八英亩的洞室‘主城’(Chief City),看到没有一个支柱支撑整个拱顶时,我感到惊异。在天堂之下,没有什么比这里更宏伟了……”
由于没有现成的地图,在洞中的导航是一个挑战。沃德的探险持续了十九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他终于到达了一处隐秘洞室,发现了传说中的木乃伊石棺。在他的形容中,这是一具约六英尺高,仅重二十磅的女性木乃伊。她直直地坐在石棺中,被宽大的石板包裹着,粗糙的衣服内藏着她的工具、首饰、羽毛和其他护身符。
当然,在现代游戏与迷宫史的视野下,这个传奇故事还有一个简单的讲述方式:一位玩家冒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后,在迷宫的尽头找到并开启了一个宝箱,获得了属于他的奖赏。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故事原型发生在现代游戏尚未出现的十九世纪早期探洞活动中,这为后来猛犸洞与现代游戏起源的交汇埋下了伏笔。
这具木乃伊起初被称为“猛犸洞木乃伊”,后来在一八五二年被命名为“伊福恩·胡夫”(Fawn Hoof)。自一八一六年,“胡夫”被一家馬戏团带到全国巡回展出,吸引了美国各地的观众,猛犸洞因这具木乃伊也迅速为全国所知。在被巡回展出六十年后,“胡夫”被美国国立博物馆斯密森学会收藏。猛犸洞在当时能被列为世界奇迹之一,一半是出于“胡夫”的功劳,而另一半则要归功于开篇的那位黑奴毕晓普。
自十九世纪初,洞穴游在欧洲已成为旅游热点。猛犸洞尽管因木乃伊而名声在外,早期游览者却不多。这跟猛犸洞的巨大规模所带来的探洞风险有关。在地质上,猛犸洞是肯塔基州中部的地下洞穴网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系统之一。
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该洞穴的蝙蝠粪是硝石的重要来源,而正是黑奴为开采提供了主要劳动力。战争结束后,硝石的价格急剧下跌,采矿获利变得不可行。为了寻找新的商机,调查猛犸洞更深层区域的工作随即展开,以进行旅游业的商业开发。由于该地区洞穴之间的商业竞争,大多数调查和地图都是保密的。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猛犸洞成为美国和欧洲旅行者的热门旅游胜地,其经济价值继续取决于奴隶劳动。在十九世纪,带领游客游览猛犸洞的向导一律是黑人,他们要么是洞穴所有者的财产,要么是由附近的奴隶主租借的。在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的种族场景中,这些奴隶成为在南北战争之前的数十年中穿梭于洞中的白人男女优雅举止的保障。
迄今为止,这些黑人洞穴向导中最著名的就是毕晓普。他的所有者富兰克林·高林于一八三八年购买了该洞穴上方的土地,自此他便开始在猛犸洞工作。直到一八五七年去世之前,毕晓普陪同成千上万的白人游客进入洞穴。不管以哪种标准来衡量,奴隶毕晓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自学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以猛犸洞的“首席统治者”著称。他在业余时间探索并命名了猛犸洞的大部分区域,在一年内将已知的地图扩大了一倍。毕晓普开创了独特的洞穴命名风格,半古典、半美国本土气息—冥河、雪球大厅、小蝙蝠大道、巨蛋……他在一八四二年凭记忆绘制的地图,四十年后仍在使用,这些地图直到二十世纪仍因其令人惊叹的准确性而备受关注。
在十九世纪出现的一手洞穴叙事中,毕晓普因其英俊而异域的外表、对洞穴地形和历史的丰富知识以及勇敢的个性而广受赞誉。直到今天,毕晓普仍然出现在美国诗歌、历史小说和儿童故事中—作为十九世纪被遗忘的浪漫英雄、黑人教养和黑人自决的代表性人物,克服了奴隶制对人的异化。但历史学家彼得·韦斯特(P e t e rWe s t)认为,猛犸洞内奴隶制的复杂性无法进行简单的理解。尽管毕晓普经常被贴上“地下世界的哥伦布”的标签,但他和其他洞穴探险者的卓越能力,始终为奴隶主的财富增长服务—因此,他的杰出成就也同时是被剥削的奴隶劳动。而地下世界的复杂性在于,考虑到环境的凶险,黑人导游在白人游客中拥有实际的绝对权威。
就此韦斯特认为,种族动力塑造了十九世纪中叶猛犸洞在美利坚民族国家想象中的独特角色。在整个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猛犸洞成为当时美国流行文化中充满活力的文学象征:抒情诗唤起了洞穴“深沉的忧郁”;伪考古学叙事,描述了长期生活在地下的人类或近人类种族的白人文明;幽灵的故事和传说,讲述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在洞中徘徊困扰着后人;哥特小说将这个洞穴用作谋杀、性背叛和复仇等耸动故事的背景。十九世纪中后叶,猛犸洞不仅成为美国及欧洲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还作为国家形象中的活跃符号,出现在旅行书、抒情诗、私人日记、情书、哥特小说和移动全景画等各类媒介物里。由毕晓普的故事可知,探洞虽然古已有之,但在十九世纪被赋予了与古代截然不同的意义。
作为古希腊神话和哲学中的常用譬喻,物理的洞穴也是先知的所在,洞穴被当作“众神的媒介”。因进入洞穴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状态,洞中的感官剥夺显然与神谕相连。更重要的是,基于爱琴海特殊的地质条件,洞穴释放的毒气会引发欣快或神经毒素反应。因此在古希腊人那里,洞穴所具有的超验属性,使得将先知和洞穴相连成为一种普遍知识。
然而,与将洞穴神秘化的古代经验相反,现代洞穴探险试图将洞穴纳入理性认知的范畴。深入洞穴的探险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项绝对的现代发明。洞穴的独特挑战在于,除了入口区域外,绝大部分是不可见的。结果,洞穴通常没有引起主流科学家和地图史研究者的注意。除了在某些地图上标明洞穴入口外,大多数洞穴在地形图、卫星影像或航空照片上都未予以标明和展现。对于这种缺少自然光,并包含巨大生理和心理障碍的环境,只有现代洞穴探险者,由好奇心和标记这些未知区域的动机驱动,涉险进入洞穴。十九世纪以来,对洞穴的物理探险运动及其衍生的田野文献和制图工作不仅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洞穴学”(Speleology),且为广泛的跨学科工作提供了基础,如考古学、进化生物学、水文学、地质学、地球微生物学、矿物学和古气候研究等。
由此,在现代洞穴勘探史的视野下,猛犸洞即是现代洞穴探险起源处的“元洞穴”之一。然而,现代洞穴探险,不仅仅是一种科学与理性化的过程,而必须同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毕晓普的故事表征了猛犸洞在美国奴隶制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而这项工作同时也为理解现代游戏的起源找到了一条隐秘的媒介谱系线索。
根据主人的遗嘱,毕晓普在一八五六年因出色的工作赎回了自己,获得了自由身。当时,猛犸洞的已探明区域有二百二十六条通道、四十七个穹窿、二十三个坑和八个石瀑。然而悲惨的是,此时的他还没来得及赎回自己的妻儿,就在一年后去世了,终年三十七岁。不过,这位伟大的黑人探洞者,因其留在洞壁上的记号、签名和他绘制的精准地图,依然被世人所记忆,依然活在各种传奇故事中。毕晓普因其对猛犸洞可探明路线的执掌,成为白人进入地下世界游玩的主持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被称作最早的“地下城主持人”(Dungeon Master)。
在毕晓普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探洞成了一门大生意,附近的洞穴遭到激烈的商业抢占。但是,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商业洞穴探险因其劳动分工的变化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隐秘,美国政府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出面,将猛犸洞区域划为国家公园,游客的商业“探洞热”开始减弱。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洞穴探险开始成为一项非营利的科学活动和极限运动。在没有了奴隶作为向导劳动后,这种极限运动只能以社群和共享的方式发展,其沉没成本和不可控性意味着其很难被商业化。
“二战”后,探洞發烧友社群中流传着一个传说—猛犸洞和附近的火石岭洞穴(Flint Ridge Cave System)有一条通道相连。六十年代,探洞社群对连接入口进行了多年的秘密探索,尝试了所有从火石岭通往猛犸洞的可能连接,都失败了。直到一九七二年九月九日,瘦削的计算机程序员派翠西亚·克劳瑟(Patricia Crowther)所领导的探险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她在通过一处被命名为“窄点”(Tight Spot)的区域后发现了一条泥泞的通道——进入猛犸洞的隐蔽途径。有趣的是,一百一十五磅的克劳瑟在挤过窄点后,发现墙上潦草地刻着“Pete H”,还有一个指向猛犸洞的箭头。通过查阅档案,探险家们得出结论,该记号来自探险家彼得·汉森(Peter Hanson),他在三十年代就到达过这里,后在“二战”中丧生。
洞穴中奇妙的相遇连通了不同的时空,发现“窄点”的七十年代初,也可被称为现代游戏历史的“窄点”时刻,奇妙的连接就发生在此刻。
一九七二年,派翠西亚·克劳瑟和她的丈夫威尔·克劳瑟(WilliamCrowther)正受雇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的承包商BBN。威尔是BBN 旗下阿帕网(ARPAnet)开发团队的创始成员之一。阿帕网作为互联网(Internet)的前身,其中威尔参与的程序开发又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可以说,他们在七十年代的工作直接促成现代互联网的诞生。同时,在冷战军工部门宽松的工作环境中,这些麻省理工的毕业生也成为刚刚兴起的桌上游戏《龙与地下城》的爱好者。两人同时是洞穴探险社群的活跃参与者,威尔利用妻子派翠西亚编写的程序绘制猛犸洞的地图,并制作成手册共享给社群。
然而不幸的是,派翠西亚与威尔的婚姻在一九七五年结束了。派翠西亚于两年后与探洞社群的另一灵魂人物约翰·威尔科克斯(JohnWilcox)结合。在与妻子离婚后,为了让两个女儿在来访时开心并改善亲子关系,悲伤的威尔于一九七六年利用业余时间,以PDP-10为平台用FORTRAN 语言编写了一款名曰《冒险》(Adventure )的文字互动游戏—游戏的舞台即用计算机模拟还原了猛犸洞中夫妇二人曾经最喜爱的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在最初版本的《冒险》里找到许多现实猛犸洞中的元素:洞穴探险者会在矿灯闪烁时回头;洞壁上神秘的标记和签名缩写—有些是十九世纪的黑奴矿工和向导留下的,还有些是二十世纪的探险者留下的。在后世电子游戏中被广泛使用的“房间”(room)一词,也是来自探洞社群命名洞室的术语。游戏同时借鉴了《龙与地下城》的要素,在后续迭代版本中加入了肯塔基中部没有的活火山、龙和矮人。游戏名称后来改为《巨洞探险》(Colossal Cave Adventure ),即现代电子游戏史上第一款冒险与角色扮演游戏。
关于这段经历,威尔在回忆中写道:
当时我正痴迷一款名为《龙与地下城》的桌面游戏,并且一直在积极参与洞穴探险运动—特别是肯塔基州的猛犸洞。 突然间,我卷入了一场离婚,这让我在各个方面都有些分崩离析,特别是想念我的孩子,探洞也停止了,离婚令社群变得很尴尬。所以我决定放空自己,写一个程序,以在幻想世界重建我和前妻的探洞经历,同时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也许还纳入我一直在玩的《龙与地下城》。 我的想法是,这将是一款不会让非电脑用户感到害怕的电脑程序,这也是我制作它的原因之一—让玩家使用自然语言来输入指令,而不是更标准化的程序命令语言。 我的孩子们认为这很有趣。
一九七六年之后,《巨洞探险》的拷贝开始在阿帕网的早期节点上扩散开来,成为军工和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中最流行的程序之一。也就是说,一款关于物理洞穴网络的文字游戏,开始在新生的数字网络——阿帕网上传播开来,而这款游戏的制作者,作为国防部的雇员,又身兼探洞者和现代互联网开发者的双重身份。由此,在七十年代这个现代游戏史的“窄点”时刻,《巨洞探险》就成为连接物理和虚拟两个网络世界的“窄点”,也成为连接冷战史与游戏史的“窄点”。
当《巨洞探险》于一九七七年春季到达麻省理工时,那里的玩家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创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文字游戏《魔域》(Zork )和第一个专注开发此类游戏的新公司Infocom,该公司开发的数款文字冒险类游戏在八十年代畅销不衰。这段时间,受《巨洞探险》启发的一系列游戏成为在计算机和其他主机上第一个风靡且被成功商业化的电子游戏类型,其中最著名的,应属雅达利(Atari)的游戏设计师沃伦·罗比内特(Warren Robinett)于一九八0年开发的2D图形游戏,也叫作《冒险》(Adventure )。该游戏被称作第一个图形版的《巨洞探险》,在八十年代售出了一百万套。
不过,雅达利的《冒险》之所以在游戏史上成名,最重要的并不是因其销量,而是因为这款游戏中埋藏了游戏史上第一个“彩蛋”。在电影《头号玩家》中,男主人公韦德在绿洲挑战赛中进入的最后一道关卡,即是在雅达利二六00(Atari 2600)主机上玩《冒险》,而通关方式也并非打穿游戏,而是通过密道抵达游戏中的“像素厅”(Pixel Room),找到作者罗比内特秘密刻在洞壁上的“彩蛋”—“沃伦·罗比内特创造”(Created by Warren Robinett)。而这个瞒着老板埋藏在游戏中等待玩家发现的彩蛋,正是为了抗议雅达利公司对游戏作者署名权的剥夺和在经济上不公正的待遇。
自此之后,作者在电子游戏中埋藏署名彩蛋成为惯例。而《冒险》中这个铭刻在“像素厅”洞壁上的数字签名,与毕晓普等黑人向导铭刻在猛犸洞壁上的姓名缩写遥相呼应,恰恰成为猛犸洞奴隶史在二十世纪游戏史中的苦涩回声。
在冒险和角色扮演类游戏中,不仅游戏的迷宫设计,对应了自然洞穴的物质性拓扑结构,其对话树的设计,也对应了洞穴探险运动中对洞穴分支结构的遍历性探索方式,即在媒介谱系研究的视野下,电子游戏的互动性叙事,也是对洞穴遍历性探险的模拟。因此可以说,现代电子游戏是在空间构造和叙事构造的双重意义上模拟洞穴探险。
由此谱系出发,可以发现,多种电子游戏的设计都具有类似的媒介特性:将裸露的开放世界“洞穴化”,成为某种有待开启的一连串未知洞室的连接。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游戏世界,就其本体而言都可被视作“洞穴”或“地下城”。例如,在早期文字MUD(多用户虚拟空间游戏,是文字网游的统称)游戏《侠客行》中,门派取代了洞穴组成了玩家需要遍历的游戏世界;进而,在图形化的《金庸群侠传》中,古代中国地图被描绘为一个由门派所连接的地理网络,在门派之外的中原世界一无所有。在游戏中,我们必须将开放的地面世界洞穴化,将不可遍历的无限世界有限化。
那么,在电子游戏的洞穴迷宫中游走究竟为何让人着迷呢?回到开篇纳尔逊的观点,他在《信息设计师手册》第四版中概述了这种游戏流派的起源—从斯蒂芬·毕晓普的故事开始,他是洞穴探险家、制图师和奴隶,他曾在巨大洞穴内担任导游,以期为妻儿购买自由。纳尔逊写道:“第一个冒险游戏的底色是由两个失落的灵魂斯蒂芬·毕晓普和威尔·克劳瑟塑造的,这让人很难不感到悲伤,他们两人都像俄耳甫斯一样无法将自己的妻子从地下带回。”游戏研究者丹尼斯·杰茨(DennisG.Jerz)认为,虽然将两个人都钟爱的山洞与奴隶制、离婚和死亡进行比较,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戏剧化,但纳尔逊却恰当地指出,正是“悲痛”,成为将毕晓普和克劳瑟在巨洞中所经历的冒险情境化的直接动力。
对于克劳瑟的孩子来说,玩这款游戏一直是在父母离婚后怀念父亲的方式。克劳瑟夫妇的一位前洞穴同伴在回忆七十年代初期的探洞社群文化时称,二人的婚姻破裂是这个社群的一场灾难。直到三十年后,这个共同的朋友本人仍然在承受这种痛苦,他说只要瞥一眼《巨洞探险》就足以立即将其识别为一种情感宣泄,这是威尔为重建失去的爱情和家庭而进行的尝试。
由此,游戏迷宫的故事并不是任意的,迷宫遍历的过程,是一个将已经破碎流逝之物还原的过程,是逆时间回溯的过程,因而也是对抗死亡的过程。在没有地图(历史)作为参照的前提下,只能通过遍历所有的分支去对抗死亡。而游戏中的存档和读档,也即意味着回到迷宫的上一个岔路口—只有出现了岔路,才需要存档,即是对可能的死亡进行标记。在这个意义上,游戏也可被理解成一种“档案媒介”。
在电影《妖猫传》中,空海和白居易跟随妖猫的指引,在长安城迷宫的尽头,终于拼凑起杨贵妃悲剧的一生;在《頭号玩家》中,韦德通过翻找隐藏在“绿洲”档案馆中的线索逐渐了解迷宫作者哈利迪(Halliday)的一生,并以此连闯三关得到三把钥匙,在迷宫的尽头开启了作者童年的房间,与哈利迪的副本相遇,并通过最终的考验战胜资本,完成对“绿洲”所有权的交接;在获奖游戏《极乐迪斯科》(Disco Elysium)中,玩家扮演的警探在迷宫尽头的海岛上,遭遇了革命逃兵和自己失落的爱情。
因此,在迷宫的尽头,玩家(洞穴探险者)往往会与迷宫作者最隐秘的内心相遇。也可以说,在任何游戏的最后,你终将会遭遇作者。然而这种体验不必然是与作者的共情,也可能正相反,在今天绝大多数氪金游戏中,玩家在绝望的充值内购的尽头所遭遇的游戏作者,只是将玩家和程序员都作为奴隶去剥削的洞穴奴隶主—氪金游戏的所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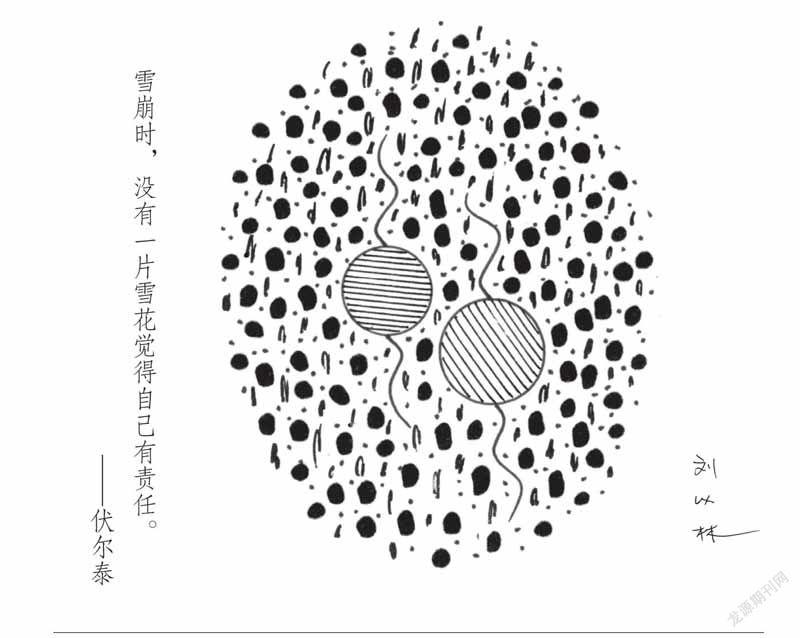
至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角色扮演、冒险和解密类游戏中,迷宫那与生俱来的“深沉的忧郁”。我们必须回到现代游戏媒介的历史物质性谱系,去破译凝结于其中的奴隶史、冷战史、物质史与情感史的交织。正是由伤感所带来的“强迫性重复”,驱动了迷宫中绝望的游走—寻回不可寻回之物,挽回不可挽回之情,反抗不可反抗的压迫,逃离不可逃离的死亡。也许正是这种绝望,成就了电子游戏作为“世纪末”媒介的魅力及其注定的局限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