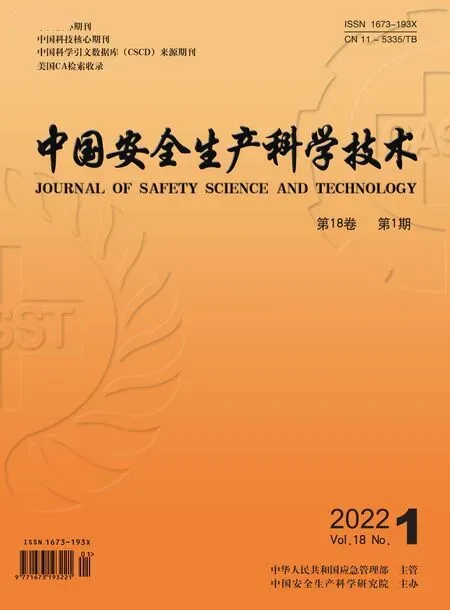防疫豁免政策下的飞行机组舱内警觉性预测仿真*
孙瑞山,孙军亚,何 鹏,卢 飞
(1.中国民航大学 飞行分校,天津 300300;2.中国民航大学 民航安全科学研究所,天津 300300;3.中国民航大学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天津 300300)
0 引言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蔓延,在带来生命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对各国各行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民航业作为全球性质的行业,其市场的发展与全球疫情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为适应疫情防控要求,中国民航局出台了多项疫情防控措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肩负起保障运输生产的重任。其中,为满足紧急情况下的客货运输要求,并有效保障机组成员的健康,民航局依据 CCAR-121 部规章要求对部分运输航空公司的机组成员值勤期和飞行时间限制实施了临时偏离批准。同时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并为进一步规范疫情期间对使用多套机组在国际洲际航线运行中实施延长机组成员值勤期和飞行时间的管理,民航局制定和发布了〔2020〕53 号文《疫情期间豁免机组成员值勤期、飞行时间限制的实施办法》[1](以下简称“豁免办法”)。由于机组成员的值勤期和飞行时间的延长,以及多套机组同时在线的工作模式,如何预测和监控机组成员超负荷工作下的疲劳状况以及航线运行过程中舱内飞行人员的警觉度变化,成为局方和公司监管的重点。
预测机组成员疲劳状况和警觉性变化的传统方法分为主观和客观评价法。其中,主观评价法因其主观性较强,存在不确定性,且在航线结束后才能收集机组成员数据,因此不能较好地在航班计划之前进行疲劳状况预测和评估;客观评价法虽然检测疲劳准确性较高,但因受限驾驶舱内的工作环境以及行业规定,也不适合飞行过程中机组成员的疲劳监测和评价[2]。2012年,国际民航组织建议各国建立疲劳风险管理系统(FRMS),指出要基于科学有效的原理和测量结果,以数据为驱动,以连续的过程来监视和管理疲劳风险,在FRMS中的预测性疲劳风险识别过程给出了另1种可行的方法——生物数学模型[3]。同时,生物数学模型也是现在国际上比较认可的1种科学分析方法。疲劳的生物数学模型可以根据人体基本的生理数据,对飞行员1天中的每时的疲劳程度进行预测,能评估和监测机组成员在值勤和飞行过程中各个时刻疲劳程度,同时解决了飞行员疲劳定量度量的问题,这对机组排班值勤之前飞行疲劳的预先干预、驾驶舱内机组成员警觉性的监测、机组成员疲劳状况的评价、以及保障航线飞行安全有着重要意义[4-5]。疲劳的生物数学模型是通过将与生物体相关的生理参数作为输入数据,建立一系列方程组形式的数学模型,其将对人体昼夜节律、睡眠、工作负荷以及警觉度等与疲劳风险相关地科学研究与航班生产计划和安排进行了整合,能够较直观体现计划值勤期内疲劳的变化趋势并预测潜在的疲劳风险。目前有关疲劳生物数学模型可以划分为理论型和应用型[4],理论型疲劳生物数学模型包括睡眠调节的双机制模式(two-process model of sleep regulation,TPMSR)[6]和警觉性3过程模型(three process model of alertness,TPMA)[7];应用型疲劳生物数学模型包括机组疲劳评估系统(system for aircrew fatigue evaluation,SAFE)[8]、睡眠、活动、疲劳和 任 务 效 率 模型(sleep activity fatigue and task effectiveness,SAFTE)[9]、昼夜警觉性模型(circadian alertness simulator,CAS)[10]、疲劳动态评估模型(fatigue audit interDyne,FAID)[11-12]、交互式神经行为模型(Interactive Neurobehavioral Model,INM)[13]、睡眠/唤醒预测器(Sleep/Wake Predictor,SWP)[14]以及警觉能心理疲劳风险模型(alertness energy mental fatigue risk model,AEMFRM)[15]等。其中一些已经商品化,作为预测与排班相关的疲劳危险的工具在市场上销售,这为民航机组成员疲劳的量化和监测提供了有利工具。
本文在警觉能心理疲劳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对“豁免办法”规定的飞行时间限制下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警觉性进行数值模拟仿真预测,以某飞行员在执飞任务前的入睡时间、觉醒时间、排班表和机上轮休时间作为输入,建立飞行员在驾驶舱内工作期间警觉度的预测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然后,以相同办法对“CCAR-121部”规定飞行时间限制下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警觉性进行仿真分析;最后,通过“豁免办法”和“CCAR-121部”的驾驶舱内机组成员警觉度的分析结果,验证局方为适应疫情防控要求所制定发布的“豁免办法”的合理性和安全性,并为其提供疲劳监控与管理的科学支撑。
1 问题描述与模型建立
1.1 问题描述
“豁免办法”规定:对于客改货航班、货班、及具有独立休息区的客班,当配备的飞行机组的数量为3套(每套飞行机组至少由1名具备机长(含巡航机长)资格及1名具备副驾驶资格的人员组成)时,最大飞行时间限制为26 h,当配备的飞行机组的数量为4套时,最大飞行时间限制为30 h;对于无独立休息区的客班,配备3套及以上的飞行机组,最大飞行时间限制则为21 h[1]。而在“CCAR-121部”R5中的P章第483条《飞行机组的飞行时间限制》并未对3套及以上数量的扩编机组的飞行时间限制做出明确说明,“CCAR-121部”规定[16]:对于配备3名驾驶员的扩编飞行机组执行任务时,总飞行时间限制为13 h;对于配备4名驾驶员的扩编飞行机组执行任务时,总飞行时间限制为17 h。因此,有必要将“CCAR-121部”现有的飞行时间限制规定作为比较基准,对“豁免办法”中延长飞行时间规定的可行性与科学性进行论证分析。
延长飞行时间限制,直接增大了飞行机组的工作负荷,从而容易导致飞行员疲劳,对航班安全运行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豁免办法”在延长飞行时间限制的同时,增加了飞行机组的数量,并提出了飞机上休息设施的要求,以期降低机组工作负荷,缓解机组人员的疲劳,保证航班安全可靠的运行。本文基于警觉能心理疲劳风险模型,从能量的角度来量化警觉性,将“警觉能”作为反映飞行机组疲劳的量化指标,以机组成员任务前的入睡时间、觉醒时间、排班表和机上轮换时间等为自变量输入建立模型,对飞行过程中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警觉性进行预测,以及通过对比“豁免办法”和“CCAR-121部”2种规定下驾驶舱机组成员警觉度的变化情况,验证“豁免办法”下机组成员疲劳精神状况符合工作要求,解决飞行过程中驾驶舱内机组成员警觉性定量度量问题以及“豁免办法”缺乏可行性与科学性论证的问题。
1.2 模型建立
当睡眠时,假设人睡眠开始时刻为t0,则如式(1)所示:
(1)

(2)

另外,警觉势能的表达式如式(3)所示:
(3)
式中:t为时刻;φ1,φ2为相位;c1、c2为余弦周期函数的振幅。
根据式(2)和(3)得出清醒时的警觉动能A的方程式如式(4)所示:

(4)

在上述警觉能疲劳风险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再通过确定模型中睡眠倾向系数β、睡眠亏损系数ξ、警觉势能节律中的相位φ1和φ2、振幅c1和c2、固有消耗率Ka、睡眠质量a、工作负荷消耗率Kw的值,即可得到人在t时刻下警觉动能A的值[15]。
由此表明,矿床成因与火山作用的关系密切,铁矿的物质来源是与火山作用同时带出的硅、铁质有关。成矿是在较稳定的远离火山活动中心的海盆地中沉积形成的。因此其成因类型为海相火山沉积变质铁矿床。
1.3 驾驶舱工作环境下模型参数赋值
首先,根据Hursh等[17]的研究,其用余弦分析法拟合昼夜节律方程,然后再依据现有的理论研究及睡眠剥夺实验[18]。本文中的警觉势能节律与昼夜节律方向相反,因此可确定出警觉势能节律中的相位φ1和φ2应取值为1.481与1.769,振幅c1和c2应取值为0.92与0.26;另外,结合普通人每日所需的睡眠时间(8 h)和清醒时间(16 h),取睡眠倾向系数β=10,睡眠亏损系数ξ=0.2;研究发现当工作负荷消耗率Kw为0时,清醒状态警觉能A由100减小为0,大约需要4 d[18],则警觉能大概以每天25%的速度减少,因此警觉能静态消耗率Ka为每小时1.042个单位,故取Ka为1.042。
睡眠质量受许多因素影响,本文选取住宿场所自评Sc、休息设施Sd、睡眠感受Sf作为评判睡眠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构建飞行员睡眠质量a的表达式如式(5)所示:
a=Sc×WQ1+Sd×WQ2+Sf×WQ3
(5)
式中:a为睡眠质量;Sc为住宿场所自评;Sd为休息设施;Sf为睡眠感受;WQ1,WQ2,WQ3分别为睡眠因素的权重,其赋值见表1。

表1 模型中相关参数等级及其赋值Table 1 Levels of related parameters and their assignments in model
警觉能消耗率K等于固有消耗与工作负荷消耗率之和,即如式(6)所示:
K=Ka+Kw
(6)
式中:K为警觉能消耗率;Ka为固有消耗率;Kw为工作负荷消耗率。工作负荷消耗率Kw应与民航飞行员的职业特点相关,本文选取飞行员的职位等级、航线难易程度2大主要影响因素,构建飞行员工作负荷消耗率
Kw的表达式如式(7)所示:
Kw=We×me+Wc×mc
(7)
式中:Kw为工作负荷消耗率;航线难易程度又受航线艰难程度因子me和航线飞行经验mc影响;We和Wc分别为其权重;相关系数的赋值见表1。
需要注意,本文公式中各类参数给定、等级、赋值和权重是充分借鉴以前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客观测量法对实验设备与实验条件要求太高,不适合作为模型的输入的参数确定,采取主观量表测量法进行确定[18]。
2 仿真与结果分析
根据建立的驾驶舱飞行机组警觉能模型,选取某航空公司飞行员排班计划进行仿真分析,通过MATLAB程序计算“豁免办法”和“CCAR-121部”2种飞行限制时间条件下的驾驶舱机组成员警觉性变化。
2.1 2种飞行限制时间条件下的排班情况
选取“豁免办法”中“3套机组/26 h飞行时间限制”,简称“3套/26 h”;“CCAR-121部”中“3名驾驶员/13 h飞行时间限制”,简称“3名/13 h”。
表2介绍了“3套/26 h”的排班表信息,表3和表4分别介绍了“3名/13 h”的排班表去程和返程信息。

表2 “3套/26 h”限制下排班Table 2 Schedule under “3 sets/26 h”restriction

表3 “3名/13 h”限制下排班(去程)Table 3 Schedule under “3 persons/13 h”restriction (departure)

表4 “3名/13 h”限制下排班(返程)Table 4 Schedule under “3 persons/13 h”restriction (return)
其中,为简化描述,在飞行中飞行员有3种状态,分别为:在驾驶舱飞行(飞)、在休息舱没有睡眠的轻松休息(休)和在休息舱睡眠(睡)。假设开始时间为上午10点,表中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2.2 驾驶舱机组成员的警觉能参数选择
在警觉能仿真中,假设初始条件:去程时飞行初始时刻机组的警觉能初始值为98,返程时警觉能初始值为95(考虑时差的影响)。飞行员警觉能模型中的参数见表5。

表5 模型中相关参数的默认值Table 5 Default values for relevant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2.3 驾驶舱警觉能仿真结果
由图1可知,“3套/26 h”限制下驾驶舱飞行员在去程飞行结束后警觉性降至77.835 1,返程飞行结束后警觉性降至80.651 8。

图1 “3套/26 h”限制下驾驶舱内飞行员警觉性变化Fig.1 Variation of pilot alertness in cockpit under “3 sets/26 h”restriction
由图2可知,“3名/13 h”限制下驾驶舱飞行员在去程飞行结束后警觉性降至73.806 7和83.114 0,返程飞行结束后警觉性降至71.543 6和82.273 9。

图2 “3名/13 h”限制下驾驶舱内飞行员警觉性变化Fig.2 Variation of pilot alertness in cockpit under “3 persons/13 h”restriction
因此,在航班去程时,“3套/26 h”限制下驾驶舱内飞行员警觉性最低值77.835 1,同比高于 “3名/13 h”限制下驾驶舱内飞行员警觉性最低值73.806 7;航班返程时,“3套/26 h”限制下驾驶舱内飞行员警觉性最低值76.619 4,同比高于 “3名/13 h”限制下驾驶舱内飞行员警觉性最低值71.543 6。并且在航班过程中,“3套/26 h”限制下驾驶舱内飞行员警觉性均相近于或优于 “3名/13 h”限制。综上,在上述排班和轮换安排下,按照“豁免办法”中的“3套/26 h”限制飞行的驾驶舱飞行员警觉性优于“CCAR-121部”规定的“3名/13 h”限制。
另外,自“豁免办法”发布之后,相关航空公司根据规定已经安全运营了万小时以上/千班航班,未发生1起不安全事件,从实际运营层面对“豁免办法”进行了有利的实践验证。
3 结论
1)通过模拟仿真结果和分析,“豁免办法”中3套机组,每3~4 h换岗1次的排班搭配,飞行26 h,整体优于“CCAR-121部”中3名扩编飞行机组飞行13 h的驾驶舱中机组成员警觉性。因此,通过对比2种规定下驾驶舱机组成员警觉度的仿真结果,验证了“豁免办法”规定下机组成员在驾驶舱内的疲劳精神状况与“CCAR-121部”相近并整体较好。
2)另外,对于客改货/货班/独立休息区客班性质的航班,采用3套机组,在飞机上给机组提供满足要求的休息场所,机组在目的地不过夜而随机返回的方式,在整个飞行任务执行期间,飞行员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安排作息,从而可以减少时差导致的疲劳。
3)在使用本文中赋值的各项参数情况下,验证了“豁免办法”可行性与科学性,模型对航空公司的航班计划与机组的轮班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