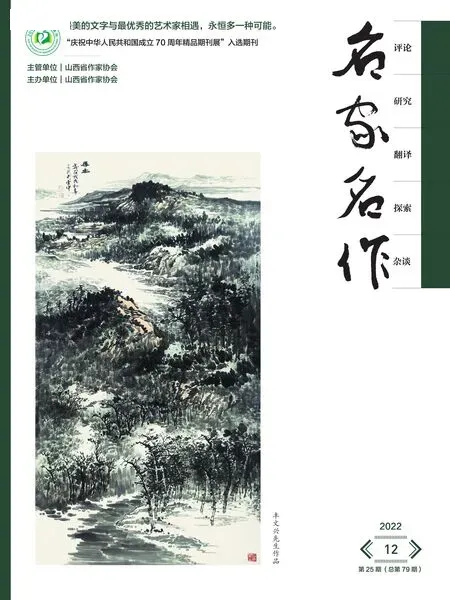以美育人的中华文化传统研究
——兼论“红色文学”信仰价值
陈艳华
以美育人,就是依托美的内容和美的形式化育人、塑造人,也就是美育。近年来中国的美育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美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实际上以美育人并不是一种“新时尚”,美育思想古已有之。古希腊的雅典教育,将智育、体育、艺术教育有机结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艺术教育就是“美育的一种雏形”[1]。几乎同时期的中国先秦,以六艺来“明人伦”。其中“乐”在当时不仅仅指音乐,还包括诗歌、舞蹈、绘画、建筑、雕镂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艺术教育,用来陶冶情操、修养道德,“也是美育的雏形”[2]。
一、以美育人与礼乐传统
根据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儒家美学其来有自,有悠久坚实的历史根源,它是‘礼乐’传统的保存者、继承者和发展者。”[3]揭示了中华美学的根源是“礼乐”传统。同样,“礼乐”传统也是中华美育的根源。
“礼”和“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礼”指的是氏族部落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活动规范;“乐”是诗乐歌舞等艺术样式。“礼”和“乐”各自的分工是什么?“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谐化;序,故群物皆别。”“礼”的核心精神是秩序,“乐”的核心精神是和谐;“礼”侧重的是外在的规范,而“乐”诉诸的是人的内心;二者的政治功能是一致的,即维护既定政治的和谐稳定。如果延伸到个人,“礼”和“乐”的作用如何?“礼”可以作为端正自己行为的标准;“乐”可以用来协调自己的知、情、意,达到内心的和谐。内心和谐是行为端正的前提,行为端正是内心和谐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
孔子是“礼乐”的坚决维护者。他的著名观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儒家教育的宗旨,也是以美育人“礼乐”传统的根基。
(一)“立于礼”
孔子的育人理想是培养君子。“立于礼”,是说人只有经过“礼”的各种训练才能自我建立。但是,孔子的以礼立人之“礼”,并非表面上的外在规范,它自有其内核,那就是“仁”。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再恪守礼节,再讲究仪礼,再奢华的礼物,再热闹的钟鼓,都是毫无价值的。不在于形式是否完备,而在于情感是否真诚,也就是孟子所主张的“仁者爱人”,对他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这里,真诚的情感、内心的善良就是一种内在的德性。这也是孔子一直主张的引“礼”归“仁”。
众所周知,“礼”起源于宗教祭祀的礼仪,对形式的要求比较严谨。到了孔子的“仁礼并重”,实际上是对“礼”的发展。“从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外在社会的伦常秩序反过来必须依赖于内在的‘知、仁、勇’的主观意识修养才能建立和存在。”[4]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明显强调内在德性对“礼”的规约作用,如此,“礼”似乎成了人表达内在需要的相应形式。所以,孔子的“立于礼”,是有“仁”做基础的,并非被动地受制于规范制度,而是有着化被动为主动的自驱力:于己,自愿习“礼”,养成良好习惯;于人,少制约,多涵泳,这也是现代美育的旨归。
(二)“成于乐”
孔子的引“礼”归“仁”,凸显了内在心灵完善的重要性。怎样达到个人内心的完善?孔子认为是“成于乐”。一个人,就算智慧、克制、勇敢、才艺等身,如果没有乐的修饰,那也不能达到内心的完善,不能成为“完人”。可见孔子对“乐”的重视程度。
孔子主张音乐以“中和”为美,所谓“乐尔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便形成了中国美育传统中的“温柔敦厚”之风。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内心的仁爱使然。比如他评价《韶》乐尽美尽善而《武》乐尽美未尽善,是因为孔子觉得周武王用武力得天下,《武》乐有杀伐之气;而舜帝禅让得天下,所以《韶》乐具有平和之美。所以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孔子对音乐教化的重视。
孔子之所以重视“乐”的教化作用,和音乐本身的特性有关。“感于物而动”,“乐”是直接发自内心的,它源自情感,情感源自外物。那么反过来,“乐”的化育作用往往能够直达人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即便是仁德的言辞也有说教之嫌,具有教化的乐声却可以让人感动,唤起人向善向美的意愿。德育的主要方式是说教,美育的主要方式是涵濡。孔子主张以“乐”成人,这就相当于美育的涵濡功能。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始终重视以感性体验方式养成人格。孔子的“兴于诗”,兴的也是人的情感。诗教、礼教、乐教,共同强调对人心的教化,促进内在自觉的提升,达成人格的完善,追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合之美,由此形成了中国美育深厚的文化传统。
二、以美育人文化传统的现代性发展
儒家“礼乐”传统孕育了中华美育精神。时光荏苒,礼乐教化的传统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从情感体验入手、注重人心涵濡的原则却一直延续。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瞄准了美育。柏拉图、康德、席勒等人的美育观念,拓展了“蔡元培们”的视野,他们一方面见识到了西方现代美育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在西方现代美学的启发下,他们不断回看并反思“礼乐传统”之下的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并逐步确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美育理论及传统。中华美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席勒等人的思想进入中国之前,它并不成体系,只是以零散章句的形式存在于古代论著之中,最早将中西美育思想与美育理论结合起来诠释的是王国维。他的《孔子之美育主义》在这方面具有开拓作用。
(一)王国维:发现并确立中国美育理论
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王国维引用康德、席勒等人关于“美可以消除一己之私欲”方面的理论来解释孔子的美学思想:“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徒言志,独与曾点……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可知也。”[5]所以,王国维如此结论:“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6]在这里,“始于美育”指的是“兴于诗”,“终于美育”指的是“成于乐”。王国维创造性地运用了席勒的“无用之用”将东西方美育思想沟通,从孔子到席勒,跨越两千多年,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彼此在审美教育理念上的惊人相似,孔子重视诗、乐涵养,推崇自然对人的陶冶,其实就是席勒以无功利的审美和艺术来消除人的熏心利欲,由此修炼成“无欲”“纯粹”之“我”,进入自由的境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王国维通过他的《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在中西美育思想的比较中确立了中国美育传统的要义:“美育是一种情育”[7],即从特性上来说,美育是感性教育;从目标上来说,美育是要实现人格的完善。在此要义上,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更进一步的发展。
(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美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中“以美育代宗教”是著名的理论。根据蔡元培先生的理论,美育之所以能够代替宗教,是因为二者都作用于人的情感,并且都指向人的信仰。宗教和美育共同的信仰是肯定某种力量的存在,宗教肯定的是超自然的力量,美育肯定的是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以美育代宗教”理论的提出,是有着世界性的学理背景的。从世界美学史或者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18世纪,西方启蒙理性登上舞台,宗教退位,而恰恰就在此时,审美及美学宣布独立,于是“审美一定程度上以现代性的人文精神转化并吸纳了宗教的信仰功能”[8]。
人的感性和情感是人类活动和发展的动力性根源。马克思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9]列宁也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0]具体到日常生活中,人的潜能和才华也是要依靠兴趣和情感来激发的,一个冷漠、索然、无爱的人,如同一具空壳,只有当感性与理性协调了,人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鲜活的人。并且也是在这一点上,“以美育代宗教”与中国“礼乐传统”中重视感性体验的化育功能一脉相承。
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是中国美育理论的第一代大师。他们学习西方美育思想和理论并将其引入中国,借以观照中国美育传统,并且发现、确立了中国本土美育理论雏形。这是中华美育传统的现代性进展,而且这种进展是大师们视野上融通古今的结果。
三、以美育人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
“以美育人”根植于“礼乐传统”,重视感性和情感的审美作用,此乃中华美育精神的根基。“礼乐传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数次将美育列入党的教育方针,赋予它重要地位:“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这是国家教育文件中对美育的定位,显而易见是对中华美育传统的赓续。说到底,以美育人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还是由它自身的感性经验价值决定的。
(一)涵濡心灵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从《荀子·乐论》中的这段话,可见美育的感染熏陶价值。新时代语境下,美育的熏染、涵濡功能依然不可替代。“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所以,美育的涵濡心灵,就是要以富含感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去滋润每个人的心灵。电视剧《人世间》、舞蹈《只此青绿》之所为被称为优秀作品,就是因为它们能够以审美的魅力温润人心,引导人们在情感体验中自然而然地被感化、被震撼,体会人生的真、善、美。
(二)培植信仰
如前文所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最终指向是信仰。如果说目标是人前行的动力,那么信仰就是一座加油站。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皮囊。美育的当代价值还在于它能够以富有感情的中华文化符号激励人们培植人生信仰,并由此获得明确而坚定的人生方向。《青春之歌》是红色经典中的上乘之作,曾经激励了几代人。其中卢嘉川在狱中写给林道静的绝笔,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现在,我等着最后的日子,心中已然别无牵挂。因为为共产主义事业、为祖国和人类的和平幸福去死,这是我最光荣的一天。当你看见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早已经丧身在雨花台上了。但是我一想到还有我们无数的、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革命同志前仆后继地战斗着,想到你也是其中的一个,而最后的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时候,我骄傲、欢喜,我是幸福的……”这是战争年代同志的遗志、知己的诀别,它激励着当年的林道静坚定对党的信仰,也激励着今天的我们热泪盈眶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树立起各自的信仰,如山站立,如灯醒路。
(三)提升境界
中国新儒学的代表冯友兰先生曾经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层次在等级上是逐层上升的。自然境界的特征是“顺才顺习”;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利己”;道德境界的特征是“行义”;天地境界的特征是超功利。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处于第二或者第三个层次,而冯友兰先生说,天地境界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笔者认为,烟火人间,芸芸众生,我们即便不能到达天地境界,至少应该努力向道德境界攀登。而这途中,美育的作用至关重要。看丰子恺与老师李叔同“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约定,感叹丰子恺近四十载风雨飘摇中为兑现承诺的呕心沥血,欣赏师生二人共创《护生画集》的天人之和……于喧嚣繁杂中,这样的中华文化符号总会让我们驻足感喟,何必为名利所累?何必为私欲所囿?像丰子恺那样简约稚拙、始终如一地过一生,岂不是天地境界吗?
之所以研究以美育人的中华文化传统,是因为它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礼乐传统”历经几千年,不断地被丰富、被完善,奠定了中华美育理论,培育了中华美育精神。走进新时代,富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美育,要主动对接美育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不断创新美育路径,以激活美育传统的生命力,如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中华美育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